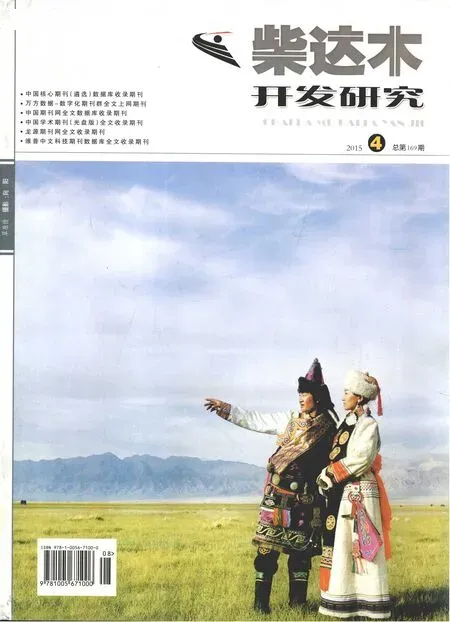德農往昔拾遺
楊東亮
德農是德令哈農場的簡稱。
德令哈農場位于柴達木盆地東北緣,建制于上個世紀50年代,是一方美麗的戈壁綠洲。如果是在春夏之際,你走進德農,便會被滿眼的綠色波濤淹沒。無垠的原野,良田萬頃;金色的麥浪,在戈壁曠野涌動;縱橫交錯的溝渠,將綠野切割成方塊;沿公路與溝渠聳立的楊柳,成排成行,仿佛守衛豐收田野的衛兵,即便是錦繡江南也不過如此。
那么,最初的德農是個什么模樣呢?
2015年元月下旬的一天,受德令哈市文聯的委派,筆者走進了德農場部所在地,即現在的柯魯柯鎮政府所在地,試圖尋訪一些當年的建設者,回憶一下德農的往昔,讓人們了解德農昔日的情景。
遺憾的是,當年的建設者們來德農時大都20來歲,如今已過去60年左右,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已遷居內地,聯系不上。經熱心人指點,我們走進了一家在當地頗有名氣的鹵肉寬粉店,尋找曾經歷德農變遷現已屆耄耋之年的汪梅先老人。
寬粉店不算大,約50平方米左右,倒也寬敞明亮,十幾張桌案分三行排在店堂內,干干凈凈。由于不是飯點,店里客人不多,而且就是吃一碗寬粉就走的。我們就在靠門邊的桌案上坐下來開始采訪。
汪梅先個頭不高,人很瘦,臉上架著一副眼鏡,像是一個文化人。談起德農,汪梅先似乎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講起了過去。
德農:世界上堪稱面積最大的農場
德農位于德令哈市西南,是柴達木盆地有名的一方綠洲。
當年的德農共有6個大隊。從戈壁梁開始自西向東,分別是一大隊、二大隊、三大隊、四大隊、五大隊、六大隊。除此之外,在德農興盛時期,野馬灘的澤令溝分場、地處烏蘭境內的賽什克分場、西邊的戈壁分場、懷頭他拉分場、南邊的尕海分場和查查香卡分場,都統歸德令哈聯合企業公司管轄。方圓幾百公里的農場,世界上哪一個農場可與之相比呢。據汪梅先介紹,當時的設想,是要把德令哈建成一個50多萬人的中型城市。
盡管德農有如此大的規模,還下設有農產品加工廠、油面加工廠、糖廠、榨油廠、鋼廠、汽車修配廠,還設有育紅中學和德農醫院,以及京劇團等。
在汪梅先的記憶里,當時的河東(即德令哈市區)非常冷清,遠不及德農繁華熱鬧。他記得只有兩個小水磨房,為一般人家加工面粉;還有一個山東人開的小飯館,買一只燒雞比買金子還貴,物質供應十分匱乏。
可德農就不一樣,德農有“柴達木糧倉”之稱,每年種的小麥、青稞、豌豆等產品都吃不完,一年上交5000萬斤公糧,比全省上交的公糧都多,創下國內記錄,也使德農聲名遠揚。同時,德農還大面積種植白菜、大頭菜、蔓菁、萵筍、芹菜等時令蔬菜,價格也便宜,吸引得市上的人都來德農買清油、豬肉和蔬菜,農產品加工廠制作的豆腐、粉條、白酒在當地很有名氣。
德農育紅中學的教學質量在全省都是數一數二的,學生最多時達到2000多人。汪梅先介紹說,教員除了正規調來的外,有一部分是從勞動改造人員當中選的,校長是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是傅作義將軍起義時的將官,曾在蘇聯留過學。其他的如語文教員是新民晚報的一個右派,物理老師是國民黨海軍的一個上尉,有些是從政治犯、“三反五反”人員當中選派的。
德農醫院當時規模比較大,醫生是農場自己培養的人手以及從勞教勞改人員中選的。像婦科醫生張家秋,特別擅長看疑難雜癥;兒科醫生杜玉鳳,臨床經驗豐富,許多小孩生病,其他地方看不好,可在杜大夫這兒手到病除。醫院還有許多好醫生,名字基本上都記不起來了。因為有這么多的好醫生,市上很多病人都慕名來德農醫院看病,病號有時多的沒地方住,只能住在地窩子里接受治療。說起農場建設,汪梅先首推郝登閣,并直翹大拇指。
郝登閣,曾任青海農墾廳副廳長兼德令哈農場廠長。原為國民黨陜西省旬邑縣縣長,1949年1月15日率部起義,起義后被任命為解放軍關中分區21團副團長,同年10月,被西北局派來青海,1954年被任命為德令哈農場廠長。他帶領廣大管教干部和青年學生。工人農民以及勞動改造犯人,挖地窩子,住帳篷,開荒種地,一年就開創了德令哈農場的基業。1962年,他被誣陷為“假起義真潛伏”的反革命分子,把頭伸進水缸里自殺了。因為是反革命,死了以后無人敢埋,被幾個犯人拉到一個荒溝里胡亂地蓋了一些沙土,連個墳堆也沒留下。后來有人說,這是個陰謀,那么大個人不可能死在小水缸里。至于真相是怎么回事,也無人能說得清了。
郝登閣死后,德農元氣大傷。后來德農撤了并,并了撤,折騰過幾回,鬧得人心惶惶,也就漸漸衰落了。
大禮堂: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
坐在鹵肉寬粉店里,窗外就是德農場部所在地帶。一個面積約400平方米的廣場,北邊是坐北朝南的大禮堂。說是大禮堂,是相對于周圍建筑而言,到目前為止,德農街道兩旁基本上還都是平房建筑。大禮堂一抹的青磚到頂,南面為三開的大門,中間為正門,內設可納800人左右的椅子,樓頂上方赫然豎立著九個大字: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
這是德農惟一保存完整的當年建筑。
在汪梅先的記憶里,大禮堂大約是在1965年左右蓋的。德農有重要事情時都是在禮堂里開大會,也放電影。因為只能容納800來人,人多了坐不下,就采用輪番放映的方式。德農有放映隊,一撥人看完,再一撥人接著進去看,放映隊不停地放,其實就一部電影,有時連放五六回。說老實話,當時也沒有什么電影可看,無非就是《草原小姐妹》、《朝陽溝》、《地道戰》等。夏天在廣場上放映,人山人海,前面沒地方,有人就在銀幕背后看,場面像是一個盛大的聚會。
當時德農有京劇團,勞改人員中有不少人會唱京劇,不少人是“上海大世界”的演員。1958年成立的德農京劇團,演出水平很高,經常在大禮堂里進行演出,連中國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也來過德農獻藝。
在筆者的記憶里,2003年曾隨“三下鄉”文藝演出隊來德農演出。當時大禮堂前的廣場上有兩個籃球架,文藝演出就在此地舉行。在看熱鬧的人群里,有一個蓬頭垢面臟兮兮,夏天著棉衣棉褲卻有不少破洞的瘋子快樂地從人群里穿來鉆去,又舞又跳地傻笑。筆者當時曾問過人,說這個瘋子是一個勞改犯,后來平反了,一高興就瘋了。也不知他家里人怎么聯系,他也沒地方去,整年就穿著一身棉衣棉褲,從不洗臉刷牙,吃住都在大禮堂臺階東側下面的墻角,好心人給他一把麥草當做床,春夏秋冬就在麥草窩里度過。農場把他補發的工資交給附近一家商店的主人,一天給他三頓飯吃不至于餓死就行了。汪梅先說他知道這個人,文化水平還挺高,叫萊玉(諧音),后來走失在戈壁里,凍死了。
大禮堂現已關閉不啟用了,只作為柯魯柯鎮的一個歷史遺跡而保存。當年的往事如過眼云煙,唯有“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幾個大字歷歷在目,昭示著這里曾經發生過的一切。
綠洲農業:建設者豎起的無字豐碑
在柴達木60多年的開發史中,無數仁人志士拋家棄子,用血與汗澆灌出如畫的家園,凝聚了“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勇于創新、團結奮斗、科學務實”的柴達木精神,農墾文化無疑是歷史長河中一朵晶瑩的浪花。
那么,什么是農墾文化?經與青海省監獄管理協會秘書長張琳探討,農墾文化可以這樣表述:以軍轉干部為主體、支邊青年積極參與,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墾荒種田與改造犯人相結合而創造的帶有地域特色的當地文化。其內涵是:白手起家,艱苦創業;不怕犧牲,甘于奉獻;墾荒拓疆,勇創佳績;同舟共濟,共建家園。這些內容都好理解,唯一的是不怕犧牲這句話。的確,有史料記載,有些軍轉干部在管教犯人的過程中,就犧牲在工作崗位上。
嚴格地說,柴達木的開發史,最早是從農場開發起始的,軍轉干部、支邊青年和工人農民功居首位。但有一個尷尬的事實擺在人們面前,開墾農場的大軍中,有不少人身份卑微,怎么去書寫他們呢?
按汪梅先的回憶,當時農場人員主要由管教干部、知青、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人員,以及國民黨軍政人員,還有吃不飽肚子自愿來德農謀生的“盲流”,而最多的是勞動改造犯人,俗稱“勞改犯”。據有關資料,德農先后接納了4萬多名犯人。
汪梅先是上海人,1958年在他26歲時來到德令哈農場,現已83歲。剛來時分在旺尕秀煤礦,專為尕海煉鋼廠提供焦煤。1963年到德農汽車修配廠當鉗工,4年刑滿后不讓回上海,說這里需要人,所以留在德農并娶妻生子,先與人合伙開了這家寬粉店,后來獨自經營。汪梅先說,感謝改革開放,他能開店做生意。由于他選料講究,質量與味道俱佳,生意特別紅火,遠近的人都慕名而來。
說起來德農的原因,老人也不隱諱。他曾是一個唱評彈的演員。當時出外演出要開介紹信,沒有介紹信就屬違法,相當于今天的“走穴”。汪梅先當時和幾個同伴出外演出時沒有介紹信,他就把曾用過的介紹信涂改了,結果被查出來,定的罪名是“涂改國家政策”,被送勞動教養四年,發配到了德農。他不服上訴,被維持原判。有人勸他說,別上訴了,才四年,你夠便宜的啦。1958年運動,要求人人寫大字報,要積極檢舉揭發右派和反革命,不揭發就有罪。同單位一個女同志,不檢舉也不寫大字報,就因為和單位領導吵過架,偏她又穿了雙高跟鞋,定為“生活糜爛、作風不好”罪,被送勞動改造。
說起勞動改造,歷史上并不乏先例。
我國商王朝之前,商部落首領湯有一個奴隸出身的著名宰相伊尹,伊尹輔佐湯成就了滅夏建商的大業。湯死后,他又輔佐外丙、中壬、太甲,但太甲年紀尚小,不太懂事,伊尹在他為王后作了幾篇文章,教他為王之道。可太甲滿不在乎,在位僅三年就暴虐異常。于是伊尹就廢掉太甲,把他押送到桐(現在為河南虞城)這個地方進行勞動改造。勞動改造效果非常好,三年時間內太甲就翻然悔過。伊尹一看他改造得不錯,又把他接回來當國王。有過勞改經歷的太甲發憤圖強,天下大治,四方來朝。
也許外國統治者也借鑒了中國的成功經驗。1988年,第一批英國人到達澳洲,而當時的澳洲荒無人煙,由270名士兵押解著1200名囚犯來到此地,成為開發澳洲的奠基人。我們也知道,俄國開發西伯利亞,全是由囚徒流犯進行墾荒的,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收獲。
1942年,國民黨青海省政府成立了柴達木農墾局,企圖開發這方沉睡了幾萬年的土地。數萬名東部農民被迫來到這塊野狼出沒、蚊蟲叮咬的戈壁灘進行墾荒,但農民不同于勞改犯,不好管理,干不下去就落荒而逃,溜之大吉,但勞改犯是嚴管高壓性的強制勞動,無處可逃,只有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而且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從而開墾出了這方讓后人稱道的戈壁綠洲。開墾萬畝良田是從平掉千萬個沙土包開始的,而且全憑人背肩挑筐抬,最先進的工具無非就是獨輪車。在這漫長的歲月中,要忍受風沙撲面,要忍受烈日炙烤,要忍受蚊蟲叮咬的痛苦,要忍受啃著干饅頭、喝著泥水湯、住著地窩子的艱辛。這些場景,今天的人是無論如何都描繪不出來的。
如果拋開身份而言,無論任何人,當他最初踏上德農這塊曠野時,首先必須解決的是吃住行的問題,正是在這解決人類溫飽最簡單原始的過程中,人類的理想與現實碰撞,迸發出改天換地的耀眼光芒,成為一部集體創造的英雄史詩。
德農,你離我們并不遙遠。
- 柴達木開發研究的其它文章
- 柴達木:閃亮的民族文化之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