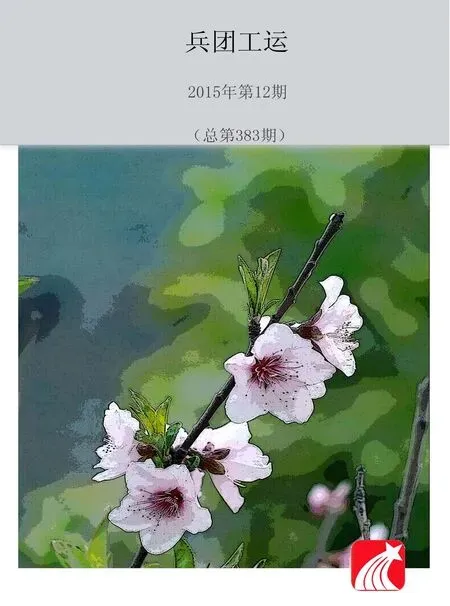父是燈塔
□ 裴桂革
父是燈塔
□裴桂革
我的父親裴顯合于1929年出生在山東省曹縣一個貧苦農(nóng)民家庭里,家中上無片瓦、下無寸土。1944年家鄉(xiāng)來了八路軍,給地主扛活的父親如枯木逢春,那時的他還沒有槍桿子高,但毅然決然地參加了八路軍。之后無論是打小日本還是連年的內(nèi)戰(zhàn),父親嘗盡了南征北戰(zhàn)、槍林彈雨的艱苦與慘烈。從此,只要見到了“南征北戰(zhàn)”字詞就會想起父親,感覺上竟是那樣的親切。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相貌英俊、身材高大魁梧,話不多但是為人和藹可親。在我還不記事的時候,母親就因一場意外事故而致殘,生活不能自理,家中的幾個孩子年紀(jì)都還小,于是奶奶(其實是外婆,情感上我們習(xí)慣稱她奶奶)來到了我家。父親對待奶奶就像對待自己的母親,很是感激和敬重。雖然貴為一連之長,但他完全“放權(quán)”給奶奶,每月領(lǐng)取工資都如數(shù)交給奶奶。每到用錢時,他則會大大方方地向奶奶要,一點也不難為情。饒是這樣,我家的日子仍然過得緊張,即便是到了80年代想要吃頓肉還要等到過年。
記得有一天,奶奶破天荒地做了一小碗紅燒肉。我們兄弟姐妹幾個看見后都垂涎欲滴,趕忙圍了過去,奶奶卻壓低聲音對我們說:“你們的爸爸這兩天在外面挖大渠,很辛苦,這是給他做的,你們到時不許跟他搶,聽見沒有?”我們只好咽著唾沫,似懂非懂地點著頭。
天快黑時,父親才回來。奶奶見他進(jìn)門,便端出了飯菜,招呼我們洗手吃飯。我伸出筷子,猶豫半天也沒敢吃紅燒肉,弟弟妹妹亦如是。
后來,父親還是看出了這其中的端倪,他不動聲色地拿起筷子,先往我最小妹妹的碗里夾了一塊紅燒肉,接著又給我和我弟弟各夾了一塊。“吃吧,好長時間都沒聞到肉味了,是該給你們燒頓肉吃。”父親憐愛地對我們說。
然后,他扭頭看了看臥床不起的母親,風(fēng)趣地對她說:
“你們的媽媽一定和你們一樣饞肉了。”說著,端起紅燒肉向母親走去。奶奶見狀卻急了,沖著父親直嚷:“你都給他們吃了,你吃啥?”父親轉(zhuǎn)過頭來看著奶奶,笑著說:“我沒那么嬌氣,吃不吃都不打緊。”
父親雖然文化程度低,卻酷愛讀書。上世紀(jì)70年代,單位給我家分了一套大約60平方米的帶套間的土塊房。里間是我們幾個孩子和奶奶的臥室,外間因為有父親用土塊砌的爐灶和火墻,也被隔成了兩個小間——外面靠門的一間是廚房,里面一間則是父母的臥室兼書房。這間小小的臥室里除了勉強(qiáng)能放下父母的床之外,剩余的空間都被一張簡陋、笨重的舊書桌占據(jù),床腳處放著一個大紙箱,箱子里整齊地碼放著許多的書報。父親吃過飯,會倚在床上看書讀報。
過去,我經(jīng)常湊到父親身邊,纏著他,指著書報上的內(nèi)容問這問那,他總是耐心地回答我那些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的問題。
有一次,我指著父親手中的書問:“爸爸,你這些書是從哪來的?”他說:“在連隊訂購的。”“那你也給我訂些書吧。”我央求他。
他笑著問我:“你想看什么書?”“《作文》《作文通訊》《故事會》《大眾電影》。”于是,我就把以前在別處看見過的雜志講給他聽。他笑笑,沒有多說什么。半個月后,這些雜志便陸陸續(xù)續(xù)被父親帶回了家。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不敢說,我寫字有多勤奮,但是閱讀卻成了我的習(xí)慣,而這習(xí)慣的養(yǎng)成與父親有著莫大關(guān)聯(lián)。
戰(zhàn)爭年代,父親曾多次負(fù)傷,殘留的彈片長期以來都折磨著他,經(jīng)常痛得他臉色發(fā)白、渾身冒虛汗。即便如此,他從來沒耽誤過工作。團(tuán)里進(jìn)行大規(guī)模的“開荒種地、挖排治堿”的勞動,有一次,父親帶著全連職工正忙著挖排堿渠,忽然舊病復(fù)發(fā),他咬緊牙關(guān),使勁扶著坎土曼才沒有倒下。然后,他慢慢地蹲下,把脊背緊貼在渠埂邊休息,蠟黃的臉頰布滿了細(xì)密的汗珠,呼吸漸趨粗重。當(dāng)大家紛紛勸說父親回家時,他卻搖著頭說:“我不能走。比起戰(zhàn)爭年代,這點疼不算啥,我得帶好這個頭。”
最終,父親因為積勞成疾,倒在了工作崗位上,被送往醫(yī)院緊急搶救。一周后,我們見到父親時,他已是彌留之際。
我記得那天見到父親時,他的臉色煞白,眼睛陷在眼窩里,似睜非睜。年幼無知的我從未見過父親這般模樣,有些害怕,便躲在奶奶身后,不敢直面父親。奶奶早已泣不成聲,她使勁地把我們兄弟姐妹幾個推向父親身邊。父親輕顫著沒有血色的嘴唇,一張一合,像是在說什么,可是聽不見一絲的聲音。他盯著我的哥哥,仿佛在向他囑咐著什么。哥哥那年剛滿18歲,看著父親的眼神,他局促不安……在父親最后的那段時間里,我們都在病房里陪著他,直到他不舍地合上雙眼,永遠(yuǎn)地離開了我們。
從此,我們陷入了對他無盡的思念中——站著,你的偉岸有如高山;倒下了,你的風(fēng)采好像江河!多年以后,我愈加清晰地意識到,我與父親雖生死相隔,但是他猶如屹立在我心中的一座燈塔,始終指引著我,讓我在這紛繁復(fù)雜的人世間做個坦坦蕩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