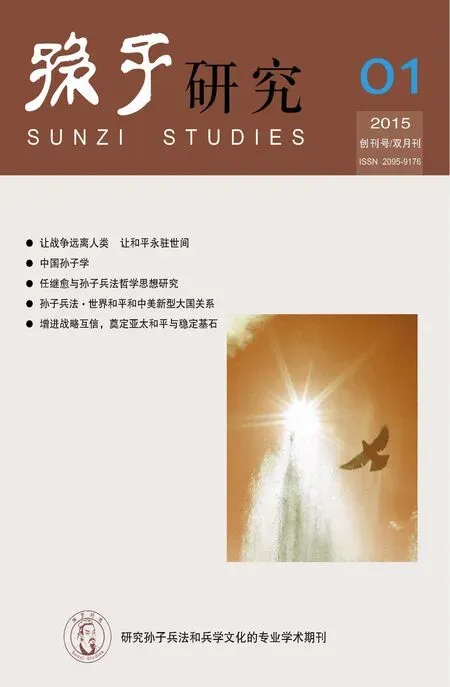中國孫子學
謝祥皓
中國孫子學
謝祥皓
《孫子研究》正式創刊了。這是中國兵學界的一件大喜事,也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喜事。她為中國兵學的研究,特別是中國孫子學的研究、開拓與交流,提供了一個寬廣的平臺;也為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大花園,增添了一支絢麗多姿的奇葩。
“孫子學”概念的提出,是近現代才出現的。它一面世,就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原因在于,它既有以《孫子兵法》為核心的中國兵學文化的穩定寬廣的學術領域,又有以孫子思想學說為軸心從而透穿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強勁生命力。中國孫子學的研究與開拓,既可以“認古”,又可以“察今”;既可撥開歷史上的諸多疑云,又可為今日國家政治、軍事的發展及國防建設與國際爭端的應對,提供睿智、犀利的武器。稱“國之瑰寶”、“國之利器”,孫子學名副其實。
一、戰爭經驗的集結與升華
認識來源于實踐,直接的感知經驗是一切理論學說的起點。人的感性認識通過對比、分析、綜合、判斷之后,就會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形成理性認識;而任何一個領域中的系統的理性認識,都會升華為系統的理論學說。而理論學說一旦形成,又可轉過來指導社會實踐,通過新的社會實踐的驗證,就會形成這一領域中的相對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兵學是關于戰爭規律的理論學說,是關于國家生死存亡的理論學說,從人類有戰爭開始,它就相伴而生;伴隨著國家與國家、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戰爭的發展而發展,并且一步步形成不同形態的理論學說。中國孫子學,以《孫子兵法》為核心的兵學理論體系,正是經過了從黃帝到孫武兩千余年戰爭實踐的經驗所凝練的兵學理論的精華所在。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寫道: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范》八政,八曰師。……《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并作。
這段引文概括了春秋之前兩千余年間,軍隊與戰爭發展的基本情況。司馬,軍隊之主官,如同今之國防部長。師,軍隊單位,編制為2500人;此泛指軍隊。弧矢,木制的弓和箭。國家政權出現伊始,就設有軍事部門;弧矢、金革,均言兵器,為早期的戰爭手段。及至殷周時代,“以禮治軍”成為軍隊與戰爭行為的基本準則;商湯的征伐與武王伐紂,是其典型的戰爭實踐。時至春秋戰國,權謀變詐興起,“詭詐之兵”成為戰爭的主流,儒家亞圣孟軻所言“春秋無義戰”,就是對這一時代戰爭行為的簡明概括。
《孫子兵法》,中國孫子學,就是上述戰爭經驗的集結與升華,尤其是三代“以禮治軍”與春秋“權謀變詐”之兵,均在孫子學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明人茅元儀言:“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就是指孫子之前2000余年的戰爭經驗,精華盡收其中。而茅元儀所言后兩句話:“后孫子者,不能遺《孫子》”,則指孫子學已經集中準確反映了軍事活動、戰爭行為的根本規律,一切用兵者、言兵者,都不可能超越其外。(見茅元儀《武備志·兵訣評》)對此,唐人杜牧有更深刻的理解:“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注孫子序》,見《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可見,孫武之書對戰爭規律的反映是如此之準確、精審。
二、道義、權謀——政治與軍事
近代德國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提出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著名命題,之后,得到了學術界廣泛的認同,從列寧到毛澤東,均對這一命題給予了明確的肯定。由此,許多人認為,政治與軍事的關系是近代以來的發現。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這一基本關系自古有之。
就戰爭領域而言,政治是講為什么要打仗,軍事是講能不能打及如何打仗,前者是目標,后者是手段,手段服從于目標的需求,是天經地義的。所以,政治統帥軍事,軍事服從于政治,服務于政治,是它們的本質內涵所決定的,從它們出現之日起,就決定了的。軍事一旦脫離了政治,就失去了頭腦,會像無頭的蒼蠅;而政治一旦失去了軍事,就等于被砍掉了手足,沒有現實的手段,必將一事難成。政治、軍事之不可割離,原因正在于此。
在中國古代的戰爭中,政治與軍事的基本表現形態,是道義與權謀。道義就是政治,而權謀則為軍事。如:
《史記·五帝本紀》寫道: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
軒轅即黃帝。為什么要“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因為“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禁暴止亂是民心之所向,是當時的“道義”,這就是“政治”。由此而“習用干戈”則是軍事。在“振兵”的同時先要“修德”,由此才能打敗炎帝,擒殺蚩尤。所以,從戰爭一開始,政治就居于“統領”的地位。
殷、周時代的戰爭,規模最大、影響最著者,莫過于湯伐夏桀、武王伐紂,史稱“湯武革命”。其基本經驗,就見于今存《司馬法》。
《司馬法·仁本第一》寫道: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司馬法》在《漢書·藝文志》中作《軍禮司馬法》,原有155篇。后,輾轉流失,至宋代,僅存五篇,《仁本》正居其首。在《漢書·藝文志》中本入于“禮”類,是“周禮”的一個組成部分。上古三代,“禮”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是裁定一切是非的最高標準,“禮”就是最大、最高的政治。表現在軍事領域,它的主導內涵就是“以仁為本”、“以義為治”。具體地說,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殺人”的目的在于“安人”;“戰爭”的目的在于“止戰”;“攻其國”的目的在于“愛其民”。基本的立足點均在于愛護人民。所以,它對戰爭的具體實施都有細致規定:“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不但愛護本國的人民,同時也要愛護敵國的人民。這就是“以禮治軍”的最高原則。在“以禮治軍”的殷周時代,軍事服從于政治,軍事服務于政治,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孫子兵法》誕生于春秋后期,此時已是詭詐公行的時代,然孫武廟算首列“五事”、“七計”,“道”字赫然居首。“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孫子·始計》)這正是道義民心之所在,民眾與君上能同安危、共生死,就是最大的政治。孫武鮮明地高舉了《司馬法》以來的“仁本”旗幟。
唐人杜牧有言:“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注孫子序》)本之以仁義,濟之以權謀,正是孫武思想學說的大局所在。
三、立足全局,廟算決策
時光已經過去2500余年,孫武及《孫子兵法》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位思想深邃的戰略家,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和一部能夠貫通古今的兵學著作,世人譽之為“兵學圣典”。這一贊譽的基本立足點,就在于《孫子兵法》對戰爭之本質及客觀規律的深刻、精準的反映。而孫武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首先在于善于把握全局,善于洞察本質。
《孫子兵法》開篇即言: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始計第一》)
第一句話,就把“兵”事提到了國家之生死存亡的高度,這正是它的本質所在。
《左傳》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成公十三年)祀,禮也,是當時政治的最高準則;戎,兵也,是保衛國家的實力所在。這就站在國家全局的高度,確立了“兵”的應有地位。
繼之,舉列“五事”、“七計”,在道義居首的前提下,全面展示綜合國力。對比雙方的軍事實力,對比雙方的戰爭條件,對比雙方的經濟基礎,通過“廟算”得失,“未戰先勝”,方可作出戰爭決策。
把握全局,洞察本質,依順規律,預見得失,是古今戰略家必須掌控的第一要義。孫武做到了,《孫子兵法》做到了,這就是《孫子兵法》在當今世界仍然具有指導與借鑒意義的原因所在。
四、全勝不斗,大兵無創
上二語,本是上古哲人關于“以德用兵”的理想狀態,見于太公《六韜》。
為推翻暴虐的商紂王,姜太公勸周文王“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待主、客觀條件都成熟時,自會有“全勝不斗,大兵無創”的效果。(《六韜·武韜·發啟》)文王修德,武王伐紂,確實引發了商紂軍隊的陣前倒戈,導致商紂頃刻覆滅。然此役并非“無創”,牧野之戰中“血流漂杵”(見《尚書·武成》),連舂米用的木棒都被血流漂了起來。
然而,作為一位沉穩深思的軍事思想家,孫武在面對上述史實背景時,卻能把“全勝不斗,大兵無創”這一理想化的戰爭效果,轉化為完全可以用具體手段去實現的戰略目標。
孫武寫道: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謀攻》)
“善之善者”,即優中之優,是最佳選擇,能不費一槍一彈,使敵方屈從于我方的意志,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兵不頓而利可全”。能“全國”而服,“全軍”而服,顯然是不動刀兵,未經廝殺。至于其具體手段,孫武又寫道: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
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很明顯,“不戰而屈人之兵”,決非“伐兵”、“攻城”之法所能實現,而只能是“伐謀”、“伐交”。“伐謀”者,以謀相伐也;“伐交”者,以外交手段制敵也。此類事例,在中國古代不勝枚舉,如晉使赴齊,齊臣晏嬰于推杯換盞之間,即挫敗了晉欲伐齊的圖謀。而當今時代,“伐謀”、“伐交”更是風靡全球。“謀”中有“交”,“交”中有“謀”,而且更要以“實力”做后盾:“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孫子·九變》)只有“信(伸)己之私,威加于敵”,“謀”、“交”才有可靠的根基。試看今日世界,“外交”使者穿梭如云,人們在利用一切場合;而實彈軍演又目不暇接,要充分展示實力;此皆欲以“謀”、“交”之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以道義為旗幟,以實力為根基,謀、交、力,交替運行于其間,方能立于不敗之地。某些國家明明挑著“黑旗”,卻多方狡辯為“紅旗”,縱然在某時某地得逞于一時,但絕不可能持久,終將以潰敗為終結。
五、道兵相通,儒兵一體
在中華文明五千余年的發展歷程中,能貫通始終的,大致有道、儒、兵三家。
先說“道兵相通”。
對“道”的追求,是華夏先民最早的思想目標之一。從伏羲“作《易》八卦”(司馬談語,見《太史公自序》)開始,即在傾力追尋天地之道,探索天地運行的規律。“日月為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就是這一追求的最早的收獲與結論。日月運行,陰陽交替,是人類生存環境的最基本的變化規律,也是人類及整個生物界產生、發展及其持續存在的主要客觀依據之一。所以,由伏羲所開創的中華文明,“作《易》八卦”,就是華夏先民自覺地探尋客觀物質世界變化發展之客觀規律的開始。知曉生存環境的變化規律,方能自覺地調整人類的行為,以利于生存與發展。這正是伏羲“作《易》八卦”,追尋“易道”的初衷所在。
至黃帝時代,追尋“至道”、“天道”、“大道”,成為圣人們的不懈追求,而“得道”,則成為超越常人的“神仙”境界。(參閱《莊子》之《在宥》《天道》《天運》諸文)至姜太公,由于助周滅商“多兵權與奇計”,被稱為“有道者”(見《漢書·藝文志》)。專論“兵道”,當以太公為起始。至春秋后期老聃,更將“道”字上升為宇宙萬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而“道”本身,則是一種先于天地萬物的自然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由此,確立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思想領域最為廣闊的學派——道家。
道家的目光,集中在客觀物質世界及人類生存發展之規律的探索,同時也兼及于戰爭規律的追求。如姜太公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分《謀》《言》《兵》三大部分(見《漢書·藝文志》),即《太公兵法》,后散失,衍生為《六韜》《三略》等。而老聃,其主體雖在于天道本原,亦論及人世用兵,并提出了“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及“哀兵必勝”等激發道義民心的著名觀點。(見《老子》五十七章、六十九章)
孫武、孫臏祖孫,皆以探索兵事規律為己任。孫武全書,字字句句都在探索“安國全軍之道”,探索各種具體條件下的“致勝之道”。至孫臏,更以“道”作為其克敵制勝的有效法寶與最高境界,提出“知兵”未必“知道”(“道”高于“兵”);“知道,勝”;“不知道,不勝”;“以決勝敗安危者,道也”等著名觀點。武、臏祖孫一脈相承的兵法,孫臏稱之為“孫氏之道”,并言:“知孫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見《孫臏兵法》之《陳忌問壘》等篇)而“孫氏之道”必合于“天地”之道,足見“道”、“兵”之息息相通,道中有兵,兵中有道。中國古代道教傳人編纂《道藏》,將《孫子兵法》收錄其中,乃事理之必然。
再說“儒兵一體”。
前已述及,就其本質內涵而言,兵與儒的關系就是軍事與政治的關系。政治是靈魂,軍事是手段,政治統帥軍事,軍事服務于政治,是它們的本質內涵所決定的。中國古代政治的實際內容,是道義民心。從伏羲“教而不誅”(見《商君書·更法》),到黃帝“修德振兵”,再到唐堯“其仁如天”,商湯“仁及禽獸”,周公“興正禮樂”,皆為當時民心之所向。民心所向就是政治,就是軍事所要實現的目標。所以,自古以來,軍事就不可能脫離政治而孤立地存在。儒兵之一體,乃客觀之必然要求。西漢劉邦“扶義而西”就能打敗項羽,項羽殺人如麻則終歸烏江自刎。明人李贄倡導以儒家“六經”與兵家“七書”合為一體,完全是合乎規律的要求。不懂政治,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軍事家。
道、儒、兵,均為貫通五千載中華文化的支柱性內涵,以孫武《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孫子學,不但占據其一,而且滲透于道、儒之方方面面。首先把握住中華文化之大局,才能真正讀懂中國孫子學。
(責任編輯:周淑萍)
Chinese Military Tactics of Sunzi
中國孫子學,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支柱性思想學說之一。數千年中華文化的豐厚積累,是中國孫子學誕生的沃土;戰爭經驗的集結與升華,是孫子學的直接來源。政治與軍事,道義與權謀,是自有戰爭以來就緊相伴隨的本質屬性;政治統帥軍事,權謀服務于道義,是它們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是客觀規律,不容倒置。立足國家安危之大局審慎決策,以“德”用兵,以“全”取勝,“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略方針的最佳選擇。以“實力”為后盾,“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是“安國全軍”的基本立足點。道兵相通,儒兵一體,兵中有道,兵中有儒。首先把握住中華文化之大局,才能真正理解并準確把握中國的孫子學。
The military tactics of Sunzi is one of the paramount thoughts in China with 5,000 years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His military principles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rich Chinese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direct experience in the war.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 morality, justice and tactics are nature of war, which determines the objective and undoubted principles that politics dominates military affairs, and tactics serve the morality and justice. It is the supreme excellence to make a decision with caution in view of the security of state, cherish virtue in the operations of war, win but take the enemy whole, balk the enemy's plans as the highest form of generalship, and break the enemy's resistance without fighting. It is the basic foothold to make the actual force as support, rely not on the likelihood of the enemy's not coming but on our own readiness to receive him, not on the chance of his not attacking but rather on the fact that we have made our position unassailable, which is the interlink of Daoism and military thoughts of Sunzi, as well as the unity of Confucianism and his military principles. Only by grasp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n we understand and hold the core of military doctrine of Sunzi.
中國孫子學 戰爭經驗 道義 權謀 實力 大局
military tactics of Sunzi; experience of war; morality and justice; tactics; power; overall situation
E0
A
2095-9176(2015)01-00016-06
2014-10-14
謝祥皓,山東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山東孫子研究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