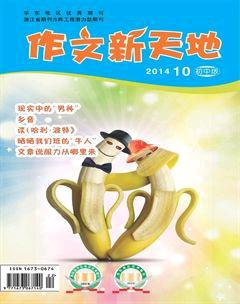文學創(chuàng)作談我與城建有緣
對已進入不惑之年的我來說,與杭州的城市建設還是很有些淵源的。
四十五年前的盛夏,我出生于城南南星橋的瓦子巷,那是南宋皇城九里皇城的核心地塊,父親因此給我取名為宸婷。四十五年來,隨著城市的發(fā)展,我不停地搬家,也慢慢地長大。反過來可以這樣說,我的成長也印證了杭州這座美麗城市的成長,有酸、有甜、有苦、有辣,更多的是生于斯、長于斯、學于斯、住于斯的愛。
進入21世紀,因為選擇了“以耕字和行走作為人生的方式”,寫杭州城市建設的文字幾乎占據了我學習工作生活的最重要篇章,經常開玩笑地說自己,“不在城建的旁邊,也在城建的周圍”。有的是親身所見,有的是親歷所為,有的是采訪所聞,有的是編撰所得,無論是西湖、西溪、運河三大綜保工程,還是“一縱三橫”“五縱六路”“兩縱三橫”“十縱十橫”,或是市區(qū)河道、中山路、之江勝景,抑或是“紅樓”問計,共建工程、民工學校、城建人的先進事跡采訪實錄,甚至是自己的散文專輯,寫就城市建設的文章足足過半。
寫杭州的城市建設,從西湖入題肯定是個正確的選擇。我在《點評西湖》一文里,字里行間流露出“西湖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是天堂的明珠、杭州的象征,是杭州的根與魂,也是杭州打造‘東方休閑之都和‘生活品質之城的‘金字招牌。縱觀杭州2200余年的建城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杭州倚湖而興、因湖而名、以湖為魂,西湖是杭州永恒的主題”。
而在《親歷建設中的西溪》的文章里,我在文中表明了“西溪的保護建設忠實于本地域文化,它是歷史的載體,是西溪古代農耕社會的真實體現(xiàn),以其古老、鮮活、包容與開放的良好形象,創(chuàng)造性的表現(xiàn)形式,保護性的開發(fā)模式,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因為我們‘生于斯,長于斯,愛于斯,也因為我們親身經歷了西溪的保護與建設,我們鐘情于西溪,服務于西溪,失落已久的西溪,踏著盛世的足音,回到了天堂——杭州。‘濃抹人文,淡妝生態(tài)的西溪,一亮相,即好評如潮,一出場,即艷驚天下”。
聽到我寫的《走近大運河》的解說詞,相信你應該是坐在漕舫里進入慢游時代的時光:“視線所到之處,兩岸的建筑也是寫不盡說不盡的古韻風情,就連河邊賣風箏的小攤販、推著童車在散步的少婦、奔跑著的孩童們、在橋邊舞劍打太極的老頭老太們、在河邊牽手走著的情侶們,臉上都有著一種恬淡悠然之色。運河的船只還是繁忙得很,來來往往,看著都是一種豐收的歡喜。看著看著,你的眼神也會癡醉迷離起來……”
杭州的春夏秋冬有著傳承歷史文脈的街景、有著鐘愛城市建設的民眾、有著驚世如畫山水的西湖。天堂也就成了世人的風景,裝飾了你我的夢。
在《探營“五縱六路”》一文中,所有的尋訪標題里,我都用了志摩先生的詩作名句作為引子,“你去,我也走”——新塘路,“我是你天空里的一片云”——環(huán)城東路,“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際云游”——東新路,“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紹興路,“尋夢?撐一支長篙”——古墩路,“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湖墅路,算是對古城杭州文化景觀廊道建設的一份深情寄寓。
在《人生若只如初見——游目“兩縱三橫”的美麗初夏》一文里,我又用了清代著名詞人納蘭容若的句子,文一路——“當時只道是尋常”,文二路——“相看好處卻無言”,文三路——“重到舊時明月路”,學院路——“憑君料理花間課”,教工路——“算來好景只如斯”。
漫步在杭州這座城市,不經意地觸摸歷史、感受文化,即便是一株大樹,一個小品,也都有一個美好的故事,也都有一組時代的信息,你的驚喜就會連同你的感動,飄蕩在城市上空特有的味道會永久地在你的心靈深處定格,與這座城市慢慢地老去。
作為一個已到中年的女子,我從小就喜歡看書寫字。除了偶爾外出聚聚之外,我最喜歡的就是晚飯后待在家中,一手執(zhí)明清小說或是唐詩宋詞,再或是后宮穿越類甚至是官場小說。兒子們總是在做作業(yè),夫君也大多會在書房寫字,嫂子永遠在操持家務。我們家是個大家庭,平時吃飯總是一大桌子。公公婆婆、哥哥嫂子侄子、兩個兒子、我們夫婦,有時還加上干兒子,剛好一桌10人。
白天的工作,要經營書院,要籌辦公益講座,要舉行會展,忙得像個陀螺。而晚上的生活,卻平淡得如白開水,自己也不覺寂寞。用我自己的話講起來,提前一天預約就可以決定能否在一起吃晚飯的。眾人眼中性情中人的生活,倒是非常的傳統(tǒng)安然,這很讓一般的朋友不解。納悶之余,多是以一句你總是劍走偏鋒作結語。
寫作對于我來講,實在是一件快樂自在的事。也因此,對待寫作,我始終心儀如初。每每走進書房前,必焚香沐浴。而到了午夜,用我自己的話形容起來,簡直可以到人機合一的地步。這時,枯燥單調的宋體字,在我看來一個個都是飄逸瀟灑的王羲之書法絕作。可以這么說,近七八年來每年三十萬字以上的發(fā)稿量,大半得益于凌晨時分的奮筆疾書。最多的一夜,我居然創(chuàng)下了一夜一萬五千字的創(chuàng)作紀錄。
創(chuàng)作城建文學,是我當初的選擇。效仿林徽因,最愛這城建與文學的不息變幻,是我終身的愿景。從園林文化起步,我一直鐘情于大杭州城市建設的文化研究、文化發(fā)展、文化保護、文化挖掘。這個選擇,體現(xiàn)了我的追求。因為,當年旅游被認為枯廟殘燈,是冷衙門,但最少競爭、最少潛規(guī)則、最少功利,卻是鉆研人文、歷史、文化的好去處。而城市建設,人們一想起就覺得充滿了硬質鋼性,除了專業(yè)性的論文,無法伸展文學的柔美和情懷。而我在十來年下來,試著用柔性的筆調寫就城市建設的篇章,我從城市道路寫到城市河道,從西湖寫到西溪、寫到運河、寫到中山路、寫到城市河道,從城市建設者寫到城市的廣大民眾。
美就是生活本身,散文的靈魂在于其豐富的生活內涵。飽含哲理和對人生的思索,有如天籟自鳴。借景觀言志,顯示人性的美與丑。尤其是寫景的散文,要表現(xiàn)出歷史濃郁的厚重感與滄桑感,就必須有一種人文知識的積淀、理性升華的根基。這是一位諸暨老鄉(xiāng)對我文字的評點,也可以作為我創(chuàng)作的要求,正在實踐和精進之中。
創(chuàng)意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寫作鑄就了自己的人生方式。作為一名女人,今生今世,我選擇了這條路,終生無悔,也算是實現(xiàn)了自己的童年夢想。
有夢,總是美好的。
我也希望,通過寫城市建設,用我的筆,我的手,我的行為所在,去引領、去傳承、去貫通、去創(chuàng)新這份薪火傳人的事業(yè),與同時代的人,共同進行一次可能時間會非常持久的傳統(tǒng)文化的保衛(wèi)戰(zhàn)。
作家小檔案
俞宸亭 女,1969年7月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浙江諸暨,中國青年作家學會副主席,杭州桐蔭堂書院堂主,城建女作家,國家二級作家,曾發(fā)表作品350萬余字,創(chuàng)作《亦閑集》《亦鬧集》《煙柳運河一脈清》《穿花泄月繞城來》《之江勝景》等,主編《杭州社科知識叢書——禮儀篇、文博篇》《吳山楹聯(lián)集》《吳山楹聯(lián)集粹》《綠色風行——文化深耕天子嶺》《種桃種李種春風》《西山》等四十余本書籍和宣傳畫冊,擔綱包括《杭州運河文化創(chuàng)意園區(qū)》《用文學的力量解讀經濟主戰(zhàn)場——東陽義烏藝術采風》《傳統(tǒng)文化村落的保護與發(fā)展——以富陽為例》等重大城建課題二十余項。
給同學們推薦的書:《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簡·雅各布斯)
給同學們的一句話: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電影《亂世佳人》斯佳麗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