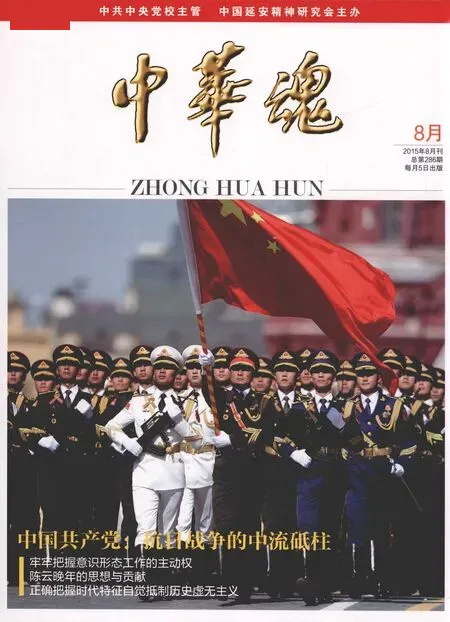漢文帝不以權壓法
文/孔見
漢文帝不以權壓法
文/孔見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是以皇權為中心的封建專制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這種皇權制度的典型寫照。皇帝獨攬一切行政、立法、司法、財政、軍事大權,因而封建專制制度必然是一種人治制度。這是從封建制度的本質特征上說的,并不排除有的比較開明的君主,為了長治久安,注意納諫,聽取不同意見,注意循法行事,不以權壓法。在這方面,漢文帝是做得比較好的。
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后,西漢的政治制度,基本是繼承了秦代的制度。及至周勃、陳平滅呂安劉后,漢文帝劉恒即位。他吸取呂后暴政危及漢室的教訓,注意與民休息,恭謹從諫,并減少刑罰。就后者而言,漢文帝時有“刑罰大省”之稱。比如,漢朝基本沿襲秦朝法律,施行“連坐法”,即對重罪犯要株連親族,漢朝雖廢除了“夷三族”的作法,但仍保留連坐法中的“收孥”作法(即將罪犯的親屬收為官府奴婢)。漢文帝說服朝臣廢除這種無辜受罪、禍害人民的殘暴作法。又如,當時有三種肉刑的規定,即黥刑,在臉上刺字;劓刑,割掉罪犯的鼻子;斬左、右止,砍掉左腳或右腳,這同樣是慘無人道的酷刑。漢文帝看到一個女子上書,愿以身為奴求免其父受此酷刑,情深意切,受到感動,認為這種刑罰是不道德的,也使人失去重新做人的機會。他主張使罪犯按其罪行輕重受到相應的刑罰,不逃亡,滿了刑期就解除刑罰當平民,使其能夠改過自新、重新做人。遂下令取消這些讓人痛苦的肉刑。此外,漢文帝劉恒還廢除了一些過于嚴苛的刑法,如“誹謗妖言罪”,這樣的定罪有極大的隨意性,且懲治極端嚴酷,不但使人有隨時喪命的危險,而且這樣做也阻塞了言路,下令廢除。
漢文帝還比較注意律己,不以天子之威胡作非為,不以權壓法。有一次,漢文帝車駕經過中渭橋,被一個行人驚了拉車的馬,使車上的皇帝受驚,這在當時叫做“犯蹕”,于是這個行人交由廷尉張釋之治罪。張釋之是一位嚴格執法、敢于堅持己見的官員,他經過調查,認定此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車馬被驚,不算“犯蹕”,按律判定“罰金四兩”。漢文帝對這個判決表示不滿,因為差一點使皇帝受傷,應該重判。張釋之則依法力爭,說:“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現在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要是判重了,就失去了依據,會使法律在百姓中失掉威信。這個案子既然交給廷尉處置,廷尉如有偏差,就會開隨意處罰的先例,使陛下失信于民。”漢文帝聽后覺得有道理,表示“廷尉是對的。” 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還有一次,有人盜竊漢高祖祠廟塑像前擺放的玉環,被捉后交廷尉治罪。張釋之同樣按照有關偷盜宗廟器件的法律規定判處棄市(斬首示眾),漢文帝對此判決極為惱怒不滿,他認為高祖祠廟是至高無上的,這種偷盜行為是大逆不道、無法無天的,應加以族刑,要求重判。張釋之見文帝大怒,不為所動,他免冠叩首說:“法律就規定到這里,并沒有規定盜哪個廟罪重,盜哪個廟罪輕。現在偷了高祖廟里器物判定族刑,萬一有愚民在高祖的長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將按什么法來判罪呢?” 漢文帝聽后為之語塞,經過慎重思考,最后還是認為廷尉是對的。
作為一個封建帝王,漢文帝能夠聽取臣下的規勸,謹慎從事,不固執己見,尊重法律,是難能可貴的。但應該說漢文帝這樣做,是為了劉家天下的長治久安,這也使得他不能不表現出歷史的局限性。如他對滅呂安劉的功臣周勃始終心存疑慮,以至將他解除職務,以致要投入監獄,就表現了這種局限性。
歷史會給后人以智慧。如何對待權與法,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課題。如果說,在人壓迫人的舊社會,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枉法,是一種常態的話,那么在人民的世紀,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一切干部都要慎重對待人民賦予的權力,永遠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就應該是我們的常態。但我們還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任何權力都具有兩重性,既可以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也可以被作為謀私的手段。那種權比法大、以權壓法的特權思想,不但違背了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也往往是一些人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一個重要的認識根源,是值得我們時刻警惕并加以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