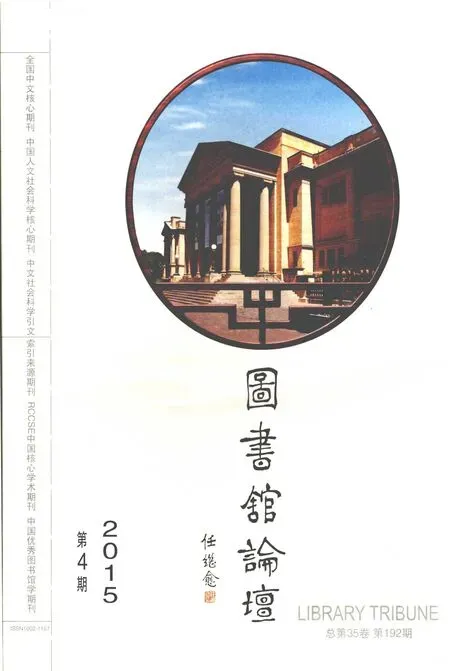在“紙張崇拜”與“數字擁戴”之間——高校圖書館信息資源建設的困境與出路*
程煥文,黃夢琪
1 數字時代——圖書館無形的蛻變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數字化和網絡化規模的迅速擴大,信息資源的載體形式、存儲方式、獲取方式、服務方式等皆發生了重大轉變。高校圖書館的信息資源建設方式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許多圖書館尚未做好應對準備,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數字浪潮之中。這種轉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1 從“紙質資源擁有者”向“數字資源使用者”的轉變
從本質上來說,圖書館從“紙質資源擁有者”蛻變為“數字資源使用者”。在紙本時代,圖書館是紙質資源至高無上的擁有者,被譽為“知識的海洋”,且以海藍為本色。可是在數字時代,隨著數字資源的迅猛增長,特別是在數量上和預算上全面超越紙質資源時,圖書館的資源已悄然從紙質資源向數字資源轉變。這種轉變導致圖書館的“資源角色”和“資源地位”也悄然發生變化:圖書館作為“紙質資源擁有者”的角色和地位日趨式微,但作為“數字資源使用者”的角色和地位日益顯著——數據商或數字出版商才是數字資源的擁有者,圖書館不過是數字資源的使用者,在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數據商的用戶或用戶代表——圖書館服務區的用戶代表。
1.2 從資源整理技術方法的“主導者”向“應用者”的轉變
從技術層面看,圖書館已從資源整理技術方法的“主導者”轉變為資源整理技術方法的“應用者”。過去圖書館是紙質資源的擁有者,在資源整理上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一切唯我獨尊,自行編制分類法、主題詞表,制定文獻著錄規則,頒布各項服務標準,所有讀者和用戶必須按照圖書館制定的規則行事。可是在如今的數字時代,圖書館不再是數字資源的擁有者,如何整理數字資源由數據商說了算,圖書館充其量不過是數據商征求意見的客戶對象,被迫從資源整理技術方法的主導者變為資源整理技術方法的服從者和應用者,完全喪失了資源整理技術方法主導者的地位。
1.3 從“讀者在館借閱”向“用戶在線訪問”的轉變
就服務方式而言,圖書館服務已經從“線下服務”轉變為“線上服務”,從“讀者在館借閱”轉變為“用戶在線訪問”,從“有線網絡服務”轉變為“無線移動服務”。過去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讀者不得不到館借閱;如今用戶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可以隨時登陸圖書館網站查閱數字資源。于是網上訪問圖書館的用戶越來越多,到館借閱的用戶越來越少。
上述三個轉變在總體上提升了圖書館的服務效率,更大程度地滿足了圖書館用戶的需求。但也給圖書館帶來了持久的困惑。
其一,關于數字資源,究竟是應該“擁有”,還是應該“獲取”?或者說“擁有”與“獲取”哪個更重要?這個問題已經討論了十幾年,起初“獲取”的呼聲甚至高于“擁有”,現在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已經不再新鮮。我的基本觀點是:“擁有”是硬道理,“獲取”是不得已。
其二,關于資源建設的方向,究竟是應該“紙張崇拜”,還是應該“數字擁戴”?絕大多數人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數字擁戴”,因為這是時代的潮流。與時俱進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盲目地“追波逐流”。正因為如此,我把“在‘紙張崇拜’與‘數字擁戴’之間”作為這次演講的題目,談談對高校圖書館資源建設的粗淺看法。
2 數字擁戴——圖書館糊涂的愛
對于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建設,我有幾個基本判斷:(1)我國研究型大學圖書館的數字資源建設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預算上已經全面超過紙質資源建設;(2)數字資源在使用上具有先天的優越性。20世紀50年代,圖書館界在用戶服務上曾提出“廣、快、精、準”四字要求,那時是紙本時代,這個要求不過是愿景。現在是數字時代,不僅可以做到“廣、快、精、準”,還可以做到“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和無遠弗界”;(3)數字資源是“土豪”的至愛,也是“草根”的悲哀。在紙本時代,圖書館的紙質資源建設需要長年累月的積累;在數字時代,圖書館的數字資源建設則無需長年累月的積累,只要有錢,一夜之間就可以從數字資源的“窮二代”變為數字資源的“富二代”。圖書館的資源建設似乎不再需要館藏發展規劃,只要有錢,一夜之間就可以從地獄升上天堂,成為我國乃至世界圖書館數字資源的最富有者。這在紙本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因為如此,隨著“211工程”和“985工程”的發展,高校圖書館在數字資源建設上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沒有錢的高校圖書館對于價格昂貴的數據庫只能望洋興嘆,徒生悲傷。
數字資源既是一個好東西,也是一味迷魂湯,我們不能被這個好東西沖昏了頭腦。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信息學家蘭開斯特教授曾預言2000年人類社會將進入“無紙的信息社會”[1],隨后還衍生了許多類似的預言。這種烏托邦式的預言誤導了許多圖書館人,以至于今天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在數字化網絡化時代沒有必要加強紙本館藏的發展。這種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的,甚至是愚昧的。數字資源相對于紙質資源的確具有許多優勢,但這種優勢不是一種“替代關系”,而是一種“優劣互補關系”。如果我們不能清醒地認識紙質資源與數字資源,而是盲目地追求數字資源,那么我們就永遠走不出數字資源帶給圖書館資源建設的艱難困境。目前這種困境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
2.1 資源壟斷
目前我國高校圖書館面臨的最大困擾是國內外數據商的數字信息資源壟斷。許多數據商為了提升其數據庫產品的競爭力,與眾多書刊出版機構簽署獨家數字出版授權協議,如中國知網的獨家授權期刊達到1,600種[2]。書刊出版機構也大多樂此不疲,特別是行業性的期刊出版機構。于是紙本出版商與數據商結成利益共同體,期刊全文數據庫成為沒有市場競爭的獨步天下的壟斷資源。在這種一家獨大的資源壟斷的情況下,數據庫的定價是數據商說了算,數據庫漲價還是數據商說了算。定價的依據是什么?漲價的依據是什么?國家沒有規定,市場沒有制約,數據商為所欲為,圖書館成了被人任意宰割的羔羊。例如,購買一年的全部紙質中文學術期刊的價格大概是150萬元,可是購買CNKI之類的中文學術期刊數據庫的價格已經超過100萬元。前幾年荷蘭的Elsevier突然提出要在數年內將在我國銷售的價格漲到與在歐美市場的價格一致,每年的漲幅高達20%-40%,大中華圈內的圖書館集體抵制,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可見“與國際接軌”也不一定是一個好東西。一位出版發行領域的教授告訴我:2013年我國的數字圖書出版投入了200億元,但收入只有50億元,入不敷出。言下之意是:數字出版的成本很高,數字出版品的價格太低,應該漲價。我不認可這種邏輯。我國的高鐵建設投入數千億元人民幣,高鐵票價甚至貴過飛機票票價,尚且需要十年才能收回成本,數字出版總不能當年投入,當年收回成本,甚至贏利吧。“有錢就是任性”,這句網絡流行語用在數據商的定價和漲價上十分貼切。
2.2 資源訛詐
在數字資源普遍被數據商壟斷的情況下,“資源訛詐”不僅順理成章,而且五花八門:
(1)捆綁售賣紙本期刊。在銷售期刊全文數據庫時捆綁紙本期刊,這是國外數據商的普遍做法,雖然捆綁的數量、比例和松緊程度各有不同,但是大同小異。捆綁紙本期刊的目的是使紙本出版商和數字出版商雙雙贏利,結果是坑害了終端客戶圖書館,使圖書館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承受難以承受的價格。
(2)拆分數據庫。一些數據商為了追求高額利潤,別出心裁,與出版商“合作”,將某類專業學術期刊,或者同類學術期刊中的高影響因子期刊從原有數據庫中拿出,裁剪成新的數據庫,進行高價銷售,原有的數據庫并沒有因此降價,圖書館必須為此付出新的代價。國際上有OCLC的BioOne,我國有中華醫學會期刊數據庫。
(3)同類重復。在數字圖書數據庫中,數字資源的壟斷相對較弱,但是同類數據庫內容的重復度非常高,有的甚至高達70%。于是圖書館為了獲得30%的差異內容,不得不為70%的重復資源重復付費。
(4)高價售賣學位論文。近年我國高校每年產出的博碩士學位論文在40萬篇以上,超過了我國年圖書出版種數。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高校一直在花錢購買自己產出的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很多年以來,我在全國高校圖書館工作指導委員會上一直呼吁教育部應該制定政策,建立“全國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和“網絡課程共享平臺”(包括網絡精品課程和慕課課程),可是一直沒有實現。高校圖書館嚴格遵守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要求,在全國層面只提供文摘服務和部分內容服務,可是各高校的研究生管理部門違規與數據商簽訂秘密協議,出賣博碩士學位論文的數字版權;個別博碩士論文呈繳本收藏單位不經允許,私自將數字化的博碩士學位論文商業化,高價兜售。于是,一方面是高校學術資源的嚴重流失,無人監管;另一方面是高校圖書館不斷地花大價錢購買高校產出的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荒唐至極,荒謬至極!
(5)用戶數據造假。長期以來,由于大量的數據庫都是網絡版數據庫,圖書館只是購買了使用權,不得不依賴數據商提供用戶統計數據,數據商也時常根據用戶統計數據來確定銷售策略。問題是數據商提供的用戶統計數據可靠嗎?前幾年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開發了一個中間件,專門用于監測用戶的數據庫點擊與下載情況,結果發現監測到的用戶統計數據與數據商提供的用戶統計數據有很大的出入,換句話說,絕大部分數據商提供的用戶統計數據有水分,很不可信。數據商用這種自己造出來的數據作為漲價的依據,訛詐圖書館,許多圖書館還蒙在鼓里!
2.3 資源壁壘
圖書館購買的數據庫越來越多,幾百個數據庫看起來非常壯觀,可是每個數據庫都是一個“信息孤島”,彼此之間壁壘重重,無法兼容共享,跨庫檢索和跨語言檢索一直是困擾數據庫使用的技術與市場壁壘。最近幾年相繼出現聯邦檢索和發現系統,已經極大地改善了跨庫檢索和跨語言檢索的困擾,當然圖書館又不得不為此付出更高的費用。現在的問題是:個別數據商在銷售合同中悄悄地增添了不允許圖書館購買數據庫后進行外部鏈接的條款,禁止圖書館對數字資源進行整合利用。這就好比圖書館購買了圖書,出版商不允許圖書館進行分類編目一樣,荒唐、荒謬至極!數字出版商為了商業利益而刻意制造的資源壁壘既給用戶造成了極大的不便,也嚴重侵害了圖書館的職業精神。
2.4 資源浪費
無論是紙質資源還是數字資源,其使用率基本上都符合“二八律”,也就是說,只有兩成左右的資源被人經常使用,八成左右的資源極少被人使用甚至無人使用。對紙質資源來說,圖書館擁有所有權,即使一直無人使用,圖書館仍然擁有一份實實在在的財產,這份財產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值。古籍就不用講了,民國書刊,甚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出版品,現在的市場價格都數倍甚至數十倍地高過當年的購買價格。可是對于數字資源來說,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圖書館只購買了使用權,每年都必須為極少甚至無人使用的大約八成的數字資源付費,這種浪費驚人!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算,即使是用數據商提供的不可靠用戶統計數據來測算圖書館用戶點擊或者下載文獻的平均價格,都不難發現其代價極其高昂:在大多數情況下,點擊一次或者下載一篇文獻的價格是幾元甚至幾十元人民幣,足以買回整本紙質書刊。圖書館在數據庫使用推廣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二八律”就擺在那里,怎么做也只是心理安慰,無法徹底改變現狀。問題在哪里?自然是壟斷數據商的大宗銷售策略造成的。
2.5 資源同質
在紙本時代,各圖書館根據各自的性質、任務和服務對象開展資源建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息資源體系。在數字時代,數字資源的可獲得性得到極大的提高,雖然圖書館在數字資源建設上也有選擇,但是總的來看,數據商的大宗銷售策略使許多圖書館失去了“選擇的自由”,而數據商最大的期望就是圖書館不加選擇地購買。在高校圖書館用戶,特別是極少數有影響力的用戶的要求下,高校圖書館在數字資源購買上不得不相互攀比,貪多求全,于是同類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的同質化日趨加劇。雖然數字資源的同質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同類高校圖書館在數字資源服務上的同等資源水準,但在另一方面,這種同質化也使各高校圖書館逐漸失去資源特色和學術魅力。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圖書館的信息資源完全數字化,且基本上都是數據商銷售的數據庫,在這種情形下,圖書館還有生命力嗎?那樣的話,圖書館無異于24小時開放的7-Eleven便利店,隨時可以被替代,因為誰都可以開設這樣的便利店。
2.6 閱讀退化
在數字資源普泛化的今天,閱讀的形式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在人們喋喋不休地爭論深閱讀與淺閱讀、紙本閱讀與數字閱讀的優劣利弊的同時,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高校圖書館紙本借閱率一直在持續下降,而數字資源的利用率并沒有明顯的提高。這表明閱讀在退化。互聯網使一代人沉湎于網絡游戲,現在移動通訊網又使一代人沉迷于微博、微信,在無休無止地發微信與轉微信、點贊與等待點贊中燃燒青春,消耗生命!社交網絡使許多年輕人失去了現實的人際溝通基本能力,不少年輕人終日呈現的是一幅“手機面孔”——全神貫注地低頭注視手機,旁若無人,表情呆滯,偶爾獨自爆笑。對網絡的依賴使學生失去了記憶的本能,大腦作為思維的機器沒有了記憶的能量。學生上課時,凡是遇到教師提問,鮮有思考者,立即查看手機的現象非常普遍。“手機控”風靡全社會,手機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異常重要的一部分,須臾離開即會令人失去安全感,焦躁不安,甚至不知道如何閱讀和學習。高校圖書館重視數字資源建設是大勢所趨,但不可以盲目地“數字擁戴”,否則,其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導致學生的閱讀能力進一步退化。
3 紙張崇拜——圖書館不可割舍的愛
在各高校圖書館的目光專注于數字資源建設的時刻,北京大學做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2013年12月,北京大學圖書館籌資1億多元,從日本回購“大倉藏書”,共計931種28,143冊,其中古籍904部,包括中國古籍716部26,260冊,日本古籍187部2,546冊,朝鮮古籍1部2冊[3]。北京大學圖書館用巨額資金回購“大倉藏書”,令人羨慕,令人欽佩,更值得我們深思和效法。
3.1 紙本的價值
2013年德國一家科技出版商在南京召開業界專家咨詢會議,這家出版商的全文期刊數據庫在我國銷售得很好,于是計劃將過去100多年出版的科技名著全部數字化,打包成一個數據庫在我國銷售,想賣個好價錢。與會者大多循著出版商的思路發表意見,而我的看法完全相左:紙本書有三重價值——內容價值、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紙本圖書數字化以后只有內容價值,沒有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正如法國盧浮宮收藏的蒙娜麗莎油畫價值連城,可是數字化的蒙娜麗莎一錢不值一樣。也就是說,相對于紙本圖書來說,數字圖書只有紙本圖書三分之一的價值。不僅如此,這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價值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應該再折半。就數據庫而言,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期刊論文在某種程度上說是片狀的,數字化以后非常便于點對點的查閱,因而期刊全文數據庫十分受歡迎。然而圖書全文數據庫完全不一樣,在某種程度上是塊狀的,在網上閱讀整本數字圖書遠遠不及閱讀紙本圖書便捷。如此說來,數字圖書的價值最多只有紙本圖書六分之一的價值,況且數字化的科技圖書充其量只有科技史研究方面的內容價值,所以該出版商開發的圖書數據庫只能友情免費贈送。出版商聞此言愕然啞然,業界專家們拍手稱快。總之,在圖書館資源建設中,千萬不要忘記了紙本的價值。
3.2 紙本的生命
“紙張是個老不死的東西。”是我的一句名言。新世紀初,美國有幾家報紙陸續倒閉,不少媒體都在炒作報紙的消亡。那時我作為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在廣州參加過一次黨報發展論壇,在論壇上,許多傳媒要人對報紙的未來憂心忡忡,哀聲四起。我可能是唯一的“另類”,我說:美國的報紙屬于私營企業,經濟效益是第一位的,不盈利即倒閉,是正常的市場現象;我國的報紙則是宣傳工具,社會效益是第一位的,黨在報紙就在,賺錢的南方報系很興旺,不賺錢的各地報紙也不會倒閉,是國情而不是市場決定報紙的命運。
近年來開放存取(Open Access)風靡全球,開放存取的確是學術資源共享的福音,天下也的確有這種免費的午餐。可是大家想過沒有,這樣的免費午餐究竟是誰在買單?如果所有的學術期刊都實現開放存取,那么誰來支付學術期刊編輯出版的費用?是富足的出版主管機構,還是貢獻智慧的作者,或者政府?期刊出版是一個產業鏈,圖書出版也是一個產業鏈,在產業鏈上游,有許多人靠這個產業來維持生活,而終端用戶卻都要免費利用,這是不可想象和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開放存取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一些富有的開明學術機構或者團體對社會的一種學術饋贈與施舍,而圖書館界奢望的全面開放存取不過是黃粱美夢。
在數字資源飛速增長的同時,紙質資源的增長是不容忽視的。現實是紙本出版與數字出版齊飛。2013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整體收入2,540億元,比2012年增長31.25%[4];出版圖書444,427種,增長7.35%,總金額1,289億元,增長8.95%[5]。從增長量看,目前數字出版漲幅雖然高于紙質出版,但圖書出版品種從“十五”末的22萬余種躥升至“十一五”末的32萬余種,2012年突破40萬種,出版數量也是一路飆升。
根據尼爾森圖書監測的統計,2014年美英德三國紙本圖書銷售回暖,美國紙本圖書增長2.4%,英國走出2013年下滑9%的陰影,2014年僅小幅下滑1.3%,德國也從2014年3月下滑3.3%的劣勢中逆轉。回頭看我國,2014全國圖書零售市場總碼洋超過500億元,相比2013年實現3.26%的增長,比英語世界中增幅最高的美國還要高[6]。
在網絡化數字化如此盛行的今天,紙本圖書不僅沒有消亡,出版量仍然在不斷增加,銷售也開始回暖。這種紙本出版與數字出版比翼齊飛的事實,難道不值得我們尊重和深思嗎?
就高校圖書館而言,有兩個現象值得反思:一是大專生、本科生很少利用學術數據庫。就本科生而言,三年級以下的學生基本上不怎么用學術數據庫,四年級的學生由于要做畢業論文,才被迫使用學術數據庫,這種現象一直普遍存在;二是在數字化網絡化環境下出生和成長起來的90后大學生,一直過著數字生活,幾乎人人都是“手機控”,可是絕大多數90后大學生在無法借到教師指定的紙本教學參考書時,都不樂意使用圖書館隨手可得的數字圖書,時常抱怨圖書館紙本圖書藏書不足,呼吁增加紙本圖書復本數量的聲音此起彼伏,這種現象同樣在各高校圖書館普遍存在。這些現象背后的本質是什么?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紙本圖書是有生命力的,具有數字圖書不可替代的優勢,至少在今天紙本圖書仍然是大學生系統學習的最佳選擇。
3.3 紙本的收藏
圖書館不能沒有紙本,如果沒有紙本,圖書館就沒有安身立命的根本。在紙本出版與數字出版齊飛的情況下,高校圖書館應該樹立正確的紙本收藏與數字訂購并重的資源建設觀,在大量購買數據庫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收藏紙質資源。
許多圖書館界的同仁,尤其是歐美大學圖書館界的同仁在談及圖書館資源變化的時候,都會不由自主地渲染數字資源的飛速增長和紙質資源的日趨式微。我們不能被這種渲染所迷惑。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雖然歐美大學圖書館的數字資源一直在飛速增長,但是紙本資源的增長并沒有因此而停止,只不過現在沒有人樂意去夸耀紙本資源的增長罷了。現在的情形是:各大學圖書館一方面普遍在減少紙本期刊的訂購品種與數量,另一方面又在不斷增加紙本圖書的品種與數量。原因顯而易見,理科的教師和研究生更加依賴期刊全文數據庫,文科的教師和研究生在依賴期刊全文數據庫的同時仍然喜好紙本圖書,而不論哪個學科的大專生、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在系統的知識學習中仍然以紙本閱讀為主。
如今我國中文圖書年出版量在40萬種以上,其中高校圖書館可以采購的學術圖書約占四分之一。大部分“985工程”高校圖書館的年圖書采購量為4萬-6萬種,這是許多高校師生抱怨借不到新書的主要原因。近十年來,很多省市公共圖書館由于沒有購買外文數據庫和外文原版期刊的壓力,大部分經費用于中文圖書的采購,其圖書品種和數量全面超越高校圖書館,個別地方的高校師生甚至熱衷去公共圖書館而不是本校圖書館,原因在于公共圖書館的藏書品種更多更全。
復旦大學圖書館從2013年開始實施單本采訪制度,新進圖書基本上不購買復本,但是師生可以向圖書館提出復本購買申請,圖書館再根據申請去采購復本,大約80%的圖書為單本,另外20%則是根據師生的要求而增加的復本,每年采訪的圖書品種數量猛增到8萬種以上,較大地提高了藏書效率和使用效率。如果一個同類的“985工程”高校圖書館不改變采購策略,每年仍然保持訂購約4萬種圖書,平均每種圖書2個復本,雖然每年的圖書購買數量也是8萬冊,但10年以后,這個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在品種上就要比復旦大學圖書館少40萬種,這是一個不小的差距。因此,我們今天必須認真地思考和研究紙本圖書采購中品種與復本的關系。
3.4 紙本的特色
特色紙本資源是研究型大學圖書館的安身立命之本。高校圖書館的信息資源無特色即無特點,無特點就無生命力。在信息資源日益同質化的今天,研究型大學圖書館依靠什么吸引學者,又依靠什么確立其學術地位?自然是“人無我有”的特色紙本資源。
20世紀20年代,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經為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草擬過一份圖書采購計劃書,其中有一個基本的觀點,那就是重點采購經史子集四部以外的民間文獻。這個理念在今天仍然值得繼承和發揚。過去十幾年來,中山大學圖書館一直把顧頡剛先生的這個理念奉為圭臬,相繼建立了一系列的學術大師專藏、喜樂斯外文專藏和民間文獻專藏。不少研究型大學圖書館也有類似的舉措,因此在學界享有獨到的聲譽。
特色館藏是高校學術競爭力的“能源”。誰擁有哪個領域的特色學術資源,誰就占領了哪個領域的學術高地。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
3.5 紙本的保存
圖書館學大師杜定友先生曾言“圖書館應該收藏一切有文字的紙片”,我的名言是“圖書館應該保存一切有文字的紙片”。這是圖書館的社會職能所在和歷史使命所然,所有圖書館都應竭力為之。
“敬惜字紙”是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盡管數字資源具有很多優勢,但是數字資源永遠無法替代紙本資源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人類的文字載體經歷了泥版、紙草、甲骨、金石、羊皮、竹木、簡帛、紙張、膠片、磁性介質材料等數千年的發展,唯有千壽的紙張最為優秀,而紙本則是文化載體的極致。“敬重紙本、珍惜紙本、保存紙本”應是每個圖書館人必須恪守的職業傳統,在數字時代,恪守這個職業傳統尤其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即使在未來,人類社會真的進入無紙信息社會,現在的圖書館也應該會成為最好的圖書博物館。
4 結論
4.1 沒有“紙張崇拜”情結的館長基本上是沒有文化的館長
不懂專業的館長不可怕,就怕館長沒文化。在我國,目前非專業背景的專家學者和干部擔任圖書館館長的現象十分普遍,這并不可怕,因為他們既可以慢慢地熟悉和學習專業,還可以依仗專業骨干,自己不作為也不亂作為即可;可怕的是館長沒有文化,又好大喜功,胡作非為。判斷一個館長有沒有文化,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有沒有“紙張崇拜”情結;如果沒有“紙張崇拜”情結,基本上可以認定為沒有文化。
信息資源建設是圖書館的基礎工作,基礎工作的好壞直接決定圖書館服務的質量。采訪采訪,有采有訪,既要采,還要訪。許多館長只知道按照書目采購,不知道還要四處訪求,所以資源建設沒有特色。上海圖書館矢志不渝地收集各地家譜、方志和手稿,以至于此類藏書獨步天下,無處可以匹敵。這就是訪求的榜樣。
如今資源建設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數據商天天圍著館長轉,鼓動館長購買數據庫;館配商也天天圍著館長轉,祈求館長多給點經費配額,于是過去的主動采購變成現在的被動采購,采購的技能在退化,訪求的本領在消失。就訪求而言,我的基本看法是:數字資源是數據商“上門來求”,紙質資源則應是館長“出門去求”。
4.2 資源為王——保持資源的多樣性和原始性
數年前我說過:“資源為王,服務為妃,技術為婢。”[7]許多人不以為然。過去國家圖書館在服務上有瑕疵,學者抱怨不少,可是再多抱怨,學者還是離不開國家圖書館,原因何在?不就是國家圖書館有別的圖書館沒有的資源嘛!有了資源,即使服務和技術跟不上,圖書館仍然是學人需要的;可是,如果沒有資源,一切就無從談起,所以“資源為王”是圖書館的根本。
在資源建設中,高校圖書館應該尊重和保持資源的多樣性,堅持客觀中立的專業理念,不受任何思想意識的影響,不論“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也不論“革命的”還是“反動的”,更不論“高雅的”還是“低俗的”,都應該盡可能地收藏和保存。
在資源建設中,高校圖書館還應該保持資源的“原始性”,盡力收集一手資料。1989年我國發生政治風波時,美國多家大學圖書館不約而同地發起收集相關資料的項目申請,最后哈佛大學圖書館成功申請到專項經費,于是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甚至派人到我國各地現場收集資料,如今哈佛大學圖書館擁有這場政治風波最原始、最全面、最完整的資料,包括書刊、報紙、傳單、照片、視頻錄像、電視節目。也就是說,今后學者要研究這段歷史,只能去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而不是我國的某個圖書館找資料。這個例子足以說明很多問題,也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圖書館的資源建設。
4.3 優化空間資源
空間資源始終是圖書館的重要資源。2003年美國學者哈羅德和肖恩對1995-2002年完工的工程面積在2萬平方英尺以上的357家大學圖書館進行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大部分圖書館面積有了較大的增加;而且在調查中發現,更大的空間會使得越來越多的讀者覺得舒適、方便、有用,更大的空間會更加受到用戶的歡迎[8]。因此,“數字時代沒有必要擴建館舍”的論調十分荒謬。事實上,在數字時代,圖書館的空間資源比過去更加重要,這不僅是因為空間資源是圖書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更是因為圖書館正在成為知識中心、學習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客觀需要[9]。在空間資源建設上,高校圖書館至少應該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優化現有的空間資源,建設更有吸引力的信息共享空間、創意空間、協同學習空間等;第二,爭取更多更大的空間資源,特別是建設獨立的貯存圖書館或共用的貯存圖書館。
4.4 拓展文化資源
文化是軟實力。高校圖書館在為教學科研服務的同時,應該大力拓展文化資源,開展與學校學術、歷史、文化相關的文化建設,特別是閱讀推廣活動,喚醒學生的讀書熱情,讓更多的學生讀更多的書。
4.5 啟動“休克療法”
面對數字資源建設的種種困境,我們還能做什么?全國高校圖書館必須聯合起來,啟動“休克療法”,堅決抵制不良數據商,迫使迷途的數據商從良,不從良即消亡。我期待這一天早日到來![10]
[1] Lancaster F. W. 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M]. New York, San Francisco, London: Academic Press,1978.
[2] 獨家授權期刊導航[EB/OL]. [2014-09-26].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n_Navi.aspx?NaviID=2&Flg=.
[3] 北京大學圖書館展出2 萬余冊從日本回購的“大倉藏書”[EB/OL]. (2014-05-04) [2015-03-04]. 新浪新聞:http://news.sina.com.cn/o/p/2014-05-04/1317 30057177.shtml.
[4] 2013-2014 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摘要[EB/OL].[2014-09-28]. http://www.chinaxwcb.com/2014-07/18/content_298251.htm.
[5] 2013-2014 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EB/OL].[2014-09-28]. http://www.gapp.gov.cn/news/1658/212700.shtml.
[6] 魏小河. 大數據告訴你,紙質書還沒玩完[EB/OL].(2015-02-26) [2015-03-04]. 新浪文化專欄:http://cul.history.sina.com.cn/zl/shiye/2015-02-26/1619 1126.shtml.
[7] 程煥文. 資源為王服務為妃技術為婢[EB/OL].(2010-04-15) [2015-03-04]. 竹帛齋主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hjob.html.
[8] 閆小芬. 新時期美國大學圖書館館舍建設趨勢[J]. 大學圖書館學報. 2006 (4):81-86.
[9] 程煥文. 圖書館的價值與使命[M].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4:234-246.
[10] 程煥文. 全國高校圖書館聯合抵制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數據庫[EB/OL]. (2014-12-30)[2015-03-04]. 竹帛齋主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 9f0102ve4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