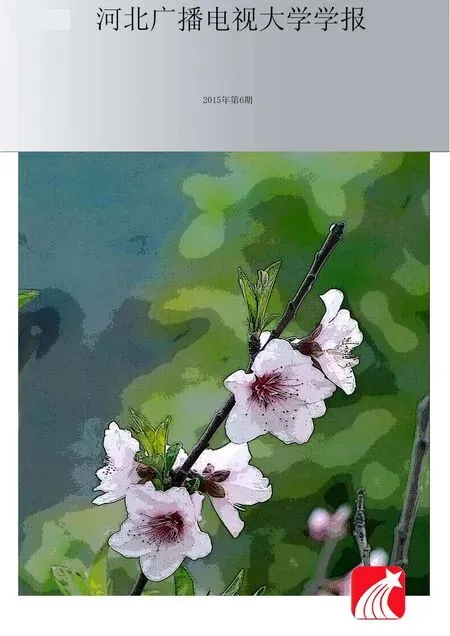近代河南蝗災(zāi)及其影響述略
王鑫宏
(黃河科技學(xué)院,河南 鄭州 450063)
?
近代河南蝗災(zāi)及其影響述略
王鑫宏
(黃河科技學(xué)院,河南 鄭州 450063)
近代河南蝗災(zāi)頻仍,是當(dāng)時河南三大自然災(zāi)害之一。蝗災(zāi)在晚清時期主要集中在1855-1857年,民國時期則以20世紀(jì)40年代初期豫東一帶的蝗患最為嚴(yán)重。蝗災(zāi)給河南社會帶來較為惡劣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蝗災(zāi)造成農(nóng)業(yè)減產(chǎn),歷次蝗災(zāi)發(fā)生之后,農(nóng)作物被蝗蟲啃噬凈盡,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進而引發(fā)饑荒;二是蝗災(zāi)導(dǎo)致民眾生活環(huán)境的惡化,滋生了大量災(zāi)民;三是蝗災(zāi)還激起迷信活動的泛濫,而迷信活動往往使災(zāi)情更加惡化。
近代;河南;蝗災(zāi);影響
全世界飛蝗有7個品種,我國有3個。[1](P281)河南是東亞飛蝗的重點發(fā)生區(qū)之一。蝗蟲,俗稱“螞蚱”,常常發(fā)生在干旱或先澇后旱的條件之下,蝗蟲的幼蟲被稱為“蝗蝻”,只能跳躍,成蟲善飛。蝗蟲有夏蝗和秋蝗之分,成蟲于5-6月份的為夏蝗,成蟲于7-8月份的為秋蝗。蝗蟲一般成群飛翔,有時把田禾“嚙食無余”,連草木也不能幸免,甚至還傷及人畜。蝗災(zāi)是近代河南三大自然災(zāi)害之一,本文對近代河南的蝗災(zāi)做一簡要評述。
一、近代河南蝗災(zāi)概況
筆者根據(jù)《近代中國災(zāi)荒紀(jì)年》《近代中國災(zāi)荒紀(jì)年續(xù)編》等相關(guān)資料統(tǒng)計,近代河南共發(fā)生蝗災(zāi)35 年次,大約3 年一次。其中,10縣以上的蝗災(zāi)共有7 年次,1843 年23縣、1856 年67縣、1928 年66縣、1929 年25縣、1933 年18縣、1943年58縣、1945年26縣,1854-1857年、1927-1929年、1941-1945這三個時間段則連續(xù)出現(xiàn)蝗害。而從表1中可以看出,近代河南的蝗災(zāi)發(fā)生頻度中,晚清時期河南蝗災(zāi)發(fā)生的頻度僅次于河北,民國時期則僅次于河北和山東,可見發(fā)生蝗災(zāi)的頻度之高。
1.晚清時期的河南蝗災(zāi)
晚清時期的河南省蝗災(zāi)主要集中在1855年至1857年。這三年,河南不僅承受了黃河在銅瓦廂改道所釀成的巨浸,與此同時又遭受了連續(xù)三年的飛蝗侵襲。1855年,南陽一帶有“旱蝗民饑”的記載。1856年,蝗災(zāi)在河南廣泛地蔓延起來,寧陵、通許、虞城、洧川、尉氏、睢州、杞縣、鹿邑、考城、祥符、鄢陵、陳留、柘城、固始、商城、許州等十六州縣相繼受災(zāi)。河南巡撫英桂在奏報這些地方的實況時,同樣地強調(diào)飛蝗過境,或蝗子生發(fā),有過而不留者,有一經(jīng)停落及甫經(jīng)萌動即時撲滅者,間有蔓延較廣,即用重金收買,自二三千金至五六千金不等。當(dāng)時已是金秋時節(jié),成片的飛蝗從天而降,所過之處,禾稼俱盡,村民們只好手扯布單,在田間分離去趕,雖捕獲了成千上萬的蝗蟲,饑荒的年景卻仍抗不過去。這年,咸豐帝曾派員往河南受蝗地區(qū)查看災(zāi)情,同時帶去了組織人力撲滅蝗蟲的旨令。但事情卻愈演愈烈,1857年蝗災(zāi)繼續(xù)肆虐河南省。
2.民國時期的河南蝗災(zāi)
民國時期河南省蝗災(zāi)同樣猖獗,如1921年,豫北淇縣及其東北部之湯陰、內(nèi)黃、安陽等縣發(fā)生蝗蝻,初則縣知事匿不報告,現(xiàn)已勢成燎原,據(jù)內(nèi)黃知事呈報,謂日前有飛蝗由湯陰飛至屬縣,遙望如黑云蔽空,所至之處,阡壟盡赤,無復(fù)青苗。安陽秋禾已大半吃壞,宜溝等處出百里內(nèi),田野已成濯濯之像。1923年5月,南陽一帶,又發(fā)現(xiàn)蝗蟲,飛天蔽日,侵食禾苗。行蹤所及之處,平鋪地面,一望無際,捕埋乏術(shù),窮于應(yīng)付,由南陽至內(nèi)鄉(xiāng)、淅川三百余里,到處皆是。

表1 清代、民國主要蝗災(zāi)省發(fā)生頻度表
資料來源:趙艷萍:《民國時期蝗災(zāi)與社會應(yīng)對》,廣州:廣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9頁.
民國時期河南蝗災(zāi)最集中的時期是20世紀(jì)40年代初期。1938 年6月,鄭州花園口決堤造成的黃河改道,使豫東平原形成了大面積的黃泛區(qū),蘆葦叢生、淤灘滿目的黃泛地帶,恰好為蝗蝻的滋生和繁殖提供了極為適宜的生長環(huán)境,直接誘發(fā)了 1941-1947 年間的嚴(yán)重蝗災(zāi)。[2](P25)這段時期豫東一帶蝗蟲數(shù)量驚人,各地縣志對這段時期的蝗災(zāi)多有記載,如太康1941 年“夏秋蝗蟲從泛區(qū)發(fā)生,初為蝗蝻,蓋地而來,地里家里亂蹦亂跳,……繼而飛蝗,遮天蔽日,忽忽作響,如同刮風(fēng)”。[3](P94)中牟劉集村,1942 年蝗蟲最多時,“村里、村外、街頭、巷尾、房上、院里、樹上、莊稼棵上到處爬得滿滿的,有些棚屋都被壓塌,各家各戶連鍋都不敢掀開,否則立刻就被爬滿,……隨后蝗蝻變成成蟲,猶如狂風(fēng)暴雨,天昏地暗,一片轟鳴;落到地上,壓塌房屋,壓斷樹枝……”[4](P110)鄢陵1943 年蝗災(zāi)發(fā)生時,“每平方米多達(dá)數(shù)百頭,飛蝗起處,遮天蔽日,行若流云,忽忽作響,聲如驟風(fēng),飛蝗墜降,鋪天蓋地,屋室鍋碗之中,也比比皆是,平地積蝗蟲后達(dá)寸余,最多處厚盈尺,腳踏如踩棉絮,草禾被食,一掃而光,喳喳之聲聞于數(shù)十丈之外,路溝之中,若用荊籃挖之,只一下可滿籃……”[5](P182)對于該年的蝗災(zāi),親歷者河南魯山人李玉震回憶當(dāng)時蝗災(zāi)的情況,“我們無可奈何地站在那里看著蝗蟲毀壞莊稼。一尺多高的五畝多谷苗爬滿了密密麻麻的蝗蟲,綠油油的谷子變成土灰色,不消吃一碗飯工夫,谷子被吃得片葉不留。我母親領(lǐng)我到其他地塊一看,玉米、高粱、小谷子等都被蝗蟲啃成光桿。我們又看了別人家的谷物,也全部吃光,無一幸免。蝗蟲把禾苗吃完了,我想著它也該遠(yuǎn)走高飛了,誰知各種草類也成了它們的佳肴,漫山遍野的青草也被它們吃得光禿禿的。第二天上午,發(fā)現(xiàn)村上蝗蟲驟然增多,從各家的房子上像流水似的滾爬而下,裹成疙瘩,蟻聚成堆。有些樹上因落飛蝗過多而折枝,有一家的草棚被壓塌,簡直成了‘螞蚱世界’。全村人面面相覷,張皇失措。各戶房門不敢開,一開門蝗蟲就蜂擁而人,亂飛亂蹦,能把窗戶紙啃碎;廚房的鍋蓋也不敢揭,一揭蝗蟲就跳進熱鍋,吐出黑水,污染飯菜,其味澀苦,不堪食用,村民吃飯不敢外出,飛蝗似乎故意往碗里鉆。一直襲擾兩天,鬧得人們惶惶不可終日”。[6](P62-63)從20世紀(jì)40年代河南豫東蝗災(zāi)發(fā)生的縣份來看,1941年、1942年、1943年、1944年、1945年、1946年、1947 年分別為 6縣、15縣、17縣、20縣、7縣、4縣、3縣,約占當(dāng)年豫東泛區(qū)總縣數(shù)的30%、75%、85%、100%、35%、20%、15%。[2](P25-28)尤其是1942-1944 年豫東泛區(qū)幾乎是無縣不蝗。由此可見,民國河南蝗災(zāi)之嚴(yán)重程度。
二、 近代河南蝗災(zāi)的影響
近代河南發(fā)生蝗災(zāi)的次數(shù)雖遠(yuǎn)低于旱澇災(zāi)害,但其造成的影響也是極為惡劣的,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1.導(dǎo)致農(nóng)業(yè)歉收
蝗蟲所到之處,農(nóng)作物往往被啃噬干凈,災(zāi)區(qū)農(nóng)業(yè)收成已無希望。1855年河南省蝗災(zāi)之中,清政府雖聲明“田禾唯有損傷,不過一隅中之一隅,不致成災(zāi)”。事實則不盡如其所報。當(dāng)時也是金秋時節(jié),成片的飛蝗從天而降,所過之處,禾稼俱盡,村民們只好手扯布單,在田間分離去趕,雖捕獲了成千上萬的蝗蟲,饑荒的年景卻仍抗不過去。民國時期蝗災(zāi)造成的農(nóng)業(yè)歉收遠(yuǎn)比晚清嚴(yán)重。20世紀(jì)40年代河南從受災(zāi)總面積看,1942年為2 386 089畝,1943年為5 323 033畝,1944年為6 360 658畝,1945年為2 306 366畝。豫東黃泛區(qū)內(nèi)蝗蟲危害的總面積每年皆超過200萬畝,其中1944年竟高達(dá)600多萬畝,可謂泛區(qū)內(nèi)處處皆蝗。1944年各縣受災(zāi)面積為開封9 770畝、中牟15 600畝、尉氏89 000畝、睢縣260 720畝、陳留200 000畝、通許148 140畝、太康43 204畝、項城568 470畝、柘城353 755畝、淮陽145 708畝、鄭縣1 184 520畝、鹿邑19 700畝、西華247 813畝、商水262 100畝、沈丘462 195畝、鄢陵478 000畝、杞縣584 300畝、廣武659 250畝、扶溝41 163畝等,遭蝗蟲危害的農(nóng)作物少則數(shù)千畝,多則五六十萬畝。[7]各地縣志對這些年份的蝗災(zāi)危害均有記載,如1942年,扶溝縣“飛蝗遮天蔽日,由北向南入扶溝境遇見禾苗,驟然落下,蠶食葉片,咬斷嫩頭,一棵谷子,從頭到頂,爬滿蝗蟲,吃的只剩光桿,再飛到別處,蟲災(zāi)造成絕收”。[8](P92)1944年秋,西峽境一度蝗飛蔽日,落下蓋地,所過之處,禾苗、樹葉多被吃光。丹水、丁河、回車、西峽口受災(zāi)尤重,一般收成僅十之一二,丁河一帶基本絕收。[9](P26)1944年7月,長垣飛蝗自南方來,遮天蔽日,勢如狂風(fēng),五晝夜不息,全縣秋禾十傷八九,蝗災(zāi)之重,前所未有。[10](P27)1945年,原、陽兩縣蝗災(zāi)嚴(yán)重,受災(zāi)面積達(dá)40多萬畝,減產(chǎn)八成。[11](P43)
2.造成災(zāi)民無數(shù)
嚴(yán)重的蝗災(zāi)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打擊往往是毀滅性的,不僅造成農(nóng)作物大幅度減產(chǎn)乃至絕收,還引發(fā)嚴(yán)重饑荒,致使大批災(zāi)民,或饑餓致死,或背井離鄉(xiāng)淪為流民。需要指出的是蝗災(zāi)導(dǎo)致的饑荒雖不如旱災(zāi)嚴(yán)重,這是因為饑餓的災(zāi)民往往會把蝗蟲作為食物來解決生存問題。據(jù)民國河南蝗災(zāi)親歷者徐輝口述:“不幾天的光景,村北各家各戶的上千畝谷子被蝗蝻吃的精光。在此情況下,……大量捕捉蝗蝻來吃。捉的多吃不完,用開水把蝗蝻燙死,攤在席上、箔上曬成干脯,儲存起來慢慢吃。”[6](P37)但饑荒總是不可遏制的產(chǎn)生。1857年,河南一些地方旱蝗交乘,災(zāi)民除了仰天號啕,只能四出逃荒,南陽一帶出現(xiàn)了饑民竟以食樹皮茍延殘喘的嚴(yán)重災(zāi)情。原籍河南光州的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在奏折中談及家鄉(xiāng)情景時稱:“秋間蝗災(zāi)較早,一食無余,民間之苦異常,有數(shù)十里無炊煙者。”[12](P182)這也是我們所見到的關(guān)于蝗災(zāi)的奏折中,有數(shù)的幾份擺脫了“勘不成災(zāi)”的框框而較為如實地道出災(zāi)況的報告,雖區(qū)區(qū)幾十字,卻概括出了蝗患害人至極的慘況,這或許與李孟群并非任職于當(dāng)?shù)氐纳矸菀约皩︵l(xiāng)梓的關(guān)切之情有關(guān)。民國時期蝗災(zāi)導(dǎo)致的饑荒更甚。如1942年商水縣蝗災(zāi)被稱為“造成五谷歉收,妻離子散,餓殍遍野的嚴(yán)重災(zāi)荒”。[13](P185)太康縣蝗災(zāi),秋季收成不及三成,除紅芋以外,其他作物基本顆粒無收。農(nóng)歷十月,四柳樹村大多數(shù)戶已經(jīng)斷炊。到了臘月人的臉上都掛了黃色。全村當(dāng)時有80多戶人家,400多人,死絕戶的16戶,餓死162口人,更有甚者賣兒賣女。[13](P185)據(jù)河南魯山人李玉震回憶,1944年“春節(jié)過后,已有絕大多數(shù)戶缺糧斷炊。那時高利貸高得驚人,貸 1升(老秤10斤)還l斗(老秤100斤),也找不到地方貸,逼得農(nóng)民沒有辦法就破產(chǎn)渡荒。當(dāng)時,我的家鄉(xiāng)沙莊村(9個小自然村),計有72戶人家,其中典當(dāng)、出賣土地和大牲畜的19戶,拋棄家園、逃生異鄉(xiāng)的15戶,家破人亡的6戶。如我的同族大哥,本是自耕農(nóng),全家6口人,自有耕地6畝,草房3間。1943年災(zāi)荒賣了3畝多地,勉強熬了過來。進入第二個災(zāi)荒年,土地、房屋全部賣完,餓死三口人。我大哥死后,嫂嫂改嫁,侄兒帶走,侄女送人做童養(yǎng)媳,數(shù)口之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遭此厄運者,比比皆是,何止我大哥一家。我所居住的自然村僅有9戶人家,春節(jié)以后,就出現(xiàn)6戶絕糧”。[6](P65)1947 年,河南蝗災(zāi)又起,以致“豫父老為之傾家蕩產(chǎn)者,流離以死者,向可以數(shù)計,及今思之猶有余痛”。[14]這樣的記載,遠(yuǎn)非個案,而從中不難看出蝗災(zāi)之下民眾生命之脆弱。
3.引發(fā)迷信傳言
蝗蟲泛濫本為自然現(xiàn)象,然舊社會民眾對此往往缺乏科學(xué)認(rèn)知,因此時常將此歸因為神鬼力量。蝗蟲危害的時候,引發(fā)陣陣迷信傳言。如一些講迷信的人,視蝗蟲為“神蟲”。說“螞蚱是老天爺派下來的神蟲,不吃有家的(家是夾的諧音,夾指豆類作物),專吃沒家的(沒夾的指玉米、谷子等),可不敢打,越打越多”。[6](P63)一些民眾跪在自己的地頭上,虔誠地?zé)憧念^,祈禱“老天爺”保佑,懇求“螞蚱爺”留情。1943年蝗蟲危害時,迷信的人挎著紙籃子,在自家莊稼地頭燒紙禱告:“神蟲恁快走吧!”“老天爺開恩哪!”聲聲求愿,不絕于耳。[6](P55)更無知的是巫婆神漢,燒香禱告,求螞蚱神保佑自己的莊稼不受侵害,還埋怨威脅群眾,不該滅蝗吃蝻(由于饑荒,不少人將蝗蝻的頭拔掉,然后炒食其腹部),為蝗蝻鳴冤叫屈說什么:“拔俺頭,吃俺肉,俺去河南叫俺舅,俺舅是個蝻,吃您個光桿。”[6](P61)此類迷信現(xiàn)象,在災(zāi)區(qū)屢屢發(fā)生,使民眾往往對蝗蟲有一定的敬畏感,打蝗除蝗變得束手束腳,加重了蝗蟲的危害。
三、結(jié)語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蝗災(zāi)在近代河南的肆虐程度,以及給河南民眾帶來的苦難。面對蝗災(zāi),只有采取科學(xué)有效的措施才能與之對抗,可悲的是當(dāng)時所處的舊社會,既無堅強有力之政府作為對抗蝗災(zāi)的核心主導(dǎo)力量,也無對抗蝗災(zāi)之雄厚物質(zhì)基礎(chǔ),更無對抗蝗災(zāi)有效之科學(xué)觀念,治蝗效果始終不佳,這也是蝗災(zāi)泛濫及造成諸多社會惡果之重要社會根源。
蝗災(zāi)作為近代災(zāi)荒類別的個案,同時也折射出其他災(zāi)害發(fā)生時的大致情況。面對以蝗災(zāi)為代表的災(zāi)荒,如何盡量減輕災(zāi)害的危害,成為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在近代社會,由于社會生產(chǎn)力的低下,民眾缺乏與災(zāi)害對抗的物質(zhì)基礎(chǔ),面對災(zāi)害,在耗費掉為數(shù)不多的生活資料之后,均不約而同地陷入困境,進而引發(fā)一系列社會亂相,究其根源,這是國弱民窮之真切反應(yīng)。因此要最大程度地減輕災(zāi)荒的危害,只能從根本上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提高國家和民眾對抗災(zāi)害的能力。但在近代社會,社會生產(chǎn)力雖有增長,但其增長的幅度與國家對抗外敵和改善民生的迫切程度來說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這顯然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制度障礙息息相關(guān),要想推動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只有實現(xiàn)社會制度的變革方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此,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表達(dá)過只有推翻反動勢力的黑暗統(tǒng)治,建立人民政權(quán),方有可能解決災(zāi)荒這一問題的想法。當(dāng)然,對抗災(zāi)荒還在于民眾認(rèn)知的提高,災(zāi)害之中,民眾一些荒謬的言行折射出的近代中國鄉(xiāng)村社會仍處于蒙昧狀態(tài),缺乏對災(zāi)害問題的科學(xué)認(rèn)知,這種蒙昧的狀態(tài)往往加大了災(zāi)害的危害程度,而扭轉(zhuǎn)這些錯誤的觀念顯然也是對抗災(zāi)害勢在必行的。因此,要高效能地對抗天災(zāi),必然與社會制度的變遷、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民眾觀念的扭轉(zhuǎn)三者緊密相連,且缺一不可。
[1]浙江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編著.農(nóng)業(yè)昆蟲學(xué)(上冊)[M].上海: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82.
[2]李艷紅.1941—1947年豫東黃泛區(qū)的蝗災(zāi)[J].防災(zāi)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2007,(1).
[3]太康縣志編委會編.太康縣志[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4]中牟縣志編委會編.中牟縣志[M].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9.
[5]鄢陵縣志編委會編.鄢陵縣志[M].天津: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1989.
[6]文芳主編.黑色記憶之天災(zāi)人禍[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
[7]省府、農(nóng)林部、行總豫分署治蝗委員會治蝗報告[Z].河南省檔案局館藏檔案:A.B10-103.
[8]扶溝縣志編委會.扶溝縣志[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9]西峽縣志編纂委員會.西峽縣志[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10]長垣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長垣縣志[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1]原陽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原陽縣志[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12]李文海,等.近代中國災(zāi)荒紀(jì)年[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13]周楠.20世紀(jì)40年代豫東黃泛區(qū)蝗災(zāi)述論[J].中州學(xué)刊,2009,(2).
[14]河南省會各界治蝗宣傳大會告民眾書[N].河南民國日報,1944-04-04.
Review about Locust Plague and Its Impact in Modern Henan
WANG Xinhong
(Huanghe S&T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63, China)
In modern times, locust plague frequently happened in Henan, which was one of the three natural disasters at the time. The plague of locusts in late Qing Dynasty mainly concentrated in 1855 to 1857,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arly 1940s. The plague brought more serious social impact in Henan,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plague caused the drop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fter each plague the crop had been gnawed completely, which brought irreparable damag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riggered famine. The second is the plague lea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people, breeding a large number of victims. The third is the plague aroused proliferation of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and superstitious activities made the disaster worse.
modern times; Henan; locust; impact
2015-09-25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河南近代災(zāi)荒史研究》(12YJC770058)
王鑫宏(1978-),男,河北吳橋人,歷史學(xué)碩士,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史研究。
K25
:A
:1008-469X(2015)06-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