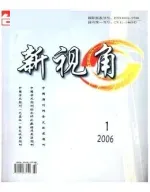老臺胞回憶臺灣光復那一天
作者丨實習記者 張明陽 鄭宏博
70年前的10月25日,臺灣光復。這一天,整個臺灣島沉浸在一片歡樂的海洋之中,家家戶戶張燈結彩,男女老幼喜上眉梢,慶祝臺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重新回歸祖國懷抱。直到今天,見證那一天的老臺胞,當我們采訪他們時,興奮與喜悅仍掛在眉梢。
徐兆麟:“我從未見過父親如此高興”
“光復那一天,臺灣民眾熱烈慶祝的情形令我終身難忘。”全國臺聯原副會長、臺籍老兵徐兆麟老先生激動地說道。
那一年,徐兆麟還不滿14歲,對于重大政治事件和國際局勢不能完全理解,但對于周圍民眾的歡樂情緒,卻充滿好奇。“我的父親平時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對于政治也漠不關心,在我的印象中他從未和別人談論過政治相關的事情。但是在聽聞臺灣光復的消息之后,他帶著家里的大鼓,走了幾十里的山路,一直走到鎮上參加了當時的民眾游行,擔任游行隊伍中的鼓手。在當時的我看來,父親的行為是非常反常的,但是后來想想,父親的‘不務正業’,正是因為他要通過游行和打鼓的方式表達出自己內心的狂喜。”
“當時我很愛熱鬧,看到鎮上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內心十分激動。我記得當天,街道上鑼鼓喧天,熱鬧非凡。游行的民眾揮舞著各色彩旗,喊著口號,舞龍舞獅慶祝臺灣回歸祖國。”如今徐老談起當天的情形依然是如數家珍。
臺灣光復后,徐兆麟考上了中學,當時學校的日本教師被全部遣返,臺灣的各界掀起了學習國語和傳統中華文化的熱潮。“我小學階段所受的教育全部是日文教育,但當臺灣光復之后,民間掀起了學習漢語的熱潮。當時我感覺能夠學習自己祖國的文化是一件相當幸福的事情,所以學的格外用心。”
在徐老的心中,臺灣光復是重要的“分水嶺”:“光復前臺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受盡屈辱;臺灣光復后,民眾才真正脫離了之前的苦難生活,成為了新臺灣的主人。”
鄭堅:“我作為助手協助在臺灣升起第一面中國國旗”
1945年8月15日至10月25日,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兩個多月的時間里,臺灣處于無政府狀態。當時18歲的鄭堅作為臺灣義勇隊的一員,于1945年9月初,作為先遣部隊回到臺灣輔助臺灣義勇隊副隊長張士德上校組織“社會服務隊”,進行臺灣被接收之前的準備工作。
在鄭堅的印象中,張士德上校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領導。“張士德上校還是第一個在臺灣升起中國國旗的人,我作為他的助手,感到非常自豪。當時的我感覺18歲的自己充滿了力量,希望在光復后的臺灣大展拳腳,為臺灣民眾多做好事。”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我的印象中當時會場外人山人海,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著中國政府正式接收臺灣的消息。接收儀式后,人群中發出了熱烈的歡呼,下午民眾舉行了規模龐大的游行活動。光復當天的臺北,成千上萬的臺灣學生和各界人士走上街頭,載歌載舞,到處是一片和樂融融的景象。中國政府對臺灣的接收意味著當時600萬臺胞恢復了中國國籍,結束了亡國奴的地位。”講到臺灣光復當天的盛況,鄭老的言語里依舊充滿著自豪之情。“當時老百姓家家戶戶都拿出了列祖列宗的牌位,準備祭品,焚燒香燭,通過這種方式告知祖先臺灣回歸祖國的重大喜訊。”
臺灣光復后,臺胞都急著要說國語,要認漢字。此時的鄭堅在臺灣義勇隊完成了光復臺灣的偉大任務之后,回到了他的故鄉彰化縣,成為了彰化女子中學的一名教員,教臺灣學生學習國語。“當時我想,我們現在擺脫日本統治了呀,在語言上也要盡快恢復國語才行。當時學校中,本省的教師也是邊學邊教,都非常認真,臺灣各界學習國語的熱情是史無前例的。”
黃幸:“臺灣同胞始終心向祖國”
1943年進入大學學習后,黃幸開始有意識地接觸一些抗日團體。“當時我和我的幾個好友一起參加了‘勵志會’的活動,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就是抵制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運動’、保護和宏揚中華文化、臺灣本土文化。”
1945年8月15日,“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和我的同學們都激動地跳了起來”,黃幸說,“從日本投降起到10月25日臺灣光復,臺灣同胞一直都是充滿期待地為回到祖國懷抱做著準備。我們學生開始學漢字、學拼音,開始學唱《義勇軍進行曲》和國民黨黨歌。一些懂國語的同學也做起了義務的‘宣傳員’,提醒大家要語言文明,行為得體。雖然處于暫時的‘無政府’狀態,但整個社會一點都沒亂,人們自發地管理和維持正常秩序。各地都在開慶祝會,人們通過各種慶祝形式表達臺灣回歸祖國的激動心情。陳儀以中國政府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的身份到臺灣接受日方投降時,我們一幫同學還到機場去歡迎他”。
黃幸講到,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舉行,“我當時沒有辦法進入會場,就在會場外面等待喜訊。當接收儀式完成后,我周圍的民眾立刻載歌載舞,歡慶回歸。被日本侵占的50年,我們臺灣同胞始終是心系祖國、心向祖國、認同祖國的,所以臺灣光復并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臺灣同胞也是幸福而激動的”。
郭平坦: “我對新中國有一種向往”
郭平坦出生時,日本正竊據臺灣。8歲時,郭平坦一家搬到了日本神戶。“我們剛到日本的時候,生活十分艱難。為了養家糊口,我的父親每天都會辛勤工作,但是仍然得不到應有的尊重。1945年,也就是我12歲以前,臺灣一直處于日本的殖民統治下,當時日本人十分歧視中國人,我們這些臺灣籍華僑在日本也處于受歧視、受壓迫的地位。”
1945年日本戰敗后,日本社會到處彌漫著悲涼、哀傷的氣息,但是作為臺灣籍華僑,郭平坦的家人為中國取得抗戰勝利感到無比振奮。“當時整個日本社會都很萎靡,我們作為中華兒女,內心為祖國的勝利感到無比自豪。雖然沒有大肆慶祝,但是從父母談話的語調和神情我能感覺到他們當時是很開心的。很多華僑都在私下議論這件事,都希望祖國能夠越來越強大。”

1945年10月25日,臺灣地區日軍投降儀式正式舉行。上午10時,陳儀代表中國政府通過廣播電臺宣布:從即日起臺灣和澎湖列島正式重新歸入中國版圖,該區一切土地、國民、政事皆歸于中國主權之下,結束了日本在臺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當時郭平坦家人也得知了這激動人心的消息:“當時臺灣處于沸騰的狀態,大家都在以各種形式歡慶臺灣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我的父親也說,以后回到臺灣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
1956年8月,這位日語流利、不大會說中文的23歲青年來到北京,成為1953年至1957年間到大陸參與新中國建設的4000多名旅日歸僑中的一名。
何標:紀念光復警惕有人反對抗日戰爭
臺灣光復至今已有70周年,到現在還有人聲稱自己是日本人、日本是祖國的論調、臺灣和日本為一個國家、抹殺臺灣同胞抗日的事實。此人就是李登輝。他說的這些話都是真心話,他不是一般的在日據時期受過“皇民化”思想影響很深的一個人,他本人也具有日本人的血統,可算是軍國主義的余孽。
據臺灣謝啟大說,1945年,當時22歲的李登輝在日本接受的是軍官訓練,他受的是日本的“死間”訓練,“死間”就是致死也不能透露自己的身份。在日本投降后,李登輝偽裝成臺灣人返回臺灣,投靠了當時在臺灣和筱原笠次郎一起共事的李金龍為義父,搖身一變祖籍成了福建龍巖市。
70年后,李登輝再次跳出來發表自己是日本人等喪權辱國的言論,有這么幾方面的原因:第一,從去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之后,國民黨越來越式微;李登輝的“女弟子”,現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有很大可能在明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獲勝,所以說這個時候李登輝無所顧忌地表明自己的身份,露出了真面目。第二,李登輝出任過臺灣地區領導人,他本人對國際形勢了如指掌,他知道臺灣光靠美國的支持是不足以在國際上站穩腳跟。所以他要把日本拉過來,促使民進黨和日本建立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緊密關系。最近蔡英文訪日與安倍晉三會見,我認為李登輝難脫嫌疑,游走于臺日之間,為民進黨和日本之間牽線搭橋。第三,日據時期,有一些人深受“皇民化”思想的毒害,這些人還有著日本人的情結。還有就是日本投降時,遺留下來一批日本人,他們在臺灣換成了中國姓名,篡改了戶口,搖身一變成為臺灣人。李登輝想登高一呼,喚醒這些日本皇民和他們的后代。另外,現今92歲的李登輝,來日無多,所以他要在生前實現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的一些理想,來獻出他最后的一把力,這也許是他的主要考慮。
在紀念臺灣光復70周年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現在還有人反對抗日戰爭,替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翻案,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兒。
吳嘉桐:至今兩岸沒有完全統一,十分遺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同年的10月25日臺灣回歸祖國。這是中國人民在近代史上反抗列強侵略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當時我深受鼓舞,熱血沸騰,高呼萬歲,連夜狂歡。可是至今兩岸沒有完全統一,十分遺憾,有無限的感慨。
第一,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重要成果,為什么至今還有人不承認這一點?這是世界上公認的一個事實,還存在李登輝這種人,在感謝日本的殖民統治。第二,日本侵占臺灣,強迫臺灣人放棄中國國籍,不準講漢語,強迫講日語,大搞“皇民化”運動,受到了臺灣同胞的強烈反抗,而這早于大陸進行的反抗日本的戰爭和活動。第三,臺灣有部分人將主張兩岸統一的人指責為“出賣”臺灣,那“臺獨”分子又將臺灣推向何處?難道又要回歸為外國殖民地嗎?二戰時期,兩岸共同做出了大量的犧牲和貢獻,犧牲就這樣化為烏有了嗎?所以說,兩岸同胞必須攜起手來,共同捍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捍衛我們的祖國。
今天,紀念臺灣光復70周年,就是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發展,最終能夠實現完全統一。
陳弘:臺灣回歸祖國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否定的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時,日本在臺北中山紀念堂向中國政府代表陳儀遞交了投降書。當天,陳儀向全世界宣布,臺灣和澎湖列島回歸中國的版圖。這是對中國、對臺灣、乃至亞洲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臺灣同胞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救出來,臺灣人民終于回歸祖國的懷抱。
光復當天,臺灣同胞非常激動,因為之前的臺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到了不公正乃至悲慘的日子終于結束了,摘掉了日本“二等公民”身份,成為了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當時的心情難以用語言來表達。在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上,“臺獨”分子有一個謬論,“臺灣地位未定論”。他們要搞“獨立”,這是錯誤的,違背了歷史的事實,臺灣回歸祖國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否定的。
我經歷了臺灣回歸的時刻,70年來,祖國大陸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作為臺灣同胞到大陸來參加建設,享受了新中國的國際尊嚴和威望,感到非常自豪。我個人還參加了審判日本戰犯的工作,并在當時做翻譯工作,曾經擔任過《人民日報》駐東京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