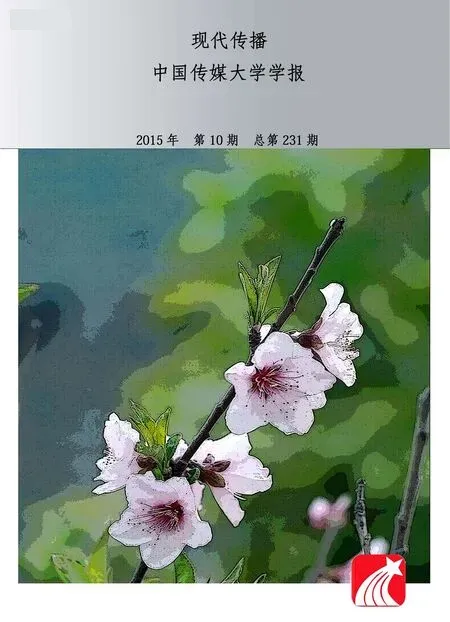意識形態的征戰:清末官方政治傳播之困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代新聞傳播史研究”(項目編號:12BXW011)、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清代新聞傳播專門史研究”(NCET-120243)的研究成果。
【內容摘要】 晚清,高度成熟的政治傳播體系已成為清廷重新調整傳播手段與格局的強大惰性和障礙;對近代報刊冷眼旁觀,無所作為,使得清廷坐失占領輿論陣地、把握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多次歷史機遇;意識形態征戰中官方主流話語被邊緣化,歸根結底在于其核心思想觀念的迷失。
遭逢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晚清社會,歷來是學界格外關注的焦點。從軍事、外交、政治及文化等多層面探索清末社會變遷的著述洋洋大觀,其中不乏反映意識形態、思想戰線激烈角逐與對抗的精良之作,但是從傳播學視角展現諸多政治理念之間的交集、爭鋒和消長沉浮,卻為眾家所忽略。清末,尤其是王朝最后十年,各派政治勢力進行了殊死決戰,意識形態領域的勝負直接決定著現實政權的更迭。誠如有學者斷言,“失去了對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也就等于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①,曾憑借周密完善的政治傳播體系行使意識形態霸權的滿清政府,何以在終場的輿論大戰中幾近失語,輕易落敗?顯然不能簡單解釋為官方主流思想的陳舊落伍;面對突如其來的意識形態危機,清廷是如何應變決策的?本文旨在通過還原清末官方政治傳播的理路與行跡,發掘清廷在意識形態領域潰敗的深層致因,進而為洞悉清末社會的政治變革提供新鮮的面相和視野。
一、官方傳統政治傳播體系積重難返,更新維艱
所謂政治傳播,是指“政治傳播者通過多通道、多媒體、多符號傳播政治信息,以推動政治過程、影響受傳者的態度與行為的一種對策” ②。運用政治傳播輸送、擴散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念,確立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維系政治秩序與統治,幾乎是所有政權施政的必要步驟。清廷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成功統治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封建帝國,建構了一個遠遠優于前朝的高效、完善的政治傳播體系。
首先,官方出版盛況空前,達到了封建時代的頂峰。書籍以其長時間、大批量的信息存儲功能,成為建構、傳承意識形態不可替代的工具,因而獲得清統治者特殊青睞。從中央的武英殿,到地方的書局、書院,形成了細密、龐大的官方出版網絡。大量“欽定”“御纂”之“殿本”的問世,在彰顯盛世繁榮的同時,也完成了按照清統治者意志重新書寫歷史、建立統治話語的意識形態改造工程;而各種“局本”“院本”層出不窮,更以規模化、權威化的絕對優勢占據了思想文化領域的主陣地,確保了官方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
其次,報業體制完備,進入空前的“有序”發展狀態。報刊定期出版、時效性強的媒介特征,決定它在意識形態建構方面以承載和塑造輿論為主。清代,干擾社會政治秩序的小報得以有效遏止,乃至“永絕” ③;官方邸報愈發完善,軍機處之設與奏折制度的實施,強化了高層統治者的報業控馭能力;邸報翻版——民辦京報的繁榮,則將大眾傳媒納入官方的政治傳播體系,進一步拓寬了官方的輿論空間。清廷通過掌控報業機器,暢通無阻地施行輿論霸權。
再者,圣諭宣講制度化。無需文化門檻的口語傳播作為底層民眾最主要的信息接收手段,在清代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官方意識形態向底層灌輸的中樞管道。早在清初,圣諭宣講便成為朝廷的規定動作。順治九年(1652),“頒行六諭臥碑文于八旗及直隸各省”。 ④十六年議準,設立鄉約制度,講解六諭原文。 ⑤自康熙九年,“講圣諭”甚至作為地方官施政的要目之一。 ⑥宣講的優勢不僅在于口語傳播摒棄了文字障礙,還在于它以嚴格的程式——從講員選取、儀典規范,到聽講位次,賦予整個過程強烈的表演性,通過激發受眾情緒,達成思想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宣講儀式與講讀內容共同構筑了一個封建政治倫理的象征體系,用最淺顯、直觀、感性的方式傳達官方主流思想,以至于鄉野村夫亦能接受。
此外,傳統的科舉與官學制度,以及龐大的政府公文系統,延演至清代已相當成熟,與上述傳播渠道緊密配合,形成了一個組織嚴謹、網絡精密的覆蓋全國的政治傳播體系。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觀的官方意識形態,通過這一體系持續不斷地向各區域、各層次的人群廣泛擴散、滲透,有效發揮著統一思想、統一輿論,進而實現政治一統的社會整合作用,滿清王朝也因此創造了以外族政權主宰中國近三百年的歷史奇跡。
清末,封建朝廷統治式微,其政治傳播體系雖弊端重重,呈衰落趨勢,卻依然表現出強大的歷史慣性,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機器高效運轉。由封建官報和京報構成的傳統報業在新媒體近代報刊問世后,非但沒有受到沖擊茍延殘喘,反而沿襲不衰,與近代報業并駕齊驅。參與《清史·報刊表》編纂的谷長嶺先生發現,“近代報刊出現后,傳統報刊不但沒有消亡,反倒曾有較大的發展,并借助近代報刊的轉載,影響達到頂峰……,在傳播國內時政信息方面,處于主流媒介的地位。” ⑦另有學者注意到,《上諭匯編》及《行在鈔報》的刊行,顯示了傳統的官方傳播形態在晚清政治危機中發揮著重要的輿論控制作用。 ⑧與此同時,圣諭宣講活動亦展露一定的生命力,成為某些新派大吏試圖重振朝綱、對抗民間話語的工具。湖南巡撫飭令“各府廳州縣儒學隨時親歷城鄉宣講《圣諭廣訓》《勸善要言》,仰遵迭次諭旨,凡有關民教者,切實開導” ⑨;直隸總督袁世凱在保定“設立宣講生數員,按日宣講《圣諭廣訓》” ⑩。1906年頒布的《學部奏定教育會章程》中,明令“擇地開宣講所宣講《圣諭廣訓》,并明定教育宗旨之上諭及原奏,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瑏瑡《學部酌擬勸學所章程清單》中亦開列“實行宣講。各屬地方一律設立宣講所,遵照從前宣講圣諭廣訓章程,延聘專員隨時宣講,其村鎮地方,亦應按集市日期派員宣講。” 瑏瑢可見,科舉制廢除后,官方的宣講活動未衰反榮。應封建專制政體而建構的政治傳播體系,在封建政權穩固時期,固然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整合力量,但當政權衰微之際,它的力量則很可能發生轉化。面對蔚然勃興的近代傳媒與新式傳播理念,傳統報刊和圣諭宣講的末日輝煌,也只能是退出歷史舞臺前的回光返照,掙扎越強烈,更新越艱難;而沒有順應時代發展需求的新型政治傳播體系,清廷失去意識形態的霸權,進而喪失政權,也只是時日問題。簡言之,晚清時節,運行良久、高度成熟的政治傳播體系已經成為清廷與時俱進,重新調整傳播手段與格局的強大惰性和障礙。
二、忽視新媒體,坐失改革政治傳播體系良機
盡管中國近代報業的序幕在南洋拉開,但是影響大陸的終極目的還是使這些天朝的違禁出版物通過種種渠道流向境內。創刊于馬六甲的第一家中文近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便是“中國境內亦時有輸入” 瑏瑣;1833年,傳教士所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甚至落戶廣州。所以,即便是在近代報刊萌生的早期,國人對這種新式傳媒也并非全然陌生。只不過,大多接觸它的人采取了盲目排斥、漠然以對的態度;而少數回應者又存在明顯的認知偏差。林則徐就誤以報刊為“內地之塘報”,可籍之獲取“夷情”, 瑏瑤因而定期輯譯外報消息,編成《澳門新聞紙》和《澳門月報》以供內參,看重近代報刊所謂的“情報”價值,對其新聞,特別是輿論功能,則無所覺察。與林氏的旨趣如出一轍,魏源也未曾留意近代報刊的新媒體特質,只在乎它的內容,《海國圖志》專辟報紙部分,匯集外報所載成書,偏執于書籍載道,傳統的媒介文化意識根深蒂固。
如果說19世紀早期與新式傳媒親密接觸者為數甚少,加之外報為爭取中國讀者小心翼翼,尚未盡展本色,故而難以準確辨識利用的話,那么,在近代報刊興起并深刻影響社會生活之后,清統治階層仍然無動于衷,就不免令人匪夷所思。60年代,《上海新報》報道太平天國與清軍戰事,銷量驟增,已初現新式傳媒的特殊能量。開創中文商業報刊新紀元的《申報》,盡管一再標榜“以行業營生為計” 瑏瑥,沒打算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從創刊起便每日首載“實有系乎國計民生”的論說,發“名言讜論”, 瑏瑦寄望通過說教掀動輿論,移風易俗,顯示出與傳統報刊截然不同的風格和意趣。何況,連續四年追蹤報道“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所蕩起的輿論風潮,應足以促動當局對近代報刊強大社會影響力的認知。事實也證明,《申報》很早就成為中國改革派重要的消息來源。著名的駐外使臣郭嵩燾、曾紀澤、張蔭桓皆常閱該報,帝師翁同騄、兩江總督沈葆楨以及他周圍的洋務官員都很重視其新聞和評論。 瑏瑧甚至有官員已意識到外商設立的“新聞紙館”具有“上以議國家之得失,下以評草野之是非”的政治傳播價值,進而倡議“仿而行之”,且小心翼翼地附加了“惟不準議朝廷得失”的條款, 瑏瑨卻仍舊沒有得到朝廷的認可。究其實,創辦于租界的外報以盈利為目的,極少觸碰清廷最敏感的政治神經,對官方的意識形態建構非但不構成威脅,反有助益。由《上海新報》《申報》首開風氣,“京報全錄”和“上諭恭錄”,幾成為中文近代報刊的保留欄目;而官方最重要的公文形式——告示,也常常現諸報端,借助大眾傳媒得以更加快捷、廣泛的播散。起碼從表面上看,近代報刊的蓬勃發展并沒有沖擊清廷的政治傳播體系,卻使其借力擴張,影響面進一步擴大。抑或因此消解了朝廷自主辦報,利用新媒體充實傳播陣營,以實現政治傳播渠道拓展與更新的動力,不經意間喪失了領先介入新興報業,搶占輿論高地,進而鞏固和維護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最佳時機。
事實上,六、七十年代的“同治中興”,恰是清廷韜光養晦,順應媒介技術變遷,及時調整政治傳播策略與機制,重建合理體系的良機。太平天國戰事平息,與列強干戈稍事停歇,以“中體西用”為指導的洋務運動方興未艾,國人早期商辦報刊應運而興。從其創辦人不外乎洋務官員和思想趨新的亦紳亦商者,以及諸刊鼓吹西學、同情洋務的價值取向來看,顯然部分洋務官紳已開始注重報刊的輿論功能,并力行實踐,進而突破了外人獨掌話語權的局面,開創了國人立言發聲的平臺。本來,這是一塊值得呵護、利用和繼續開發的輿論陣地,清廷卻未加留意扶持,極盡打壓之能事。致使上述報刊除了在香港出版的幾份外,大多命運多舛,存世短暫,《匯報》只出版了一年半,《昭文新報》《述報》存續尚不足一年,《新報》和《廣報》一個自動停刊,一個以“妄談時事,淆亂是非”的罪名被地方當局查禁了事。 瑏瑩可惜歷史不允許假設。如果清廷能夠適時借用國人早期商辦報刊的政治傳播力,并順勢創構官方的新媒體輿論平臺,掌握話語先機,洋務思潮很可能不會僅限于部分官紳的狹小圈子,難獲士人階層的廣泛認同和支持,無法壯大輿論聲勢;而經過幾十年的辦報經驗,清廷也不致在世紀之交面對突如其來的輿情危機,猝不及防,喪失招架之力。
前有外商報紙示范,后有國人商辦報刊表率,清廷卻視若無睹,兩度與歷史際遇擦肩而過,可以揮霍的機會已然極其有限。九十年代,當西方傳教士所辦《萬國公報》公然標榜“主持輿論,闡發政見,評議時局,常足為一國前途之導向方針也,砥柱也” 瑐瑠,故大量刊載政論鼓吹西方立場的中國改革觀時,清王朝的執政者們,上自皇帝,下至各級官紳,或爭相訂閱,或捐資助銷,皆成為毫無原則的膜拜者。據李提摩太回憶,張之洞等高官便積極為傳教士所辦報刊輸金 瑐瑡;甚至連光緒皇帝都經常閱讀《萬國公報》。 瑐瑢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些政治精英在充分感受近代報刊非凡的輿論作用同時,仍未產生官辦新式報刊以充實、改進政治傳播格局的沖動,又一次錯失良機,坐視外人壟斷中國報壇,獨控改良話語,侵蝕主流意識形態。
總之,清統治者目睹了近代傳媒萌生、滋長、壯大的整個過程,對其功能及所表征的近代精神與文化,從不屑一顧、認知偏差,到猶疑忽略,及至頂禮膜拜,始終以旁觀者的姿態,無所作為,任由主動占領輿論陣地、把握輿論主權的機會一次次喪失。終至19世紀末,民間第一次辦報高潮來臨,在新創辦的百余種報刊中,唯有《官書局報》和《官書局匯報》以官方面目出現。在民間政治思潮的沖擊下,清政府措手不及,因缺少有力、快捷的傳播媒介而被邊緣化,幾乎處于失語狀態。出版周期漫長的書籍自不必說,老舊的邸報以傳達政治新聞為主,不具有快速匯聚、發動輿論的戰斗力。維新派卻充分發揮了近代報刊的輿論功能和戰斗作用,大肆推行其政治理念,鼓蕩變法風潮,直接威脅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直到20世紀初,當意識形態總決戰已然打響之際,才有管學大臣張百熙應詔上疏,建議創辦官報,以與民間輿論相抗,“報紙所以寄耳目,……中國通商各埠,由民間自行辦理者不下數十種,然成本少而宗旨亂,除略佳之數種外,多不免亂是非而淆視聽。又多居租界,掛洋旗,彼挾清議以訾時局,入人深而藏刀固,聽之不能,阻之不可,惟有由公家自設官報,誠使持論通而記事確,自足以收開通之效而廣聞見之途。” 瑐瑣新式官報遂倉促出籠。且不論報紙辦得如何,由于各派政治勢力早已搶灘輿論陣地,非官方意識形態的先入為主,決定官報很難擠占新的話語空間。針對變法輿論,清廷又錯誤地采用高壓手段鎮壓,將本可以爭取的力量推向對立面,結果只能適得其反。維新派轉移政治傳播戰線,在海外發起更為猛烈的宣傳攻勢,一定程度上牽制了清廷對革命思潮的注意力,縱容其做強做大,為自己準備了掘墓人。
三、主體失語,官方核心思想觀念的迷失
在清末思想戰線的喧嘩與騷動聲浪中,各派政治力量競強爭勝,大都采取直抒胸臆的政論方式,有組織有計劃地借重近代報刊進行直接的政治動員,而這期間,由于清廷對新式傳媒表達官方意志重視不夠,其政治傳播始終處于散漫無章、游離主流的狀態,顯得力不從心,抓不住要害。
擁有絕對優勢的官方出版在邁向近代化的路途中,實已占盡先機。洋務派的江南制造局翻譯館、京師同文館等開國人近代出版之先河,與外國傳教士的墨海書館等新式出版機構并駕齊驅,曾一度主導著出版文化。其中,19世紀下半葉上海乃至中國最大的翻譯出版中心江南制造局翻譯館,1896年前譯刊西書120種,占全國出版總數的341%。 瑐瑤可見,當民辦近代出版尚未登場之時,洋務出版機構以其大量介紹西學的譯著引領著文化風向。非惟出版業,幾乎可以和近代報刊相提并論的重要口語傳播渠道——宣講,亦始終是官方可以操控與主導的領地。一方面,由于從清初就首推重用,朝廷對這種政治傳播手段駕輕就熟;另一方面,較之可以借助租借、海外出版轉而內銷的報刊,宣講需要特定場所,受時空局限,易于把控。臺灣學者李孝悌研究證實,清末宣講所的設置“先由私人開其端”,但政府跟進參與后,漸漸使其成為制度化的機構。不僅不能隨意宣講,而且宣講用書亦需學部審定。 瑐瑥
此外,縱使是出道較晚的新式官報,也擁有著資金和發行等多方優勢。民間出版動輒有資金斷流及銷售渠道萎縮之憂,頗受追捧的《求是報》只存續半年便被迫停刊,主要是缺乏辦報經費所致。 瑐瑦甚至連《時務報》這樣的報中翹楚,亦需官府助銷,靠人脈關系維系銷售業績。 瑐瑧而新式官報由官府主辦,既沒有資金匱乏之虞,又可依憑政治手段派銷。據統計,起自1902年,直隸總督兼署理北洋大臣袁世凱率先在天津創辦《北洋官報》,迄1911年底,10年內至少有106種官報問世。在地域分布上,22行省除新疆外,都辦有官報 瑐瑨,從而形成覆蓋全國的報刊網絡。綜上,清政府掌握的傳播資源堪稱優厚,按說在輿論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不是沒有可能。然而通觀清末官方的政治傳播,即便是上述可以縱橫捭闔之區,也沒有獲得預期的宣傳效果。意識形態征戰中官方主流話語被邊緣化,固然與未能及時搭建強有力的輿論平臺不無干系,而關鍵恐怕還在于官方核心思想觀念的迷失。
政治傳播,不僅僅是輸送政治訊息,更重要的是傳揚政治家、政治集團的核心價值觀念,建構有利于自身的意識形態格局。就清廷而言,向民眾迅速廣泛、連續不斷地宣傳、擴散以“中體西用”為核心價值的理論與主張,當是其政治傳播的重心。洋務派的出版與辦報活動雖然活躍,但都停留在對西方器物文化的淺表介紹層面,少有依據官方價值體系進行理性的判斷與取舍,服務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王爾敏先生回顧國人早期對待西學的態度時便犀利地指出,“中西接觸,自道光間已開始頻繁,而士大夫所見者,外國船炮之堅利而已,外洋器物之精絕而已,所言者洋務而已,富強而已。” 瑐瑩在政論主宰社會輿論的報業“政論時代”,當維新派、革命派以政論為利器搖旗吶喊之際,新式官報卻“主要是為上下交流、中外溝通而辦”“政論甚少”“與革命派報刊之間幾乎沒有交鋒”。 瑑瑠最富戰斗力的政論遭致冷落,可能與辦報者的刻意回避有關,《北洋官報》就聲稱“不取空言危論” 瑑瑡;再就是朝中缺少梁啟超、章太炎那樣一批精于辦報、擅寫政論的吹鼓手;而最大的可能還是表述官方意識形態的經典文獻的缺失。清末,西學東漸,新思潮滌蕩,傳統儒家政治倫理體系發生動搖,為挽救王朝命運,清統治精英試圖以“中體西用”為核心價值觀整合社會思想,對官方意識形態系統進行調整。但很顯然,無論是作為其表述系統的經典圖書結構,還是作為其傳播系統的媒介渠道,都未能得以及時建立。在清末官方的政治傳播過程中,既沒有產生梁啟超《變法通義》 瑑瑢、孫中山《民報·發刊詞》 瑑瑣那樣富有影響力和旗幟作用的政治綱領性文獻,以統一思想,引領輿論;又沒有圍繞官方核心價值觀念進行引申闡發和理論補充之作,更遑論具體改革方案的設想與擘畫之論了。少數洋務精英的思想大多通過書籍流轉,由于缺乏有效的傳播途徑而應者寥寥。與此同時,征戰意識形態領地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僅擁有各自明確的政治綱領、頗具規模的報刊網絡,而且培養了精干的報人隊伍,使得報刊的政治作用得以最大限度的發揮。打沒有準備的仗,清廷在社會輿論的總決戰中徹底潰敗,實屬情理之中。
綜觀清末官方的政治傳播表現,對西方改良觀的頂禮膜拜,對改良主義者由曖昧到鎮壓,最終又不得不步其后塵施行新政,歸根結底是核心思想觀念的混亂所致。由于政治傳播不力,“中體西用”始終僅限于少數政治精英的官樣文章和實踐,沒有成為統一統治集團認識的指導思想,最終導致以“中體西用”為核心價值重塑官方意識形態的工程失敗。
當然,政治傳播策略的失誤,或許不能構成清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延續千余年的王道價值體系,在改良、革命的聲浪中顯得那么不堪一擊。西方資產階級大革命綿延數十乃至百年之久,此前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而中國資產階級僅用了十幾年,就革了清王朝的命,實在引人深思。
事物的復雜性決定其發展結果,而結果卻常常出人意料。清末官方的政治傳播在維護封建專制政體方面效果不著,卻對社會文化的變遷發揮了特有作用。且不論洋務出版機構數量可觀的譯著,具有無法估量的開啟民智意義;官府大量的白話告示,以及定期宣講的《圣諭廣訓》及其白話讀本,直接為晚清的白話文運動作了強有力的鋪墊。難怪學者夏曉虹認為,晚清白話文運動有著不容忽視的官方資源。
瑑瑤
注釋:
① 白文剛:《應變與困境:清末新政時期的意識形態控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頁。
② 邵培仁:《政治傳播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頁。
③[清]蕭、朱南銑點校:《永憲錄》(卷四)(卷二下),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0頁。
④ 《清實錄》(三)《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六十三,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90頁。
⑤ 《清會典事例》(五)卷三百九十七,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422頁。
⑥ 王爾敏:《清廷〈圣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⑦ 谷長嶺:《晚清報刊的兩個基本特征》,《國際新聞界》,2010年第1期。
⑧ 王天根:《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建構》,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⑨ 《湖南巡撫趙通飭宣講章程公文》,鄧實輯《光緒癸卯(二十九年)政藝叢書·內政通紀》卷五,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28輯,第272冊,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第367頁。
⑩ 《裁宣講生》,《大公報》,1904年8月29日。
(11)《學部奏定教育會章程》,《浙江教育官報》,1909年第8冊,第47頁。
(1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學部成立檔案史料》,《歷史檔案》,1989年第1期,第57頁。
(13)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1820,p270
(14)林則徐:《答奕山防御粵省六條》,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頁。
(15)《論本館作報本意》,《申報》,1875年10月11日。
(16)《本館條例》,《申報》,1872年4月30日。
(17)邵志擇:《近代中國報刊思想的起源與轉折》,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1頁。)
(18)《附呈藩司丁日昌條說》,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六冊卷五十五,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268頁。
(19)(33)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1-62、329頁。
(20)范:《〈萬國公報〉第二百冊之祝辭》,《萬國公報》第200冊,1905年9月,第38本,第23611頁。
(21)[英]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頁。
(22)王林:《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47頁。
(23)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頁。
(24)鄒振環:《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頁。
(25)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92頁。
(26)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08頁。
(27)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頁。
(28)(30)李斯頤:《清末10年官報活動概貌》,《新聞研究資料》,1991年第3期。
(29)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頁。
(31)《〈北洋官報〉序》,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公元724年-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
(32)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670頁。
(34)夏曉虹:《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官方資源》,《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作者系遼寧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張毓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