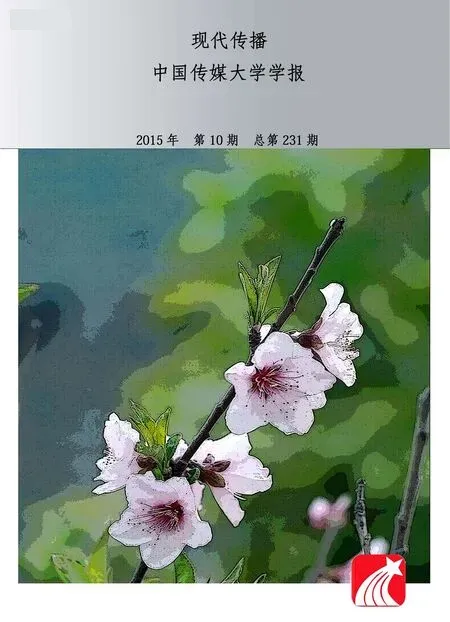新中國官方體育紀(jì)錄電影中的政治傳播研究
【內(nèi)容摘要】 建國初期,官方體育紀(jì)錄電影在意識形態(tài)敘事框架下形成了一整套革命話語表達(dá)體系,對體育進(jìn)行泛政治化表達(dá)。改革開放后,現(xiàn)代化話語取代革命話語,同時新一代導(dǎo)演追求影片的藝術(shù)性和體育精神的傳達(dá)。進(jìn)入新世紀(jì),體育紀(jì)錄電影“去政治化”的表象下,政治性表達(dá)依然存在。本文從傳播學(xué)的視角對體育紀(jì)錄電影中的政治傳播進(jìn)行研究,描摹體育紀(jì)錄電影與政治、文化之間關(guān)系的宏觀社會圖景。
從20世紀(jì)開始,人們就意識到了紀(jì)錄電影巨大的社會功能,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紀(jì)錄電影都發(fā)揮了極大的鼓動宣傳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后,體育紀(jì)錄電影作為文藝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體現(xiàn)宣傳部門的意識形態(tài)導(dǎo)向;另一方面,體育紀(jì)錄電影也參與意識形態(tài)整合,所以說,體育紀(jì)錄電影是實(shí)現(xiàn)政治傳播的傳媒藝術(shù)重要形式。在國內(nèi),關(guān)于媒介與政治傳播的研究多聚焦于新聞媒介與政治傳播的關(guān)系,作為廣義大眾傳播媒介的一種,作為重要的傳媒藝術(shù)形式,電影與政治傳播的關(guān)系則很少被研究,幾乎為空白。而作為一種被忽略的具有政治影響的溝通媒介,影像具備更廣泛地接觸無限多觀眾的可能性,能創(chuàng)造更多的公眾意見 ①,本文就以體育紀(jì)錄電影為研究對象,對影像中的政治傳播進(jìn)行研究。美國研究體育電影的學(xué)者認(rèn)為體育就是一個微觀社會(Coakley,1998;Eitzen,1996;Swift,1994) ②,體育紀(jì)錄電影記錄的是體育事件,反映的是時代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現(xiàn)狀,傳遞出的則是價值觀、習(xí)俗與信仰。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中央新聞紀(jì)錄電影制片廠(以下簡稱“新影廠”)拍攝的體育紀(jì)錄電影,時間范圍從1953年到2008年,共計(jì)120部之多。由于單純地進(jìn)行文本分析會使得研究不夠宏觀,所以,本文在對體育紀(jì)錄電影進(jìn)行文本分析的同時,又不僅僅局限于文本分析,而是采用傳播學(xué)視角,把體育紀(jì)錄電影還原到當(dāng)時的歷史環(huán)境當(dāng)中,與國家的政治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包括文化政策、體育政策相關(guān)聯(lián),對體育紀(jì)錄電影中的政治傳播進(jìn)行研究。為此筆者查閱了大量關(guān)于這些體育紀(jì)錄電影的背景資料,對體育紀(jì)錄電影的拍攝背景、拍攝過程及文本進(jìn)行了比較詳細(xì)的解讀,并對顧筠和陳光忠兩位體育紀(jì)錄電影的重要導(dǎo)演進(jìn)行了訪談。
一、“十七年”時期的體育紀(jì)錄電影(1949—1966年)
194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guān)于中央政府成立后黨的宣傳部門工作問題的指示》,規(guī)定將所屬電影管理局改為電影局,隸屬于文化部,國家電影局的成立標(biāo)志著國家行政力量對電影事業(yè)的統(tǒng)一管理與協(xié)調(diào),意義重大,有研究者概括說:“電影局的成立在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歷史上是一個分水嶺,它預(yù)示著電影作為一個行業(yè)將告別以往行走江湖似的個體生存狀態(tài),而進(jìn)入主流政治話語和國家行政規(guī)劃,從此,在不排除電影應(yīng)有的企業(yè)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外,還必須被國家事業(yè)的宏大概念所覆蓋,并且要最大程度地傳達(dá)出思想領(lǐng)域的聲音,它承載了意識形態(tài)、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文化宣傳的多重功能。” ③由此開始,新聞紀(jì)錄電影成為黨和國家政治傳播中的重要媒介。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曾寫到,“圖像始終是最可靠的觀念傳達(dá)方式,其次則是能夠喚起記憶圖像的詞語。” ④中國的體育紀(jì)錄電影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話語體系,鏡頭中人們的表情總是熱情洋溢的,情緒總是高漲的,而影片的解說詞總是慷慨激昂的,影片通過影像和“權(quán)威之聲”的解說,渲染影片的政治色調(diào),而這個敘事框架也影響了以后幾十年里體育紀(jì)錄電影的生產(chǎn)。
從作品的數(shù)量上來說,這段時期是體育紀(jì)錄電影歷史上的第一個繁榮時期,17年間總共拍攝了52部體育紀(jì)錄電影;從內(nèi)容上來說涵蓋的體育項(xiàng)目也非常廣泛,包括綜合性運(yùn)動會、群眾體育、田徑、體操、乒乓球、武術(shù)、冰雪項(xiàng)目以及足籃排三大球等,其中綜合性運(yùn)動會、乒乓球、登山和冰雪項(xiàng)目屬于拍攝較多的題材。這一時期的體育紀(jì)錄電影主要是“新聞紀(jì)錄電影”,紀(jì)錄電影附加新聞功能,總體特征可以概括為“形象化的黨報”。
1體育紀(jì)錄電影是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武器
“在國家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中,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jī)器同鎮(zhèn)壓性國家機(jī)器同樣重要,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在掌握政權(quán)的同時把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jī)器并在這套機(jī)器中行使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話,那么它的政權(quán)就不會持久。”這是阿爾都塞在《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jī)器》中的論述,同時,他還認(rèn)為,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jī)器也許不只是階級斗爭的賭注還是階級斗爭的場所,阿爾都塞在文章中列舉了列寧的例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diǎn),同樣,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紀(jì)錄電影作為“形象化的黨報”是重要的斗爭武器。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也非常重視這個武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紀(jì)錄電影的創(chuàng)作,1958年時,他提出了“藝術(shù)性紀(jì)錄片”的概念,指導(dǎo)紀(jì)錄電影的創(chuàng)作。
既然是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武器,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紀(jì)錄電影制作隊(duì)伍的純粹性。“新影廠”的編導(dǎo)都是來自各地方制片廠的精英,大部分是建國以前就開始拍攝新聞紀(jì)錄電影的無產(chǎn)階級藝術(shù)工作者,本身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zhì),另一方面紀(jì)錄片作為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充分發(fā)揮其記錄歷史的作用和宣傳作用,對攝影工作者進(jìn)行教育,使其思想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非常關(guān)鍵,“為了完成新聞紀(jì)錄電影的歷史使命,從新聞紀(jì)錄電影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牢牢把握從理論教育、實(shí)踐學(xué)習(xí)和戰(zhàn)斗與生產(chǎn)第一線造就鍛煉有素的革命文藝戰(zhàn)士,培養(yǎng)、建立起新聞紀(jì)錄電影創(chuàng)作、生產(chǎn)的革命隊(duì)伍。” ⑤正是這樣一支隊(duì)伍把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理論思想帶到了體育紀(jì)錄電影當(dāng)中。
《青春萬歲》拍攝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第一屆全國運(yùn)動會,這次運(yùn)動會上共有7名運(yùn)動員打破游泳、跳傘、射擊、航空模型4項(xiàng)世界紀(jì)錄,打破世界紀(jì)錄就意味著擺脫“東亞病夫”的帽子,這極大地鼓舞了國人的熱情,這部影片也是新影廠規(guī)模空前的一次拍攝。展示體育事業(yè)成就的目的在于展現(xiàn)社會制度的優(yōu)越性,而這一時期拍攝的《永遠(yuǎn)年青》《青春的花朵》《征服世界最高峰》等,目的在于反映新中國不同于舊社會的精神面貌。
《征服“冰山之父”》講述中蘇兩國爬山運(yùn)動員登上了從來沒有人登上過的慕士塔格山最高峰,中蘇運(yùn)動員一起生活、考察,舉行足球賽,最后克服重重困難登上了“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最高峰,展現(xiàn)出大無畏的英雄精神,影片最后的解說詞說:“現(xiàn)在中蘇兩國的國旗已經(jīng)飄揚(yáng)在慕士塔格山頂,31名中蘇爬山運(yùn)動員正在冰山之父的頂峰歡呼勝利,我們祝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像冰山之父一樣永恒。”影片旨在展現(xiàn)中蘇社會主義陣營的偉大勝利,也是中蘇關(guān)系處于蜜月期的一種見證。同樣,《第一屆新興力量運(yùn)動會》也旗幟鮮明地體現(xiàn)出沖破美國等西方強(qiáng)國體育壟斷的勝利之情,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顯性宣傳在這一時期的體育紀(jì)錄電影中普遍存在。
2體育紀(jì)錄電影構(gòu)建民族身份認(rèn)同
比爾·尼克爾斯曾經(jīng)寫到,不管意識形態(tài)以何種面貌出現(xiàn)——比如《權(quán)利法案》、“五年計(jì)劃”、溫和專制或競爭精神,它的作用就是提供故事、影像和神話,用某一套價值觀來取代其它的價值觀,有了集體歸屬感,人們就會舍棄那些(被認(rèn)為是)偏離常規(guī)的、有破壞性的或非法的價值觀和信仰。紀(jì)錄片電影和電視的政治性,反映出紀(jì)錄片對那些在特定時期、特定地點(diǎn)構(gòu)成(或爭取成為)社會歸屬感(或集體歸屬感)的特殊形式的價值觀和信仰,并為信仰和價值觀的建立提供一種具體可感的表達(dá)方式。 ⑥紅紅火火的群眾體育運(yùn)動場面,加上配音演員慷慨激昂的解說,在那個消息閉塞、文化產(chǎn)品匱乏的年代,這些影片就像具有魔力一般,激勵民眾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懷。
《征服世界最高峰》(1960年,攝影:牟森、王喜茂;編輯:吳均、應(yīng)小英)記錄了中國運(yùn)動員第一次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全過程。1960年,我國正處于三年自然災(zāi)害最嚴(yán)重的時期,外交方面與蘇聯(lián)的關(guān)系也面臨著僵局,在這種背景之下,國家領(lǐng)導(dǎo)人周恩來、賀龍決定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影片中的解說詞激情豪邁地說:“幾十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登山隊(duì),多次想要攀登珠穆朗瑪峰,但從北坡攀上頂峰,沒有一個獲得成功,歷史將再一次證明,在中國人民面前,無深不可測,無高不可攀,我們一定能從以往登山家失敗的地方踏出一條通向勝利的道路。”
珠穆朗瑪峰北坡被稱為“死亡路線”,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從北坡登頂珠峰,在七八千米的高山上攝制紀(jì)錄片,當(dāng)時在世界上也是從來沒有過,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壯舉,登山隊(duì)員的英雄事跡給全國各族人民帶來了極大鼓舞,在社會主義起步的艱難階段,在內(nèi)憂外患的環(huán)境下,《征服世界最高峰》這部影片給國人帶來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強(qiáng)了民眾對于民族主體性的認(rèn)同,從而可以引導(dǎo)民眾對建立一個現(xiàn)代的、獨(dú)立的民族國家的想象。
《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biāo)賽》是一部新聞紀(jì)錄電影,男子團(tuán)體在決賽中戰(zhàn)勝日本隊(duì)的比賽尤其激動人心,比賽一直打到第八局,最后容國團(tuán)在最后一局21∶18,以總比分2∶1戰(zhàn)勝日本選手星野,中國乒乓球代表團(tuán)奪得了男團(tuán)、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的世界冠軍,攝影師沈杰在他的書中寫道,“中國人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以英姿勃勃的形象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在困難時期大大長了人們的志氣,激發(fā)了民族上進(jìn)心。” ⑦由于“他者”的存在,自我意識、自我主體才得以確立,體育比賽中必然存在那個“他者”,在實(shí)現(xiàn)了民族獨(dú)立的情況下,通過體育比賽中戰(zhàn)勝“他者”可以更好地來確立民族主體性,實(shí)現(xiàn)民族身份認(rèn)同。在那個年代,乒乓球比賽的政治意義大大超出了比賽本身,也正是看到了這類紀(jì)錄片的政治傳播效果,在膠片極其緊張的條件下(據(jù)編導(dǎo)陳光忠老人回憶,那個年代“新影廠”的膠片比是1∶35),“新影廠”仍然相繼拍攝了《中日乒乓賽》《北京國際乒乓球邀請賽》《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biāo)賽(上下)》等體育紀(jì)錄電影。
二、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體育紀(jì)錄電影(1967—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新影廠的大部分人員也都去參加“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影片數(shù)量較以前大幅下降,在藝術(shù)性上,與“十七年”時期相比更是沒有任何進(jìn)步。新影廠體育紀(jì)錄片編導(dǎo)陳光忠曾經(jīng)談到,新聞電影被迫按照“四人幫”的框框去套,單調(diào)乏味,千篇一律,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大行其道,板起臉孔訓(xùn)人。 ⑧這一時期,新影廠總共拍攝了12部體育紀(jì)錄電影,包括綜合性運(yùn)動會、乒乓球以及其它球類運(yùn)動、武術(shù)、登山等項(xiàng)目。“文化大革命”全稱是“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宗旨是以無產(chǎn)階級文化革資產(chǎn)階級文化的命,所以這一時期的指導(dǎo)思想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再加上后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tuán)企圖利用紀(jì)錄片來服務(wù)于自己的政治野心,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也成為他們所利用的政治符號,階級斗爭再也不像建國初期那般溫和,甚至成為西方人眼中的另一場革命,而這一“革命”主要發(fā)生在文化領(lǐng)域,所以體育紀(jì)錄電影中也充斥著“階級斗爭”色彩,革命話語成為影片唯一的表達(dá)方式。
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體育紀(jì)錄電影是《再次登上珠穆朗瑪峰》(1975年,編輯:沈杰、葉同荷;攝影:劉永恩、沈杰等),影片記錄的是1975年中國登山運(yùn)動員從北坡再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壯舉,由于1960年登頂時是在夜里,攝影機(jī)沒有記錄下中國人登頂珠峰的鏡頭,有些國家不承認(rèn)這一世界記錄,于是有了二次登頂。1975年5月27日,以潘多為首的九名男女運(yùn)動員從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頂峰。《再次攀登上珠穆朗瑪峰》當(dāng)時在上海放映不到一個月,觀眾就超出三十萬,此片外語版在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放映要達(dá)一個月之久。影片“大字報式”的解說詞體現(xiàn)出鮮明“時代特色”,如“我國男女登山運(yùn)動員滿懷革命豪情,從拉薩出發(fā),決心把76年的任務(wù)提前一年完成,再次從北坡攀登珠穆朗瑪峰,為毛主席爭光,為社會主義祖國爭光。杯杯青稞酒,碗碗酥油茶,把親人的囑托全咽下,全心全意為人民,事事都聽毛主席的話。”
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作為政治符號的表述在這一時期的文化作品中屢見不鮮,也是文化作品階級性的一個重要標(biāo)志。《乒壇盛開友誼花——第31屆乒乓球世界錦標(biāo)賽》(1971年,編導(dǎo):張孟起等;攝影:李振羽等)記錄的是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乒乓球世界錦標(biāo)賽,尤其對中國代表團(tuán)到達(dá)日本參加相關(guān)活動,以及比賽過程進(jìn)行了記錄:“經(jīng)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中國運(yùn)動員帶來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問候”。
體育一直是新中國對外交流的鑰匙,“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沒有中斷國際交流,體育成為中日、中美關(guān)系的一個突破口,而作為政治傳播媒介的體育紀(jì)錄電影則成為重要的輿論宣傳工具,對中日、中美建交之前的輿論營造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三、新時期的體育紀(jì)錄電影(1977—1999年)
十年“文革”結(jié)束后,整個中國社會百廢待興,體育事業(yè)開始迅速發(fā)展,1979年11月26日,中國恢復(fù)了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合法席位,80年代,中國女排豪取五連冠,1990年北京成功舉辦了亞運(yùn)會。體育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也為體育紀(jì)錄電影的拍攝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體育紀(jì)錄電影迎來了又一個黃金時期。1977年到20世紀(jì)末,“新影廠”總共拍攝了約60部體育紀(jì)錄電影,其中涉及綜合性運(yùn)動會、體操、三大球、乒乓球、冰雪項(xiàng)目、群眾體育、民族體育等,大部分拍攝于上世紀(jì)80年代,所以說80年代是迄今為止體育紀(jì)錄電影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以1990年北京亞運(yùn)會為題材,“新影廠”又先后拍攝了《亞運(yùn)之城》《亞運(yùn)之星》《亞運(yùn)之情》3部短片,亞運(yùn)期間拍攝了9集系列片《難忘的十六天》,1992年“新影廠”還拍攝了3集短片《奔向巴塞羅那》。
“八十年代初的‘傷痕’文學(xué)、尋根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現(xiàn)代派小說、現(xiàn)代主義詩歌、星星美展和‘第五代’電影的興起等都一度成為八十年代‘文化熱’的重要標(biāo)識,與此同時新一批作家、畫家和導(dǎo)演的崛起都使得這個群星閃耀且成果豐碩的十年格外光彩奪目。” ⑨從“文革”結(jié)束到89年,這段時期也被認(rèn)為是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中日合拍《絲綢之路》《話說長江》等幾部紀(jì)錄片之后,國外的紀(jì)錄片拍攝理念進(jìn)入中國,同時國內(nèi)電影界也開展了關(guān)于電影理論的大討論,體育紀(jì)錄電影的創(chuàng)作者們躍躍欲試,試圖打破“文革”時期的條條框框,回歸到紀(jì)錄電影的藝術(shù)本質(zhì),泛政治化表達(dá)開始退場,體育精神慢慢回歸,影片開始展現(xiàn)體育的力與美。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隨著電視的發(fā)展以及電視新聞的興起,紀(jì)錄片附加的新聞功能逐漸淡化,紀(jì)錄片與新聞片漸漸分離,紀(jì)錄片也開始由國家的宏大敘事轉(zhuǎn)向個人敘事,這一時期體育紀(jì)錄電影中的政治傳播呈現(xiàn)出新特點(diǎn)。
1意識形態(tài)、民族主義仍是宣傳重點(diǎn)
計(jì)劃體制下的體育紀(jì)錄電影始終是主旋律的,始終發(fā)揮著塑造民族主體性、宣傳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新影廠”編導(dǎo)陳光忠的“體育三部曲”《新起點(diǎn)》《奪標(biāo)》《零的突破》,分別記錄了中國體育發(fā)展的三個階段:《新起點(diǎn)》拍攝的是第四屆全運(yùn)會,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體育新的起跑線;《奪標(biāo)》拍攝的是新德里亞運(yùn)會,中國力壓日本成為亞洲第一;《零的突破》為中國奧運(yùn)代表團(tuán)壯行,之后中國隊(duì)在洛杉磯奧運(yùn)會實(shí)現(xiàn)了金牌零的突破。影片對新中國成立以前與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影像用黑白和彩色作對比處理,形成強(qiáng)烈的視覺沖擊,突出社會主義新中國體育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展示出政治制度上的優(yōu)越性。
《乒乓英豪》中中國隊(duì)在第36屆世乒賽上豪取七個項(xiàng)目的冠軍,《拼搏——中國女排奪魁記》《新的搏擊——記中國女排四奪冠》等記錄了中國女排的五連冠,國歌奏響、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時的那種民族自豪感,使國人感受到,一個獨(dú)立的現(xiàn)代化民族國家已經(jīng)不僅僅存在于想象當(dāng)中,而是正身處其中,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被點(diǎn)燃之后又迅速集聚。也正是意識到了這種政治影響力,在國力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提出優(yōu)先發(fā)展競技體育,要“沖出亞洲,走向世界”。
2革命話語向“現(xiàn)代化話語”轉(zhuǎn)變
“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以后,“實(shí)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口號響徹神州大地,盛行于中國文藝界幾十年的革命話語開始發(fā)生變化,“現(xiàn)代化話語”成為主流表達(dá),一時之間,神州大地上飛揚(yáng)的口號不再是“階級斗爭”,而是建設(shè)四化、振興中華。《騰飛吧,中華健兒》(1983年,總攝影:沈杰;編導(dǎo):木鐵)是為第五屆全國運(yùn)動會拍攝的紀(jì)錄電影,在1984年意大利都靈國際體育電影節(jié)上獲得了二等獎。影片中說道:“體育事業(yè)的興旺發(fā)達(dá),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shè)具有重要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shí)現(xiàn)了歷史性轉(zhuǎn)折,十年浩劫中飽受創(chuàng)傷的體育戰(zhàn)線,重振旗鼓突飛猛進(jìn),中國乒乓健兒長盛不衰,女排姑娘贏得了三大球的翻身一仗,新的世界記錄和世界冠軍不斷出現(xiàn),捷報頻傳,人心大振,體育健兒譜寫的中國之歌在神舟大地匯成一股振興中華的交響樂。”
體育比賽的有形賽場與四化建設(shè)的無形賽場實(shí)現(xiàn)了高度的重合,受眾所看到的賽場上的拼搏、感受到的賽場上的激情移情到了社會主義建設(shè)當(dāng)中。《拼搏——中國女排奪魁記》(1982年,張貽彤、沈杰等)記錄了1981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三界世界杯女子排球賽中奪取冠軍的情況,片中不但有球賽,場面緊張、精彩,而且中國女排表現(xiàn)出來的為祖國爭榮譽(yù)的拼搏精神特別富有感染力,這種拼搏精神正是當(dāng)時建設(shè)四化、振興中華所需要的時代精神。
3國家敘事向個人敘事的轉(zhuǎn)變
這一時期的體育紀(jì)錄電影的生產(chǎn)仍然是由國家主導(dǎo),敘述方式也依然沿襲了“十七年”時期社會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創(chuàng)作準(zhǔn)則,同時集體主義仍然是體育紀(jì)錄電影突出的表現(xiàn)主題,但這是一個轉(zhuǎn)折的時期,80年代的導(dǎo)演追求影片的藝術(shù)性和體育精神的回歸,體育紀(jì)錄電影也開始由國家宏大敘事向個人敘事轉(zhuǎn)變,體育紀(jì)錄電影不再是“只見政治不見體育”“只見精神不見人”,影片開始關(guān)注到運(yùn)動員個人,開始關(guān)注到體育運(yùn)動中“人”的精神。第一次以單個運(yùn)動員作為拍攝對象的紀(jì)錄片是李連杰19歲時拍攝的,介紹了李連杰的成長經(jīng)歷,12歲在第三屆全運(yùn)會上奪得武術(shù)冠軍,蟬聯(lián)五屆全國全能冠軍,影片突出了運(yùn)動員個人的勤奮、刻苦和拼搏精神。
體育紀(jì)錄電影《離隊(duì)之后》向觀眾介紹了老女排隊(duì)員孫晉芳、曹慧英、陳亞瓊、陳招娣、楊希離隊(duì)之后的生活,有的當(dāng)起了體育記者,有的進(jìn)入了體育院校讀書,有的當(dāng)起了領(lǐng)導(dǎo),還有的是人大代表,片子更多地關(guān)注到了運(yùn)動員個人的生活方面,但影片對運(yùn)動員個人故事進(jìn)行講述,目的還是在于突出退役老運(yùn)動員作為普通人繼續(xù)為四化建設(shè)、為祖國作貢獻(xiàn)的主題。
四、新世紀(jì)的體育紀(jì)錄電影(2000年至今)
進(jìn)入21世紀(jì)以后,隨著媒體環(huán)境的變化,體育更多地與電視聯(lián)姻,直播成為更能夠突出體育魅力的呈現(xiàn)形式,體育紀(jì)錄電影作品屈指可數(shù)。2001年北京成功申辦第29屆夏季奧運(yùn)會,“新影廠”拍攝了《加油中國》和《筑夢2008》兩部體育紀(jì)錄電影。雖然“新影廠”導(dǎo)演顧筠受邀拍攝了北京奧運(yùn)會的官方紀(jì)錄電影《永恒之火》和廣州亞運(yùn)會的官方紀(jì)錄電影《緣聚羊城》,但這兩部片子的投資方都是賽事組委會,影片旨在展現(xiàn)奧林匹克文化和奧林匹克精神,并不體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政府的官方意志,因此不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筑夢2008》和《加油中國》從片名就能夠看出這是一種“強(qiáng)國夢”敘事,一方面,自上世紀(jì)張伯苓提出:中國何時才能派一名運(yùn)動員參加奧運(yùn)會中國何時才能派一只代表隊(duì)參加奧運(yùn)會、中國何時才能在本土舉辦一次奧運(yùn)會等問題,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的舉辦是中國人百年奧運(yùn)夢的實(shí)現(xiàn)。另一方面,自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提出要建設(shè)富強(qiáng)、民主、文明的新中國,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2008年北京奧運(yùn)會的舉辦更是我們強(qiáng)國夢的一種體現(xiàn)。這一時期,紀(jì)錄片成為國家提升“軟實(shí)力”的重要舉措,黨和政府強(qiáng)調(diào)“去政治化”的文化輸出,所以,在《筑夢2008》中,導(dǎo)演顧筠沒有用意識形態(tài)的敘事框架對體育作泛政治化的表達(dá),“金牌戰(zhàn)略”“為國爭光”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被“夢想”“拼搏”這樣的普世話語所取代,夢想、拼搏是體育的本質(zhì)文化,這既實(shí)現(xiàn)了體育精神的回歸與傳達(dá),又實(shí)現(xiàn)了政治傳播的目的。影片中的普通拆遷戶高桂蘭、特警隊(duì)員、運(yùn)動員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符號,他們代表著每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他們的集體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情感通過紀(jì)錄片傳遞給觀眾,政治化的說教被包含進(jìn)抒情化的敘事之中,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無一例外受到召喚而在紀(jì)錄片中獲得延續(xù)。 ⑩由此可見,進(jìn)入新世紀(jì)以后的“去政治化”文化輸出與上世紀(jì)80年代的淡化意識形態(tài)、淡化階級意識不同,“去政治化”不過是一種表象 瑏瑡,政治性的表達(dá)還是被安排其中。
五、結(jié)語
體育紀(jì)錄電影是體育發(fā)展的影像書寫,更是政治經(jīng)濟(jì)與社會文化發(fā)展的影像書寫,官方拍攝的體育紀(jì)錄電影作為主旋律影片,承載著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宣傳功能,同時也參與意識形態(tài)整合。從“十七年”電影時期革命話語式的泛政治化表達(dá),到“現(xiàn)代化敘事”,再到“強(qiáng)國夢”敘事,體育紀(jì)錄電影的敘事與政治文化變遷是相契合的,同時,從體育紀(jì)錄電影的敘事中也能夠反映出冷戰(zhàn)時代到后冷戰(zhàn)時代政治話語的轉(zhuǎn)向。
如今,在國家政策的有意識引導(dǎo)和市場經(jīng)濟(jì)無意識的滲透之下,商業(yè)資本強(qiáng)勢介入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官方投資拍攝的體育紀(jì)錄電影作為政治傳播的傳媒藝術(shù)形式、大眾傳媒手段要在市場上占領(lǐng)一席之地非常困難,在受眾選擇多樣化的今天,政治性訴求也只有在藝術(shù)性包裹之下才能更好地實(shí)現(xiàn),這也是我們所仰望的“好萊塢模式”成功的法寶,把價值觀念寓于蕩氣回腸的故事、震撼的特效之中,才能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筑夢2008》作了一次類似的嘗試,可以成為官方體育紀(jì)錄電影創(chuàng)作的有益參考。
注釋:
① 劉君:《從制度到文化:政治傳播范式下的中國電影變遷》,《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0年第2期。
② Demetrius WPearson,Russell LCurtis,CAllen Haney,James JZhangSport Films:Social Dimensions Oveeq1930-1995Journal of Sport&Social Issues,Vol27,No2,May 2003,pp145-161
③ 沈蕓:《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史》,中國電影出版2005年版,第137頁。
④[美]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世紀(jì)出版集團(tuán)2006年版,第123頁。
⑤ 馮駟驥:《新聞電影——我們曾經(jīng)的年代》,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
⑥[美]比爾·尼克爾斯:《紀(jì)錄片導(dǎo)論》,陳犀禾等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1頁。
⑦ 沈杰:《我的足跡》,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版,第52頁。
⑧ 陳光忠:《從框框里跳出來——紀(jì)錄片〈美的旋律〉創(chuàng)作談》,http://xuewencnkinet/CJFDDYYS197903005html,訪問時間:2015年7月24日。
⑨⑩ 陳婷:《影像的歷史書寫》,復(fù)旦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2年,第7、84頁.
(11)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傳播與社會學(xué)刊》,2009年第8期。
(作者孟婷系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新聞學(xué)博士研究生;甘險峰系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責(zé)任編輯:劉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