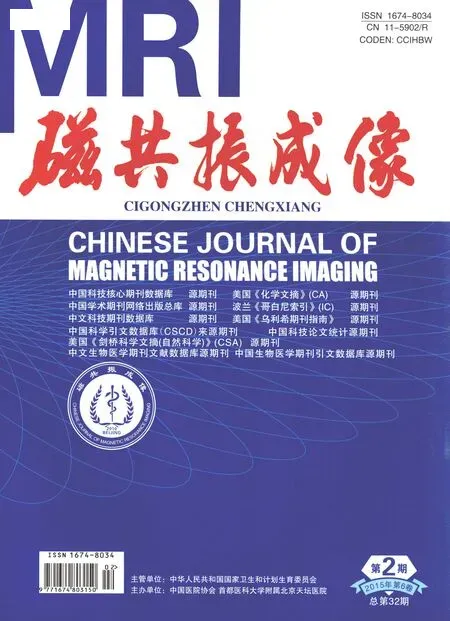磁共振成像技術在肝細胞癌中的應用進展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編號:81171338,81471658)
作者單位:
1. 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2010級8年制研究生,成都 610041
2.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放射科,成都610041
通信作者:
宋彬,E-mail:cjr.songbin@vip.163. com
收稿日期:2015-01-16
接受日期:2015-01-27
文獻標識碼:A
DOI: 10.3969/j.issn.1674-8034.2015.02.003
蔣涵羽, 劉曦嬌, 宋彬. 磁共振成像技術在肝細胞癌中的應用進展. 磁共振成像, 2015, 6(2): 91-97.
[摘要] 目的 探討磁共振成像在肝細胞癌診斷、預后評價、治療方案選擇、療效評估中的應用進展。材料與方法 收集并分析國內外最新相關文獻。 結果 功能磁共振成像及肝臟特異性對比劑等磁共振新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使磁共振成像不僅有助于早期診斷肝細胞癌,還可以反映腫瘤的發病機制、生物學行為特點和細胞水平的基因表達異常,為肝細胞癌的預后評價、治療方案的選擇及療效評估提供了重要信息。結論 磁共振成像是診斷、評估、監測、隨訪肝細胞癌重要的有效手段。
Progresses i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IANG Han-yu 1, LIU Xi-jiao 2, SONG Bin 2*
12010 grade eight year system graduate, West China School of Medicin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Song B,E-mail: cjr.songbin@vip.163.com
Received 16 Jan 2015, Accepted 27 Jan 2015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recent advances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techniques in the diagnosis, prognosis,treatment decision making and early assessment of therapeutic respons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 (HCC).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newest related published literatures about the MR imaging of HCC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With recen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functional MRI and liver-specific MR contrast agents in HCC, MRI is not only able to diagnose HCC in the early stage, but also reveal the tumor pathogenesis, biological behaviors and abnormal gene expressions at cellular level, thus providing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for the prognosis evaluation, treatment decision making and response assessment of HCCs. Conclusions: MR imaging plays a vital and effective role in the diagnosis, evaluation, surveillance and follow-up of HCC.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原發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是全球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我國是原發性肝癌的高發國家,其發病率與死亡率均居世界首位 [1]。PLC中90%以上的組織學類型是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根據我國國家衛生計生委、美國肝病研究學會、亞太肝臟研究協會、歐洲肝病學會等最新指南 [2-5],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是HCC診斷與監測的重要手段。近年來,隨著磁共振功能與代謝成像技術以及肝臟特異性對比劑的發展與應用,MRI不僅有助于早期發現和診斷HCC,并且可以反映HCC的發病機制、生物學行為特點和細胞水平的基因表達異常,為HCC的預后評價、治療方案的選擇及療效評估提供重要信息。本文結合2014年北美放射學會年會的相關熱點,總結了近年來功能與代謝MR成像技術在HCC中應用的研究進展,并討論了未來的研究方向。
1 MRI與HCC的生物學行為
大多數HCC是在肝硬化的背景上經再生結節(regenerative nodule, RN)、低級別不典型增生結節(low grade dysplastic nodule, LGDN)、高級別不典型增生結節(high grade dysplastic nodule, HGDN)、含有微小癌灶的HGDN、小肝癌逐步發展而來 [6-8]。目前多項研究表明,MRI某些與HCC的組織病理分型、生物學行為等密切相關的征象在HCC預后評價、治療方案選擇及療效評估方面有重要價值。
1.1 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
MVI是HCC預后不良的重要標志之一。MVI 與HCC的組織病理學類型、病灶大小等因素密切相關。研究發現,單結節型、單結節伴結節外生長型、多結節融合型HCC中MVI的發生率依次增高。直徑大于4 cm的HCC中,MVI的發生率是直徑小于4 cm的HCC的3倍。此外,低分化或未分化的HCC中MVI發生率是高分化HCC的6倍。目前的影像學檢查手段還難以直接顯示MVI,但一些影像學征象可以間接提示MVI的存在。研究發現,MVI的發生與HCC的多灶性 [9]、MR肝膽期HCC病灶周圍低信號環、 18F-FDG-PET的攝取程度等相關 [10]。MVI的早期影像學識別對HCC的評估具有重要意義,是目前HCC影像學研究的熱點之一。
1.2 纖維包膜與假包膜
許多HCC病灶周圍存在纖維包膜或假包膜,它們是與HCC預后相關的重要因素。HCC的纖維包膜通常分為內外兩層,內層為較致密的纖維組織,在T1WI、T2WI呈稍低信號;外層通常為擴張的血竇和新生小膽管,呈T1WI稍低、T2WI稍高信號。假包膜由擴張的血竇和瘤周纖維組織組成,在增強T1WI的延遲期表現為環狀強化 [11-12]。研究發現,纖維包膜是進展期結節性HCC的特征性表現,且具有完整纖維包膜的HCC病灶治療后的復發率低于沒有包膜或包膜不完整的病灶,提示纖維包膜可能可以阻止HCC的播散 [11-12]。
1.3 結節中結節(nodule in nodule)
許多HCC病灶可以表現為大結節灶(通常是DN,特別是高級別DN,少數可以為早期HCC)中出現進展期HCC小結節灶,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HCC特殊的生長方式。其中,小結節灶的MR信號特點與強化方式通常與典型進展期HCC相似;而大結節灶的MR表現則常常接近分化較好的肝臟組織 [13-14]。結節中結節在監測、隨訪肝硬化相關結節及診斷、評估早期HCC中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1.4 T1WI高信號結節
肝臟再生結節、DN及部分高分化HCC病灶在T1WI上可以表現為高信號結節,這是由結節內組織出血壞死,伴隨銅蛋白等順磁性物質、淀粉、脂肪或糖蛋白堆積,鐵沉著等病理過程所致 [13]。研究發現,HCC病灶在T1WI上的信號強度與疾病的預后相關,低信號的HCC結節通常組織學分級較低,而高信號的HCC組織學分級通常較高,提示HCC的預后相對較好 [13]。
1.5 脂肪成分
T1加權同/去相位掃描能夠明確HCC病灶內是否含脂肪成分。HCC內部是否含有脂肪成分與疾病的預后相關。研究發現,脂肪較常出現在1.5~3 cm大小的腫瘤灶內,而很少出現在較大的腫瘤內 [15]。且含有脂肪成分的HCC腫瘤生長和進展較緩慢,較少發生轉移,預后相對較好 [15]。
2 MRI新技術進展
2.1 動態對比增強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DCE-MRI)
作為一種MRI灌注顯像技術,DCE-MRI可以無創地評估組織及腫瘤的血流動力學特點。在肝臟病變的應用中,DCE-MRI能夠顯示不同掃描時間順磁性對比劑在肝臟中的分布變化并測量容積轉運參數(volume transfer coefficient,K trans)、速率常數(K ep)、血管外細胞外容積分數(V e)等參數,從而定量地反映正常肝臟組織及病灶區域的血流動力學變化。
目前,多期DCE-MRI與動態對比增強多排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multiple detector row computed tomography, MDCT)是HCC診斷、分期的影像學標準 [2-5]。動脈期快速不均質血管強化(arterial hypervascularity)及靜脈期或延遲期的快速洗脫(venous or delayed phase wash-out)是診斷HCC的可靠征象。由于DCE-MRI能夠定量反映正常肝組織及HCC病灶的血流動力學特點,故DCE-MRI不僅有助于早期識別和評估HCC結節,還能夠描繪出HCC病灶周圍微血管的浸潤情況、預測患者的預后及評估不同療法的療效 [16-27]。
2.2 肝臟特異性對比劑
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第一代磁共振非特異性對比劑釓類螯合物(Gadolinium chelates)已經廣泛運用于臨床肝臟MRI之中,并且明顯提高了MRI對肝臟病變的診斷能力。病理學研究證實,肝臟大多數RN及DN主要由門靜脈供血,而HCC的血供則主要來源于腫瘤動脈,這使得典型的肝臟良、惡性結節在動態釓增強MRI上具有不同的增強模式。然而,大多數早期HCC結節在動態釓增強MRI上缺乏典型的HCC增強表現,多難以早期診斷。近年來,新型肝臟特異性對比劑已經逐漸應用于臨床,它們不僅可以明顯提高MRI對早期HCC的診斷能力,還能夠幫助預測HCC的分化程度,從而為疾病的預后、治療及療效評估提供重要信息。目前常用的肝臟特異性對比劑主要包括肝細胞特異性對比劑及網狀內皮系統(reticuloendothelial system, RES)特異性超順磁性氧化鐵(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 SPIO) 顆粒。
肝細胞特異性對比劑可被肝細胞攝取,并在T1WI上產生明顯的高信號,之后經膽管排泄,故能夠特異性顯示肝細胞功能和組織微血管形成情況。目前常用的肝細胞特異性對比劑包括釓-多貝酸二葡甲胺(Gadobenate dimeglumine, Gd-BOPTA)和釓噴替酸葡甲胺(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triaminepentaacetic acid, Gd-EOB-DTPA)兩種類型。但研究發現,Gd-EOB-DTPA的安全性及對病灶的顯示均顯著優于Gd-BOPTA [28]。大多數HCC表現為動脈晚期快速的明顯強化、均衡期洗脫及肝細胞特異期呈明顯低信號 [29-30],故可與一些肝膽期表現為高信號的肝臟結節相鑒別 [31-33]。不僅如此,Gd-EOB-DTPA增強的MRI還可以反映HCC的分化程度 [30-31],分化程度高的HCC,腫瘤保留了部分肝細胞的功能,可攝取一定量的對比劑,因而在肝細胞特異期表現為等或高信號,反之分化差者則無強化而呈低信號改變。
SPIO可被肝臟RES內的Kupffer細胞特異性攝取,并使正常肝組織在T2WI上呈明顯的均勻低信號。然而,HCC組織內一般沒有或僅有少量Kupffer細胞 [34],故腫瘤組織信號強度明顯高于周圍肝臟組織。由于SPIO-MRI中組織的強化程度與Kupffer細胞的數量密切相關,SPIO-MRI可以有效鑒別早期HCC與其他良性肝臟結節,此外,該技術還有助于預測HCC的分化程度 [35-38]。
2.3 磁共振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基于組織細胞間水分子的布朗運動,DWI可以定量地反映水分子在組織中的彌散情況,從而無創地展現不同組織的結構特點及其微循環的灌注情況 [39]。其中,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可以定量地表現組織水分子的活動能力。大多數HCC病灶的組織密度高于周圍正常肝組織,因此水分的自由彌散受到限制,故HCC病灶在DWI圖像上呈現為高信號,且ADC值低于周圍組織 [40-43]。
首先,通過定量分析組織中水分子彌散情況及計算相應的ADC值,DWI能夠幫助鑒別肝臟的良性結節(如RN、DN等)以及HCC結節 [44-47]。因此,DWI能夠顯著提高微小HCC病灶的檢出率,增加HCC早期診斷的敏感性與準確率,還可用于腫瘤局部復發的監測與隨訪 [18, 47-50]。其次,DWI可以預測HCC的病理分級 [51-53],從而為患者預后評估提供重要信息。第三,DWI有助于指導HCC患者治療方案的選擇及評估抗腫瘤治療的療效。研究發現,DWI能夠定量評價HCC患者接受TACE等局部消融治療 [54]及系統性治療 [55]后腫瘤細胞壞死情況。此外,DWI還具有掃描時間短 [17],且不需要使用釓造影劑 [39]等優點。
然而,DWI圖像較容易受相鄰臟器運動及氣體偽影的干擾,有時難以確切識別靠近膈肌的肝臟病變。不僅如此,雖然DWI對小肝癌的敏感性已明顯高于其他傳統影像學檢查手段,但由于廣泛纖維化的肝臟組織也可限制水分子的彌散,因此在此背景下HCC病灶與周圍組織的對比度可有所降低,從而造成部分微小病灶的漏診。
2.4 體素內不相干運動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maging, IVIM)
IVIM是一種特殊的新興磁共振DWI方法。與傳統利用單指數模型對組織中水分子擴散運動狀態作定量分析的DWI相比,IVIM能夠通過雙指數模型分別獲取反映組織中水分子擴散情況以及微循環毛細血管灌注效應的參數,從而將來自于組織中水分子布朗運動的彌散信號和來自于毛細血管微循環的灌注信號區分開,從而更好地描述生物體內復雜的信號衰減方式 [39, 56]。如前所述,傳統DWI在HCC中容易受到鄰近臟器運動及呼吸偽影的干擾,且對纖維化背景下的微小病灶的檢出率較低。不僅如此,利用ADC值鑒別良、惡性肝臟結節的準確性極大地依賴于b值的選擇,但b值受到組織灌注的影像較大 [57]。因此,IVIM與傳統DWI相比能夠顯著提高對微小HCC病灶的檢出率及準確性。此外,近年來也有研究表明,高級別HCC的IVIM成像中D及ADC值均明顯高于低級別HCC,且f值與動脈期增強分數有很好的相關性,其結果表明IVIM鑒別高級別HCC與低級別HCC的能力顯著優于DWI,說明IVIM可用于預測HCC的組織學分級 [58]。
然而,目前針對IVIM在HCC中的研究較有限,未來仍需要大量大樣本、高質量的研究來證實IVIM在HCC診斷、監測中的確切地位。
2.5 動脈自旋標記(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
ASL是一種利用磁性標記的動脈血作為內源性標記物定量反映組織灌注情況的磁共振灌注成像方法。目前常用的ASL脈沖方式主要包括脈沖式動脈自旋標記(pulsed arterial spin labeling, PASL)及連續動脈自旋標記(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CASL)兩種。ASL不需要使用對比劑,可以無創、可重復地反映組織器官的血流灌注情況,目前已經廣泛應用于腦、肺、腎、心臟等器官中。近年來的研究發現,ASL可以很好地顯示腸系膜上靜脈及肝內門靜脈的結構及血流灌注情況 [59-60],表明ASL可以用于顯示正常肝臟及肝臟良、惡性病變的微血管結構及評估其血流動力學特征。目前雖尚無ASL在HCC中的相關研究,但ASL可以在不使用對比劑的情況下無創地反映出HCC及周圍正常肝組織的灌注情況,并且具有早期評價HCC微血管侵犯情況的潛力,因此可能具有較好的應用前景。
2.6 磁共振彈性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 MRE)
MRE是基于彈性成像技術的磁共振成像手段,通過定量分析對組織施加一個正應力或剪切應力后組織產生的反作用響應的大小及性質可以判斷組織的彈性程度。如前所述,肝臟纖維化在HCC的發病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MRE可以定量無創、定量地檢測并評估肝臟纖維化程度 [61-62]。不僅如此,HCC等肝臟惡性腫瘤的平均剪切彈性明顯高于正常肝組織、纖維化的肝組織或肝臟良性腫瘤 [63-64],表明MRE能夠鑒別肝臟良、惡性腫瘤。盡管如此,目前針對MRE在HCC中的研究仍十分有限,未來仍需要大量的研究來證實MRE在HCC中的確切地位。
2.7 磁共振波譜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MRS)
MRS是評估組織器官生化代謝的無創影像學手段。目前,應用于臨床及科研之中常用的MRS波譜包括 1H 、 31P及 23Na譜等,其中H質子在所有射頻激勵的原子核中敏感性最高,故最適用于MRS的研究 [65]。目前,在肝臟領域MRS主要用于彌漫性肝臟疾病(如肝臟脂肪化程度的定量評估 [66])及局灶性肝臟疾病的研究。然而,MRS在肝臟惡性腫瘤的診斷上敏感性與特異性均較低 [67],在HCC中的應用仍處于探索階段。MRS易受到鄰近臟器運動偽影的干擾,故其診斷價值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設備及儀器的改進。但MRS可以無創地反映出HCC及周圍肝組織的代謝及生化情況,在HCC的早期診斷、預后評估中的應用價值及前景不可忽視。
2.8 磁敏感成像(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SWI)
SWI是一種以T2 *加權梯度回波序列作為序列基礎,根據不同組織間的磁敏感性差異提供對比增強機制的MRI新技術 [4]。SWI對組織中的血液或鐵十分敏感。SWI可以反映HCC的組織病理特點,評估HCC假包膜、腫瘤內部微出血、HCC鑲嵌征等微觀征象。雖然目前有關SWI在HCC中應用的研究非常有限,但其在HCC中具有一定的應用前景。
2.9 血氧水平依賴(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BOLD)
BOLD是通過評估組織血紅蛋白含氧量,定量反映組織的氧代謝情況的新興磁共振成像技術。BOLD具有無創、可重復性強且無需注入對比劑等優點,目前已經運用于中樞神經系統、腎臟、肝臟等領域。BOLD的主要參數包括自旋-自旋弛豫時間(spin-spin relaxation time, T2 *)、表觀自旋-自旋弛豫率(apparent spin-spin relaxation ratio, R2 *)等。近期的研究發現 [68-69],正常肝組織在氧氣的刺激下R2 *明顯增強,而纖維化的肝組織R2 *無明顯變化,后者的ΔR2 *明顯小于前者,表明ΔR2 *可以作為反映肝臟血流動力學及纖維化程度的良好指標。不僅如此,BOLD還有助于鑒別肝臟良惡性結節和反映肝臟腫瘤的血管生成情況 [70-71],并且能夠反映栓塞化療在HCC中的療效 [72]。
然而,BOLD較易受到運動偽影的干擾,目前有關肝臟領域BOLD的研究十分有限,且其中大多為動物實驗。但BOLD在肝臟良、惡性病灶的診斷與評估中擁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因此尚需大量高質量研究來證實其在HCC中的應用價值。
3 小結
HCC是肝臟組織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具有起病隱匿、診斷時多數患者已經為局部晚期或出現遠處轉移、治療難度大等特點,嚴重威脅著我國及全球人民的健康。根據最新指南 [2-5],多期DCE-MRI與動態MDCT已成為目前HCC診斷、分期首選的影像學手段,肝穿刺活檢僅用于無法憑借影像學及血清學檢查確診的少數HCC病例。近年來,隨著MRI技術的不斷發展,DWI、IVIM、MRE、MRA、SWI、ASL、BOLD等多種磁共振功能成像技術及新的肝臟特異性對比劑等已經可以運用于HCC的影像檢查,并顯著提高了MRI對HCC的早期診斷與監測能力,在HCC的早期診斷、預后評價、治療方案選擇、療效評估及復發轉移監測中擁有廣闊的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