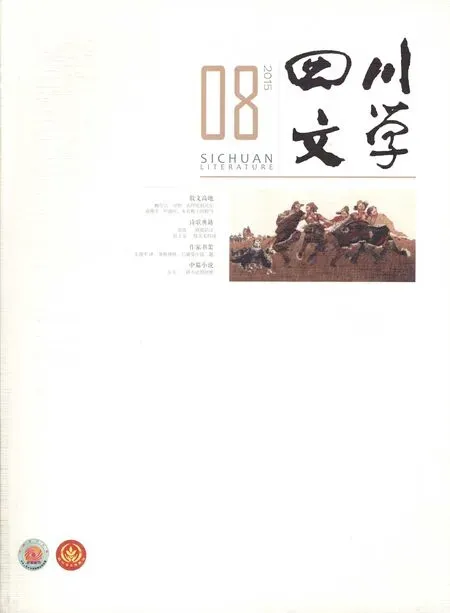寧肯:藏地秘密時光的漫游者
撰文/葛筱強
寧肯:藏地秘密時光的漫游者
撰文/葛筱強
秋天不僅僅是一個適合安靜閱讀的季節,也是思念常起的季節。比如在清晨或黃昏里散步,忽而會有一片落葉觸摸到你的頭頂或掌心,就會讓你心弦一撥,讓你想起某個夜晚閃閃發光的詞語,或居于遙遠之地的、燈火一般的舊朋老友。譬如此刻,我從逼仄的街巷里穿行之后,在長久的閱讀之后,眼望著窗外散亂飄零的樹葉,忽然憶起和作家寧肯的一些交往,并開始重新翻讀他的幾部散文和小說。
那是1999年7月,在散文作家葦岸去世兩個月后,我第一次來到北京,通過詩人黑大春,我得以與寧肯相識。彼時寧肯雖在年輕時發表過詩歌和小說,但尚未暴得大名,供職于《中國環境報》社,主持副刊工作。而他此前的成績和經歷更令我驚訝和嘆服。他大學畢業后主動去西藏工作兩年,回京后在報社下設的廣告公司當經理并取得驕人成績。在別人眼中已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成功弄潮兒時,他卻交出公司的車鑰匙和一切俗塵雜事,沉潛于自己的夢想之中,重新開始文學創作,并寫出了《沉默的彼岸》這一新散文領域中的扛鼎之作,發在云南的《大家》上。為此,作家葦岸還專門寫了一封題為《藝術家的傾向——致友人書》的信刊發在報紙上,和寧肯暢談了對新散文的看法和認識。稍后的2002年,我遠游內蒙后在返回東北時,
途經北京,寧肯不僅攜妻女請我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還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版的長篇小說《蒙面之城》,正是這部作品,讓寧肯獲了諸多實至名歸的榮譽,如老舍文學獎。也因為這部小說,寧肯的工作也有變動,從《中國環境報》調到《十月》文學雜志社任副主編。
《蒙面之城》的問世,對于寧肯,無論是哪個角度來說它的重要性都不過分。作為中篇小說《青銅時代》的升級擴容版,寧肯最大的體驗是“在三年的寫作中,我恍如隔世,身非是我,忘記一切,幾乎過著一種飛翔的生活”,寫完它,就覺得自己“一下子老了,一切都在離我而去”,覺得“像是快要走不動的人”,“我與這個世界已經無關,好像已經寫盡了某種東西。”《蒙面之城》最早發于新浪網,是一部關于愛與生命的小說,作品以近乎音樂的四個聲部描述了一個叫做馬格的年輕人七年的人生經歷,展現出北京、秦嶺、西藏、深圳等截然不同的地域生活畫卷,涉及了原始藝術、詩歌、商業、地下音樂等領域。在這部小說里,寧肯以其出色的才華創建了一座屬于自己的無所不包的“城市”,“它所展示的生活場景的廣度、時代問題的深度、地域空間的跨度、哲理思考的力度、情感體驗的濃度都是網絡文學中罕見的,它提供了20世紀中國小說中一些尖銳或異質的‘人類的內分泌物’(福克納語)。”(袁毅《通往自由的途中》)
在這本書中,最令我心動的,仍是關于主人公在西藏的種種經歷,以及作家關于西藏的傾心描述與抒寫。在這部小說里,西藏,是主人公精神起跑的“飛地”,是其人格與精神得到凈化與升華的煉金容器。作家以平靜克制的敘說語調,在描寫了西藏碩大壯美的自然景觀的同時,也完成了小說主人公心靈波瀾狂卷的涅槃:
“他翻過那道山。遙遠的牙齒般的地平線,是牙齒般銀色的雪峰。雪峰之下,山脈與大地裁出一角蔚藍色的天。不,那不是天,是水。湖水掛在天邊,僅能看到湖的一角,以為是天。太遠了。不可能走到湖邊,但他無法停住腳步。那湖仿佛一種宿命……他幡然醒悟,立刻掉頭——這應是動物的直覺,人就得思考。”
這些年來,我雖然與寧肯聯系得很少,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中斷了聯系,這主要緣于我個人的性格使然。因為我覺得,寧肯的創作已抵達了某種高度,他獲得了塵世的名聲(雖然這名聲與他真正的創作成績仍有差距),我已不便和他主動親近,給他添任何麻煩,即使我深知他為人的真誠與胸懷的寬廣。他這幾年出版的小說《環形女人》、《沉默之門》和散文集《說吧,西藏》、《大師的慈悲》,我都在第一時間買來并認真地閱讀,我覺得這樣最好,喜歡一個作家,認認真真地閱讀他的作品就行了,這是對作家最高的敬意。
波蘭詩人米沃什在其《詩的見證》一書說:“詩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寫的羊皮紙文獻,如果適當破譯,將提供有關其時代的證詞。”在我看來,寧肯截至目前的所有寫作,都是在為其短暫的西藏生活提供終將跟隨一生的精神活動的證詞。用他自己的話說:“人的任何一次表面經歷事實上都不過是內心經歷的冰山一角。有人輕視內心,而一個輕視內心生活的人顯然是一個不完整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以他的散文為例,無論是他早期的《一條河的兩岸》、《西藏日記》,還是近年的《沉默的彼岸》、《喜馬拉雅隨筆》,我們會發現,兩年的西藏生活,風景,人物,雪水一樣自然的磨礪,鷹一樣神性地沉思,都融匯為寧肯血液里日夜奔流的回望,并最終在他的骨骼里結晶為閃閃發光的硬核,在他自己不知不覺的修煉中,甚至成為佛教中的舍利,穿透時空的重重帷幔,令我們望而起敬,彰顯出遺世獨行的精神加持。直到今天,我還清晰地記得2002年在寧肯家中,他為我朗讀散文《藏歌》的情景,語言是純凈的藏藍色,聲音是低緩的風琴,二者完美地結合為一種震撼和籠罩:
“寂靜的原野是可以聆聽的,唯其寂靜才可聆聽。一條彎曲的河流,同樣是一支優美的歌,倘河上有成群的野鴿子,河水就會變成豎琴。牧場和村莊也一樣,并不需風的傳送,空氣中便會波動著某種遙遠的、類似伴唱的和聲。”
如果說這樣的靜思與敘述是漸合的暮色,那么寧肯后來的越來越闊大的敞開的言說則是從地表隆起的黎明。這個“被西藏囚禁起來”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被時間囚禁起來”的人,不僅為西藏所塑造,也在以自己獨特的虔誠之心同步塑造著只屬于他的西藏,他的步履越來越沉穩,他的目光越來越澄澈,他的文字越來越像暗夜中的燈火,在拂掉我們內心灰塵的同時,
也凸顯出漢語純粹的光芒:
“冬天,依然溫暖,陽光強烈,但植物還是回到了土地。冬天漫長,天空簡明,自然界安靜。一場雪降臨,兩三天融化。河岸上殘雪點點。殘雪聚集著陽光,燃燒自己,也點燃了陽光。”(《一條河的兩岸·冬天》)
2010年6月,時在北京魯院培訓的海南作家趙瑜,因與寧肯同期學習,便將一冊寧肯的新著《天·藏》簽名本寄我。我興奮地發現,在這本書里,寧肯不負自己的多年沉潛與思索,也不負眾人所盼,終于寫出了一個足可以屹立于精神世界的,不同于諸多關于西藏文本的自己心中的西藏。他在談關于這部小說的創作時說:
“我的寫作不是講述一個人的故事,而是講述一個人的存在,呈現一個人的故事是相對容易的,呈現一個人的存在幾乎是不可能的。我還說道:西藏給人的感覺,更多時候像音樂一樣,是抽象的,訴諸感覺的,非敘事的。兩者概括起來可稱為‘存在與音樂’。這對我是兩個關鍵性的東西,它們涉及我對西藏總體的概括,任何針對西藏的寫作都不該脫離這兩樣事物。至于故事,敘事,它們只能處于‘存在與音樂’之下,以致我多少有點否定敘事的傾向。”
上海批評家程德培在評價《天·藏》時的說法更是深契寧肯之心,也道破了作家創作此書的真正目的、文本特點和價值所在:“《天·藏》的敘述者是一位形而上的思考者,他聰明而饒舌,給我們講述的卻是沉默的內涵;他處理過去仿佛它就是現在,處理那些遠離我們日常生活的故事,好像它就在眼前。對于寧肯來說‘空間’總是慷慨仁慈的,而‘時間’總是一種不說的情況。小說力圖向我們展示一種文化的全貌,這種展示既面向我們,也面向與世隔絕的人。”
而實際上,我閱讀《天·藏》的最大感受是,在寧肯眼中,存在是巨大的,它包含一切,又遠遠大于一切,“包含了故事,又遠遠大于故事”,單一的線性時間根本無法容納它,表達它,映證它。存在是多維的,有無數的入口,也有無數的出口,是迷宮,是博爾赫斯筆底“小徑分岔的花園”。這讓我想起勒維爾與里卡爾的那本對話集《和尚與哲學家》,在幾近繁復沉重如黑夜般的長談之后,和尚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要過一種有質量的生存的惟一方法,就是給予生存以一種內在意義;而給予它一種內在意義的惟一方法,則是認識并改造我們的精神。”如果說“經驗就是道路”,那么,關于西藏隱秘的個體經驗,就是寧肯用一生來行進的創作道路,對于寧肯來說,經驗帶來血液的沸騰,創作則帶來靈魂的安靜。
在我看來,之于西藏,不管是神秘的,還是自然的,或者是歷史的,它既是《蒙面之城》中主人公馬格的“精神飛地”,也是《天·藏》里主人公王摩詰的“靈魂故鄉”。這個“精神飛地”和“靈魂故鄉”既是馬格和王摩詰的,說到底,我倒覺得,它更是作家寧肯自己的。如果說西藏在無言中擁有著立體的秘密時光,寧肯無疑就是這秘密時光中最優異的漫游者、沉思者和傾訴者,因為他用自己的心靈之眼記錄了多維度的西藏,也用哲學之眼和詩性之筆觀照和點燃了跨越時空的、普世意義上的西藏。
時間是一條奔流不息的大河,河面看似平靜如鏡,但河底之光卻如箭疾飛。這篇較為冗長的文章斷斷續續地寫了三年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創造力旺盛的寧肯,幾年來一直新著不斷,時有讓我驚喜甚至興奮異常的作品問世。隨著閱讀的不斷跟蹤與深入,我對寧肯的期待也越來越大,越來越迫切。2014年11月,寧肯同時推出了他的兩本書,一本為長篇小說《三個三重奏》(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另一本為中短篇小說集《詞與物》(河南文藝出版社,此書列“名家·最意味小說”叢書)。這兩本書公開發行后,我立即從網上先后購來。在這兩本新著中,我不僅閱讀到了寧肯血液里一直流淌的關于西藏的精神延續,比如《巖畫》和《維格拉姆》,更讀到了他在小說創作中對新題材新領域的探索與開掘,在這方面,不僅有意味雋永如風鈴、結構精致如銀器的《詞與物》《死于某年》《我在海邊等一本書》等中短篇小說讓我迷醉低徊,特別是他用兩年時間潛心創作的長篇小說《三個三重奏》,更是讓我眼前“忽“地一亮。這部長篇雖然將筆尖伸到了貪污腐敗的領域,卻又并未落入通俗官場小說的窠臼,寧肯以穩健而又先鋒的手法,采取身份置換的敘述模式與架構,塑造了一個讀書人身份的敘述者來講述官場,這個敘述者服務的是文本主題思想,他對這個陌生世界自然有自己視角下的人性關切和思考。有了這種方式,也就拋開了一般官場小說的樣式,進入了純文學的機理,使這部長篇小說基本實現了揭示人性的初衷,把人的豐富性體現出來,交給讀者一個非常完整的人。讀完這部長篇,讓我深深地察覺到,寧肯在西藏這個巨大的精神停機坪上真的是飛得太高,也太過眩目了。之于這部長篇小說,評論家陳曉明說:“寧肯是當代小說的‘刺客’,他太特殊了,他用刀雕刻了我們的骨髓,那種痛感,是寧肯的,更是我們的,《三個三重奏》以音樂般的刀法,再度雕刻了我們的骨髓。”我以為此語是對寧肯小說的結構藝術與語言藝術切中肯綮的批點。而寧肯自己關于這部長篇小說在結構上的技法闡釋是,“三個三重奏,復雜的交集跳宕后,又舒緩地各自流淌了,如三條河流交匯激蕩,如數控的音樂之水。但是,不能太久了,之后必須分道揚鑣。而再次交集、激蕩是必然的,因為一條大河絕不僅僅是自己,而是多條,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多部。”在接受新浪讀書的采訪中,他更為明晰地表達出這樣的,關于長篇小說的創作體會與觀點:“長篇小說是一口長氣,要慢慢吐,邊吐還要邊含著,邊聚氣。事實上應該是吐得少,越聚越多,越聚越飽滿,整個氣息差不多相當于太極。也就是說長篇小說要壓著寫,對于太精彩的情節要節制,要峰回路轉,不能孤注一擲攻取山頭,力氣用盡就會形成小說的斷氣,長篇小說的氣一定是連著的,看似到山峰了又下去了,再慢慢起,又到了,更高了,但遠不是山峰。這一切都要有一個全局意識,總體控制,長篇小說是復合結構藝術,是建筑藝術,有這樣的意識把握起氣息與節奏應該不難。”
如果說寧肯的中短篇小說有著讓我屏住呼吸的美,那么,他的長篇小說緩慢而強大的推進力量則讓我的呼
吸不能自制,只能跟隨著他的敘述時而緊張,時而平緩,時而要停頓下來向遠方眺望,陷入某種游離的沉思。就個人的閱讀胃口來說,我一直喜歡寧肯在小說敘述與鋪排中那種看似閑淡而又恰到好處的“自言自語”,這種“自語”, 有時以小說主人公的面目出現,有時直接就是作家自己的強力介入。這些碎片式的“自語”,有哲思,有詩意(雖然寧肯在一次訪談中提到詩意對小說敘述的一些損害,他說:“詩人的結構意識不亞于小說家,在對人的幻覺認識上有過之,然而在具體的敘事行為和敘事意識上詩人往往缺乏耐心,這是詩人寫小說最大的障礙。跨越這個障礙非常難,很多時候詩的習慣總是在干擾敘述,甚至把你引到誤區。”),但這些“方向不明的敘事,反而是自然的、原生態的,如同沼澤自身的魅力。”這些延宕之筆,既增強了閱讀的趣味與吸引力,也讓人感受到一種類似電影中旁白的通透舒爽,甚至直指人物內心世界與靈魂深處,為小說敘事與情節的展開與深入起到回環上升的旋梯作用。這些延宕之筆,經常讓我反復品咀,甚至是流連不前。比如在短篇小說《死于某年》中,他借人物之口寫道:
“是的,我最近總是想一些舊人、舊事,很平靜,很有味道。我可能老了,但如果老了是這樣也完全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說很幸福。現在我有一種罕見的與時間同步的感覺,年輕時可沒這種感覺,年輕時不是覺得時間快了,就是慢了,總之總是與時間不合拍,現在沒什么不合拍的,我就是時間,時間就是我。”
就目前寧肯的創作成就與勢頭來看,我可以毫不懷疑地說,寧肯確乎為一個復合型的、既有創造雄心也極具創造力的作家,他體內所蘊藏的創作潛力,是詩性的語言張力、智性的思辨活力、神性的冥想魔力以及收放自如的結構控制力的共生并存,四者之間互為源頭活水,也互為山峰呼應,以此形成了寧肯有別于其他作家的自己的藝術穹頂,這個穹頂,因他的存在與設計而顯得風姿卓特,超拔不群。用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莫言的話說:“寧肯是一位有著非凡勇氣與才華的作家,他的作品將尖銳的政治批評與深刻的人性解剖結合在一起,將現實的無奈生活與對理想人生境界的苦苦追求融為一體。但更為重要的是,他用豐沛的想象力和博取眾采的胸懷,創作了屬于他自己的故事和文體。”
【征途帆影】賀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