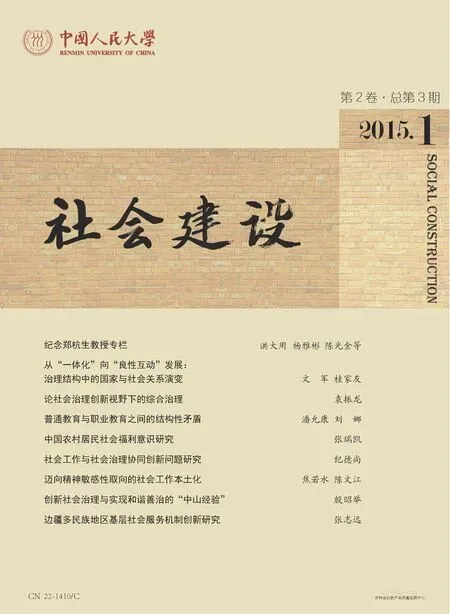中國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樣調(diào)查
張瑞凱
?
中國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樣調(diào)查
張瑞凱
摘 要:社會福利意識是影響一個國家社會福利體系效能的直接因素。本研究顯示,我國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福利意識呈現(xiàn)混合福利偏自由主義的傾向,更多地將提高自身福利水平寄希望于自己的勤勞努力和聰明才干上,認為個人、家庭、工作單位、村集體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為重要;在福利分配原則上更傾向于“選擇性”這一原則;在供給機制上,更贊同社會福利領(lǐng)域采用市場機制分配資源。就影響其福利意識的因素,研究顯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深深影響著該群體的福利意識;個體的人力資本因素對其選擇偏向自由主義傾向發(fā)揮了重要影響。
關(guān)鍵詞: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福利混合主義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福利研究中的“文化轉(zhuǎn)向”,福利文化在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引起研究者重視。福利意識作為福利文化的集中體現(xiàn),更是得到了學術(shù)界的重視。學術(shù)界認為,社會福利意識是影響社會福利體系效能的直接因素,在塑造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體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有學者明確提出“影響一個國家做出何種福利選擇和安排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此前很多研究中辯稱的政體類型或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而更多的是國家精英和普通民眾對彼此的看法和期望,以及一國當時對國家和市場職責劃分的主流態(tài)度”①蘇黛瑞:《社會救助的根源:對福利體制,目標與方法之差異的初步思考》,《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1)。,因此,美國會建構(gòu)個人主義取向的社會福利制度,英國會在二戰(zhàn)之后選擇建設(shè)“福利國家”。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居住在鄉(xiāng)村的人口為6.7億,占全國總?cè)丝诘?0.32%,其中外出務(wù)工人員達2.2億,異地務(wù)工達1.3億。如此大規(guī)模群體的福利狀態(tài)直接關(guān)系到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剖析這一群體關(guān)于社會福利最根本的價值理念以及影響因素,對于有效安排福利制度、改進政策效果,具有突出的實踐和理論意義。
一、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及其操作化
(一)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的界定
關(guān)于什么是“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學術(shù)界的界定多元不一。王思斌認為,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是指一個社會或群體所具有的關(guān)于社會福利的價值體系,包括如何看待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的責任觀、獲得社會福利的正當性等問題,其是個人對社會福利定型化的思考模式與觀念,一旦形成再促使其改變是非常緩慢與不易的。社會福利的意識形態(tài)不但能引導個人審視與評判社會福利的現(xiàn)況,且能夠作為社會福利未來發(fā)展的參考依據(jù)。①王思斌:《底層貧弱群體接受幫助行為的理論分析》,載王思斌主編:《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第11頁。臺灣學者林萬億認為福利意識形態(tài)是指一組對福利的意見、態(tài)度、價值,以及一種關(guān)于人與社會的思考方式。②林萬億:《影響臺灣民眾社會福利態(tài)度的因素》,《臺灣大學社會學刊》,1997(25)。謝美娥在林萬億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對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進行了明確界定,即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是影響社會福利發(fā)展的一套邏輯性概念組合,也就是社會大眾對于社會福利的意見、信仰、態(tài)度和價值的組合體,用以思考人與社會福利的關(guān)系,可以引導認知社會福利,提供對社會福利現(xiàn)況評估和未來社會福利發(fā)展的概念組合。③謝美娥:《大臺北地區(qū)一般民眾與低收入民眾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福利需求之比較研究》,《臺灣大學社會學刊》,1995(24)。呂寶靜則從國家與福利的角度來界定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認為“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是一組共享的社會福利理念,其用來解釋與批判政策。易言之為一組對福利國家的構(gòu)思。通常這組社會福利的意識形態(tài)指涉國家對社會福利介入的深度與廣度,而其形成受到國家的組成、文化以及政治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與發(fā)展的影響。”④呂寶靜:《社會福利的意識形態(tài)》,載《臺灣地區(qū)社會意向調(diào)查八十年六月專題調(diào)查報告》,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
綜上,雖然學術(shù)界對福利意識形態(tài)的界定存在分歧,但都強調(diào)福利意識形態(tài)的基礎(chǔ)性、穩(wěn)定性和指引性。基礎(chǔ)性指社會福利意識是一個社會或群體所具有的關(guān)于社會福利的價值體系,包括如何看待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的責任觀、獲得社會福利的正當性等問題。穩(wěn)定性指其一旦形成就不易改變。指引性指社會福利意識不但能引導個人審視與評判社會福利的現(xiàn)況,且能夠作為社會福利未來發(fā)展的參考依據(jù)。本研究認為,社會福利意識是社會成員關(guān)于獲得社會福利的正當性、福利產(chǎn)品的分配原則、福利產(chǎn)品的供給主體、供給方式等方面定型化的意見和態(tài)度。
(二)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的操作化
系統(tǒng)梳理人類社會福利實踐中產(chǎn)生和形成的各種思想、意識、態(tài)度等,不難發(fā)現(xiàn),其討論的核心議題可歸納為五個“W、”一個“H”:為什么要提供福利(why)? 誰來提供福利(who)? 給誰提供福利(whom)?提供什么內(nèi)容的福利(what)?社會福利在整個社會中的定位(where)?怎樣提供福利(how)?⑤畢天云:《社會福利場域的慣習——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實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第3頁。考慮到“提供什么內(nèi)容的福利”受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歷史文化傳統(tǒng)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內(nèi)容涉及領(lǐng)域過多,本研究沒有將其列為測量福利意識的維度。就其他五個維度,借鑒澳門學者賴偉良、臺灣學者林萬億等人的操作化語句,本研究構(gòu)建了由社會福利權(quán)認知、社會福利功能定位、福利分配原則偏好、福利供給主體偏好、福利提供機制偏好五個維度組成的“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測量量表”(見表1)。

表1 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測量量表

續(xù)表
該量表總計包含11條操作性語句,讓受訪者選擇回答:“十分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分別記為5、4、3、2、1分。
本研究在正式調(diào)查前選擇了30名農(nóng)村居民進行重復測試(間隔一周),根據(jù)兩次測量結(jié)果計算重測系數(shù)為0.95,顯示該量表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就量表的效度,本研究使用因子分析對30名農(nóng)村居民測試結(jié)果進行結(jié)構(gòu)效度分析,將12項測試語句正交旋轉(zhuǎn),11個陳述語句可以綜合為3個因子,其因子負荷量大于0.756,累積方差貢獻率為49.07%,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gòu)效度。
(三)研究方法及調(diào)查對象基本情況
鑒于現(xiàn)實條件限制,本次調(diào)查采取非概率抽樣中的判斷抽樣方法,從北京市農(nóng)村戶籍人口多的區(qū)縣中抽取了房山、門頭溝、延慶三個區(qū)縣進行了調(diào)查。本次調(diào)查共發(fā)放問卷380份,回收380份,經(jīng)過兩步篩選,即邏輯關(guān)系設(shè)定相關(guān)的未填項標準,及以性別、年齡、社會身份等基本變量篩選,有效問卷340份,有效回收率達89.5%。

表2 被訪者年齡分組
從年齡結(jié)構(gòu)來看,本次調(diào)查對象平均年齡為36歲,年齡最小為16歲,最大為81歲。其中,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nóng)民工占了樣本量的42.9%。從性別結(jié)構(gòu)看,女性占了55.3%,男性占了44.7%,女性高于男性。在民族構(gòu)成上,本次調(diào)查的農(nóng)村居民主要以漢族、回族、滿族為主,其中漢族比例最高,占了95.5%,回族、滿族分別占了1.2%、3.3%。在文化程度上,被訪農(nóng)村居民的文化程度以高中(包括中專、職高、中技)為主,占22.4%;其次是大專學歷(20.9%),大學本科學歷排在第三位(20.4%),初中學歷排在第四位(19.1%)。
二、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現(xiàn)狀、群體分化及影響因素
(一)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現(xiàn)狀

表3 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量表各指標得分

表4 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總量表、分量表得分
1.對社會福利權(quán)的認知。福利獲得的正當性理由經(jīng)歷了“剩余觀”、“恩賜觀”、“解決社會問題、實現(xiàn)公共利益”等觀念變化。自從馬歇爾提出“公民權(quán)”的概念后,“享受社會福利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quán)利”得到了不同國家的普遍認可。因此,本研究將“福利獲得是一項基本的公民權(quán)”、“領(lǐng)取政府救濟金并不是代表自己失敗”作為福利獲得正當性理由的操作化語句。調(diào)查顯示,“獲得社會福利是每位公民的權(quán)利”這一語句的平均得分僅為2分,只有7.4%的被訪者表示同意這一觀點,高達79.2%的被訪者不認同這一觀點。就“領(lǐng)取政府救濟金并不是代表自己失敗”這一語句的得分也僅為2.08,高達73.9%的被訪者不認同這一觀點。這一結(jié)果非常明確地顯示出農(nóng)村居民不認為福利是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的社會權(quán)利。
2.對社會福利體系地位的態(tài)度。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福利政策淹沒在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的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之中,成為實施國家經(jīng)濟政策的輔助工具。直到進入21世紀,伴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轉(zhuǎn)型、和諧社會目標的確立,社會福利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才開始受到重視。在農(nóng)村居民心中,社會福利制度占據(jù)著什么樣的位置?調(diào)查顯示,“政府應該首先重視經(jīng)濟政策,然后才是社會福利政策”這一語句的平均得分為3.41,高達44.7%的被訪者贊同這一觀點,有39.9%的受訪者選擇了“中立”,還有15.4%的被訪者明確表示“不同意”。由此可見,農(nóng)村居民對社會福利政策在國家運行中地位的判斷依然處在較為弱勢的位置。當問他們對“政府應該有限度地提供社會福利,以免出現(xiàn)養(yǎng)懶漢現(xiàn)象”這一語句的態(tài)度時,其平均得分為3.9,有72.3%的受訪者同意這一看法。從這一指標反映的情況看,我國農(nóng)村居民認為經(jīng)濟政策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認為社會福利政策是促進經(jīng)濟增長的一種輔助工作。并且,他們不接受龐大規(guī)模的福利制度,擔心這類體制會對個人的自助能力造成影響。
3.福利供給對象偏好。對于福利供給對象的選擇標準上,本研究主要圍繞普遍性原則、選擇性原則兩個主軸進行設(shè)計。選擇性原則強調(diào)對社會成員進行甄別,那些收入低、患病、傷殘、喪失工作能力等弱勢群體才能享受福利服務(wù)。普遍性原則認為享有福利是全體公民的權(quán)利,強調(diào)應該一視同仁地為全部有特定需要的人(甚至全體國民)提供服務(wù)。對于普遍性原則,只有3.9%的受訪者同意“政府應該發(fā)展更大規(guī)模的福利服務(wù),使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得到較好保障。”這一看法(平均得分為1.94),高達78.8%的被訪者明確不贊同這一觀點。就代表選擇性原則的操作語句“政府的社會福利應當只提供給那些生活最困難的人”(平均得分為3.9),高達59%的被訪者表示同意,表示不同意的被訪者僅占17.1%。從統(tǒng)計結(jié)果來看,在福利對象上,農(nóng)民居民更傾向于選擇性這一原則。
4.對福利供給主體的偏好。“由誰提供社會福利”是社會福利運行過程中至關(guān)重要的環(huán)節(jié)。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在社會福利供給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用越來越突出,由私營企業(yè)、雇主、慈善團體、志愿機構(gòu)等主體組成的私人系統(tǒng)的作用被長期忽視,甚至于“國家 ( 依托單位、集體) 是社會福利的唯一主體”①李迎生:《國家、市場與社會政策:中國社會政策發(fā)展歷程的反思與前瞻》,《社會科學》,2012(9)。。20世紀90年代之后,福利供給主體的類型和數(shù)量不斷增加,并日益呈現(xiàn)出由政府、初級群體(包括家庭、親屬、朋友、鄰里等)、就業(yè)組織、互助組織、志愿者組織、商業(yè)性服務(wù)機構(gòu)、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組成的多元化趨勢。②畢天云:《社會福利供給系統(tǒng)的要素分析》,《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5)。那么,中國農(nóng)村居民在福利供給主體的選擇上有何偏好呢?當問及志愿體系在福利供給中的角色時,有22.7%的受訪者不同意“社會福利主要應由社會公益組織提供,而不是政府”(平均得分為3.26),持中立意見者達37.7%,表示同意者占了39.6%。對于工作單位在福利供給中的角色,有49.1%的被訪者同意“福利最主要應由鄉(xiāng)村集體/工作單位提供” (平均得分為3.45),持中立意見者占34.7%,表示反對的占16.2%。就家庭和親屬的責任,“當個人遇到問題時,親屬是最有責任提供幫助的”這一語句的得分為3.62,高達55.8%的被訪者表示認同這一觀點,有33%的被訪者持中立立場,僅有11.3%的被訪者表示反對。就個人的責任,“每個人應該為自己的生活負起最大責任”的平均得分為4.14,高達82.3%的被訪者表示認同,有15.6%的被訪者持中立立場,僅有2.1%的被訪者表示反對。
由此可見,在政府、第三部門、工作單位或村集體、家庭、個人這些重要的福利供給主體的排序上,在農(nóng)村居民看來,個人、家庭、工作單位、村集體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為重要,政府的福利角色比慈善團體及志愿機構(gòu)重要。其中,個人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家庭,工作單位、村集體排在第三位。
5.福利供給方式偏好。社會福利供給方式即資源落實到受益者的機制,直接影響著社會福利體系的效果。國內(nèi)外的實踐顯示,由政府直接供給或運營、通過市場機制供給是兩種主要機制。本研究對這一維度操作化時主要強調(diào)“市場機制供給”這一方式。“在提供社會福利時,政府應該向有錢的人收取服務(wù)成本”這一語句的得分為3.58(滿分為5分),有47.5%的被訪者表示非常同意這一方式,有30.4%的被訪者表示中立,表示不同意的僅占了13.4%。這顯示農(nóng)村居民比較贊同社會福利領(lǐng)域采用市場機制分配資源。
(二)農(nóng)村居民福利意識的群體分化
近年來,農(nóng)村居民的分化已然成為事實。不同農(nóng)民群體在職業(yè)特征、收入狀況、年齡結(jié)構(gòu)等方面呈現(xiàn)出不同的發(fā)展趨勢,產(chǎn)生了不同的社會保障需求。以11個描述語句為變量基礎(chǔ),對農(nóng)村居民福利意識量表得分進行聚類分析,可將其區(qū)分為意識導向特征互異的3個分群體。①利用判別分析法檢驗聚類結(jié)果,340個樣本中290個被正確判別,正確判別率為85.3%,聚類效果較好。根據(jù)每一類群體量表得分的特征,可將農(nóng)村居民分為三個群體。
第一類群體高度反對普遍福利權(quán),在“獲得社會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權(quán)利”得分僅為1.65,在三個群體中得分最低。在社會福利地位這一維度的兩個表述上,其得分分別為4分、4.23分,顯示他們非常不認同福利制度占據(jù)重要位置。在福利覆蓋對象維度上,他們強烈反對福利分配的普遍性原則,認為福利只能提供給特定困難人群。就福利供給主體,他們高度贊成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認為工作單位、家庭等主體的重要性高于政府。就福利供給機制,他們高度贊成市場機制,得分高達4.27。根據(jù)這一群體的福利意識特點,本研究將之命名為“自由主義型”,占樣本總量的30.7%。

表5 第一類群體的量表得分
相對于第一類群體,第二類群體非常重視公民普遍的福利權(quán)利,在“獲得社會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權(quán)利”上的得分為3.1573,遠遠高于第一群體。在福利分配原則上,該群體更傾向于普遍性原則;在福利供給主體上,其對政府的期待高于工作單位、親屬等;在福利分配機制上,其不太贊同市場化這一機制。根據(jù)這一群體福利意識的特征,本研究將之命名為“國家干預主義類型”,占樣本總量的24.2%。

表6 第二類群體的量表得分
第三類群體在福利意識的維度上的得分與第一類群體很相似,他們也反對“社會福利是每一位公民的權(quán)利”這一觀點,但是反對程度低于第一類群體。就福利對象偏好,他們贊同福利應當只提供給那些生活困難的人,但同時也贊同政府發(fā)展更大規(guī)模的福利服務(wù)、使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得到較好的保障。就福利供給對象,他們同樣認為個人、家庭、工作單位承擔主要責任,但對政府承擔責任期待增加,高于第一類群體。該類人群既重視社會公平,也強調(diào)個人責任,強調(diào)服務(wù)成本的合理分擔,本研究將之命名為“福利混合主義”,占樣本總量的45.1%。

表7 第三類群體的量表得分

續(xù)表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認為,我國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福利意識可分為三種類型,占主導地位的是混合福利偏自由主義傾向,即其更多地將提高自身福利水平寄希望于自己的勤勞努力和聰明才干上,認為個人、家庭、工作單位、村集體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為重要。他們不認為福利是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的社會權(quán)利,因此,在福利分配原則上雖然同時支持普遍性及選擇性的分配原則,但更傾向于“選擇性”這一原則,即福利只提供給特別困難人群。在供給機制上,更贊同社會福利領(lǐng)域采用市場機制分配資源。對于社會福利制度的地位,他們認為是從屬于經(jīng)濟政策的。
三、影響農(nóng)村居民福利意識的因素
蒂特馬斯指出,社會政策(即社會福利制度)不是處于真空狀態(tài)之中,它總是置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在研究別國的福利制度時,我們見到它所反映該社會的主導文化和政治的特征”①蒂特馬斯:《社會政策十講》,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第172頁。。因此,人們在回答和解決“為何提供福利”、“福利應該給誰”等五個問題時,文化的作用會一再地體現(xiàn)出來,并進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福利模式。②畢天云:《福利文化引論》,《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因此,本研究將文化因素作為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在問卷中的操作化語句為“遇到困境時會向誰尋求幫助”、“對貧富差距的認知”、“個人遇到問題時如何解釋和歸因”。
除了文化傳統(tǒng),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總是會受到一個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主導價值觀念、權(quán)利教育的普及程度等因素影響。對于社會結(jié)構(gòu)這一影響因素,本研究主要從農(nóng)村居民對已參加的社會福利制度效果的評價、作為現(xiàn)代公民的社會參與意識兩個維度進行研究。問卷中,體現(xiàn)社會福利制度效果評價的題目是:“對養(yǎng)老保險效果的評價”、“對醫(yī)療保險效果的評價”、“對工傷保險效果的評價”、“對失業(yè)保險效果的評價”。測量公民意識的題目為:“如果有機會參加縣長、區(qū)長的直接選舉,我一定會積極參加投票”、“我了解我們社區(qū)的事情,所以我有權(quán)參與社區(qū)的事務(wù)。”(選項為:“十分同意”、“同意”、 “不同意”和“十分不同意”,分別記為4、3、2、1分)。
從個體層次看,一個人的社會福利意識水平還會受其年齡、教育程度、身體健康程度、收入等個體人力資本、個人生活中客觀風險存在情況、對未來風險的感知和評價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在問卷中,體現(xiàn)個人生活中客觀風險存在情況的題目由“過去3年內(nèi)的失業(yè)次數(shù)”構(gòu)成。對未來風險大小的評價操作化為“對失業(yè)的擔心程度”、“對未來養(yǎng)老的擔心程度”、“對生病后醫(yī)療費用的擔心程度”三個語句。
以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福利權(quán)認知、社會福利在整個社會中的定位、福利分配對象偏好、福利供給主體偏好、福利供給方式偏好為被解釋變量,以文化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個人因素(年齡、收入、文化程度、身體健康程度、客觀風險存在情況、對未來風險的感知和評價)為解釋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其中,Y 表示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福利意識分量表的得分;Xk表示解釋變量,包括;ε為未被解釋的殘差。

表8 回歸結(jié)果分析

續(xù)表
(一)對社會福利權(quán)的影響
回歸結(jié)果顯示,人力資本中文化程度越高的農(nóng)民,越不認同普遍福利權(quán)(標準回歸系數(shù)=-0.116 )。客觀風險存在情況中,失業(yè)次數(shù)越高(標準回歸系數(shù)=-0.100),越不認同普遍福利權(quán);主觀風險評估中,對未來失業(yè)擔心程度越低,越傾向不認同普遍福利權(quán)(標準回歸系數(shù)=-.058)。
就文化因素對社會福利權(quán)認知的影響,回歸結(jié)果顯示,越傾向于向家庭、親屬、朋友求助的農(nóng)村居民,越反對社會福利權(quán)(標準回歸系數(shù)=-0.073);越認同貧富差距是不公正的農(nóng)村居民,越認同普遍福利權(quán)(標準回歸系數(shù)=0.223);越傾向于將個人問題原因歸因于社會、政府的農(nóng)村居民,越認同普遍社會福利權(quán)(標準回歸系數(shù)=0.132)。
(二)對社會福利地位的影響
回歸結(jié)果顯示,個體因素和社會結(jié)構(gòu)因素對農(nóng)民居民關(guān)于社會福利地位認知的影響均不顯著,只有文化因素的影響顯著。具體來說,越傾向于向家庭求助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認同提高社會政策的地位(標準回歸系數(shù)=-.017);越傾向于向親屬求助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認同經(jīng)濟政策比社會政策重要(標準回歸系數(shù)=0.086)。越傾向于將個人問題歸因于社會、政府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提高社會政策的地位(標準回歸系數(shù)=-0.140)。越認同貧富差距是不公平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提高社會政策的地位(標準回歸系數(shù)=-0.205)。
(三)對福利對象選擇原則的影響
回歸結(jié)果顯示,社會結(jié)構(gòu)對福利對象選擇原則的影響不顯著。個體因素中,文化程度越高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選擇性標準(標準回歸系數(shù)=-0.098);客觀風險中失業(yè)次數(shù)越多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選擇型原則(標準回歸系數(shù)= -0.092);主觀風險中對失業(yè)擔心程度越低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普遍性原則(標準回歸系數(shù)=0.118 )。
文化因素中,越傾向于向家庭、親屬、朋友求助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選擇性原則(標準回歸系數(shù)=-.092 );越傾向于把個人問題歸因為社會、政策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認同普遍性原則(標準回歸系數(shù)=0.113);越認同貧富差距是不公平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選擇普遍性原則(標準回歸系數(shù)=0.189)。
(四)對福利供給主體選擇的影響
回歸結(jié)果顯示,社會結(jié)構(gòu)對社會福利供給主體選擇偏好的影響不顯著。個體因素中,人力資本、客觀風險的存在情況影響不顯著;對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選擇多元主體(標準回歸系數(shù)=0.160);主觀風險中,對失業(yè)、養(yǎng)老問題擔心程度越高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多元主體(標準回歸系數(shù)=0.114 、0.027);對醫(yī)療風險擔心程度越高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政府承擔主要責任(標準回歸系數(shù)=-0.095)。
文化因素中,越傾向于向政府求助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多元主體(標準回歸系數(shù)=0.108);越傾向于把社會問題歸因于社會、政府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政府作為福利主體(標準回歸系數(shù)=-0.258);越認同貧富差距是不公平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政府承擔主要責任(標準回歸系數(shù)=-0.133)。
(五)對福利供給方式的影響
回歸結(jié)果顯示,社會結(jié)構(gòu)對福利供給方式選擇的影響不顯著。個體因素中,文化程度越高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采用市場化機制進行福利供給(標準回歸系數(shù)=0.029);客觀風險中,收入越高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非市場化的供給機制(標準回歸系數(shù)=-.089*);失業(yè)次數(shù)越多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非市場化的供給機制(標準回歸系數(shù)=-0 .109*)。主觀風險中,對失業(yè)擔心程度越低的農(nóng)村居民(標準回歸系數(shù)=-0.126 ),越傾向非市場化的供給機制。
文化因素中,選擇政府作為求助對象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非市場化的供給機制(標準回歸系數(shù)=-0.133 );越傾向于把個人問題歸因為社會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非市場化的供給機制(標準回歸系數(shù)=-0.258);越認同貧富差距是不公平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非市場化的供給機制(標準回歸系數(shù)=-0.143)。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認為,對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的影響因素中,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最顯著。儒家的福利觀念傳統(tǒng),如強調(diào)依靠家庭而不是國家,強調(diào)自立、勤勞致富等觀念深深影響了農(nóng)村居民的福利意識,使得他們將提高自身福利水平寄希望于自己的勤勞努力和聰明才干上,認為個人、家庭、工作單位、村集體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為重要。樸素的公平觀又讓他們希望政府在增加社會公平、減少貧富差距方面發(fā)揮較大的作用。
農(nóng)村居民的個體因素中,個體人力資本、職業(yè)風險的影響顯著。文化程度越高者,越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善弱勢狀態(tài),越傾向于自由主義的福利觀;主觀上對未來失業(yè)風險擔心程度越低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自由主義的福利觀;客觀風險上失業(yè)次數(shù)越多的農(nóng)村居民越傾向于政府發(fā)揮主導作用的國家干預主義。
相對于前兩個影響因素,社會結(jié)構(gòu)因素對農(nóng)村居民的福利意識影響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政府出臺的關(guān)于農(nóng)村居民、農(nóng)民工的福利政策、制度尚未對農(nóng)村居民的生活帶來顯著的影響,進而暫時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福利觀。
四、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一)基本結(jié)論
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長期并行著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兩個流派。自由主義流派認為市場機制具有完美的自動均衡能力,強調(diào)社會成員個人對自己生活的責任,強調(diào)在福利提供方面?zhèn)€人的責任和市場作用的發(fā)揮,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當經(jīng)濟的“守夜人”。國家干預主義則主張由國家干預和參與社會經(jīng)濟活動,強調(diào)政府在應對社會風險發(fā)揮主要作用、強調(diào)自上而下地實行經(jīng)濟和社會改革,承擔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責任。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第三條道路”、福利多元主義、社會資本理論等新興社會福利理論的興起并逐漸獲得重視,社會福利領(lǐng)域不再片面強調(diào)市場或國家的單獨作用,而是開始強調(diào)市場、國家、家庭、民間組織等多元主體在抵御社會風險、增加社會福利中發(fā)揮作用。這就是說,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開始出現(xiàn)了一種介于國家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新的模式,這一利模式跨越左與右,兼容市場的靈活性與政府的保障性,強調(diào)福利供給的多元主體和公眾的參與,有學者稱這種福利意識為“福利混合主義”。

表9 中國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
綜合調(diào)查結(jié)果,可以看到,我國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福利意識呈現(xiàn)混合福利偏自由主義傾向。他們認為社會政策經(jīng)濟政策的附屬,對社會政策不太重視,不認為福利是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的社會權(quán)利;認為個人、家庭、工作單位、村集體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為重要,政府的福利角色比慈善團體及志愿機構(gòu)重要。其中,個人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家庭,工作單位、村集體排在第三位;他們同時支持普遍性及選擇性的分配原則,但更傾向于“選擇性”這一原則,即福利只提供給特別困難人群。他們贊同社會福利領(lǐng)域采用市場機制分配資源。
(二)對完善農(nóng)村社會福利制度的幾點建議
基于當前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及影響因素,本研究認為針對該群體的社會福利制度未來的發(fā)展需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提升政府責任,建構(gòu)基于農(nóng)村居民“公民”身份的“普惠型”福利制度。我國農(nóng)民的社會福利制度具有非常顯著的“自保障”特征。政府在福利政策制訂、福利經(jīng)費資助等方面承擔更為重要的角色,建構(gòu)基于農(nóng)村居民“公民”身份的“普惠型”福利制度,使農(nóng)村居民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基本福利保障。
(責任編輯:方舒)
□社會工作
第二,適應農(nóng)村居民混合福利偏自由主義傾向的社會福利意識特點,考慮傳統(tǒng)文化影響,將中國農(nóng)村以“自保障”為特征的鄉(xiāng)村互助福利和國家福利有機結(jié)合,促進農(nóng)村居民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在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下,長期以來,中國農(nóng)民的社會福利意識具有非常顯著的“自保障”特征,強調(diào)社會成員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包括家庭、社區(qū))去應對各種風險和意外,強調(diào)以家庭和社區(qū)等人際互動密切且能夠共同參與的地域共同體為場所,以互幫互助、互惠互濟為形式,以家庭、鄰里、朋友、親屬、社會性法團等構(gòu)成的支持性網(wǎng)絡(luò)為依托,以向生活困厄者提供緊缺資源和服務(wù)為核心,以向受助人群提供經(jīng)濟供給、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為宗旨,以規(guī)避化解居民的生產(chǎn)生活風險為歸宿①章長城、劉杰:《傳統(tǒng)保障的現(xiàn)代構(gòu)造與重塑》,《學習與實踐》,2006(5)。。而本次調(diào)查結(jié)果也顯示,我國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福利意識是混合福利偏自由主義傾向,在福利供給主體上,認為個人、家庭、工作單位、村集體在提供福利的角色上比政府更為重要。根據(jù)這一特點,當前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福利制度應在大力發(fā)展國家提供的普遍性保障基礎(chǔ)上,通過多種渠道弘揚、保持鄉(xiāng)村互助福利,并使其與國家保障相結(jié)合,從而能夠更加靈活、更加全面地保障農(nóng)村居民的生活質(zhì)量。
第三,探索農(nóng)村居民職業(yè)分化狀態(tài)下的職業(yè)福利,使其成為提升農(nóng)村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補充。職業(yè)福利是伴隨雇傭關(guān)系的產(chǎn)生而產(chǎn)生的一種福利形式,但是長期以來一直處在被忽視的地位,尤其是在西方福利國家興起之后更是一再被忽視,直到20世紀70年代福利國家財政危機出現(xiàn),才開始受到重視。在過去30多年間,以職業(yè)福利替補公共福利已成為西方福利國家改革和發(fā)展的重要趨勢,在保障員工生活質(zhì)量、應對生活風險方面發(fā)揮著越來越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后,農(nóng)民在職業(yè)分布、人力資本、收入結(jié)構(gòu)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尤其是職業(yè)方面的分化更是顯著。如有學者提出根據(jù)農(nóng)村居民從事的職業(yè)可以將其分為糧農(nóng)、經(jīng)濟作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大戶、農(nóng)業(yè)個體戶、非農(nóng)個體工商、農(nóng)民工等①秦雯:《農(nóng)民分化、農(nóng)地流轉(zhuǎn)與勞動力轉(zhuǎn)移行為》,《學術(shù)研究》,2012(7)。。本研究的研究結(jié)果也顯示,被訪農(nóng)村居民曾經(jīng)經(jīng)歷的失業(yè)次數(shù)和對未來失業(yè)的擔心程度都對其福利意識有顯著性影響。因此,探索、發(fā)展農(nóng)村居民職業(yè)分化狀態(tài)下的職業(yè)福利是未來農(nóng)村社會福利項目發(fā)展的重要方向。當然,在發(fā)展職業(yè)福利時,必須使其區(qū)別于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單位福利”。
第四,根據(jù)農(nóng)村居民外出務(wù)工家庭遷移的特點,探索以家庭為單位的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人員福利政策。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是每一個人生存、生活和發(fā)展的微觀環(huán)境。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國家清楚地認識到,家庭的發(fā)展在人口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應對社會風險時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因此,西方發(fā)達國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的發(fā)展,在強調(diào)家庭責任的同時紛紛采取了支持家庭或重返家庭的行動,試圖設(shè)計和實施以家庭為中心、以上游干預為導向的家庭政策與家庭服務(wù)②韓央迪:《家庭主義、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福利國家家庭政策的實踐與啟示》,載家庭發(fā)展司與中國人口學會聯(lián)合編輯:《家庭發(fā)展理論與實踐獲獎?wù)魑膮R編》,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3,第26頁。。國內(nèi)多項研究顯示,中國農(nóng)村居民外出務(wù)工的生活方式呈現(xiàn)“家庭整體流動”這一特點,因此,應綜合考慮外出務(wù)工農(nóng)村居民的家庭需要,以此為基礎(chǔ)構(gòu)建、調(diào)整、完善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人員福利政策。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asants ' Ideology of Social Welfare——Based on the Sample Investigation in Beijing
ZHANG Rui-kai
Abstract:Ideology of social welfare plays a direct rol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olicy.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peasants ' ideology of social welfare is close to the Welfare Pluralism. On one hand, they expect the government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welfar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believe that the working units,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should also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than the government. The peasants tend to “selectivity” and “market mechanism” in welfare distribution. Analyz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peasants' human capital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ir ideology.
Key words:peasant;ideology of social welfare; welfare pluralism
作者簡介:張瑞凱,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社會福利政策理論與應用、社會工作本土化。(北京,100102)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shè)中的社會政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