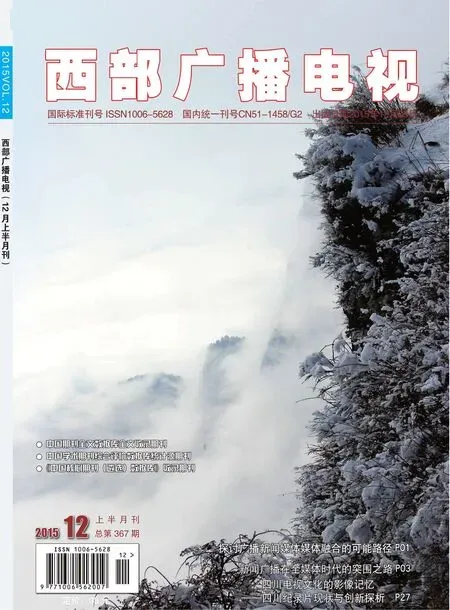民間技藝傳承人口述史田野實踐中的理性思考
王淑慧 楊東伶
民間技藝傳承人口述史田野實踐中的理性思考
王淑慧楊東伶
(作者單位:河北傳媒學院影視藝術學院)
非遺口述史實踐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訪談模式單一,采訪者與口述者缺少深入交流;對傳承人人生價值觀念、信仰、心靈以及情感對民藝創作的影響等深層次研究極少等。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可以通過社會、個人以及高校等渠道,來探討解決問題的措施。
口述史;民間技藝;理性思考
近些年來,應用口述史的方法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保護的研究日漸增多,應用口述史的方法加強非遺保護,進行田野作業的方法也引起了有關人士的重視,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是,在非遺口述史實踐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進行理性思考,并研究解決問題的對策,將有助于更好地推進口述史在非遺保護中以及在其他領域的開展。筆者主要通過對民間技藝傳承人口述史實踐過程中的問題進行分析,進而探索解決辦法。
1 民間技藝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必要性
口述史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的保護是一種很重要的方法,這與口述史自身的特點有關,與民間技藝傳承人的文化程度及民間技藝的獨特表現形式等都有很大的關系。
首先,一般民間技藝傳承人自身文化程度不高,這就使用口述史的方法保護民間技藝成為一種必要的方法。在過去,從事傳統工藝的工匠大多沒有機會受教育,雖然他們的作品能夠留傳下來,但是技術的傳承只能靠口耳相傳。在現代,有些技藝很少有人去學習,瀕臨滅絕的危險,通過書面表述這種方式來保留一些技藝資料還是比較困難的。所以,用口述史的方法去記錄和保護就更加迫切。
其次,有些民間技藝的表現形式決定了通過口述史的方法來保留資料更加豐富并有活力。有些技藝如戲曲、音樂、曲藝等的表現形式以口頭表達和表演為主,這些技藝資料的保存僅用書面資料是不能體現藝術自身的活力的,需要通過多種形式來保留資料。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口述史工具越來越先進,可以用照片、錄音、錄像以及文字等多種形式來保存資料,這樣就使保留下來的文化資料更加豐富,也更加有活力。
最后,口述史自身的特點使口述史的方法更加有利于民間技藝資料的保存。上述口述史多樣性的保留資料的形式,不僅對后期研究和考證資料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記錄了傳承人及相關技藝保護者當時的音容笑貌,把他們對藝術的那份熱愛的情感以及執著追求的精神以影像的形式保留下來,這是彌足珍貴的資料。
2 民間技藝傳承人口述史實踐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在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的相關研究中存在一些問題,民間技藝傳承人口述史研究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更有利于推進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進程。
2.1所選擇的口述史訪談對象以代表性藝人為主,忽視周圍相關的文化受眾
在遴選藝人進行口述史研究的時候,一般的研究者會想到以代表性的藝人為主,這也無可厚非,畢竟以對某項技藝的傳承來說,有代表性的傳承人更有說服力,對這項技藝的傳承譜系及制作流程更加清楚。但是,這些研究者忽略了除傳承人之外的其他保護人員的作用,這些人對技藝本身及技藝的傳承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們在做民間藝人口述史實踐過程中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有位非傳承人,從對技藝資料的整理到對這項技藝的保護,他所起的作用非常大。這位老人就是井陘縣南張井村的尹海柱,他受過初等教育,曾在本村任教。南張井老虎火早在2008 年6月入選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尹海柱老人負責整理非遺項目“南張井村老虎火”資料,默默無聞,無私奉獻。老人對老虎火的保護與發展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令后人敬佩。
2.2訪談模式單一,訪者與口述者缺少深入交流
在實踐過程中,往往是采訪者提前設計所要采訪的內容,采訪過程中按照既定的內容進行采訪,致使訪談模式比較單一。實際上,有時在實際采訪過程中才發現設計好的內容并不合適,或者受訪者對這個問題并沒有說出有價值的東西,又很難再深入下去,這個時候就需要采訪者靈活機動地處理。有研究者提出,其實口述史是訪談者與受訪者的雙向互動,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需要采訪者和受訪者心靈的溝通,這樣才能使受訪者說出發自本心的東西。
2.3對傳承人人生觀、價值觀、信仰以及情感對民間技藝創作的影響等深層次研究極少
傳承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信仰以及情感會直接影響到其創作效果,這在繪畫等藝術創作方面尤其明顯。畫家的繪畫風格往往是其價值觀、信仰的真實寫照,但是對這方面的研究基本是空白。其實,傳承人人生觀、價值觀、信仰、情感等因素對民間技藝的創作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筆者與同事嘗試通過深度訪談來挖掘民間技藝傳承人及主要參與者,發現傳承人和主要參與者對技藝本身的情感,以及他們對技藝傳承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是遠非我們這些年輕人能夠理解的,也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有的傳承人甚至把自己所傳承的技藝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甚至尊其技藝為“老祖”。因此,研究這些傳承人及傳承主體的口述史,不僅僅是一項研究,更是很好的精神食糧。這種對技藝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于年輕人而言無疑是一筆難能可貴的精神財富。從這一角度來說,技藝傳承它不是靜止的,而是富有生命的,傳承的也不僅僅是技藝本身,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
3 民間技藝傳承人口述史實踐的理性思考
王小明在《口述史給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提供的新視角》一文中,首次對“非遺”口述史進行了概念定義:“經過學術和技術準備的訪談者,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傳承人合作,有計劃、有目的地錄音、記錄、整理、保存并研究他們的個人自述,以便為當代以及未來的文化遺產研究提供有聲的備忘材料。”從這個概念可以發現,“非遺”口述史的實踐不僅僅是對受訪者個人的采訪和記錄,對口述史的資料進行整理、保存并研究其自述也非常重要,因為口述史是采訪者和受訪者雙向互動、共同發展的一個創作過程,對采訪者的素養要求也很高。為了更好地開展“非遺”口述史研究工作,需通過各種渠道培養采訪者,提高采訪者的素養。
第一,有關部門對“非遺”口述史的采訪者進行專門的培訓,提升其素養及操作技巧,使“非遺”口述史研究更加規范化。采訪者要具有職業道德和專業素養,應持中立和客觀的態度,不應誘導、引導對方去說自己要他們說的話。主訪者或加工者只能在理順文法、調理邏輯結構等“技術”層面上進行整理加工。
第二,口述史研究者應有意識地加強自身修養及素養,并在田野實踐之前,通過占有大量資料,更多地了解研究對象本身,使在田野實踐過程中,能夠與口述者進行更深入地交流,提高口述史料的質量和價值。
第三,高校應開設相關課程,使口述史這種研究方法成為一種常態的研究方法,應用于各個領域,這將更加有利于推動非遺口述史的研究和發展。國內高校還很少有開設口述史課程的,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口述史學研究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幾乎每所大學都根據自己的特點,開設了口述歷史的教學課。可見,美國對口述史這種研究方法的重視程度。可喜的是,口述史在國內已經開始引起重視,尤其是在非遺保護中。
第四,注意口述史研究方法與其他方法結合應用,以保證民間技藝傳承的可持續性和發展性。口述史可以運用到文化遺產的保護,但是由于它的特性原本是注重歷史研究的,而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具有活態性特質,這就決定了不僅要研究歷史還需要兼顧到現實,要求文化的延續性。口述史可以完成資料留存的功能,這一步實現之后,還需要考慮結合其他方法來保持文化遺產的繼續發展。這就涉及到開拓創新其傳播渠道,如通過創作其衍生品等途徑,使文化遺產能夠在一個活態的發展中存活。
綜上所述,“非遺”口述史的研究趨向應盡快從“行動的實踐”上升到“理性的思考”。這種方式的轉變不僅是圍繞對“非遺”傳承人進行有針對性和目的性的口述訪談,來獲取傳承人對民俗文化、手工技藝等歷史記憶與解釋,更應是在此基礎上建構“非遺”傳承人階層“草根文化”的獨立體系,以增強他們的集體認同感和文化自信和自覺。
[1]王拓.“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與向度[J].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13(11).
[2]施曉燕.淺談口述史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中國博物館學會紀念館專業委員會 第三次年會贊城市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論壇論文集[J].
河北傳媒學院第四屆校級立項“河北民間藝術保護與傳承的方法之口述史研究”(項目編號: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