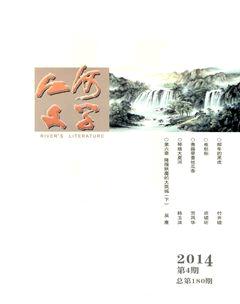夜航船
歡鏡聽
1、鄉(xiāng)愁
人,抑或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種動物。倘若把見異思遷這句成語里的貶意去掉,人的本性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當(dāng)我竭盡全力從寧靜的環(huán)境中一步接一步艱難地走進(jìn)大城市、走進(jìn)《大都市》編輯部以后,接踵而至的便是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感,宛如潺潺的溪水,流淌在編輯部里,流淌在我的心頭。
在婦產(chǎn)科醫(yī)生預(yù)言妻子還不到一個多月就將分娩的第二天,我請了十天假。通情達(dá)理的妻子為我收拾好了行裝,然后自問自答:“那個地方有一位基礎(chǔ)挺不錯的作者,是嗎?石河,你要早去早回啊!”
四周的景物跟過去一模一樣:腳下是一片寬闊的沙地,沙地上鋪滿了野草,草地上開放著星星點(diǎn)點(diǎn)淡黃點(diǎn)的花兒。草地的邊際,聳起綿綿無盡高高矮矮的群峰,氤氳的云煙在群峰之間纏來繞去,云團(tuán)的外層又抹上了一層薄紗似的霞光。草地上有一條彎彎拐拐的小路,一頭通向德感鎮(zhèn),一頭通向幾江渡。我沿著小路朝草地深處走去。青草葉兒蹭著我的腳,紙做的心扉被帶齒的草葉兒漸漸鋸裂開來。
夏季里的一個下午,天上翻卷著滾滾烏云,雷聲從天宇深處撲下來,草地籠罩著一片悶熱而又恐怖的氣氛。一會兒,狂風(fēng)吹起來了。狂風(fēng)推著草浪從幾江渡方向朝德感鎮(zhèn)一層一層地?fù)溥^去。狂風(fēng)中,隱隱約約地出現(xiàn)了一位小伙子,他一邊跑一邊呼喊:“紅英,紅英,紅英……”忽然,他被潛伏在草叢里的一塊石頭絆倒了,他掙扎了一下,也許是疼痛,他終究沒能站起來,索性全身撲倒在草叢里,嗚嗚嗚地哭泣著。一邊哭一邊說:“紅英,紅英,紅英……”盡管如此,他聲聲呼喚著的紅英卻不在他身邊。
倒是另一位姑娘注視他很久了。
那位姑娘肩上扛著一圈纖繩,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姑娘認(rèn)識他,知道他叫石河。石河也認(rèn)識姑娘,知道姑娘叫水燕。他倆生活在同一座德感鎮(zhèn)上。
水燕走到石河身邊,俯視著他那痛苦不堪的樣子,“唉……”她嘆息一聲,用腳尖踢踢石河的屁股,問:“石河,你哭啥子啊?”心里卻想,狗日的,屁股瓣兒好軟和啊!
石河慢慢翻轉(zhuǎn)身來,終于看見了姑娘那張鵝蛋形的臉龐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
“喂,石河,你跑到這兒來哭啥子啊?今天又不是清明節(jié),你家的祖墳也沒埋在這兒啊!”
石河忿恨地盯住水燕,繼而想到自己這一副哭相,便將雙眼移開,望著渡口方向。許久,才喃喃自語道: “她叫紅英,她住在江那邊,她和我耍了兩年的朋友,現(xiàn)在她不要我了。”他又恢復(fù)到那種癡呆呆的神態(tài),說:“我要找她,我要過河去找她。”
“那……石河,跟我走吧,我劃船送你過河。”
事后想來,當(dāng)初,假如不是為了追回我那無法追回的愛情,我一定會仰面躺倒在草地里,任狂風(fēng)和即將到來的暴雨撲打著我陰沉沉的臉。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我也許就不會與幾江河結(jié)下不解之緣,更不會有如今這許許多多縈繞心際的往事了。
一只小木船停泊在渡口。
石河和水燕剛剛走到渡口,暴雨便鋪天蓋地下起來。頃刻間,天地之間白茫茫一片,轟隆隆的雷聲沒有了,嘩嘩嘩的雨聲響徹整個世界。水燕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朝著座落在沙灘上的一個窩棚獨(dú)自飛快地跑去。窩棚的門關(guān)著,她跑到竹門前,轉(zhuǎn)身彎下腰,將屁股朝那扇竹門呼一聲撞去,身體隨著竹門的移開倒進(jìn)窩棚里面去了。
“喂,石河,快點(diǎn)跑進(jìn)來躲雨啊?”
石河站在沙灘上,雙眼望著雨蒙蒙的江面。
“喂,石河……”水燕從窩棚門里探出頭來,望著木然站在沙灘上的石河。她又喊了幾聲,對方似乎沒有聽到。她縮回頭,從窩棚角落找出一個竹葉編成的斗笠戴在頭上,鉆出了窩棚,雨點(diǎn)打在斗笠上,撲撲的響。她一步一步朝著石河走過去,然后在距他不遠(yuǎn)的地方站住了。她看見石河臉上流淌著的不全是雨水,還有比雨水更為晶亮的淚水。天下干啥會有這種男娃兒呢?她想,大不了就是人家不和你耍朋友了嘛,值得傷心落淚么?水燕取下頭上的斗笠,掂了掂,呼一聲朝著石河扔過去,斗笠在半空中旋轉(zhuǎn)著,不偏不倚恰好套到石河的頭上。石河駭了一跳,轉(zhuǎn)過頭驚訝地望著水燕。水燕望著他,忽然咯咯咯地大笑起來。然而,這笑聲似乎把另一位少女的姿影恍恍惚惚地推到石河眼前,他頓時反常地快活起來。跟著也嘻嘻嘻地笑了。水燕走到石河身邊,拍了一下他的肩頭,問:“喂,石河,我們不過河了吧。”
石河的眼睛里突然閃出灼人的光芒,就像他第一次和紅英悄悄約會時那樣,他說:“我們不過河了,從今后,我們就這樣生活在一起。”
水燕的臉兒倏地緋紅,做出一副惱怒的樣子,用一根手指頭點(diǎn)著石河的額頭,嗔怪道:“喂,石河,說話小心點(diǎn)啊,要不然,我這根手指拇釘進(jìn)你的腦殼里頭,一勾,把你的腦水花花全勾出來。”
石河仍舊嘻嘻嘻地笑著,猛然抓住水燕的兩個肩頭,說:“紅英,我們不過河了。”
水燕先是一愣,繼而明白過來,石河把她當(dāng)作昔日的戀人紅英了。她重重打了石河一個耳光,又用力一推,將他推倒在沙灘上。然后雙手叉在腰間,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聲,一句話也沒說。石河怔怔地望著水燕,漸漸清醒了。接著,他調(diào)頭望著江面,像是說給水燕聽又像是自言自語:“我們是在這個渡口分手的,她住河那邊。我要去找她。”
水燕用腳尖輕輕地蹭著他的脊背,冷冰冰地說:“走啊,我送你過河,送你過河去找那個不要你的女人。哼,沒出息的東西!”
石河瞪大眼睛,“你真的要送我過河?”
水燕彎下腰一把抓住他的頭發(fā),一邊往上提一邊說:“走啊,沒出息的東西!”
2、媒婆
能夠從喧囂的都市中解脫出來,頭上的云朵、腳下的草地、以及遠(yuǎn)方那些彼此手挽著手的群峰,全都默默地沉寂在我周圍。這,反而使我感到一陣惶恐,胸中那些日日夜夜鬧得我心神不寧的許許多多的情感,一剎那化為烏有。我停下腳步,宛如陀螺般旋轉(zhuǎn)了一圈,寬敞的草地上渺無人跡。一只鳥兒吱一聲長鳴,從半空中俯沖下來,潛伏在草叢里的一條小蟲子被鳥兒叼在嘴里,騰云駕霧似的飛上天空。
我朝前走去,步子比先前慢了許多。
石河坐在船艙里,水燕手持竹篙,將船兒嗖一聲撐離了江岸。
水燕的衣服被雨水泡濕了,身體的每一條曲線都完完全全地展現(xiàn)出來。水燕撐船的姿勢非常獨(dú)特,就像她獨(dú)特的個性一樣:她雙手將竹篙插進(jìn)江底,雙腳使勁往后一蹬,旋即跳起來,待重新落在船板上時,她已經(jīng)從船艙中央站到了船尾上。
一只小木船從對岸劃過來,撐船的是一位戴著斗笠、披著蓑衣的中年婦女。她看見了石河,也看見了水燕,打著招呼:“水燕,把船停下來,我給你說一件事。”
“啊,幺娘,是你啊。”水燕把竹篙豎起來,從船尾上的一個孔洞里插進(jìn)河底穩(wěn)住了木船,“幺娘,你又來給我做媒啊?”
那位中年婦女沒有急于回答水燕,卻狐疑地打量了石河一陣,問:“水燕,他是哪個?”
“他么?啊呀,幺娘,他是鎮(zhèn)上的那個小白臉啊,叫石河,先前遭一個不知從哪條石縫縫里鉆出來的女妖精勾去了魂,今兒個那個女妖精不要他了,他呢,拼死拼活也要過河去找人家。”
中年婦女笑嘻嘻地說:“石河,另外找個女娃兒吧,天底下,哪個女娃兒都是一樣的生娃兒嘛。”跟著,她又轉(zhuǎn)頭望著水燕說,“幺哥明兒個要到渡口來喲。”
水燕笑容可掬的臉一下子陰沉起來,默默地不說一句話。
“還有,”那位中年婦女說,“他老巴子(父親)也要來。”
水燕將竹篙從船孔中抽出來,對中年婦女說:“幺娘,你給他們打聲招呼,空手不要來。”一邊說一邊將木船撐得遠(yuǎn)遠(yuǎn)的。
“水燕,你聽我說嘛。”身后又傳來中年婦女的喊聲,“明下午我跟他們到渡口來。”
雨還在下著。
《大都市》編輯部。
一天下午,我收閱了一份詩稿:《草綠花黃》。
這是一組用擬人手法寫成的敘事長詩。
我尚未完全看完,渾身的血液便有悖常理地冰凍起來。
水燕氣呼呼地將船劃到江心,停住竹篙,又氣呼呼地從船艙中跨到船頭上,咚一聲坐下來,索性連船也不撐了。小木船失去了控制,順著水流往下游漂去。他大驚失色地嚷道:“水燕,船……船……”
“船船船船船,”水燕狠狠瞪了他一眼,不耐煩地說,“船要漂到龍王爺那兒才好呢。”
他沒料到水燕的氣性會這樣大,脾氣會這么古怪。他撲過去,企圖從水燕懷中把竹篙奪過手。那時候,他沒有仔細(xì)想一想:竹篙對于他來說有什么用?他可不會撐船啊!但,沒讓他抓住竹篙,水燕猛地身子朝后一仰,張開雙腿,他的頭剛好伸到水燕的兩條大腿之間。他還沒醒悟過來,水燕又將雙腿一夾攏,他的脖子頓時被夾住了。他沒料到水燕的力氣會這樣大。他徒勞地掙扎了幾下,臉孔臊的通紅。于是,他奇跡般地破口大罵起來:“水燕,你他媽的這叫什么話,羞死你他媽的祖先。你他媽再不放開,老子要咬你的肚皮了。”
這一句話奏了效。水燕大喝一聲:“石河,放開了,放開了。”她把雙腿分開,石河長長地喘了一口氣,剛想把頭抬起來,水燕突然重新將雙腿一并,重新牢牢地夾住了石河的脖子。這一次,石河不僅僅是掙扎不動了,而且下巴頦頂在水燕的小肚子上,仰臉望著天空,嘴巴大張著,再也合不攏了。話,更是沒法說出來。雨水澆到石河的臉上,然后又源源不斷流進(jìn)他嘴里。“喂,石河,曉得我的厲害了吧?哼!”水燕幸災(zāi)樂禍地說,話里充滿了快樂,好像早先抑郁在她胸中的不快,在這時候、在小船中、在石河身上得到了痛快淋漓地發(fā)泄。把石河折磨夠了以后,她才松開了雙腿,兩腳一蹬,將石河蹬倒在船艙中,等對方站起身握緊雙拳想撲上來和她打一架時,她卻早已手持竹篙站在船頭,竹篙的一端頂著對方的心窩。“石河,老實(shí)點(diǎn)。要不然,我用竹篙從你的胸膛上穿過去,掛起來,晾成魚干!”
幾江河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個模模糊糊的輪廊。
愈接近那個地方,我的腳步愈慢。草地靜靜的,一種身臨冥冥世界之中的心理上的感覺靜悄悄地裹住了我那顆怦怦跳動的心。靜謐中,我聽到陽光漸漸熱起來的轟轟聲,聽到一絲一縷的白汽從沙地里冒出來繚繞著草葉兒的沙沙聲。不久,這些細(xì)微的幾乎只能依靠感覺才能聽到的聲響神秘地隱沒了,取而代之的是恍如一滴一滴的清水掉進(jìn)心坎兒上發(fā)出的難以言喻的響聲。
《草綠花黃》的作者就在本市。
我給作者寄了一封信去,約定星期天在湖畔公園見面。我明白《草綠花黃》是一組藝術(shù)質(zhì)量較高的詩,那種低沉的灰色的調(diào)子宛如把讀者的心兒放置在一座冰窖里,對著冰冷的雪墻面壁思過——冷靜地面壁思過!但是,作者有做詩人的才華,有做詩人的激情,然而,作者缺少一種需要別人去提醒他(她)的東西:注意……
星期天,公園的水泥凳前。
一位西裝革履的老頭握住了我的手。老頭不下八十歲,滿頭花發(fā),但天庭飽滿,容光煥發(fā);尤其是系在他脖子上的那條燃燒著青春火焰的鮮紅色的領(lǐng)帶,迫使我不得不用新的目光重新估量這個老頭。老頭笑瞇瞇地說:“吃驚了吧,編輯先生——啊,不,石河先生,以后,你也許會疑惑不解地對別人說,一位有著萬貫家產(chǎn)的海外華僑,到了快進(jìn)棺材的年齡,為什么突然間心血來潮,眼紅起那微乎其微的幾塊錢稿費(fèi)來?”
那位老頭在我身旁坐下來。
他說:“我從未有過做詩的雅興,更沒想過要當(dāng)一名詩人。兩年前,我從海外回到大陸定居,便到各地旅游。我不喜歡到那些名聲在外的名山大川,反而去尋找那些無名的但充滿了大自然野性情調(diào)的地方,因?yàn)槟欠N地方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要質(zhì)樸和真誠得多。在一個極其偶然的機(jī)會里,我到了一個偏僻的地方——幾江渡。在那兒,我遇見了一位神情呆滯的婦人孤伶伶地坐在江邊。經(jīng)過耐心的交談,我終于零零星星地了解到一些情況。她被人欺騙了,她曾經(jīng)愛過的一位男人拋棄了她。”
我的心忽然沉落在一條幽深的峽谷里……
水燕突然驚慌地嚷起來:“啊呀!船……”
她那銳利的尖叫聲把石河嚇了一大跳,他怔怔地望著水燕那一副驚慌失措的模樣。
“啊呀,石河!你看船都漂到哪兒來了。”
他醒悟過來,這才注意到船兒漂流的速度是越來越快了。他驚慌地嚷起來:“水燕,咋辦呢?”
“咋辦?你問我,我又問哪個龜兒子?!”
船已經(jīng)漂到幾江河的下游了。越往下漂水流就越急。
水燕瞪大雙眼,一只手持竹篙,另一只手指著他的鼻尖,責(zé)罵道:“石河,你這個昏腦殼的,你這個背時的,你這個挨刀剮的,你……你……你……你不是一個好龜兒子!”
天開始擦黑了,雨珠兒照舊啪啪啪地拍打著船板。
出于自尊,石河有些心虛地辯解道:“水燕,責(zé)任應(yīng)該一分為二,你負(fù)一半,我負(fù)一半。”
水燕雙眼瞪得更大,正要大大地發(fā)作一番,卻猛然瞧見了手中的竹篙,她一下子想起了什么,沒再理會石河那斤斤計較的話,將竹篙高高舉在半空中,惱怒地說:“滾開點(diǎn)!我要靠船了。”
石河剛一彎下腰,水燕手中的竹篙立即從他頭上嗖一聲滑過去,竹篙穿過船尾那個小小的孔洞直插河底。船兒終于靠下來了。水燕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緊張的心情終于得到了緩和。
但是,他們跟著又犯起愁來:這半船艙水怎么辦?
一片白色緩緩移進(jìn)我的眼簾,我精神為之一振:幾江河就在眼前了。
那消失了許久的情感又回來了,并且還融進(jìn)了一種新鮮的燦然的色彩,重新轟擊著我的心扉。
當(dāng)我大步流星地朝前邁去時,那久違了的綠色草浪又呼呼呼地吹起來了……
3、舀水
幾塊青石板橫七豎八地擺在河灘上,這就是幾江渡。
一葉漁舟漂在江心順流而下。我以為是渡船,沒等開口呼喚,漁舟已經(jīng)離我遠(yuǎn)去。
使我魂不守舍的幾江渡原來這么簡單。
世界上恐怕沒有多少這么簡單的渡口。
天,漸漸黑下來;雨,早已停了;風(fēng),輕輕吹拂著;船兒,在他們腳下?lián)u晃著。
盡管是夏天,但一則到了傍晚,空氣中的熱度早已被雨水沖散,二則他們又濕透了渾身衣褲,河風(fēng)吹來,冷冷浸人,石河禁不住渾身冒出了雞皮疙瘩。石河和水燕各自把手抱在胸前,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到后來彼此都苦笑起來。
水燕笑著說:“石河,你是個大災(zāi)星。”
石河苦笑著說:“任何事物都是辨證的,一個巴掌拍不響。水燕,你說是么?”
水燕半張著嘴巴,睜大雙眼,說:“石河,我沒有你那么多文酸氣。你看,這半船水咋辦呢?”
“舀出去。”
“舀?哼!你拿啥子?xùn)|西來舀嘛?”
這次,輪到石河半張著嘴巴,睜大雙眼了。可是,沒多久,他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水燕,我們用手舀,手不是很好的舀水工具么?”
“嘖嘖嘖,你以為別人都是豬頭?”水燕仍舊將雙手抱在腦前,“用手舀?哼,說得輕巧,提根燈草。這種舀法,要舀到牛年馬月啊?”
石河彎下腰,雙手合在一起以掌當(dāng)瓢,一下一下地舀著水往船艙外潑去。的確,這太吃力了。
水燕冷冷地望著石河。一會兒,她說:“喂,石河,書呆子,船中的水怎么沒見少啊?”
石河直起酸脹的腰,看了看船艙里的水。
“喂,石河,快點(diǎn)舀啊!”
石河又彎下腰去——并非他要聽水燕的話,而是在爭一口氣。他一邊舀一邊自我解嘲道:“愚公能夠移山,我難道還不能舀干船艙里的水么。”
水燕吃驚地反問:“愚公?愚公是個啥子?xùn)|西啊,能夠把大山都搬走?”
石河說:“愚公是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一位老人,他要把擋在他家門前的那座大山搬走。”
水燕說:“那座大山擋了他們家的路,干啥子不搬家而去搬山啊?”
石河說:“故事中蘊(yùn)藏深刻人生哲理。水燕,你不懂。”一邊說一邊彎下腰,繼續(xù)舀水。
水燕靜靜地觀察著他,眼神是復(fù)雜的。她覺得石河變了,不再提那個紅英姑娘了。聽著石河舀水弄出的嘩嘩聲,她忽然童心大發(fā),搞起了惡作劇:趁石河彎腰舀水時,伸出右腳插進(jìn)對方的胯下用力一勾,沒有絲毫防備的石河撲通一聲翻過船舷栽進(jìn)江水里。“哈哈哈……”水燕開心地大笑起來。突然,水燕吃驚地看見石河的雙手在江水中亂搖亂擺。她明白了:這位在江邊長大的男人原來是旱鴨兒。她立刻嚇得面如土色。江邊長大的男兒不會水,這倒是一個比較少見的現(xiàn)象。水燕急中生智,抱住靠船的竹篙用力往上一提。竹篙取出來了,可船兒又開始往下游漂去。她額頭上冒出了冷汗。如果船兒漂遠(yuǎn)了,那就……她不敢再想下去。她將竹篙的一端伸到石河手邊,驚慌地說:“石河,抓竹桿。”
石河準(zhǔn)確無誤地抓住了竹篙。他嗆了幾口水,嗆得他眼冒金花。
“喂,石河,抓緊喲。”水燕一邊慢慢地收著竹篙,一邊緊張地說道。聲調(diào)里居然帶著哭音。
終于,石河上了船。得救后,他感到軟弱無力,全身似乎虛脫了一樣,身不由己地癱倒在船頭上。水燕嚇得臉色蒼白,急忙靠住船,將石河抱在懷內(nèi)。石河虛弱地睜開眼睛,看見自己被水燕抱著,立刻氣不打一處來,舉起手打了水燕一個耳光。水燕沒有任何還擊的舉動,也沒說一句怨言。她更緊地抱緊了石河。石河掙扎了幾下,沒掙脫,于是滿臉羞紅地吼道:“放開我!”
水燕沒有放開他,眼眶里反而掉出了一顆一顆的淚珠兒。一會兒,她忽然哇一聲大哭起來,并把自己蒼白的臉,貼到石河同樣蒼白的臉上去。石河被水燕擁抱著,而且擁抱的那么緊,那么牢。他掙扎了幾下,卻是連身子也動彈不了。于是,他放棄了這種徒勞的掙扎,也放棄了羞怯,軟軟地癱在水燕的懷內(nèi)。他太疲乏了。水燕把蒼白的淚臉從石河同樣蒼白的淚臉上移開,帶著哭腔輕聲呼喚道:“石河……”一邊說一邊松開他,卻又將另一只手貼到對方臉上。她流著淚說:“石河,我對不起你,我以為河邊長大的娃兒都會浮水。”
石河冰涼的身子在漸漸暖和起來,水燕的身子緊緊地貼著他的身子。
見石河露出不相信的樣子,水燕著急地解釋起來:“石河,哄你我就會變成……”后面的話,她感到難以說出口。
石河冷冰冰地仰視著水燕,其實(shí),他的心早已被水燕的溫柔和柔情所動。
水燕輕聲問:“石河,你還不相信么?”
石河已經(jīng)在心里答應(yīng)了,可是該死的眼睛,卻依舊冷冰冰地仰視著水燕。
水燕以為還沒取得石河的信任,她神情莊重地詛起咒來:“石河,如果我哄你,我就會變成大伙兒的婆娘!”詛完咒,水燕的臉轟地?zé)猛t。
石河驚駭?shù)貜乃龖驯е袙昝摮鰜恚敬舸舻囟⒆∷J由钪瑢τ谝晃晃椿樯倥畞碚f,她盡可以詛“挨千刀萬剮”之類的咒語,卻沒有一個敢于拿自己的貞操和一生幸福來作詛咒。
水燕忽然聲淚俱下地哭起來,“我詛這么大的咒都不能使你相信,我只有死了算了,嗚嗚嗚……”
石河一陣激動,雙手搭在水燕的肩頭上,柔聲細(xì)語地說:“水燕,我相信你。”
水燕停住哭泣,狐疑地望著他,輕聲問:“石河,你真的相信了?”
“水燕,我真的相信了。”
她仍舊狐疑地望著他,“你詛個咒,我才放心。”
石河想了想,一眼瞟到幾江河,便咬牙切齒地詛起咒來:“我石河說了假話,淹死在幾江河里。”
水燕破涕為笑了,說:“石河,你已經(jīng)死過一回了。”
石河一愣,是的,他已經(jīng)死過一回了。于是,他清了清嗓子,正要重新詛咒,卻不料嘴唇被水燕的一只手捂住了。
“石河,我相信。”她把手緩緩移到石河的臉頰上,輕輕地?fù)崦缓笥志o緊地抱住了對方濕漉漉的身子。
石河也把水燕緊緊抱住,那種暖暖的體溫在他和她的身體之間融合起來。在漸漸濃郁起來的暮色中,在搖搖晃晃的木船上,石河感到有些離不開她了。
水燕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diǎn),她很不情愿地松開手,石河的雙手卻還摟著她的腰肢。她臉一紅,似嗔似怒地瞪了石河一眼,猛然將對方一推,罵道:“呸!石河,不要臉。”
石河撲通一聲仰倒在身后的半船艙水中。
“哈哈哈……”水燕大笑起來,是那種無拘無束的大笑。
石河狼狽地站起來,原本就水淋淋的衣褲現(xiàn)在更加水淋淋了。似乎是受到了水燕清越笑聲的感染,他居然沒發(fā)脾氣,反而跟著水燕哈哈哈大笑起來。一陣開心大笑之后,他和水燕開始犯愁起來,望著船艙里的水,他們一時間都感到束手無策。
他愁眉苦臉地問:“水燕,你往常沒遇到過這種情況嗎?”
水燕扁了扁嘴,說:“這種事兒我遇多了。”
“那……往常你是怎么舀干的呢?”
她直勾勾地盯著石河,慢條斯理的說:“往常?往常船上沒你這個大災(zāi)星啊。”
石河疑惑不解地望著她,“我在船上礙了你什么事?”
“什么事?裝瘋賣癲的。告訴你,往常遇到這種情況,我只需要把褲兒衣裳一脫,踩住船梆梆,一踩一跳,這船就翻個底朝天,再把船翻過來,水不就全倒出去啦。”
石河頓時高興起來,說:“那我們一起來踩,一起來跳。”
“那好啊,”水燕仍舊站在原地,“只怕船一翻,又要淹死你。”
石河站到船頭上,猛然醒悟過來,慌忙說,“不行,我不會游泳。”
“哈哈哈……”水燕又開心地大笑起來。
石河站在那兒,啞然無語,心里卻在罵著自己,石河,你他媽的真是一個大災(zāi)星啊。
看見石河一副懊惱樣兒,水燕收住了笑聲,正色道:“辦法倒是有一個……”
“什么辦法?快說!”一聽說有辦法,石河便迫不及待起來。
水燕瞪了石河一眼,“把褲兒脫下來,褲兒腳腳挽成死疙瘩,兩根褲腳就成了水桶。只要動作搞快點(diǎn),這半船水一會兒就‘提干了。”
這算什么辦法啊?他望著一本正經(jīng)的水燕,哭笑不得。他和她都只穿單褲,脫掉了,豈不……這辦法不行。他試探著問:“還有其他辦法么?”
她挺干脆地答道:“沒了!”
石河雙手抓住濕漉漉的頭發(fā),自言自語:“這,該怎么辦啊?”
水燕笑瞇瞇地望著他,用一種戲謔的口吻說:“喂,石河,你就把褲兒脫下來吧。”
“不行!”他說:“你怎么不脫褲兒呢?”話剛說完,他立刻后悔了——這句話說得多么蠢啊,這句話使得我斯文人的面子喪失殆盡。
水燕急忙雙手按住自己的褲腰,仿佛對方真會強(qiáng)迫她脫褲子一樣,急忙說:“石河,你好不害羞啊!你穿了窯褲(內(nèi)褲)的都不脫,難道還要我這個沒穿窯褲(內(nèi)褲)的脫?哼!”
“不行,不可能。”
水燕誤會了對方話中的意思,為了證明她的確沒有穿內(nèi)褲,她的手掌在屁股上飛快地摩擦著,說:“你看,石河,我屁股上伸伸抖抖的沒得一點(diǎn)點(diǎn)楞楞角角。”接著,她將雙手叉在腰上,抬起一只腳,大腳指拇翹起來,一上一下地活動著,像一個小小的蛇頭,蛇頭伸到石河大腿上,一上一下地刮著,腳指甲把貼在對方大腿上的褲子刮得刷刷直響。她說:“石河,你穿了窯褲(內(nèi)褲)的嘛,你窯褲(內(nèi)褲)的楞楞角角都現(xiàn)出來了。”
濕褲子貼到大腿上,現(xiàn)出里面內(nèi)褲的影子,這沒什么奇怪的。
石河啪一巴掌打掉了她的腳,旋即蹲到船頭上哈哈哈地大笑起來。
水燕也笑了,一邊笑一邊說:“我的腳指拇刮得你的腿皮子發(fā)癢,石河,是不是啊?”
石河站起身,揉了揉滿眼淚花的眼睛,爽快地說:“好吧,我脫褲子。”
石河的褲腰帶被雨水濕透了,不知怎么打成了死結(jié),他解了許久也沒法把死結(jié)解開。水燕看著他一副狼狽樣兒,禁不住嘻嘻嘻地笑起來,說:“石河,褲腰帶打不開了么?”
他難為情地搔著頭皮,沒說話。
水燕笑嘻嘻地走過來,笑嘻嘻地注視著他。突然,她一只手猛地插進(jìn)他腰間。他大吃一驚,感覺到一條泥鰍滑溜溜地貼著他的肌膚,沒等他醒悟過來,褲腰帶已被水燕砰一聲拉斷了。水燕便笑嘻嘻地說:“石河,褲腰帶斷了,快脫褲兒啊!”
他剛一撩開褲腰,卻又趕忙緊緊地捂住,臉孔比先前燒得更燙了。
水燕依然笑嘻嘻地催促道:“快脫褲兒啊!”
“我的內(nèi)褲……撕破了。”原來,水燕把石河內(nèi)褲的褲帶也扯斷了。
水燕又大笑起來,開心地說:“石河,你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災(zāi)星。”
他不愿在這個問題上與水燕繼續(xù)扯下去,岔開話題,問:“水燕,怎么辦呢?”
“石河,你脫吧。我轉(zhuǎn)過身背對著你。船里的水呢,你一個人舀。”
他使勁搖著頭。
水燕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那如何辦呢?”
夜色從四面漸漸逼近過來,漸漸染黑了他們眼前的景物。夜色啟迪了他。他忽然想到了一個根本不能叫作辦法的辦法,高興地說:“水燕,等天黑盡以后,我就脫褲子。”
水燕仍舊是那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攤開雙手說:“石河,你真的是一個十足的書呆子。”
4、哨葉
我沿著曲折的江岸朝上游走去。古樸的土地,旖旎的風(fēng)光,映襯著我心中一小片暮云般淡淡的哀傷。我想,一旦進(jìn)入這塊土地,被一片綠草野花包圍,爽心悅目的色彩擠滿胸膛,抑郁在心中的悲悲戚戚的愁云,沒有理由不散開吧!
前方,一位挎著竹籃的婦女蹣跚著朝下游走來。
天黑了,就并非什么事都做得出來。當(dāng)夜色把他和水燕完全籠罩了時,當(dāng)水燕伸過一只腳捅他時,他忽然感到羞愧極了,臉孔轟一下燃燒起來。他仍舊坐在船上,假裝想什么心事,一動也不動。可是,水燕卻火爆爆地大吼一聲:“石河!”
石河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地答道:“干什么?”
“我以為你死過去了呢。”水燕站起身,雙手交錯抱在胸前,兩片嘴皮兒故作不滿地翹著。
石河仍舊坐在船頭上,頭低垂著,“水燕,你喊我有什么事?”
水燕踢了石河一腳,笑著說:“天已經(jīng)黑完了,你干嘛還不脫啊?”
“我……我忘記了。”
“呸!石河,你又瞞我。”
“嘿嘿嘿……”石河尷尬地笑著,然后裝模作樣地觀望著其實(shí)什么也望不到的夜空。
水燕伸出一只手,半真半假地說:“石河,我來幫你脫褲兒,要不要得?”
石河大吃一驚,緊緊地捂住褲腰,躬著身,急忙告饒:“水燕,絕對不行!”
水燕往前跨了一步,手仍舊那么伸著,仍舊那么半真半假地說:“我來幫你脫嘛。”
“我脫 ,我脫我脫。”這一次,石河是真的脫掉了褲子。
萬事萬物都像凝固了一樣,我和那位面容憔悴的婦人面對面地站著,彼此都吃驚地注視著對方。
她那灼熱的目光喚醒了我記憶深處許許多多的往事,我不清楚這些往事是甜呢還是苦。
“水燕。”我輕輕地喚道。
水燕淡淡地笑了笑,沒有說話。我細(xì)致地端詳著她,我力求從她身上尋找到往日那位渾身野性又柔情滿懷的少女的姿影。可是……我嘆息道:我的確不應(yīng)該現(xiàn)在回來;如果早幾年回來,那么,往日那位少女的姿影,仍舊會在我的眼前翩翩起舞,她那既野性又柔情的迷人的氣息,仍舊會彌漫在我身旁、縈繞在我心中。
水燕還是那么淡淡地笑著,每一絲紋路里都漾出母愛般的慈祥,她輕輕地說:“你,回來了。”
鼓起了好大的勇氣,石河終于羞羞答答地把長褲脫下來了。他一只手提著隨時都會滑下去的內(nèi)褲,另一只手將長褲遞給水燕,甕聲甕氣地說:“褲子在這兒,你拿去吧。”
水燕接過來,用力抖了抖,湊到鼻孔前聞了聞,笑嘻嘻地說:“好大一股騷臭氣味啊,呸!”
她把褲腳倒提在手上,用力絞成一個疙瘩,又扯了扯褲腰,說:“石河,你提那邊褲腰,我提這邊褲腰,一起來舀水。”
石河左手緊緊地提住身上的內(nèi)褲,右手捏住長褲的褲腰。
“石河,我喊一,就彎腰;我喊二,就灌水;我喊三,就倒水。馬上開始了。”
“一。”
他和她一齊把腰彎下去。
“二。”
他和她一齊把整條褲子按進(jìn)船艙的水里。
“三。”
他和她提起褲腰站起身,兩只褲腿里裝滿了水,飛快地往船艙外倒去。
這種舀水法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可是,卻害苦了石河,他既要應(yīng)著水燕的口號聲,彎腰、灌水、倒水,又要提防稍有疏忽就會滑下去的內(nèi)褲。
水燕忽然喊了一聲:“停!”她一邊喘著粗氣一邊說,“石河,像你這樣,要舀到哪年哪月啊?”
石河把內(nèi)褲使勁往上提了提,說:“我又有什么辦法呢?”
“干啥子沒有辦法啊?你把窯褲(內(nèi)褲)脫了,早點(diǎn)把水舀干,你早點(diǎn)穿褲兒。”
“不……”
水燕早料到石河不會這樣做的,沒等石河把“不行”兩個字說完,她突然把手插進(jìn)他的褲腰,用力一扯,隨著嘶啦的清脆的響聲,內(nèi)褲撕成了兩大塊。
一切都無遮無掩地暴露在黑沉沉的夜空中。
石河從驚愕中回過神來,低頭看了看被撕破的內(nèi)褲,雙手胡亂摸了幾下,只摸到一塊碎布條。他惱羞成怒地舉起拳頭,怒吼道:“水燕,老子打死你!”但是,他的拳頭舉在半空中沒有打下去。
水燕早已轉(zhuǎn)過身,背對著他,冷冷地說:“石河,打吧。”
石河憤怒地望著水燕,拳頭仍舊在半空中高舉著。
水燕轉(zhuǎn)過身,幽幽地望著石河,說:“石河,這時候,你稍稍有點(diǎn)男人氣味。”
石河的手緩緩地放下來。
“石河,我把眼睛緊閉起來,要不要得啊?”她果然把眼睛緊閉起來。那神態(tài),那語氣,嚴(yán)肅得不能再嚴(yán)肅,莊重得不能再莊重了。
石河氣呼呼地哼了一聲。
接下去,他倆又舀起水來。
“一。”
他和她一齊把腰彎下去;
“二。”
……
“三。”
……
“得!”
這一次,是石河喊出了聲。他丟了長褲,雙手捂住下襠,那副驚惶的模樣把水燕搞得莫名其妙。
“石河,你又在搞啥鬼名堂啊?”
“你……你……眼睛睜起的,看見我……不行不行!”
“石河,你這個人啊!”水燕感到可笑又可氣,原來她的眼睛真的睜著。可,閉著雙眼又怎能舀水呢?想了想,她終于想到了一個辦法,說:“石河,把你的衣裳脫下來包住你的屁股,行了吧?”
他脫下濕漉漉的衣服緊緊系在腰上,前后左右地看了看,這才放心地說:“水燕,行了。”
“一。”
……
“二。”
……
“三。”
……
我和水燕朝上游走去。我們默默走著,誰也沒說話。水燕的一只手緊緊的捏住我的胳膊,腳踩在沙灘上,聽到細(xì)微的沙沙響聲。我瞥見她挎著的竹籃裝滿了哨葉草。我張了張嘴,想問點(diǎn)什么,卻終究什么也沒問。
水燕主動打破了沉默,解釋道:“我采哨葉草做成哨哨,賣給街上的小娃兒。”
“哦……”
水燕突然站住了,再一次細(xì)微地端詳著我,然后沉重地嘆息了一聲,埋著頭默默地朝前走去。
“水燕,幾江渡怎么沒人過河?”
“改了,”她指了指上游,“那上頭去了,還是叫幾江渡。石河,你不會無緣無故回來吧。”
我覺得心中一痛,急忙望幾江河。
“你還記得這條河?”
“水燕,我……”
水燕平靜地說,“走吧,你難得回來,我請你吃豆花飯。”
我望著幾江河,心里一會兒激動,一會兒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