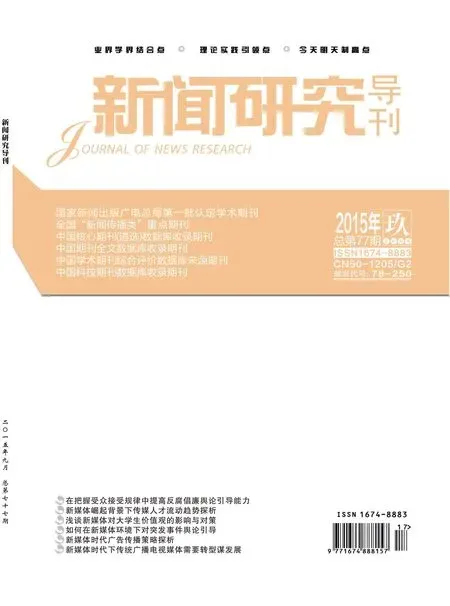言論自由與真實威脅的劃定——伊奧尼斯案
作者簡介:劉澤達(1989—),男,遼寧沈陽人,遼寧大學新聞學專業研究生在讀。
摘 要:說起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許多人都略知一二,人們對言論自由總是心生向往。然而自由不是絕對的,在一個涉及言論自由的案件中,第一修正案對言論的保護往往取決于法院對其的劃定。在劃定的過程中,“真實威脅”作為一個關鍵要素往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2015年6月1日,美國最高法院的審判的伊奧尼斯案吸引了大眾的眼球,不僅因為此案涵蓋了家庭破裂、言語攻擊、社交網絡、說唱音樂等娛樂元素,還因為該案對真實威脅與言論自由之間關系的劃定產生了深遠的意義。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15)17-0257-01
一、案件陳述
2010年5月,生活在賓州的伊奧尼斯與結婚7年的妻子塔拉分居,妻子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搬離了住所,他非常低落,無法專心工作,還被同事投訴性騷擾。2010年10月,伊奧尼斯在臉書上傳了張照片,他身穿戲服并持刀對準投訴他性騷擾同事的脖子,圖片配字“我希望”。上司看到后,立即炒了他魷魚。憤怒的伊奧尼斯化名在社交網站臉書上發布了個人風格的說唱歌詞,歌詞內容充斥著清晰的暴力語言,目標暗指他的妻子、同事、幼兒園、政府和聯邦法律機構。
盡管這些歌詞帖子大多附綴了否認聲明,即歌詞只是虛構,并不針對某個真實的人,而且還附帶聲明伊奧尼斯本人在使用來自第一修正案的權利,但許多熟知他的人都認為這些帖子暗含威脅。當伊奧尼斯被前雇主告知聯邦調查局之后,聯邦調查局開始監控他的臉書并最終逮捕了他。他被起訴違反聯邦法條例——禁止傳播含有傷害他人的威脅的內容。該案上訴到最高聯邦法院是因伊奧尼斯的辯護律師認為言論是否為“真實威脅”的法律標準應是“客觀的人”是否認為他發布的內容具有威脅性。被告本人也認為應該檢測他的言論是否會被理解成威脅。經過了漫長的審判,2015年6月1日,該案件最高法院被駁回,伊奧尼斯是否有罪有待判決。
二、案件分析
(一)何為“真實威脅”
伊奧尼斯案中的一個復雜因素是法院尚未研究在網絡環境中“真實威脅”的定義。上一次評估“真實威脅”是在2003年的十字架縱火案。美國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設立了勘界標準:只要是“真實威脅”,就不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行為人還必須為此承擔刑事責任。為了保護人們免于暴力恐懼、阻斷暴力恐懼和降低暴力行為,最高法院對“‘真實威脅’”做了比較寬泛的解釋:那些沒有實行、甚至并不打算實行的暴力威脅,都屬于“真實威脅”。具體而言,根據法律條文:任何傳播含有威脅綁架或威脅傷害他人的人都應被處以罰款或被監禁不超過5年或者并罰。可見,刑法條文只規定了行為這一客觀要素,而對于犯罪心態完全未置一詞,正如法院意見所說的,單從“威脅”一詞出發,對于這一條款所要求的犯罪心態是無法得出結論的。當然,不能因為條文未對此做出規定就認為“真實威脅”在心理上不做要求,于是大法官們用刑法來解釋問題。
(二)說唱歌詞是否可作為證據使用
另一個微妙之處在于說唱表達方式,是藝術作品,還是普通言論,可不可以直接將說唱作品中的言論,作為證明犯罪意圖的證據?陪審員和法官反射性地傾向于認為說唱歌詞是一種藝術形式而不是證詞,正如伊奧尼斯在他給最高法院的上訴書里說道:“藝術是與限制相矛盾的。”然而研究顯示,近十年來,充滿暴力的說唱歌詞,越來越多地被司法機關用作不利于被告的罪證,而且不少針對業余說唱歌手,他們多為有色人種。法院、控方正通過司法力量將說唱定義成罪證,而不是藝術。
(三)來自伊奧尼斯的辯護
伊奧尼斯聲稱“威脅”一詞,根據定義,表達了一種強加傷害的打算,而在《第一修正案》下,政府必須證明他有主觀威脅的意圖,而他否認這種意圖,聲稱他寫的歌詞是在回應說唱歌手阿姆。同時,伊奧尼斯要求政府證明他真的有這種傷害他人的打算,而不僅僅是推理性懷疑。此外伊奧尼斯辯護人認為,在社交媒體這個語境里,發言人的“主觀意圖”更加模糊、難以確定。線上交流固有的非人格化特點,讓交流傳達出的信息更易遭到誤解。
(四)最高法院對此案的意見
美國刑法上,犯罪心態有四種:蓄意、明知、輕率、疏忽。最高法院認為將此案解釋為疏忽來給被告定罪是不可接受的。要構成“真實威脅”,行為人必須在主觀上對其言論是對他人的恐嚇具有一定的認知。例如,行為人如果認為自己是在開玩笑,那無論“理性的第三人”怎么看,都不能給行為人定罪。在這里,首席大法官羅伯茨特意指出,理性的人是侵權法上確定民事責任的判斷標準,刑法上確認責任應該采取的標準是: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誤的。至此,案件告一段落。由于該案定罪時法官給陪審團的指示中對行為人的主觀意圖沒有任何要求,采取的是疏忽標準,所以定罪的判決不能成立。既然如此,本案也就沒有了再去探討第一修正案的必要,于是案件發回重審,伊奧尼斯是否有罪有待判決。
三、總結
雖然伊奧尼斯案從頭到尾并沒有探討第一修正案一個字,但是它對言論自由的影響卻是不言而喻的。為何法官們會拒絕疏忽標準?判決書中闡述的刑法解釋路徑固然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還是強調言論自由的利益這一思想的主導。在言辭犯罪中,處于利益橫梁兩端的是言論自由與生命權。當言論自由被當作至上的利益,對于犯罪心態的要求自然會采取嚴格的標準;而當生命權、社會秩序等被當作至少與言論自由同等重要的利益時,對犯罪心態的要求就會采取更為寬松的標準。不得不說,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思路中,我們經常會看見的,是對于言者利益的強調,而不是對社會安定,事件中受害者利益的強調。這一判決的直接后果將是,執法人員要證明恐嚇犯罪成立將比以往困難得多。相應的,社交網站上恐嚇他人的言論也就更容易泛濫。值得注意的是,言論自由并非一切。與言論自由同等重要,甚至比它更重要的利益有很多。并非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應向言論自由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