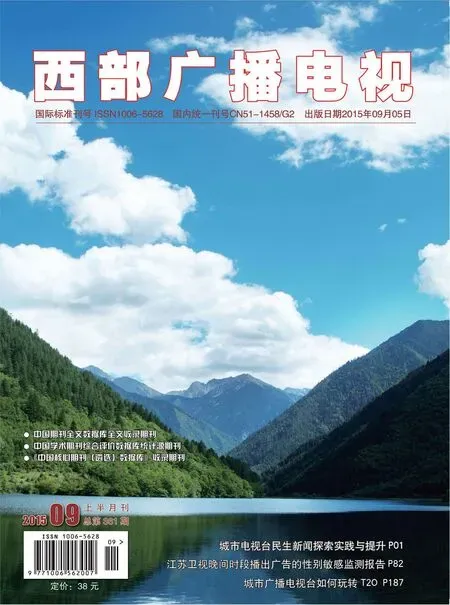新媒體語境下紀(jì)錄片敘事方式的演變
摘 要:畫面加解說、訪談加解說、客觀紀(jì)錄是紀(jì)錄片的3種經(jīng)典敘事方式。新媒體技術(shù)語境之下,自媒體打破了傳統(tǒng)傳播平臺的壟斷性,同時,新媒體傳播中碎片化、去中心化、個性化和多元化的諸多特征也構(gòu)成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語境,這些都在影響著紀(jì)錄片敘事方式的演變。
1 新媒體促發(fā)了微紀(jì)錄片的出現(xiàn)
新的技術(shù)語境加速了影像傳播的速度,微紀(jì)錄片正是適應(yīng)了更短小精悍、更快捷傳播的需求。同時,新媒體技術(shù)的發(fā)展也為眾多的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教程和工具,眾多創(chuàng)作者借助新的技術(shù)手段更方便地進行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和加工。拍攝設(shè)備的大眾化和簡便化以及后期制作軟件的日益“傻瓜化”打破了影像創(chuàng)作的技術(shù)壁壘,人人都可以成為影像創(chuàng)作者。得益于新的技術(shù)背景,影像創(chuàng)作和傳播都更加大眾化、私人化和自主性,也正是這樣的新媒體技術(shù)為微紀(jì)錄片的出現(xiàn)提供了技術(shù)可能。
新媒體的發(fā)展伴隨著新的文化語境,新媒體的發(fā)展同時也塑造著新的文化語境。一方面新媒體讓交流和傳播變得更加自由和民主,另一方面,新媒體傳播中碎片化、去中心化、個性化和多元化的諸多特征也構(gòu)成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語境。微紀(jì)錄片基于新媒體而存在,新媒體的后現(xiàn)代主義精神氣質(zhì)也深深影響著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微紀(jì)錄片的內(nèi)容和形式、題材及創(chuàng)作手法都深受其影響。
2 新媒體影響著紀(jì)錄片敘事題材的選擇
與故事片一樣,紀(jì)錄片也是屬于影視制作當(dāng)中的一種類別,倘若將故事片比作小說,則紀(jì)錄片就可以稱之為報告文學(xué)了。紀(jì)錄片以現(xiàn)實生活的題材作為講述內(nèi)容,在進行制作的時候不必對所講述的內(nèi)容做過度的渲染,一部優(yōu)秀的紀(jì)錄片常常因為其敘事題材的選擇得當(dāng)和敘事方式的有效利用。
隨著新媒體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得人類社會的交流和傳播可以在更廣的范圍、更短的時間和更寬廣的維度展開。依托于新媒體技術(shù),自主性和互動性更強的傳播平臺和自媒體蓬勃發(fā)展,視頻網(wǎng)站、BBS、APP、電子雜志、博客、微博和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為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和傳播提供了渠道。在此背景下,更多獨立創(chuàng)作者和更多私人化的選題開始涌現(xiàn),對傳統(tǒng)媒體來說不重要的、邊緣的、過于個人化的一些紀(jì)錄片選題大量出現(xiàn)在自媒體領(lǐng)域。可以說,新媒體讓紀(jì)錄片的敘事題材更加多元化和個人化。
3 畫面加解說的敘事方式重獲新生
紀(jì)錄片這樣的敘事方式曾經(jīng)在國內(nèi)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在進行創(chuàng)作時,多是先確定紀(jì)錄片所要講述的主題,其后創(chuàng)作工作者再根據(jù)主題加以文字說明并上報領(lǐng)導(dǎo)審核。經(jīng)審核批準(zhǔn)后可以開始進行紀(jì)錄片的拍攝工作。在對紀(jì)錄片進行后期制作時,根據(jù)所寫的文稿進行配音,再依據(jù)配音來進行畫面的編輯。此類方式有兩個弊端,一是過于重視文稿的作用,整個紀(jì)錄片通過較多的解說詞將內(nèi)容加以解釋。發(fā)展到后期,基本上演變成了圖文說解的形式,過分追求解說與音樂元素,對于能夠支撐片子的圖像與別的因素沒有投入關(guān)注,造成做出來的紀(jì)錄片失去了原來功能,而只是成了向觀眾進行說教的工具。二是就創(chuàng)作理念來說,紀(jì)錄片所呈現(xiàn)出來的內(nèi)容充滿了說教意味,而不是結(jié)合主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傳播。過分追求共性而忽視了片子本身的個性,使紀(jì)錄片的內(nèi)容過于統(tǒng)一,主題也較為單一,最終導(dǎo)致紀(jì)錄片的內(nèi)容過于泛泛,失去了可觀賞性。
然而在新媒體時代,由于制作周期的縮短和傳播速度的加快,畫面加解說以其制作周期短,傳播信息量大的優(yōu)勢再次獲得青睞。《舌尖上的中國》等一大批優(yōu)秀紀(jì)錄片都主要采用了這樣的敘事方式,在經(jīng)歷過猛烈的批判后,在新媒體時代和商業(yè)紀(jì)錄片不斷發(fā)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創(chuàng)作者開始重新認識此種敘事方式的優(yōu)勢。同時,“畫面加解說”也不斷通過更多的融合同期聲和采訪等要素讓敘事更加生動。
4 訪談加解說的敘事方式成為主流
訪談在敘事中的運用,使單純解說的比重下降,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強紀(jì)錄片的客觀性。此外,此類敘事方式,能夠使觀看者更多的了解過去以及未來,增強了紀(jì)錄片的渲染力。觀眾的需求可以在觀看過程中得到滿足,而且采訪與解說2種方式交叉,使片子更有節(jié)奏韻律。這種形式當(dāng)中的采訪也可以是發(fā)生在采訪人員與被采訪對象之間的言語溝通,把被采訪對象所講述的內(nèi)容合理安排在紀(jì)錄片當(dāng)中。有些紀(jì)錄片將采訪的元素加強,幾乎通篇使用這種方式來進行。因而采訪就相當(dāng)于紀(jì)錄片的敘事元素。如紀(jì)錄片《忠貞》,該片當(dāng)中將采訪貫穿始終,講述志愿者從被俘虜?shù)绞芷群Γ俚阶詈髿w國的經(jīng)歷。由于沒有過去的影像資料,并且講述的內(nèi)容又發(fā)生在以前,因而只能利用采訪作為片子的敘事工具。而有些紀(jì)錄片為了彌補畫面加解說這種方式的不足,將內(nèi)容元素與采訪相結(jié)合來完成紀(jì)錄片的敘事功能。如《廣東行》的第一集《開放市場》,片子當(dāng)中為了使所講述的內(nèi)容突出,因而采用了大量的聲音采訪。有些片子沒有過多使用采訪作為主元素,而是讓它承擔(dān)部分?jǐn)⑹伦饔谩?/p>
在新媒體時代,訪談加解說的敘事方式成為電視紀(jì)錄片、電視紀(jì)實類節(jié)目的主流敘事模式,這既是基于制作周期和制作成本的考慮,也有新媒體時代傳播特點的需求。
5 客觀紀(jì)錄的敘事方式更加深入
客觀紀(jì)錄的敘事方式重視紀(jì)錄片的客觀性與真實性,不贊成主觀因素的過多介入,反對過多地對紀(jì)錄片內(nèi)容進行解說,從而保留紀(jì)錄片的原生態(tài)。這就要求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工作者能夠?qū)⒆约喝谌氲奖徊稍L對象的實際生活當(dāng)中,能夠身臨其境地體會他們的思想與生活,并且將精華提取出來形成自己的題材。相對于故事片而言,紀(jì)錄片的取材內(nèi)容是真實的,它反映了被拍攝對象的生活,不存在虛構(gòu)。因此,倘若創(chuàng)作人員沒有進行細膩深度的探索,就很難制作出優(yōu)良的作品,此類敘事方式應(yīng)該是將主客觀進行了完美融合所表現(xiàn)出來的敘事方式。此類敘事方法對創(chuàng)作人員要求較高,不僅應(yīng)該具備技巧性的采訪手段,還要具備較深厚的采訪功底。進入正式拍攝環(huán)節(jié)的時候,要注意不要讓創(chuàng)作者的聲音和影像介入。后期制作編輯時,以故事型內(nèi)容展開講述,運用同期聲來取代解說。創(chuàng)作理念多從細微處著手,強調(diào)故事的個性化與人的差異性,主張故事情節(jié)化,這樣片子就具備了較強的觀賞性,以便吸引更多的觀看者。
盡管此種敘事方式的創(chuàng)作成本較高,但在新媒體時代,隨著創(chuàng)作渠道的多元化和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仍然有一大批獨立紀(jì)錄片人傾心于此種方式進行創(chuàng)作。并且在新媒體更加多元和自由的語境下,客觀紀(jì)錄的敘事方式一改過去僅僅記錄的通病,對社會現(xiàn)實和人生命運的觸及更加深入和大膽。
新媒體語境之下,傳播學(xué)五要素的變革對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全方位的影響,從類型到選題,從敘事到傳播,紀(jì)錄片正在發(fā)生著新的變化,其中敘事方式的變化除了新媒體的影響,也常常受制于成本的考慮。2015年8月,獨立紀(jì)錄片人李斌在微博上為自己的新片《瘋?cè)嗽骸钒l(fā)起了一次眾籌,短短幾天便超額完成了2萬元的目標(biāo)。新媒體正在為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提供著無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