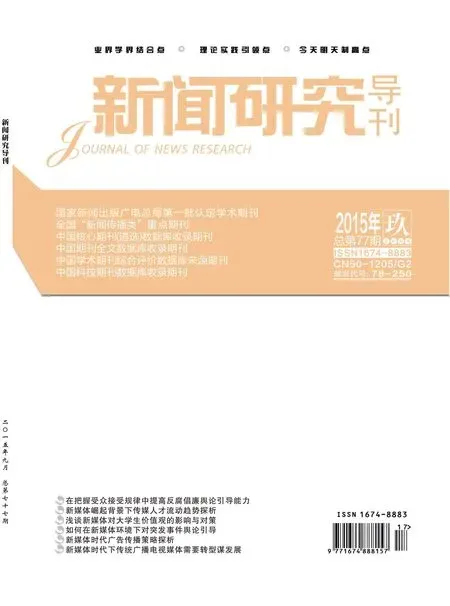民初報屆三杰之一——徐彬彬之再發現
摘 要:民國初年,在袁世凱對報界的高壓政策下,自清末以來以政論形式為主的報刊文章急劇萎縮,新聞通訊逐漸占據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涌現出一批知名記者,其中,徐彬彬與黃遠生、邵飄萍一道被譽為“報界三杰”, ①在我國近現代新聞史上留下不可忽視的一筆。然而,有關徐彬彬的研究,特別是有關他的報刊作品的資料是極少的。這與其在這一方面曾獲得的較高聲譽相比是不相稱的。本文通過所尋獲的、徐彬彬于20世紀40年代末發表在《申報》上,有關抗戰期間一些政壇人物和日偽政府的數篇作品,得窺其文章魅力之一隅,希望能夠借此為重新認識這位近現代史上的知名報人提供一點新的素材。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15)17-0294-01
一、從“洋舉人”到名記者
徐彬彬(1886~1961年), [1]譜名仁錦,字云甫,齋名凌霄漢閣,筆名彬彬、凌霄、凌霄漢閣、老宵、老漢、宵、漢、燭塵、一塵等。原籍江蘇宜興,因祖父應順天府鄉試而寄籍 ②直隸宛平,成為北京人。徐家為宜興世家望族,科舉興盛。徐彬彬的祖父徐家杰(字冠英,號偉侯)、父親徐致愉(字子怡)、二伯徐致靖(字子靜)均為進士出身,分別官至地方縣令、知縣及翰林編修,堂兄徐仁鑄(徐致靖長子)為翰林編修及湖南學政、徐仁鏡(徐致靖次子)為翰林編修。徐致靖父子三人為清末維新變法名臣,對徐彬彬日后走上新聞報國之路有重要影響。
徐彬彬隨父宦游,居于山東,接受了良好的書塾和家庭教育,于13時以第一名考中秀才。時值清末“廢科舉,辦學堂”,徐彬彬于是考入位于省城濟南的山東高等學堂,成績優異。后經過學部考試,取得舉人出身,成為“洋學堂”出身的“洋舉人”。此后,徐彬彬考入位于北平的京師大學堂,攻讀土木工程專業。因一次赴長江考察橋梁工程之時,為當時官場腐敗所觸痛,發文于上海《民生報》,疾呼當培養能夠應用西方引進技術的新式人才,方能興國。文章一出,回響非凡,上海、北京、天津的大報《時報》《申報》《大公報》等相繼而來約稿。最終,徐彬彬棄工從文,走上文章報國、著述為業的道路。
1916年起, [2]徐彬彬擔任上海《時報》和《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開始長期為兩報撰寫北京通訊,并很快就以其在《時報》的“彬彬特約通信”,與《申報》邵飄萍的“飄萍北京特約通信”、《新聞報》張季鸞的“一葦特約通信”并稱于世。徐彬彬的文章反帝、反袁、反封建軍閥、反日寇,著名報人徐鑄成稱其“分析局勢和各方面的利害關系清清楚楚,而且文筆恣意,鞭撻入里,刻畫那些軍閥、政客,如‘鬼趣圖’,個個躍然紙上。”
二、“內容雋趣、文筆曉暢”的彬彬通訊
與徐彬彬同一時代的很多著名人物對其文章常常不吝溢美之詞。“筆致風趣”、“富有情趣”、“文筆曉暢”、“文字優美”是最常見的評語。然而這些曾在20世紀前半葉的30、40年代,照亮過整個報壇的珍貴文章,未曾輯錄成冊過,如今能夠找尋得到的只是寥寥數篇。無論是時人還是今人的評語,都不能替代其作品原貌所能夠呈現出的魅力。以下所摘錄為徐彬彬于20世紀40年代末發表在《申報》上,有關抗戰期間一些政壇人物和日偽政府的3篇文章。值此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可通過這位以史家秉筆直書為做通訊、做文章原則的報人之筆,回望當時的中國政壇。
其一,講述自日軍攻陷華北至日本投降期間,王克敏、王揖唐、王蔭泰三人先后任偽“臨時政府”行政委長,以“古有‘世修降表’李家,今有‘專扮傀儡’王家,可云相映成趣”一語做結,喻譏諷于風趣幽默之間。又借“偽”與“假”二字的考辨,使日本在華侵占區實行統治的虛偽面目躍然紙上。
二十七年一月偽“臨時政府”出現,在國府以及中國人的立場上斥之為“偽政府”,理所當然。妙在日本報紙亦稱為中國的“假政府”,中國斥之為“偽”,乃“□偽”之偽,即駱賓王討武則天檄“偽臨朝武氏者”之“偽”也。而日人所稱之“假”,則韓信下齊愿為“假王”之假,即王□稱“假皇帝”之假,“假”者,權也,暫也,“假”之下文則“真”,“臨時”之下文為“正式”。故“假”字確有“臨時”之一襲。日人尚酸文,喜用古典,于是把他一手包辦的“臨時政府”亦稱為“假”了。而“假”與“偽”義本想通,似乎日人自認扮演傀儡,可云“不打自招”,妙不可言。(《申報》,1948年1月17日,第9頁:凌霄漢閣《偽與假》<摘錄>)。
其二,評價吳佩孚,不以其人之惡而掩其美。在徐彬彬的筆下,將吳佩孚堅決拒絕與日本合作,拒任偽職、大膽抗日的形象刻畫的精彩之至。
況老吳雖舊軍閥,亦有其倔強之本質,在敵氛包圍之下,談起新組織,亦以敵軍全部退出國境為第一條件。日人則斷章取義,抹去“條件”的話真以贊成新組織,“掩耳盜鈴”,打算就此捧上臺去,并舉行一個招待各界大會,請吳氏宣布“和平”大方針。及期,吳氏果被簇擁而出,當眾致辭,開口便教訓日本,滔滔不絕,左右見情形不對,幾名預伏之攝影者,將全景速入鏡頭,一面將吳氏由“其語未畢”之狀態中,挾之后退,更囑各報記者不可照錄吳語,后將照片洗出,另以代撰之詞發刊。此一幕怪劇,亦夠上“駭疾”二字,吳氏從此即被隔離,未幾而以病聞,以拔牙變癥聞,以逝世聞,繼之以大出喪等等。在吳氏如此收場,不失為硬漢到底。(《申報》,1948年1月13日,第9頁:凌霄漢閣《吳佩孚與徐世昌》<摘錄>)。
其三,借悼念熊希齡(字秉三),將汪精衛其人先時以激昂愛國示人,日后卻投日叛國、成為“漢奸”首腦的矛盾、多變形象,通過對比的手法予以鮮明地呈現。
“九一八”變后,綢以“一二八”,政府召集“國難會議”,熊氏被邀。時汪精衛在洛陽紀念週漬稅,忽云“一九一五年對日本之二十一條,系袁世凱所簽訂,為當今國難會議會員熊秉三所□署。此人尚在上海,如果到進此間,我們就殺掉他!”熊見報導,怒而且笑,即而致汪氏曰:“一千九百十五年為民國四年,弟于民國三年三月即已交卸國務總理,相距一年有余,此副署何人。公司查明政府公報,便知其誤”。一此事真是笑話,非尋常“張冠李戴”可比。按民四中日交沙,與日使日置益共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