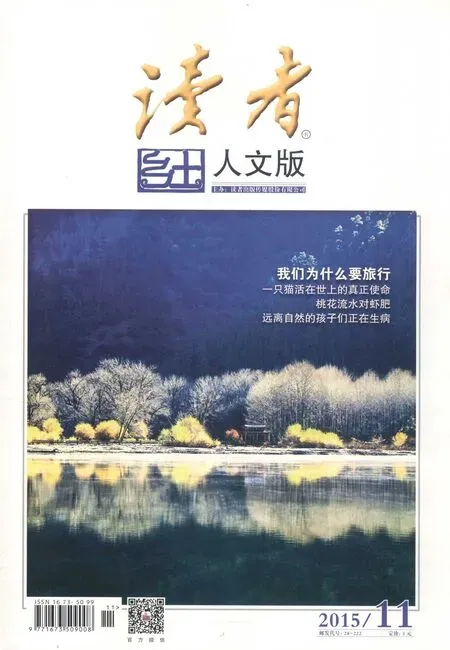朝花夕“食”
文/西 窗
?
朝花夕“食”
文/西窗

唐朝的宮女采集各種各樣的花朵,與糯米一起搗碎蒸熟,制成一種糕點(diǎn),名叫“百年糕”;楊萬里拿梅花蘸糖吃;慈禧發(fā)明了玫瑰甜醬;袁枚做過藤花餅、玉蘭花餅;張愛玲做過玫瑰燒,讓《金鎖記》里的七巧和三爺對飲;張大千不僅畫花,還親手烹花,和家中的廚師合制“蘭花鵝肝羹”。
吃貨們記下幾行字:“牡丹花煎法與玉蘭同,可食,可蜜浸。”“夜來香的花蕾可以煲湯,或者切碎攤進(jìn)雞蛋餅里。”如此這般,都是被韓愈的這個詞語教唆的:含英咀華。可人家說的是讀書,沒讓你真的去吃花啊。
春天,北方人吃槐花,南方人吃梔子花。
秋天了,北方?jīng)]花可吃了,南方的桂花“花氣熏人欲破禪”。吃桂花,參照桂花藕粉,在菜里、粥里、湯里、隨便撒一把。復(fù)雜的就做不來了。把白玉蘭花放在雞蛋、面粉調(diào)的面糊里拖過,在油鍋里一炸,金黃金黃的,撈上來,吃在嘴里脆生生的,它有一個很學(xué)究的名字,叫“白翰林”。玉蘭花也叫“木筆花”,能混進(jìn)翰林界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吃貨們太能掰了。
我沒吃過白翰林,但我吃過的花也不少。我曾生活在寡淡的年代,小時候雖沒怎么挨過餓,但饞過,吃遍野果還不夠,把山野能吃的花也都吃遍了。
金針花,就是黃花菜,自然不必說;瀑布般的紫藤花,拌飯吃;木槿花可蒸著吃,也可炒著吃;梔子花是近幾年吃到的,涼拌、清炒、蒸食,花樣挺多;紫云英俗稱紅花郎,地毯似的花錦,掐嫩苗炒來吃;杜鵑花可把花蕊扯了,幾十片花瓣一起塞進(jìn)嘴里,酸酸甜甜。
南瓜花,算正常的農(nóng)家菜。印象深的是在鳳凰,將它和著面糊油炸,吃了念念不忘。去年在西遞再吃,竟吃不出記憶中的味道。
永遠(yuǎn)難忘,娘和奶奶去山上摘金銀花時,都會帶回來野果子泡泡,它們和黃金白玉似的金銀花及其翠綠的葉子混在一起,既好看又芳香。
我的吃花經(jīng)歷不關(guān)風(fēng)雅半點(diǎn)事,只為果腹和解饞。
吃花有兩種,一種是“花是花”,就是說盤碟里看到的還是花,吃的時候多少有褻瀆美的感覺,暴殄天物似的,難以下箸;第二種是“花非花”,家常菜蔬,是生活本身,入腹是它的使命,坦然吃吧。
第一種吃法,往往是“文藝了不好吃,好吃了不文藝”。以我之見,對于那些已負(fù)責(zé)美的花,就放過它們吧。
我贊同美食作家沈宏非的觀點(diǎn),他在一篇談吃花的文章里說:“花是用來看的,不是用來吃的,不能太貪心。”若要人人吃花,怎么會有“黛玉葬花”這等絕世的風(fēng)雅事呢?
極喜歡李白的《山中與幽人對酌》:“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fù)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倘若他不是對花飲酒,是摘花飲酒,就大煞風(fēng)景了。
真戀花,和李白一道“花間一壺酒”,喝完學(xué)史湘云醉臥花叢里。
我覺得,抱著一束從街頭小販?zhǔn)掷镔I來的時令花,翩然走在夕陽里,那畫面絕對美過在餐桌前張嘴吃花的場面。
花開的聲音,讓蜜蜂去翻譯;花落的后事,讓流水去安排吧。
實(shí)在要吃花,就學(xué)川人,管豆腐腦叫豆花,管豬蹄叫蹄花。
(梁冰冰摘自新浪網(wǎng)西窗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