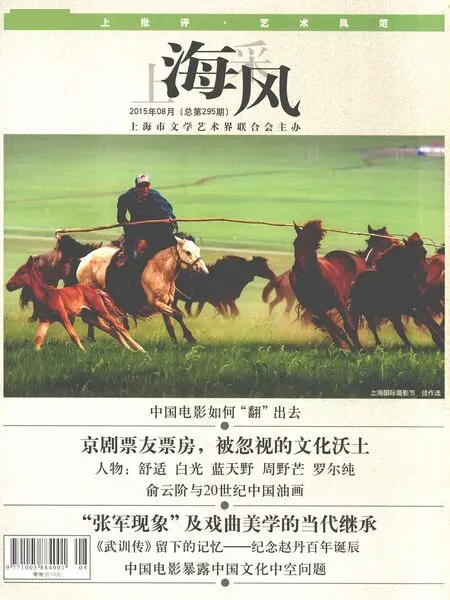油畫大師羅爾純的色彩、力度與人格
文/顏 榴
油畫大師羅爾純的色彩、力度與人格
文/顏榴
2015年4月27日,中國油畫界的著名隱士,今年85歲的羅爾純先生的藝術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這是他首次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畫展,筆者有幸參加了藝術展的開幕式和研討會。四個展廳,近三百幅作品的展示彌足珍貴,除了油畫,還有水墨畫,像是一部西畫與國畫的奏鳴曲。展廳里羅爾純的作品帶給人一種強烈的沖擊力與感動。他的繪畫色彩與西方大師擱在一起毫不遜色,同時他的技術表現、情感表達以及對繪畫的理解,獨步于當代畫家群。從這些跨越四十多年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羅爾純早年未囿于泛意識形態化的藝術創作方向的桎梏,中年后未迷失于中國繪畫界的時髦思潮。他幾乎排除了所有非藝術的干擾,只專注于繪畫的技術與藝術本身,從而給了我們一種純粹繪畫的美感。這種美感的呈現,一在于色彩,二在于力度。
羅爾純對中國繪畫界的最大貢獻是他成熟而完美的色彩。中國古典藝術講究意境,氣韻生動的美學體系同時也造就了一個黑白為主、色彩為輔的世界。但西方繪畫是個光學與色彩的美學體系,色彩是科學、詩學與美學的結合。西畫進入中國后,色彩范疇一直沒有太多突破,醬油色普遍存在于油畫作品中。上世紀70年代末,西方印象派及現代主義油畫原作第一次在中國展出后,畫家們才普遍意識到這一差距。羅爾純是他們那一代畫家(又稱“第三代畫家”)中跟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或者更早的后印象派藝術接氣接得最早,繪畫技術尤其是色彩上最過關的一位中國油畫家。他對于色彩的初步覺醒始于上世紀70年代(《桂林三月》),經過了10年的迷茫與摸索,在80年代嶄露風采。《西雙版納的雨季》突破了當時畫界較為沉悶的境況,把人們的眼睛照亮。之后油畫界內部引發了對色彩的關注,那時油畫家最渴望解決的問題是色彩。到90年代,羅爾純的油畫在海外引起轟動,得到認可。
從歷史維度看,民國時期的一大批油畫家曾經在色彩領域為之奮斗,惜戰亂與時事的變遷使多數人未能得以自我完成,即便是先驅林風眠先生也還停留在東方題材、東方美人上,基本表達的還是題材的視覺愉悅感,對色彩的復雜性未能揭示。1949年后,從徐悲鴻到“馬訓班”,中國油畫很長一段時間在尋求造型與政治歷史內涵的表達,沒有解決色彩的核心問題。但盡管如此,在20世紀后半葉,中國本土還是出現了兩位色彩過關的油畫家,筆者認為他們既受到了良好的油畫基本技法的訓練,又是有所表達的集大成者。第一位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的衛天霖,第二位是90年代以后的羅爾純。衛天霖早在上世紀40年代的靜物畫中,色彩技法已經成熟,到70年代他的花卉色彩爐火純青,發出一種深沉而燦爛的光感,尤其是他提煉的藍色調十分高貴。羅爾純一開始是從家鄉的雞冠花與紅土那里,獲得了精神的原動力,后來營造出彌漫畫面的紅色調,非常感人。衛天霖的“藍”與羅爾純的“紅”,堂堂正正,是這兩位畫家避免了食洋不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中國油畫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模仿難以避免,但只有既掌握了技法,又提煉出中國題材,構建出中國美學,才能產生堪與西方大師比肩的中國油畫大師。在藝術上受到吳冠中啟發的羅爾純因“形式感”獲吳先生贊譽。兩相比較,吳冠中的色彩更多具有裝飾性,羅爾純作為集大成者,提升了中國油畫的色彩品位,是不折不扣的色彩大師。
中國油畫一度深受印象主義的影響,包括早期印象主義簡單的感官愉悅。然而繪畫給人的不應只是愉悅,只有進入事物的結構方顯藝術的偉大,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簡約抒情,不及那種對勞動者的悲憫,以及參透大自然泥土、沾滿淚水與血的苦難含義的書寫。在羅爾純的畫作前之所以感到興奮,是因為他畫面中那種力度是中國幾代畫家的作品中都非常少見的,無論是雞冠花、植物、紅土系列等田園景象,還是苗族婦女與現代都市人的各種形象。隨著后現代藝術的進入,年輕一代畫家與中年畫家都在迅速轉型,在此過程中,藝術家對色彩、對大自然本身的感受都在減弱,中國藝術界很快地經歷了美學上的三級跳、四級跳,其激進程度已與世界同步。面對擺脫架上、扔掉畫筆的當代藝術潮流,羅爾純對布面油畫的立場一直堅守,這源于他很深的對大自然、對泥土的感情。他說:“我對農民有種特別的感情,我的鄰居都是農民,雖然我家里并不種地。”他提醒我們這片幾乎快要遺忘的泥土的存在,這片深沉和沉重的土地的存在。
我們時時能感受到羅爾純畫面里感情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像當年凡高給我們的感覺一樣。凡高革命性地使色彩變成線條,有強度有力度的線條。羅爾純其實也是使色彩真正有了塊面的質感,有了線條的硬度,而又來源于真誠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一般中國人對印象派藝術的接受更多偏于像雷諾阿那種對早期光影的抒情,也就是所謂甜美,對后印象派那種強調力度的抒情沒有合格的傳人,而羅爾純的抒情性是一種有質感有密度的抒情。正如凡高的偉大并不在于技術與色塊的強烈沖擊,而在于他對神學與哲學的理解內涵,塞尚對物質結構的強調也是基于神學支撐,從而這種抒情本質上是苦澀的,比早期印象派對大自然萬物的書寫有著更深刻的理解。羅爾純畫面中樹的三角形、錐形,樹像石頭一般的造型以及道路的扭曲與直線的確立,等等這些都擺脫了江南那種吳儂軟語式的抒情,獲得了畫面的深度與力度。
一位藝術家的人格決定了他的道路能走多遠,羅爾純藝術的價值還在于他的人格榜樣。西方大師為何地位崇高?在于藝術家與表達對象的合一,甚至是嚴絲合縫的自我物化,幾乎達到了物我兩忘的那種境界。從偉大藝術家的作品里往往能看到他們的人格畫像。塞尚就是圣維克多山與水果,向日葵痙攣般地燃燒就是凡高的生命。這種精神來源于西方人文主義最根本的一點——認識自我,尋找到自我,而自我只能通過犧牲、為藝術殉道來實現。塞尚作畫時,小孩用石子砸他,凡高依靠弟弟的接濟過活。通過藝術認識你自己,實現自我拯救,中國畫家最缺乏這種精神。羅爾純在這一層意義上與西方大師接近,他把自己擱在湘西的紅土、村寨以及廣袤的土地與狹長的天空里,融進描繪的對象世界里。
羅爾純是一個孤獨者,他雖然也曾以鄉土表現題材的作品得過全國美展的各類獎項,但始終處于邊緣的位置上。淡泊名利、自甘寂寞,捍衛了繪畫的純粹性。可以說,色彩就是羅爾純的全部美學、道德以及人性的追求。他那殷紅的雞冠花與彎曲的大地帶來人性的感動,他筆下的土地與植物就是在謳歌生命。很難想象,一個人在60歲之后,感情開始爆發,技巧那么的嫻熟,形式感非常考究,畫面非常成熟,還具有某種年輕的情感。這100年來,中國繪畫界不缺題材,最缺乏的就是情感的強度。這或許是有人說羅爾純是東方凡高的原因。這種稱謂是否準確不重要。凡高幾乎更改了印象派的修辭,對人類繪畫作出了巨大貢獻,羅爾純作為一個繪畫大師能改變中國繪畫的面目嗎?他就像停留在淺水域的鯨魚,而那片水域的面積太小,容不下他內心的規模和情感的強度。然而羅爾純從來就不懂得靠權力學以及利用有效的行政資源,甚至他難于應付一些投機畫商的欺騙與隱瞞。
對羅爾純先生的敬意隨著我對油畫的理解以及對中國油畫百年歷史的探尋而與日俱增。由于政治歷史的原因,20世紀許多畫家命運不濟,或被邊緣化,或被耽誤,他們也容易在政治上被定性后,夸大受排擠的成分。但藝術史評價藝術家的標準是作品,只有作品是最大的標準,比政治對藝術的結論更靠譜、更長久。有人提到羅爾純現象,其意在于說他不幸,但這恰恰是他的幸,他的自我邊緣化維持了對藝術本身的堅守,所謂“戲大于天”(北京人藝的名言),繪畫大于天,藝術命題具有超越政治歷史命題的獨特內涵。
藝術史永遠存在著某種不公平的現象,巴赫當年的沉寂、凡高當年的貧困……這些現象都不重要,真正的藝術家往往領先他所在時代的100年。與羅爾純藝術展幾乎同時,美國畫家大衛·霍克尼來京開展,所到之處備受擁躉,中國美術界對這位波普藝術與嬉皮文化的英國傳奇畫家的興趣遠遠大過于本土藝術家。然而,中國繪畫界不缺大師,在美術館不無寂寥的展廳里,人們似乎還沒有意識到羅爾純這位謙卑的繪畫大師的存在,不過,這絲毫不影響他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