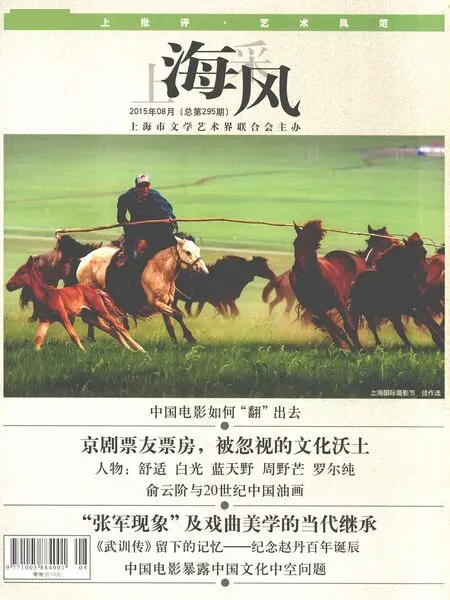附錄:舒適,不求人間舒適
文/許成章
附錄:舒適,不求人間舒適
文/許成章
老藝術家舒適溘然長逝,驚悉噩耗,黯然悲慟,昔日交往的情景,不由地浮現于腦際……我和他相處的日子不多,先后三次,相加起來也不過四十余天,然而,他留給我的印象卻非常深刻。
1983年夏末,上海電影制片廠準備拍攝黃梅戲神話藝術片《龍女》,舒適是這部影片的導演,作為編劇之一的我,與他初次相見在合肥稻香樓賓館,時逢溽暑,他卻滿面春風,交談中,絲毫不以老藝術家自居,出言親切,神情和藹,剎那間,縮短了彼此之間的心理距離,我感到這位長者既可敬,又可親……這次他是專程來約作者到上海修定劇本的,僅僅逗留了十多個小時,當夜便匆匆返滬。原來他是上海盧灣區老年籃球隊的中堅隊員,隔日有場與少年隊的比賽等著他的哩。
幾天后,我們一行三人,遵照約定的日子到了上海,舒適已在車站相迎,并為我們的住所和生活作了妥善安排。我們落腳點在安福路上影廠文學部,舒適辦公點在漕溪路上影廠廠部,兩點之間有好幾公里的路程。他一面抓攝制組的案頭工作,一面抓劇本修改,足蹬單車,兩頭奔波,時令入秋,氣溫未減,他短褲汗衫運動帽,精神抖擻,活脫是名訓練有素充滿活力的運動員,令人難以置信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舒適為人隨和,沒有架子,進進出出,熟人特多,大伙都叫他“阿舒”,喊的順口,應的自如,這是一種十分親昵的稱呼,他和門衛格外親切,每次見面,互道問候,我分明覺得在他周圍似乎不存在隔閡。
《龍女》原是六場舞臺劇,改成三十六場電影本,我們胸中無底,可舒適心中有數,他和責任編輯小謝費了不少時間,為劇本電影化,逐場列出修改提綱。我們照著提綱一場一場地改動,改一場,他倆看一場。尤其是舒適,他白天沒空,就利用晚上休息時間,看得那么認真而細致,每每第二天清晨,我們就能聽到他的中肯意見。舒適的知識面很廣,然而謙虛恭謹,從不輕易否定或擅自改動詞句,總是以商討的口吻來啟發作者。我記得在修改過程中有兩件小事,盡管時隔三十多年,至今仍記憶猶新:第一件,劇中有一場“雨后定情”的戲,書生姜文玉聽罷龍女傾訴愛慕之情后,隨之唱出:“公主美意我心領。”舒適覺得“心領”二字,未能充分表達男主人公的受寵若驚之情,甚至還有那么一點婉言謝絕之意,他建議略加改動。怎么改動?我們一時想不出準確的詞,他成竹在胸地說:“改‘愧領’可不可?”當然“可”了,“愧領”比“心領”更為貼切,有情有意,一字千金、我們自愧弗如。第二件,為表現主人公才思敏捷,修改本中加了一場“殿試”的戲,導演提示:讓姜文玉金鑾殿前對楹聯,這副對聯,既要表現書生的學識廣博,又要與劇情相吻合。我們編了一副,雖對前者有所體現,但未免游離于劇情之外,可又苦于一時想不出恰當的對聯代替,權且湊乎。舒適深知作者的甘苦,并未否定,而是說再斟酌斟酌……幾天之后,他興高采烈地遞來一副對聯,讓我們推敲。我們一看,果然是副“兩全齊美”的佳聯:“雛鳳學飛,萬里風云從此始;潛龍奮起,九天雷雨及時來。”這是他連夜翻閱多本書籍,從《楹聯趣話》中摘來的。說真的,從舞臺到銀幕,劇本修改過程中,他付出的勞動,決不比作者少,然而,他百般推卻不愿署名。這種高尚風格,著實使我們感動和汗顏。
舒適性格開朗,豁達大度,間歇時,與我們談笑風生,他的“普通話”講得標準,“上海話”也說得流利,與北方人、南方人皆有“共同語言”。十年浩劫中,挨過批斗,當過幫廚,受過罪,吃過苦,他回憶起來有滋有味:“嗨!那真是吃得下、睡得香、清閑極了!”說起已故夫人慕容婉兒病中情況,眼眶盈淚,頗為動情:“唉!疼痛有時會產生巨大的力量,婉兒患癌癥臥床已久,一日,疼得居然蹦起身,站在床上,握拳撫胸……”講到現在的夫人鳳凰,美滋滋的,說她戲稱他為無“恥”之人,說著隨手脫下口中的假牙,果然“無齒”。唯有一件小事,令他痛心,在“五·七”干校時,有一回適逢假日,他被指名留在干校,學習《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原來這天,有位外國元首路過上海,所謂“學習”,不過是“工宣隊”使用的一種“防患于未然”的手段罷了。事后,他知道底細,深感知識分子的人格遭到褻瀆……至今提起,仍音顫聲啞。
九月中旬,劇本修改,基本定稿,人物造型、服裝設計業已完成,他馬不停蹄地帶領攝制組,奔赴福建沿海選擇外景拍攝點,其時,排戲、投拍、分鏡頭、總格調以及各行當協調安排,已在導演的運籌帷幄之中……影片于翌年夏天拍攝完畢,剪輯后,經有關部門審定,列為慶祝國慶35周年的獻禮片。
1984年9月中旬,《龍女》公開放映前夕,舒適不辭勞頓,千里迢迢攜樣片來到作者當年工作所在地(安徽泗縣)試映,小城哄動,萬人空巷,爭睹老藝家的風采。舒適和我又見面了,就像初次見面那樣,仍然行色匆匆,只逗留了一天一夜。不用問,還有許多待辦的事情等著他哩。相見時難別也難,分手時,我請舒適代為問候他夫人鳳凰安好,并贈他一副由書家寫就的對聯:
舒適不求人間舒適,
鳳凰但作火中鳳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