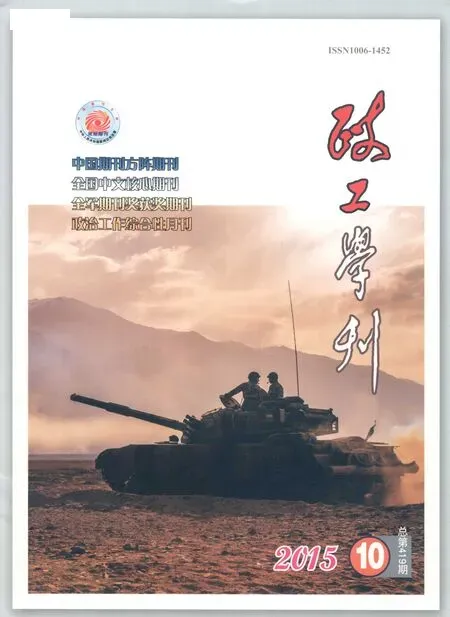“海上絲路”安全形勢與利益維護
☉廖世寧
“海上絲路”安全形勢與利益維護
☉廖世寧

2013年9月至10月,習近平主席出訪中亞四國、印尼、馬來西亞期間,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宏偉構想。這一戰略的提出,是習主席和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科學判斷,在國家改革步入深水區、國際形勢進入轉折期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國家戰略,是實現中國夢以及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藍圖。“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兩年來,已經發揮了巨大的牽引作用,由構想向現實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海上絲路”的重要地位
根據2015年3月中國政府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21世紀“海上絲路”有東西兩個重點方向,西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經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東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經過南海到南太平洋。與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相比,“海上絲路”具有尤為重要的戰略意義。首先,它與中國正在大力推行的海洋強國戰略相契合,順應了中華民族開發海洋、經略海洋的戰略需要。海洋是未來人類資源的接替區,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海上絲路”與海洋強國戰略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二者互為補充,互相促進。其次,它途經中國海外投資和能源運輸的重點區域,直接影響中國能源和經濟安全。據統計,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有30多條海上航線通達世界150個國家的1200多個港口,對外貿易90%通過海上運輸,其中“海上絲路”所經的北非和中東是中國重要的能源進口地區,經過這條路線進口的原油占中國進口原油總量的66%。再次,它所經過的國家和地區大多為世界戰略要地,是大國競爭的重要舞臺。東南亞、印度洋周邊地區被稱為世界地緣戰略的邊緣地帶,歷來是大國競相爭奪的焦點區域,地區矛盾相互交織。這種狀況決定了“海上絲路”具有戰略地位的極端重要性、國際斗爭的復雜性和安全形勢的嚴峻性。總的來看,隨著中國總體實力不斷增強,軍事實力不斷發展,應對風險的能力不斷提高,我們既要對國家捍衛海外利益的決心和能力保持信心,同時對面臨的嚴峻形勢也要充分估計。
海上安全形勢的重大機遇
首先,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海上安全,實施了有力的宏觀籌劃與指導。國家將海洋作為重要戰略方向,從理論上,深入研究海洋發展戰略,出臺了相關政策;從領導上,建立了領導機制,加大了領導力度;從政治外交上,加大了統籌與行動;從建設上,整合管海力量,成立國家海警局,加大力量投入與協調。其次,中國軍隊、特別是海空軍及遠程投送力量的建設、發展與運用,為海上方向安全奠定了堅實基礎。從戰場準備看,已由近至遠,逐步展開,對西沙、南沙加大建設力度并常態駐守;從兵力行動看,已經實現海軍常態化的護航行動,陸軍常態化的維和行動,海空軍常態化的參加重大國際災難救助、搜尋等行動,成功實施多次撤僑、護送化武行動;從裝備發展看,各軍兵種遂行海外行動能力都有長足發展;從保障機制看,海上補給與碼頭保障、空中航線與通信導航保障等都進一步完善。再次,中國的國際地位、處突機制、民間交往等,都為海上安全建設創造了良好條件。
海上安全形勢的嚴峻挑戰
美國加緊在海上方向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成為威脅與挑戰中國海上安全的源頭。近年來,美國推行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意圖圍堵中國的發展空間,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在外交、軍事、安全、經貿等領域實行了一系列新舉措。如強化《日美安保條約》,拉攏日、韓、菲、澳等國締結“小北約”,打造環繞中國東部的“三條島鏈”,構建從日本東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新月形”包圍圈,插手東海、南海問題,駐軍澳大利亞、重返菲律賓,炒作“空海一體戰”、離岸作戰,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等,意欲繼續主導亞太政經格局,遏制中國的發展崛起。由于美國對地區事務的直接干預和選邊站隊,慫恿一些國家利用地區矛盾與中國為敵,導致中國周邊安全問題和矛盾不斷激化,海上安全問題不斷升溫。可以說,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和防范是中國海上安全問題的根源所在。
地區大國對中國走向海洋存有敵意,從海上方向對中國進行制衡和牽制。日前,日本安倍政府強行表決通過了安保相關法案,右傾化日益加劇,并大力加強軍事力量建設,軍事實力不斷提升。同時,日本以釣魚島為借口,不斷加強針對中國的戰備建設,加強西南方向布防的監控,與美國開展以登島為主要內容的聯合演習,以中國為假想敵的企圖日益明顯。日本還在南海、東海等周邊問題上進行攪局,拉攏菲律賓、越南、印度等國家與中國為敵。
印度是有著濃厚大國情結的國家。隨著經濟發展和實力的增強,印度不甘心于地區大國的角色,把“立足南亞、控制印度洋,爭當世界一等強國”作為國家戰略目標,全方位調整軍事戰略,將軍事戰略的重點由陸地為主轉向陸海并重,積極向中亞、西亞地區滲透軍事力量,力爭在大國角逐中搶得一席之地。印度將印度洋及其周邊視為本國的勢力范圍,對中國在印度洋的活動高度警惕。這就增加了中國“海上絲路”通道安全的不確定性。
周邊國家積極發展海軍,大力爭奪海權,控制歷史上屬于中國的島礁、領海,影響中國海上通道安全。“海上絲路”所經地區同時也是民族矛盾突出、局部戰爭和熱點高度集中的地區。尤其是個別國家不尊歷史、不照法理、不顧承諾,妄圖以小搏大、以先占形成事實。
中日釣魚島爭端、東海劃界爭端、南沙島嶼爭端等問題持續升溫,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問題上不斷采取進攻性態勢,挑戰中國忍耐底線,推動地區局勢不斷升溫。為加強對海洋的爭奪,各國紛紛加強海軍建設,推動了地區軍備競賽不斷升級。
周邊地區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在東南亞,中國傳統友好國家緬甸局勢持續動蕩,與美國關系十分微妙,直接關系到中國周邊安全穩定,成為影響中國東南方向戰略通道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南亞,印巴矛盾長期持續,阿富汗安全環境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隨著美軍撤出重新抬頭,安全形勢不容樂觀;在中東,由民族和宗教問題引發的矛盾沖突時有發生,伊核問題、巴以問題、伊拉克問題等熱點導致地區局勢長期動蕩,“伊斯蘭國”異軍突起,占領了伊拉克境內大片地區,威脅伊石油產地安全。
“顏色革命”有繼續蔓延趨勢。近年來,美國企圖將“顏色革命”引向其他地區,在美國的推動下,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巴林、埃及等國家發生了“顏色革命”,先后推翻了4個國家政權,敘利亞、約旦等國也爆發了內亂或沖突。美國幕后推動“顏色革命”的目的,既有扶植親美政權為本國利益服務的考量,又不排除搞亂中國能源產地和投資目的地、為中國發展設障的圖謀。
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突出,對地區安全產生不可忽視的溢出效應。除了傳統安全威脅之外,海盜和海上犯罪、海上自然災害、海上重大安全事故、海外疫情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成為影響“海上絲路”的重要因素。
保障中國海外利益
“一帶一路”戰略的建設是一項重大的國家性戰略,這一戰略能否取得成功,安全問題是先決條件。為此,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必須把海外利益的保護作為重中之重突出出來,做好充分準備,有效維護海外利益。
以強大的海上軍事實力為后盾。海上力量能夠為海外利益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和支撐。我們需全面提高海空軍遠海作戰力量現代化水平,不斷增強遠海機動作戰、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能力,形成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堅強的后盾和實力支撐。
建立海外利益應急聯合保護機制。國家海外利益的保護涉及駐外使領館、軍隊、中資企業和駐外機構以及個人等多方面行動,具有很強的復雜性和聯動性,必須多個部門聯動和密切配合才能順利完成。這就要求在國家層面建立融合外交、軍事、商務、交通、企業等各個部門為一體的海外利益保護機制,形成各方聯動、相互配合的局面,有效維護中國海外利益。
(摘自《軍事文摘》,題目和內容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