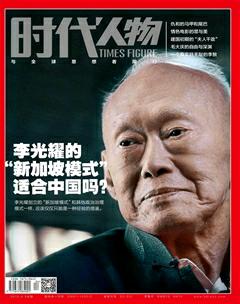3·15晚會,“選擇性揭黑”仍將繼續
鄭東陽

3·15晚會這樣的舞臺已經成了體制內媒體隱形權力的一部分,讓執掌權力者放棄權力,無異于與虎謀皮。
雖然在社交媒體上充滿了爭議,但這并不妨礙每年一度的央視3·15晚會成為除春晚外這家國家電視臺制造的最重大的議題。
對這臺晚會,輿論呈現出兩極化評價——在一些上了年紀的居民眼里,央視3·15晚會更像是一次消費者維權、甄別騙局的常識教育課。而在社交媒體上,則是網友們各種“3·15”晚會內幕的陰謀論和揣測。被點名的企業紛紛在第一時間進行回應,但回應中多少流露出企業對央視報道的被動接受和隱含的無奈。一些輿論對央視審判的角色表示質疑,對其“選擇性揭黑”更是報以不信任的態度。尤其是對一些洋品牌的點名,幾位主持人總會不知不覺地在言語上拔高到民族大義、國家歧視的層面。
因為特殊的體制和國情,在權力不斷釋放市場的初級階段,引入一些新聞專業理念的媒體在源源不斷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利益的衛道士,如3·15晚會抓反面典型式的做法確實起到了震懾不良企業,傳播維權觀念的效果。但市場越來越開放,它的弊端也開始逐漸顯露,人們質疑,消費者權益日,是否還需要類似公共審判、游街式的做法?央視應該在3·15這一天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3月13日下午,《西部商報》記者在暗訪中發現,甘肅會寧縣交通局副局長在工作時間看黃片、玩游戲。還在該局長的硬盤中發現存有200多部黃片。兩個媒體的影響力不同,報道的群體不同,但扮演了同一個角色:公權力的化身。如果說央視在3·15晚會上所展現出的是質檢總局加工商總局的意志,《西部商報》更像紀委、糾風辦。
許多批評的聲音總是從新聞專業主義來衡量央視,批評央視居高臨下扮演審判者。但從效果以及晚會前后的議程設置、官方配合力度來看,3·15晚會和春晚、新聞聯播沒有什么本質不同。央視此刻扮演的角色不是獨立調查者的角色,而是體制內權力設置的一個環節。而且,無論是在北京或者地方,黨報、市場化報業集團的管理者有不少是兼任宣傳要職的官員。
從這個角度說,對類似媒體在特定時期的一些舉動用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去解讀是費力且徒勞的。但央視還戴著一頂市場化的帽子,這讓觀察類似的問題的角度變得稍微復雜了一些。與醫院、高校等事業單位相比,媒體的市場化程度較高,但其權力和體制的色彩同樣也比公共服務色彩高。3·15晚會和春晚一樣有商業價值,因此央視又是消費者維權的裁判員,還是參與廣告市場競爭的運動員,以至于一些網友質疑“上了央視廣告就不會上3·15晚會”,但這并不意味著整個議程設置是出于商業邏輯,只能說增加了人們的不信任程度。
相比之下,《西部商報》暗訪官員作風的報道更簡單。在媒體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城市,許多媒體扮演“喉舌”外,同時也是體制內的另類監督者。有不少媒體從業者更是把自己當成基層部門的“紀委”、辦案者。《西部商報》可以暗訪縣科級單位,但絕不會暗訪和自己同一級別或者比自己層級高的省直政府部門。央視3·15晚會或許可以曝光大型央企,還會批評地方監管部門的不作為,但矛頭絕不針對國家質檢總局和工商總局。
許多傳統媒體在探討生存危機時,也有不少被視為體制內一員的“新聞工作者”依然在熱衷探討職稱、級別等話題。一些被權力賦予權威的媒體的權力似乎比公檢法還大,對于被曝光的個人和法人來說,很多時候沒有可辯護、商榷的余地。中國有不少起訴市場化媒體侵權的案例,但極少有黨媒被起訴的案例。就像許多媒體討論高校去行政化,但他們的一把手依然是體制內的官員,哪怕是被視為市場化媒體標桿的南方報業集團。
理論上,扮演3·15晚會角色的應是一些獨立第三方機構,但類似3·15晚會這樣的舞臺已經成了體制內媒體隱形權力的一部分,讓執掌權力者放棄權力,無異于與虎謀皮。除非有更高的權力要求放棄,3·15晚會還會準時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