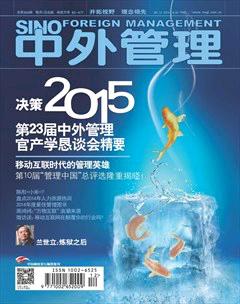互聯時代傳統企業的新領導力
鄧純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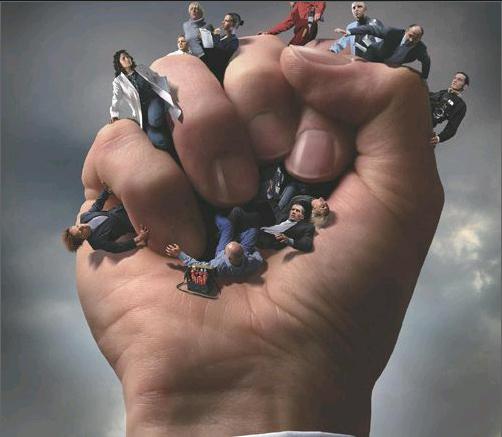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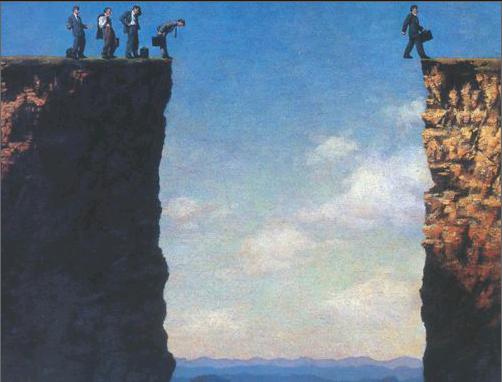
“砸電腦”的金蝶與O2O的雷士
楊光:傳統企業具有不可復制的全產業鏈優勢,但在互聯網時代,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技術和新模式的挑戰和顛覆。我們在談領導力之前,希望各位老總從自身行業出發,來解析一下在各自行業中遇到挑戰之后的應對之道。
王冬雷:照明行業確實面臨著顛覆性的技術革命,預計不到3年時間,LED產品將成為絕對的主流,如今我們雷士的產品已經四成為LED產品,這個比重還將不斷加大。但比這個顛覆更可怕的地方是什么?是商業模式的顛覆,是移動互聯網時代對傳統行業的商業模型的顛覆。
比如:雷士在全國3000多家專賣店將會面臨著移動互聯O2O技術的改造。而從零售業的轉型來看,為什么不僅僅是技術會改變行業,我想還必須回到零售的本質,無限接近客戶,服務客戶。因此我們行業面臨的顛覆就是:必須回歸客戶需求的本質,這也是未來幾年我們努力的主要方向。
徐少春:說到全新的行業挑戰,對于金蝶而言是向移動端做徹底轉型。
最近4年時間里,我們早已孵化出一系列移動端的產品,比如:全國市場占有率第一的面向個人的記帳軟件——“隨手記”。還有中國最大快遞查詢服務——快遞100,此外在云端的ERP還做了很多部署。
但是轉型到今天,特別是深入到我們的內在流程,我發現我們一些研發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思維瓶頸還沒有打破。所以在今年5月4日我自己首當其沖跳上公司前臺,把自己的筆記本電腦給砸了,一直到現在為止,我不再用PC,單單就憑一部手機鬧革命。這樣無形中給公司員工下達了最后通牒:從我摔電腦開始,你的思維要轉換到移動端,不能像以前那樣工作和思考。
我認為顛覆自己的不是別人,就是自己。一個公司衰敗,絕對不認為是由于別人給他造成的壓力和競爭,很大程度上是企業內部出了問題。所以一個企業的內部思維習慣、行為習慣、組織文化發生改變,企業才有可能根本改變。我覺得讓市場發生改變,應先讓自己改變,而讓自己改變,首先要讓自己的內心改變,心改變了行為就會改變,環境就會改變。
變革時代的領導力重塑
楊光:當行業發生巨大變革時,領導者必須重構組織形態和經營模式,必須對行業未來進行深刻洞察,為未來而變,為客戶而變。但這種變革時代,對領導力的挑戰和沖擊格外劇烈,甚至會出現重重危機,領導者在主導變革時,會被周圍的員工乃至合作伙伴與客戶質疑,面對這種情況,作為領導者該如何應對?
印建安:肯定是第一時間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比如:團隊不能夠理解,為什么不理解?前期團隊培養和團體學習的過程中,為什么沒有對變革有充分領悟與認可?當發生不理解時,是否能在團隊里進行有效的溝通并及時解決問題?
我們在轉型初期,要砍掉很多業務,甚至關閉了許多車間,然后把非核心業務統統外包。很多員工非常不理解,我們就組織大家通過多種模式來進行討論和溝通,最經典的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組織大家觀看《南征北戰》這部電影,為什么看這個電影?是想告訴大家,做企業和戰爭一樣,為了整體利益有時候必須放棄局部利益,必須有所舍棄。通過這樣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模式讓員工感受到企業變革的必要性。
當然除了日常和普遍的溝通之外,我們也需要用數字和報告來說話。
比如:我們在轉型過程中,第一個關口就是做工程總包,為客戶提供系統解決方案而非僅僅提供產品,很多員工并不理解這么做的必要性。為寶鋼提供了第一個系統解決方案之后,我們趁熱打鐵拿出了分析報告,明明白白告訴大家,這樣做為客戶提供了什么附加價值和高效服務,又為我們自己提供了哪些超額利潤。很鮮明的對比之后,大家發現,一個只做幾個月的工程,比以前做一年的產品還要賺錢,當然就開始支持轉型。
實際上,企業不是一個人做成的,需要團隊的力量,我們要獲得客戶的接受和員工的支持,就必須拿出真東西,光說漂亮話沒人會相信。
徐少春:我認為,作為領導者必須能夠預見未來,果敢變革,這也是我們從4年前就開始轉型的原因,我們不是今天才發現移動互聯這個方向,而是早有部署和準備,不僅僅在技術層面,在整個市場和營銷策略層面,我們一直都在做準備,因為軟件這個行業的競爭激烈程度,大家都有所了解,你一不留神可能就真的很難追趕。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領導者首先自己要有好的狀態,首當其沖要有好的身體和心態。
談到心態,我的經驗是:要想順利應對變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信任自己和他人,信任自己很好理解,信任他人則需要不斷學習,很多企業的老總在做大之后都可能出現一個問題——引入空降兵,以為這樣可以增強企業實力,后來發現,你最值得依靠的人永遠是和你長時間一起工作的人,只有這些一直在你身邊的人,看似沒有那么亮眼和出彩,但在風暴來臨時,他們是最堅定的和你一起戰斗的人。
上一個月我去劍橋學習進修一個月,這是我多年來離開公司時間最長的一個月,和公司的其他領導者幾乎沒有聯系,我發現效果很好,他們做得很出色,因為對于企業的使命已經在10年乃至更長時間里,在他們的心中有了烙印,我所要做的就是充分給予授權,充分給予他們信任。
互聯網思維是一種回歸
楊光:說到顛覆,就不能不提所謂的互聯網思維,特別是對傳統企業而言,全新的思維模式將顛覆組織形態和人們的心智,也將改變經營業態。那么,在這個過程中,什么才是各位心目中互聯網思維的精髓?互聯網思維又將如何影響我們的經營模式和管理模式呢?
王冬雷:這個問題很關鍵,領導力的體現必須依賴環境的配合,無論是現實空間還是虛擬空間,核心都是你要帶隊伍、搭班子,然后生產產品或者提供服務以滿足市場需求。我想即便是互聯網時代,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本質。
互聯網思維的精髓在于:你不是僅僅關起門來和同行去競爭,你的競爭者可能來自于你不知道的行業和領域,新技術的不斷顛覆,讓企業不能再以原來的模式去運營。
面對這樣高度開放和透明的競爭環境,企業家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善于利用形勢和先進技術順勢而為,既沒有必要固守傳統,也沒有必要一味求新,而是要了解,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到底在哪里?是在技術和產品上,還是在整個供應鏈上?我們要保持一種包容心態,夯實自己的能力,但善加利用各種資源,和時代一起革新。
印建安:講到互聯網思維,大家覺得這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似乎要和傳統思維決裂,其實大可不必。
我個人認為,互聯網思維不是創新而是回歸,回歸人類的本性需求。工業時代的批量化、規模化的生產和運營模式,讓每個個體的本性和需求一定程度上被抑制和湮滅了,而如今利用更加先進的技術和生產模式,個性化、定制化成為了主流。
對于企業而言,這其實也是對于客戶需求的一種真正的回歸和重視。比如:我們也曾大膽暢想,未來我們的機械產品可能會變成免費的,我們會依靠個性化服務和方案來賺取更高的利潤,這在目前看很大膽,但未來也許就會成為現實。
方興東:我們最近一直在研究的一個核心課題就是:網絡空間的領導力。互聯網思維對于傳統企業的沖擊,在于我們的交流模式和連接模式都在改變,我們不再像以往是那種直線型或者金字塔形的組織形態,我們生活在一個錯綜復雜的數據網和信息網當中,我們與客戶的關系維護也變成了必須360度全渠道跟蹤,我們需要在其中不斷接受顛覆式創新對我們的沖擊。
那么我們如何應對呢?我想還是必須有一種清晰的認識,認識到在這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世界中,我們作為領導者必須構建屬于自己的核心領導力,這種領導力絕對不是僅僅針對流程或某項具體產品的,而是根據時代需求和客戶屬性,以及市場現狀來確定的一種最富有競爭力的運營模式。
比如:微軟雖然曾經技術領先現金流充足,但它的產品和很多服務如今卻面臨關閉的命運,它本來最有可能成為全新互聯網時代的弄潮兒。而馬云沒有那么復雜的產品與技術,卻打造了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成功的網絡平臺,這兩者的分別不言而喻,高下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