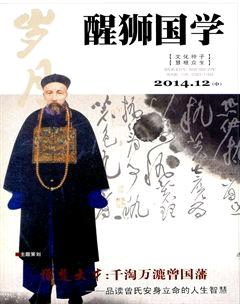從富厚堂看曾國藩的智慧
張榮生

毅勇侯第體現了曾國藩的建功立業
富厚堂地處湖南雙峰縣荷葉塘,從半月塘的拱橋上望去,腳底是一片荷花,在群山環抱之中,富厚堂的青磚、粉墻、青瓦儼然在目。到得堂前,大門上有“毅勇侯第”的巨匾,因曾國藩統帥湘軍攻陷天京平定太平天國,同治皇帝封曾國藩為一等毅勇侯。
富厚堂體現曾國藩簡樸的智慧
富厚堂是四合院布局,進入大門是一片開闊的庭院房前走廊的廊柱有14根之多,由此可以想見其氣派之大。曾國藩手書“富厚堂”三字匾額懸掛正中,兩旁邊是他的兒子、外交家曾紀澤書寫的篆書對聯“清芬世守,盛德日新”。進入正廳,內墻不是青磚而是土磚,一反雕梁畫棟的做法,門板上只有簡單的雕飾,梁柱則沒有任何裝飾。中廳的匾額為曾紀澤手書的“八本堂”,抄錄的曾國藩制定的八本準則。這所大院占地面積4萬多平方米,主體建筑近1萬米,由三正六橫組成,大院后面圈進了半座山坡,沿著高大的土夯的院墻拾級而上,樹木茂盛,清香襲人。
藏書樓體現了曾國藩廣闊視野和博大胸懷
富厚堂包含三個藏書樓,一為曾國藩的求闕齋,一為曾紀澤的歸樸齋,一為曾紀鴻夫婦的藝芳館,收藏中外圖書數十萬卷。曾國藩的生活是簡樸的,但舍得花錢買書,在給曾紀澤的信中指出:“余將來不積銀錢留與兒孫,惟書籍尚思買耳”,他曾多次對曾紀澤說:“買書不可不多”,他認為作為精神財富的遺產對子孫后代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同治五年,曾國藩打算回家養老,叫曾紀澤在湖南老家修理一所房子,節儉辦事,盡量低調。曾紀澤盡量遵從父親的意愿,匯報說,打算在院內建一座藏書樓,曾國藩欣然同意說:“家中造樓藏書,本系應辦之事”。
曾國藩本想花幾百兩銀子修繕老房子就行,想不到同治六年房子修好后,一共花了七千串銅錢,即五千兩銀子,曾國藩寫信責備曾紀澤和具體辦理此事的大弟弟曾國潢說:“修理舊屋,何以花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應費錢許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買田起屋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爾行之。澄叔(曾國潢字澄侯)諸事皆能體我之心,獨用財太奢與我意大不相同。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實不清,尤為造物所怒”。
曾國藩認為修個舊房怎么花了這么多的錢,即使新蓋個房子也花不了這么多錢,我一輩子認為做大官買田蓋房是令人羞愧的事,想不到我家竟這樣做了,沒有按我的意見辦事,這是很不應該的。接到曾國藩的信,曾紀澤嚇壞了,可他的叔父曾國潢并不著急,寫信給曾國藩說,這房子花錢多,主要用到藏書樓上去了,“富厚堂造書屋七間,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點,蓋以地基昔系澇田,石腳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價已占千馀串;通體用青磚,料木多杉樹,尤非可以尋常計算也。”曾國潢知道曾國藩處處節儉,只有買書藏書值得花錢,經過一番解釋,曾國藩也就釋然了。
富厚堂建筑簡樸,可這座藏書樓舍得花血本,由于地基比較軟,用石頭砌了一丈深的基礎,這就花了一千多串,一樓外走廊全以花崗巖為柱,為的是防白蟻,一樓到三樓通體用的是青磚,修有專用以上下書籍的通道;二樓四周有外走廊,可用來曬書;書室設在三樓。整個藏書樓用的木料全是上好的杉木;頂層四周均有窗戶,四面通風,可以避免書籍霉變。和富厚堂其他建筑相比,這座藏書樓的確別具匠心,曾國潢和曾紀澤沒少費心費力,由于曾國藩在外任職,回鄉愿望一直沒有實現,到死也沒有親眼看到這座藏書樓。
富厚堂的特點就在于它的三座藏書樓,作為學者型的曾國藩,他的學問是相當扎實的,他曾頗為自傲地說:“若如此做去,將來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藏書樓數十萬卷藏書中不乏珍本,這些藏書及文件最珍貴的部分被曾寶蓀、曾約農帶到了臺灣,寄存在臺灣的“故宮博物院”。其他比較珍貴的圖書,一共200多擔,1950年冬天被湖南省文管會運往長沙封存,僥幸的逃過了“文化大革命”。被認為沒有價值的很多藏書,經過“土改”“四清”“文化大革命”早已片紙皆無了。
富厚堂的匾額對聯體現曾國藩的文化精神
富厚堂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的匾額和對聯,作為耕讀起家的曾氏家族,制定了很多家訓并寫成匾額對聯懸掛在富厚堂內,比如曾國藩手書父親曾麟書的箴言,“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曾國藩自撰有“萬卷藏書宜子弟,一尊滿意說桑麻”,“看書寫作一日無閑,勤儉敬信終身可行”,“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愿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堂里還有巨匾“篤親錫祜”,均以談耕讀持家為內容。也有講為人處世的:“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憂以終身,樂以終身”,這些體現了曾國藩一貫主張的慎獨、謙忍的人生哲學。
思云館里的反思體現了曾國藩勇猛精進的自我完善精神
從藏書樓下來,繞過后山的林蔭路,在富厚堂主體建筑之外,還有一座獨立的二層小樓,它就是思云館。咸豐七年(1857)二月,父親去世,曾國藩從江西軍中奔喪回家。為了紀念父母根據古人“望云思親”之義在鰲魚山下筑思云館,在這里居住了一年零四個月,因此是先有思云館,后有富厚堂。
鄉居期間,曾國藩閱讀老莊著作,對自己過去進行了深刻反思,認識到自己在官場上一再碰壁,除了客觀原因外,自己個性甚強,鋒芒畢露,說話太沖,辦事太直,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正如二弟曾國華所言,“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而老子認為,“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江河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過于剛烈者,表面上好象是強者,其實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真正的強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柔弱的退讓者,通過切切實實的內省,曾國藩把鄉居這兩年稱之為“大悔大悟”之年,后來回憶自己這一變化時說:“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即1857—1858年)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咸豐八年復出之后他運用黃老之術,無人不拜,無信不回,與左宗棠捐棄前嫌,重歸于好,在政治、軍事、人格修養上均有飛躍的發展,終于成為“中興第一名臣”。
讀懂了富厚堂,也就讀懂了曾國藩
富厚堂經歷了一百多年至今屹立而不敗,固然和“文革”期間被鄉政府占用有關,但富厚堂崇尚簡樸厚重也是重要原因;而曾國荃用從南京擄掠的大量金銀財寶在老家建起由曾家家廟、獎善堂、敦德堂組成的龐大建筑群“大夫第”,據傳有9進18廳、148間房屋成為當時湘鄉以至湖南省最為豪華的官僚住宅,建筑面積達4萬平方米,光天井就有24個,綿延近一公里,木料用的都是珍貴的楠木、樟木、梨木,石料全是花崗巖,那些七八米高的柱子用的全是整塊花崗巖鑿成,門窗精雕細刻。時光流逝,富厚堂基本完好,而大夫第已破敗不堪,兩相對比富厚堂形象地體現了曾國藩的智慧。 endprint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