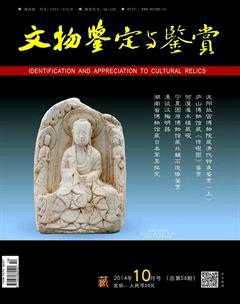宋慶齡臥室里的一塊鎮繃石
宮潔菁


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是宋慶齡曾經長期居住的地方,是她在上海的家。1981年宋慶齡去世,她淮海中路的寓所被作為永久性紀念地保存了下來。隨后,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成立,這幢寓所以及寓所內的遺物便成為了紀念館中的館藏文物。
紀念館館藏文物種類繁多,有文稿、書信、照片、印章等反映孫中山、宋慶齡革命軌跡的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文物,還有一些本身即具有一定價值的藝術品和大量的生活用品。宋慶齡的生活用品很普通,與一般家庭所使用的并無二致。但由于存放得當,很多民國時期,乃至清代的物品都仍保持著較好的面貌。這些物品在那個年代或許并不鮮見的,但安然保存到了今天,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價值。
故居主樓宋慶齡的臥室里就放置著這樣一件非同一般的物品,長期以來,它都“安靜地”躺在臥室門前,“默默地”發揮著它的作用。故居每天迎來送往,人流不息,但幾乎沒有游客會注意到它的存在。因為相對于臥室里的其他擺件,它著實不起眼,它只是一塊被放置在房門前,用來抵門的石頭。之所以把它當作“抵門石”,自然是沿襲宋慶齡本人生前對房間物品的擺放方式。而事實上,這塊看似其貌不揚的石頭卻是大有來頭,這塊石頭其實是有著極高藝術價值,現在在上海幾乎已經絕跡的女紅工具——鎮繃石。
鎮繃石,即用于鎮、壓繡花繃架的工具,因材質為石,故名。古代女子皆擅女紅,她們在繃架上繡花,為使繡面挺括、平整、勻稱、不起皺,就在繃架的四角用重物鎮平或吊平。最初的鎮繃之物,僅是一些有重量的東西,后來在漫長的使用過程中,逐漸藝術化起來,鎮繃石就是這種藝術化的結晶。隨著藝術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鎮繃石也慢慢從普通的生活用品演變成了不折不扣的藝術品。
據考證,明代已有鎮繃石,清代、民國最為普遍,原產地為浙東的寧波、紹興地區,后寧波籍人士移居上海,也就在上海流行起來了。明清時代的石雕藝術不乏珍品,但多為大型遺存,如石獅、影壁、牌樓等,像鎮繃石這樣的小件藝術品是很鮮見的。
鎮繃石是地道的石雕藝術,所用材質大多為青石,也有灰石與紫石。此類石質比較細膩、緊密,適宜于細雕,且時間一長能產生光滑锃亮的包漿。鎮繃石通常為秋葉狀,秋葉上雕刻著千姿百態的美女,或讀書,或小憩,抑或懷抱嬰兒……均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實場景,散發出濃郁的生活氣息。
宋慶齡臥室里的這塊石頭可以說是鎮繃石的典型代表。石頭為秋葉形,葉形輪廓十分優美,葉面底部有一圓孔,用來系扎繩索,與繃架相連;葉面上方雕刻著一個頭梳發髻、身著對襟衣衫的婦人,她面頰豐腴,慈眉善目,身倚圓枕,環抱一小童,雕刻形態頗為生動自然,又極富女性柔美之感。這塊鎮繃石的特別之處在于,石頭外面還上了一層彩色的釉。因為是實用物品,而且年代久遠,釉色稍有斑駁,但仍可看出,這位婦人的衣衫顏色鮮亮、紋飾繁復,且頭戴首飾,發髻華美,顯然這里所雕刻的是一個富貴人家的夫人和孩子。
得益于宋慶齡的妥善收藏和幾十年來紀念館工作人員對室內環境的恰當保護,這塊鎮繃石除釉色有些剝落之外,整體外形完好如初,對于一類瀕臨絕跡的藝術品而言,這著實難得,其價值亦不言而喻。
那么,這樣一塊鎮繃石出現在宋慶齡的臥室里,它和宋慶齡究竟有著怎樣的淵源?若作鎮繃之用,那應該有四塊這樣的石頭才符合常理,這里卻僅有一塊,而且也沒有繃架、繡線等其他繡花的必備工具。宋慶齡到底是否使用過這塊鎮繃石呢?
宋慶齡出生在清朝末年,在父母的安排下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學習英語、拉丁語、鋼琴等,9歲即進入用英文教學的中西女塾讀書,14歲遠赴美國求學,大學畢業嫁給孫中山之后,就開始投身于民主革命。基于宋慶齡的受教育狀況和成長經歷,筆者推測她對于中國傳統的女紅是不擅長的,即使在幼年時有所接觸,之后長期的海外求學生涯以及顛沛流離的革命生活也不可能讓她有機會重拾女紅活計。
埃米莉·哈恩在《宋氏家族》一書中寫道:那個時代,有出息的中國姑娘都懂得如何在絲綢上刺繡……宋夫人自己不喜歡針線活……她卻渴望女兒們精通這項技藝……藹齡對靜坐半天才繡出一條邊的光景感到沉悶無聊……她的小妹妹們自然也都跟她學……宋耀如對小女兒們厭恨女紅活計寄予同情……他提醒妻子,既然花幾美元就能買到最好的刺繡,那么用這種精工細活去損害孩子們的眼睛就完全沒有必要……宋夫人對此可能信服了……
由此可見,這塊鎮繃石的使用者應該不是宋慶齡,自然也不是她的姐妹宋藹齡或宋美齡。那它又怎么會出現在宋慶齡的臥室里?有沒有可能是宋慶齡的母親倪珪貞使用過的?
倪珪貞1869年出生川沙一基督教傳教士家庭,父親倪蘊山是上海倫敦會天安堂牧師,母親徐氏是明代禮部尚書、著名科學家徐光啟的后代。倪珪貞自幼讀書家塾,四、五歲入學校,十五歲升西門裨文女學,她精算學,擅鋼琴,還會英文。基督教家庭背景讓倪珪貞不同于傳統的中國婦女,她受到了良好的基礎教育,包括一些西式教育;但相比于宋慶齡那一代,倪珪貞顯然傳統得多,她沒有留學經歷,所受的教育大部分都是中式的,她像一般中國婦女一樣,婚前待字閨中,婚后相夫教子。而女紅在當時來說,幾乎是女性必備的手藝,對于有錢人家的小姐、婦人而言,繡花可能就是一種消遣的方式。因此,倪珪貞會繡花這個假設是能夠成立的。
埃米莉·哈恩在她的書中說倪珪貞強迫女兒們精通刺繡,自己卻不喜歡針線活。筆者認為,不喜歡不等于不會,而且埃米莉·哈恩所說的“不喜歡”是否屬實,值得商榷。
據倪珪貞胞兄倪錫令的女兒倪愛珍1984年的回憶,“……老二倪珪金是大娘娘,很兇,幾個妹妹都聽她的話,繡花繡得很好,教中學。老三倪珪貞,很聰明,有錢,買縫紉機,小孩衣服都自己做……”顯然,倪愛珍的回憶和埃米莉·哈恩的敘述是截然相反的。
又據宋慶齡原警衛秘書隋學芳的女兒隋永清所述,宋慶齡生前曾贈送給她多幅繡品,都是宋慶齡的母親當年留下來的。這些繡品多是絲綢質地,繡的圖案各不相同,有花草、魚蟲、鳥獸等,其中有些是可直接用作擺設的繡片,有些則可用來做衣服的花邊,還有一件是尚未繡完的半成品,每件繡品都極為精美。
筆者認為,和當時的大多數中國女性一樣,倪家姐妹包括倪珪貞,應該都是自幼就學習女紅的。暫且不論倪珪貞對此是否喜歡或者在行,從她保存那么多繡品以及要求女兒們學習刺繡來看,她對于這門技藝是熟悉并且推崇的,不能排除她在閑暇時小試身手的可能性。
綜上基本可以推斷,宋慶齡臥室里的這塊鎮繃石是她母親倪珪貞所使用過的。那么,倪珪貞使用過的鎮繃石又如何到了宋慶齡的寓所?
倪珪貞于1887年婚配宋耀如,婚后即隨丈夫赴昆山、七寶、太倉巡回傳教,之后生育子女六人,主持家政,教育子女。如前文所述,鎮繃石上雕刻的是一個懷抱小童的婦人形象,因此筆者推測這塊鎮繃石不是倪珪貞出閣前在娘家使用的,而是與宋耀如結婚生子后在自家使用的。
1918年宋耀如去世,倪珪貞攜子女遷居至上海西摩路139號(今陜西北路369號)寓所,前后居住了10余年。1931年倪珪貞去世,西摩路139號即由當時居住在上海的宋慶齡料理使用。
為便于保管,宋慶齡陸續將西摩路139號內的一些家具、物品搬至自己的寓所。或許宋慶齡幼時在家曾看到母親使用這塊鎮繃石,又或許她覺得這塊石頭造型別致,所以就把它一起搬回了自己的寓所。因為是娘家帶來的物品,具有特別的紀念意義,宋慶齡很珍視,一直把它放在自己的臥室里。
當然,鎮繃石在新的時代,在宋慶齡這里是徹底失去用武之地了,最終由于石質沉重,被用來抵門,也算是發揮了它最后的實用價值。可能宋慶齡本人都沒有想到,這件原本十分普通,幾乎每家都有的生活用品,若干年后竟由于它的藝術性和稀缺性,成為了一件極具歷史價值的珍貴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