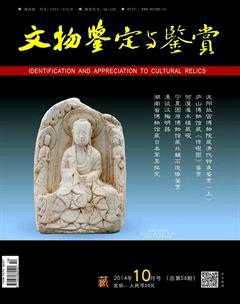大都會博物館藏《呂洞賓過岳陽樓》圖研究(下)
杜浩遠



編者按:我國傳統繪畫藝術是我國藝術花園里的一朵奇葩,是全人類的寶貴財富,也是研究古人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但是現存中國古代繪畫數不勝數,其中真偽并存、魚龍混雜,對其進行仔細的個案研究和甄別就顯得十分重要。宋代是中國傳統繪畫的一個高峰時期,中國以及海外諸多博物館都有收藏。本文試圖對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藏的《呂洞賓過岳陽樓》這一被定為宋畫的畫作進行分析研究,并嘗試對其真偽性進行判斷。上一期刊物中,作者通過“呂洞賓與岳陽樓相關的傳說”以及“《呂洞賓過岳陽樓》圖中的建筑形象”兩個方面來論證《呂洞賓過岳陽樓》圖為明代仿宋之作。
三、《呂洞賓過岳陽樓》圖中的人物形象
《呂洞賓過岳陽樓》圖中的人物共有42人,其中岳陽樓上層17人,下層及樓外22人,墻上壁畫2人,天空神仙1人。
宋朝規定庶民百姓只許穿白色衣服,后來又允許流外官、舉人、庶人可穿黑色衣服。但實際生活中,民間服色五彩斑斕,根本不受約束。本畫中可見三名女性內穿裙子外套窄袖褙子(見圖17),兩名男性上穿旋襖下穿長褲(見圖18)。
畫中可見樓上兩名樓下三名男性小伙計或商販,身穿短袖窄身上衣應為短褐,下身穿長褲(見圖19)。
空中神仙應為呂洞賓,身穿淡黃色道袍,但是未見宋代道袍明顯的深色邊緣,應是示意之作(見圖20)。與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宋代佚名《呂祖過洞庭圖》中呂洞賓形象作對比可以看出(見圖21),兩者形象基本相同,服飾樣式也是大同小異,不同在于本畫中為斜領,而《呂祖過洞庭圖》中為圓領。
其余眾人男性均身穿長袍,頭戴高裝巾子,為典型的宋代文人裝束(見圖22)。另有少數人物由于形象較小或特征不明顯等原因難以準確判斷其性別,然而其頭部裝飾為白色方巾狀物體,既不同于男性高裝巾子以及幞頭的常用深色,也不同于宋代女性高大發髻的特點(見圖23)。
從人物服飾方面來分析基本符合宋代服飾的造型和樣式,然而宋代人物畫已經十分成熟,其筆墨技法高超,大體上可以分為精細寫實與逸筆寫意兩大風格。然而無論哪種風格,優秀作品都十分講解筆墨與造型,比如梁楷利用筆墨的頓挫飛白來表現人物服裝的質感(見圖24),王居正利用顏色的仔細暈染來配合線條描繪服裝的立體感(見圖25)。本畫中的人物形象基本可以歸為較寫實的一類,但可明顯看出用筆簡單隨意,線條輕柔浮躁,染色基本平涂而不見層次,使得每個人物形象都顯得比較簡單樸拙。這可能是由于人物形象較小不易描繪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由于畫家水平較低的原因。
四、《呂洞賓過岳陽樓》圖中的鈐印
1 鈐印概述
《呂洞賓過岳陽樓》圖中共鈐印四方,全部集中在畫面的右上角。印文自上而下分別是“機暇清賞”“潘延齡印”“葉蔗田珍賞章”“蓮樵鑒賞”。
(1)“機暇清賞”印
宋代周密在《齊東野語·紹興御府書畫式》中記載:“趙世元鉤摹下等諸雜法帖……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內府書記印,后用紹興印。”趙世元,南宋高宗時人,書法家,尤善鉤摹法帖。“機暇清賞”印為宋高宗趙構的收藏印。
(2)“潘延齡印”印
潘延齡,號健庵,廣東番禺人,書畫收藏家,所藏宋元名家書法頗富,活動時間大約在清咸豐時期。
(3)“葉蔗田珍賞章”印
葉夢草,字春塘,號蔗田,清嘉慶、道光間南海(在今廣東)人。清代廣東著名藏家葉夢龍從弟。
(4)“蓮樵鑒賞”印
字或號為“蓮樵”的有兩人,一為湛天潤,二為陳炳奎。史料記載:“九世天潤,來之繼子,字貌卿,號蓮樵;歲貢生,官國子監學錄,升廣西平樂府通判。生正德辛未九月二十九日,卒萬歷丙申二月二十九日,享壽八十六。”陳炳奎,字蓮樵,約生于嘉慶年間,卒于光緒年間,清涼州府(今甘肅省武威市)人。因其父早亡,家計累身,遂棄學業,以家務自任。生平愛好文學詩詞,也擅長書法繪畫。其詩以抒發心情,描寫景物者居多。
“蓮樵”所用鑒藏印除此之外還見有“蓮樵曾觀”和“蓮樵成勛鑒賞書畫之章”兩方,見于辛棄疾著名法帖《去國帖》(見圖26、圖27)。關于“蓮樵”究竟為何人沒有準確的記載,但是其所鈐蓋鑒藏印的書畫作品不乏名家珍品,與其同時鈐蓋的鑒藏印往往還有綿憶“南韻齋印”、永理“皇十一子成親王詒晉齋圖書印”,可見其收藏實力不容小覷。考察兩位似乎都沒有收藏頗豐的記載和可能,相比之下陳炳奎雖然在寫詩的同時也擅長書法繪畫,與收藏書畫有所關聯,但其基本以務農為生,恐怕難以支撐具有實力的收藏事業,況且“潘延齡印”和“葉蔗田珍賞章”兩方印的主人都是廣東收藏家,與陳炳奎籍貫相差甚遠,所以無法推斷“蓮樵鑒賞”印的主人。
所以從時間順序來看,除了“蓮樵鑒賞”以外三方印中最早鈐蓋的是南宋印璽“機暇清賞”,然后鈐蓋的是“葉蔗田珍賞章”“潘延齡印”兩枚印章。
2 鈐印辨析
通過三方印章的對比可以發現,《狩獵圖》與《中國鑒藏家印鑒大全》中的“機暇清賞”印十分相似,應為同一印璽(見圖28、圖29),而本畫中“機暇清賞”印則有多處明顯不同,如“清”字的“月”,“機”字的“幾”,“暇”字的“段”等等。而且這方印印文四字有石刻的感覺,不同于另兩方有明顯的盤條鑄造感,因此可以推測本畫中這方印為偽印(見圖30)。
“葉蔗田珍賞章”不見于館藏書畫,2001年香港佳士得曾經拍出了一幅王原祁仿黃公望山水圖,其上鈐蓋有相同印文的鑒藏印一方,不知是否為同一方印章。另外還有幾幅散見于拍賣會的書畫作品也有“葉蔗田珍賞章”,但都為流拍拍品。
通過比較本畫中的與《中國鑒藏家印鑒大全》中的“潘延齡印”可以看出,兩者除了少數細節部位有少許不同外,基本可以斷定為同一印章(見圖31、圖32)。
雖然對于“蓮樵鑒賞”印的主人不能做出判斷,但是比較現藏上海博物館的米芾《章侯帖》上的這方印章,可以發現兩者相同(圖33、圖34)。
結語
根據以上比較詳盡的分析,可以看出承認這幅畫作整體繪畫水平并不高超,造型能力和運用筆墨的能力都與名家名作有很大差距,可能是出自民間藝人之手。其中的各種形象在考慮其繪畫水平的基礎上可以認為是基本符合宋代實際,然而岳陽樓作為當時負有盛名的建筑其建筑形象應當被人熟知,將其描繪成本畫中的簡單形象應當歸結于作者自身條件的限制或者其創作意圖的主導,同時根據建筑結構示意性強、構圖呈現與園林相結合的文人情趣等方面,可以將其理解為界畫衰落期的風格特征。從鑒藏印上來看,由于南宋“機暇清賞”印為偽印,那么本畫屬于宋畫的可能性又大大降低。另外如果暫時排除其他印章的疑點,可以發現本畫基本是在清代中后期流傳于廣東一帶,而一張宋代絹本畫作自從被南宋宮廷收藏后直到清代中期這段較長的時間里一直沒有被鈐蓋鑒藏印,不符合書畫收藏的一般規律。再考慮到本畫的題材為神話傳說類,也并非主流的風俗畫,將其繪畫在絹本團扇之上也較少見于宋代民間以出售書畫為職業的畫工之手,況且如果其真是作為藝術品來出售,其繪畫水平也恐怕難以得到市場認同。綜合以上觀點本人傾向于本畫為明代臨仿宋畫的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