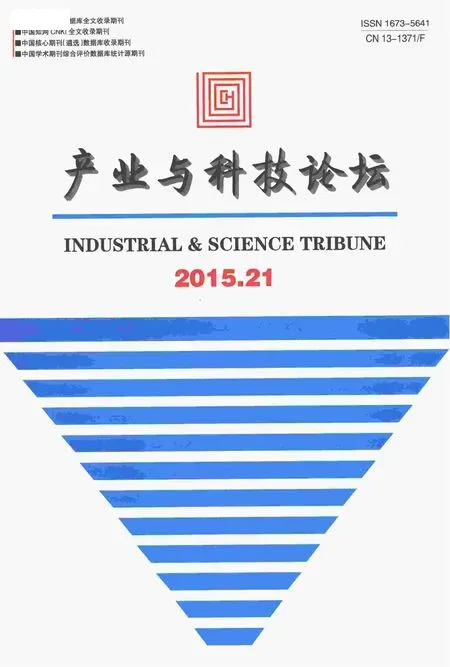李大釗“民彝”思想中的“階級觀”探究
□賴偉鈞
聚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課題研究,據華南師范大學陳金龍教授的觀點,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視域拓展,其理論根據包涵“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源于西方的理論,是在西方社會特有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由此決定了它所表達的思想內容、所蘊含的思維方式與中華民族傳統有較大差異”。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課題研究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歷史過程。胡錦濤同志在2011 年7 月1 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事實充分證明,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壯闊進程中,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共產主義自1848 年《共產主義宣言》發表標志誕生,為什么幾近70 余年后才為中華民族所選擇?回答這個問題,局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課題本身難免捉襟見肘,改革開放以來,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理論核心的“現代化”課題研究與之相得益彰。中國近現代史,按“現代化”課題研究的視角,其過程大致可以分成兩個歷史階段:一是“被動現代化”進程;二是“主動現代化”進程。無須贅言,以中華民族為主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范圍內的傳播,其目的是須將“被動”現代化改變成“主動”。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在其文章《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回顧了這段歷史:“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歷史應當完結了。”
現代化課題研究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為主體,以世界現代化進程視野為背景,驗證中華民族融入世界、實現“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得失。但世界現代化進程標準已然為西方現代化國家所建立,即“現代化”闡述是以“西方”話語體系為標準。由于歷史的原因,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演繹方式與“西方文明”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在短時間內,以華夏話語體系來理解“西方話語體系”存在一定困難。由于文化之間的差異,中華民族在追求“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必然出現曲折。相當部分歷史學家將這個曲折“現代化”過程稱為“被動”。正如毛澤東同志上面所闡述的,中華民族將現代化“被動”轉變成為“主動”的關鍵,是通過同樣來源于“西方話語體系”的馬克思主義,使之實現中國化(改造華夏話語體系)實現的。此據,陳金龍教授相關文章觀點闡明,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視域,將中西文化差異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有其重要性。
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視域,重點在于拓展研究對象,將李大釗相關思想納入其中,其理由和意義不言自喻。就李大釗對中西文化差異之間關系的理解而言,認為其文章《民彝與政治》具有相當代表性。該文章寫于1916 年,發表于李大釗旅日期間所創雜志《民彝》創刊號。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凱竊國,一些具有深厚傳統華夏文化底蘊的“官僚士族”,祖述所謂“華夏文化”之要義,為袁世凱辯護、歌功頌德。他們固執地認為,中國“帝制”是華夏文明的根本,是“體”;西方話語體系中的一些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只能對“帝制”起改良的效果,是屬于“用”的范疇。
李大釗作《民彝與政治》,核心思想在于批判袁世凱之流“竊國”行為:“民彝何為而作也?大盜竊國,予智自雄……不得其邏輯之用,以彰于政治,而倫紀憲章,失其常矣。”李大釗批判袁世凱之流借所謂“華夏文化”為其“竊國”行為辯護,其所謂源自“華夏文化”之竊國“理論”,存在問題主要有:一是“理論”與實踐嚴重不符,導致該“理論”與社會現實存在自相矛盾,即“邏輯”上出現謬誤;二是該“理論”實施于現實社會,“倫紀憲章,失其常矣”,完全與華夏話語體系核心思想不符,不具華夏文明之“正統”,其執政不具合法性。
此據,李大釗闡述了“宗彝”與“民彝”的含義,就“宗彝”與“民彝”的關系認為:“宗彝可竊,而民彝不可竊也;宗彝可遷,而民彝不可遷也”。其核心思想大致為,華夏文明幾千年,起源于“宗彝”,形成為“民彝”。此后,“宗彝之遷”,演繹為不同姓氏宗族之間的王朝更替;“民彝不可遷”,是說盡管“宗彝”代表的王朝出現更替,始終如一、應當貫徹的是華夏“民彝”思想。若“宗彝”之遷,“民彝”不失,是為在很長時間內代表華夏話語體系——儒家思想所表達的“鄉愿”得暢,該宗族(政治集團)符合華夏文化之正統,執政具有合法性;若“宗彝”之遷,“民彝”已失,是為儒家思想所表達的“大盜竊國”,該宗族(政治集團)實為“大盜”,執政未遵循華夏文化之正統,不具有合法性。
此據,李大釗認為,華夏話語體系內理解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集團執政理念是否真正體現“民彝”,是否能選用實現并暢揚“民彝”的政治模式,是檢驗該政治集團執政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依據(恰如儒家思想所表達的,符合“大一統”之“正統”理念)。為此,李大釗認為,以華夏“民彝”思想看待世界,世界各國莫不如此:“茲世文明先進之國民,莫不爭求適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李大釗認為,“民彝”為內核,“政治”為形式;“民彝”為體,“政治”為用。如此,“民彝”為“本”以明確,“帝制”與“代議政治”都只能是“用”。只要“民彝”不失,能“信其民彝,彰其民彝”,西方話語體系內的“代議政治”皆可用;“民彝”若失,華夏話語體系的“帝制”棄之不可惜。尤其是,李大釗通過對西方“代議政治”考察,對之褒獎有加:“夫代議政治,雖起于階級之爭,而以經久之歷驗,遂葆有絕美之精神焉。”認為“代議政治”“葆有(‘民彝’)絕美之精神”!“代議政治”能暢“民彝”,能為華夏文明所用,以此駁斥袁世凱之流堅持“帝制”的錯誤觀點。
在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關系上,李大釗通過“民彝”思想與“代議政治”關系的闡述,表達了自己的基本觀點。盡管李大釗對西方文明的“代議政治”,較華夏“帝制”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更能暢揚華夏之“民彝”,而對之褒獎有加,也注意到“代議政治”實是“起于階級之爭”。從文中的語氣中不難發現,李大釗認為“階級之爭”是“代議政治”的缺點,抑或會影響到“民彝”的實現與暢揚。本文盡管并未對李大釗“階級”之義與“民彝”思想,以及中西文化之間關系展開分析,但綜合李大釗此后思想,我們有必要對其“民彝”思想中的“階級觀”引起足夠的重視。
[1]李大釗.李大釗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1 卷
[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4 卷
[3]陳金龍.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教學與研究,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