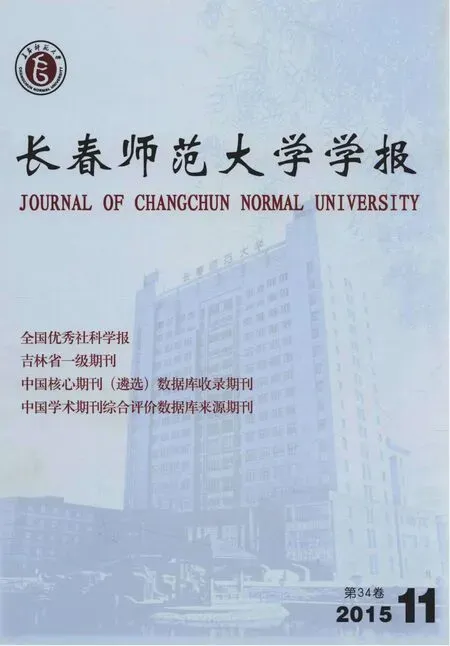近年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文本學研究述評
陳金山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871)
自20世紀以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在全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并生發出許多的理解和爭論。在國外,圍繞著《提綱》的寫作時間、動機和思想史地位及其與其他文本的關聯等問題,陶伯特和巴加圖利亞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對于這些問題,國內學者近年來在文本研究中也給予了重點關注,并取得了一定進展。綜觀當前研究,既有對《提綱》思想的整體把握,也有對其中某一條目的細致解讀。可以說,無論是研究視域還是深度都得到了較大的拓展。
一、對《提綱》寫作動機的文獻學考證
一種觀點強調《提綱》的寫作與《神圣家族》的關聯性。以聶錦芳為代表的學者依據德國的文獻學專家英格·陶伯特的考證成果提出一種新穎的觀點,認為《提綱》的寫作動機與《神圣家族》有關。陶伯特提出,《提綱》的寫作很可能是馬克思對《維干德季刊》第2期上涉及《神圣家族》的評論文章回應的結果,因此《提綱》的寫作與馬克思以前所著《神圣家族》具有相關性。聶錦芳對陶伯特的解讀思路和最終結論表示了支持。他同樣認為,《提綱》第1條第53頁的“四行文字”是解讀《提綱》的重要線索[1]。依據這一線索,可以考證得知:“《提綱》寫作的契機并不是為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做準備,理論工作和研究計劃的尚未完成,以及當時圍繞《神圣家族》所展開的討論,可能是寫作《提綱》的直接動因。”[2]
另一種觀點則強調《提綱》的寫作主要是受赫斯影響。麥克萊倫在《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馬克思》中曾經提到赫斯的“生活就是行動”的行動哲學影響了馬克思的“實踐”觀點。這一觀點在國內受到學者贊同。贊同者強調,馬克思寫作《提綱》正是由于受到了赫斯的影響。其論據有兩點:其一,馬克思所闡釋的“實踐”概念與赫斯的哲學概念極為類似。例如馬克思的“感性活動”“對象性活動”和“勞動”等概念分別對應于赫斯的“行動”“活動”和“生活”等概念。其二,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也與赫斯的兩維度分析相一致。赫斯的“實踐”概念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的實踐,即異化狀態的實踐,二是從“‘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角度來理解的實踐,即符合人的本質的本真狀態的實踐。與此類似,馬克思在《提綱》中對實踐概念的論述也是從兩個維度展開,即作為“感性活動”的“革命的實踐”和社會交往實踐。學者們通過具體考證提出,赫斯在《晚近的哲學家》中強調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等人所做的工作僅僅是從理論上解釋“類”與“個體”的矛盾,赫斯相信只有共產主義的實踐才能解決“類”與“個體”的矛盾。馬克思在《提綱》第11條中的那句經典話語則完全與赫斯的觀點類同,很可能是馬克思讀過赫斯著作后寫下的“同感”[3]66。
第三種觀點強調《提綱》寫作動機的綜合性。這種觀點批評了陶伯特的觀點,認為《提綱》是馬克思通過研究經濟學、哲學和社會主義實踐后形成的綜合性思想成果。1844年至1846年間是馬克思思想產生重要變化的時期,對《提綱》的理解應被置于馬克思思想轉變的具體語境中。[4]89
仔細分析上述研究可以發現,這一問題之所以進入學者的視野,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學者們對《提綱》的寫作時間出現了分歧。德國文獻學專家英格·陶伯特認為根據文獻考證,《提綱》的寫作時間應該在1845年7月《維干德季刊》第2期之后,但這一觀點遭到了巴加圖利亞的激烈反對。巴加圖利亞認為寫作時間最遲不會晚于1845年7月,而后巴加圖利亞在MEGA2版本的研究中將時間定為不會晚于6月。總之,巴加圖利亞傾向于判定寫作時間為1845年4月。國內學者的主流觀點是贊同巴加圖利亞的,但也有部分學者有不同觀點,這就造成了對《提綱》寫作動機的理解差異。第二,對《提綱》寫作動機的考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判定《提綱》與其他著作的思想關聯,進而確立這一著作的思想史地位的依據。強調《提綱》的寫作動機與《神圣家族》或赫斯相關,就意味著《提綱》的主要思想立意在于延續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思想這一主題,而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為創作《德意志意識形態》進行思想準備。換言之,《提綱》與后來的《形態》之間的思想關聯性將大打折扣。
二、如何確認《提綱》的思想史地位
《提綱》開始只是作為《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的附錄而產生。1845年4月左右,居住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在1844-1847年的筆記本中寫下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起初他并沒有以此命名,只在筆記本上端寫下:“1.關于費爾巴哈。”1888年恩格斯在完成并將出版《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時,發現“十一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完成了馬克思對包括費爾巴在內的舊哲學的系統批判,于是把它作為附錄刊印出來。恩格斯還對馬克思的原稿筆記稍加修改,以便更為通俗易懂。恩格斯這樣做的初衷在于他認為《提綱》與他的著作在觀點上,尤其是在批判費爾巴哈的部分存在一致性和互證性,因此他認為將兩者放在一起有助于讀者深入理解。恩格斯在其著作出版序言中強調了《提綱》的歷史價值:“它作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是非常寶貴的。”[5]
《提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視為《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附錄,而被遮蔽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獨立文本價值。在國內早期文本研究中,也長期存在忽視《提綱》價值的問題。不過近年來隨著研究資料的豐富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學術界對《提綱》的獨立價值越來越重視。對《提綱》存在不同的文本解讀,導致對其思想史地位和價值的不同理解。總體來看,學界對此存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提綱》是介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之間的過渡性著作,不宜脫離語境對其作過高評價。具體而言,《提綱》中所提出的實踐唯物主義思想不過是馬克思由自然唯物主義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媒介,僅僅是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萌芽,因此《提綱》的歷史價值主要在于它構成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中間橋梁。在這種觀點看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雖然也有實踐唯物主義的表述,但是它在概念內涵上是與歷史唯物主義相重疊的,并沒能形成區別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的概念。[3]65這種觀點的另一闡釋則傾向于《提綱》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思想聯系性,認為相較于《德意志意識形態》而言,馬克思在《提綱》中呈現的思想更接近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筆記本Ⅲ[6]。
第二種觀點認為,《提綱》是對《神圣家族》中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延續。這種觀點所贊同和附和的是陶伯特的觀點。陶伯特依據《提綱》第1條第53頁的“四行文字”提出,《提綱》中所闡述的無論“實踐”概念還是人的社會本質概念,都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得到提及,其最重要的理論價值在于通過對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的唯物主義進行批判,進一步闡述了《神圣家族》中所涉及的唯物主義主題。國內學者對此研究結果表示支持和贊同,并進一步認為:“《提綱》的思想只能視為馬克思進一步論證新世界觀的前提,而不能把《提綱》解釋為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直接契機,也不能把它看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提綱。”[7]
第三種觀點主張《提綱》與《德意志意識形態》是綱舉目張的關系,強調《提綱》是對馬克思的新思想體系的高度凝結,是唯物史觀形成的標志。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在理論主題上具有一致性,馬克思在《提綱》中所論述的如理論與實踐關系、人和社會的本質、哲學的功能等一系列基本原則在后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得到了具體的展開,兩者共同形成和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新的范疇。因此,“把《提綱》和《形態》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標志是恰當的”[8]。就理論任務而言,兩篇文獻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清理舊的世界觀基礎上力圖確立新的思想體系的力作,是深化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批判之作。[4]93
三、對《提綱》的馬克思版本與恩格斯版本的比較研究
在對上述兩個問題的文獻考證研究過程中,關于《提綱》的馬克思版本與恩格斯版本的比較研究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這一研究的實質是要回答和解決《提綱》的馬克思版本與恩格斯版本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的問題。在MEGA2版本出來前,學者們大多贊同“統一論”,即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完全一致,即便存在差異,也是可以忽視的細枝末節的差異。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如諾曼·萊文和特雷爾·卡弗等的著作被譯介入國內,這些強調馬克思與恩格斯二者思想差異性的學者開始被國內學者熟悉,使得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興趣大增,于是出現了“馬克思恩格斯思想決然對立”的觀點。事實上,無論是“統一說”還是“對立說”都是趨向一端,有待商榷。
更多的學者選擇相對中庸的觀點,即在強調二者思想的基本點一致的前提下,正視存在的差異,而且認為這種差異只是個性層面、細小層面的差異[9]。具體而言,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原始文本進行了文法、句法等技術性修改和細致加工,在與原稿思想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使《提綱》更為通俗易懂。但馬克思的原稿較之恩格斯的修改版本在內涵上有所不同,比如強調“人的自我改變”和環境的關系,更加凸顯了馬克思哲學實踐功能的外在對象性和內在指向性的雙重特征。又如馬克思在《提綱》第11條沒有加“而”這一語氣詞,更加凸顯馬克思將“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機統一起來而非將二者對立起來的意思。因此,當前學術界對馬克思的原版本的重視程度遠遠大過恩格斯修訂版本。學者們依據馬克思的版本更加深刻和系統地理解與闡釋《提綱》的文本含義,提出了諸多富有啟發的新見,如對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理解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拓展到人與自我的關系[10],從而大大提升了研究水準。
四、“實踐”范疇的內涵解析
基于《提綱》中馬克思所闡釋的“實踐”概念,近年來國內學者也掀起了對“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研究,其中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實踐”?概括而言,對此問題的研究有以下幾種思路和觀點:
其一是從社會生產關系的角度去理解實踐。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是從人們的物質生產和現實生活中抽離出來的,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形成的關于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關系的哲學范疇,其基本原則是從實際出發[11]。這種觀點強調馬克思的實踐概念“與其它哲學實踐觀不同,馬克思所講‘實踐’并非指單個人行為,而是確指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12],其彰顯的是實踐的社會現實性。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看來,馬克思在《提綱》的第1條中就將實踐理解為主客體的對立統一,強調主客體的矛盾是實踐的動因和結果,并由此生發出對實踐的社會現實性質的闡述。順此邏輯,“實踐”就與馬克思其后闡述的唯物史觀在理論內涵上存在頗多重疊。由此需要解答的問題是:實踐范疇與唯物史觀的聯系和區別在哪?由此也就涉及對《提綱》的思想史地位以及《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之間的思想關聯等問題的探討。
其二是從主客體關系的角度來探討“實踐”概念的內涵,提出在解決當代人類生存困境的意義上來研讀《提綱》,把握主體問題的實踐本質。持這種解讀思路的學者認為,“實踐”是主體的本質,是主體性的來源。在實踐之外,既沒有主體,也沒有客體,更沒有歷史。“馬克思哲學乃是通過實踐環節‘由物見人,由物見史’的‘實踐唯物主義’”[13]。可見,這一觀點強調實踐是人保持主體性,消除主客體對立,實現人的自我解放的方法論依據。
其三是強調馬克思的“實踐”概念與以往哲學家的不同。有學者將《提綱》中實踐范疇與費爾巴哈的實踐范疇進行對比,指出費爾巴哈是在貶義層面使用“實踐”概念,他依據“利己主義原則”或功用主義,將實踐與科學認識相對立,認為實踐是宗教貶低客觀自然的隨意活動,“是宗教出于隨心所欲的創造手段”[14]。換句話說,費爾巴哈的“實踐”概念是在批判宗教的意義上使用的。而馬克思是在研究勞動或制定勞動異化概念時注意實踐的。
其四是從經濟學研究思路出發來揭示“實踐”內涵。這種觀點認為《提綱》中的實踐規定并不是對德國以往思想成果在哲學意義上的簡單指認,而是馬克思通過經濟學研究對社會物質活動的肯定。具體而言,就是從狹義的經濟學語義上的“工業”向一般的“社會的物質活動”的總體——實踐的過渡[15]66。這一思路強調,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的實踐規定,不是立基于哲學上的抽象演繹,而是基于其豐厚的社會經濟歷史積淀得以形成的。[15]64
其五是對“實踐”概念進行中國哲學式解讀。這一頗為新穎的思路將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概括為三個認識和把握世界的環節:知道—成道—行道。“知道”即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對象。“成道”即認識和把握物質世界的本質和規律,將其推進到對自然、社會和個體范疇的考察分析,實現認識對象與人的內在性的統一。“行道”則是把客觀世界的規律對象化于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不僅是解釋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16]。這一解讀模式力圖超越“以西解馬”、“以蘇解馬”和“以馬解馬”的模式,更加強調以本土化思維去理解馬克思的思想,更加注重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接,因而也更具本土理論意識。
總體來看,上述學者對“實踐”概念的內涵作了全方位的揭示和闡發,對我們理解“實踐唯物主義”概念、理解《提綱》甚至是理解馬克思思想的整體面貌都極有助益。當然,有些問題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討論以便更加明晰,比如有的學者強調“實踐”概念與“唯物史觀”概念兩者在內涵上重疊,但對其差異性并沒有進行清楚的揭示。這就需要我們通過進一步研讀文本來廓清兩者的界限,以便更為準確地把握概念。同時,還有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明確,如有學者從《提綱》這一文本中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概念,而馬克思在文本中明確表述的是“新唯物主義”。那么,這兩個概念之間又存在怎樣的關系?我們應當如何來理解呢?上述疑問都有待于在日后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的理解和澄清。
[1]聶錦芳.思想的傳承、決裂與重構(下)——《德意志意識形態》創作前史研究[J].河北學刊,2006(5).
[2]聶錦芳.清理與超越——重讀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礎與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24.
[3]魯克儉.《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寫作原因及其再評價[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8(5).
[4]姚順良,夏凡.《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寫作時間的判定及其思想史定位[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8).
[5]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8年單行本序言[M]//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 -213.
[6]魯克儉.《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與歷史目的論[J].河北學刊,2009(6).
[7]聶錦芳.如何解讀《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J].光明日報,2005-10-18.
[8]黃楠森.馬克思主義哲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4.
[9]王東,郭麗蘭.《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新解讀——馬克思原始稿與恩格斯修訂稿的比較研究[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6).
[10]孫熙國.唯物史觀的創立與人的本質的發現[J].哲學研究,2005(11).
[11]孫伯鍨.馬克思的實踐概念——紀念《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寫作150周年[J].哲學研究,1995(12).
[12]胡義成.“實踐”即社會生產-生活(上)——重讀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兼論馬克思哲學即唯物史觀[J].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
[13]張青蘭.主體問題的存在論本質——重讀《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J].哲學研究,2011(8).
[14]馮景源.論《關于費爾巴哈提綱》的唯物史意義[J].南京社會科學,1990(3).
[15]張一兵.實踐:在何種意義上成為馬克思科學方法論的基石——經濟學視域中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J].學習與探索,1998(6).
[16]孫熙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對話[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