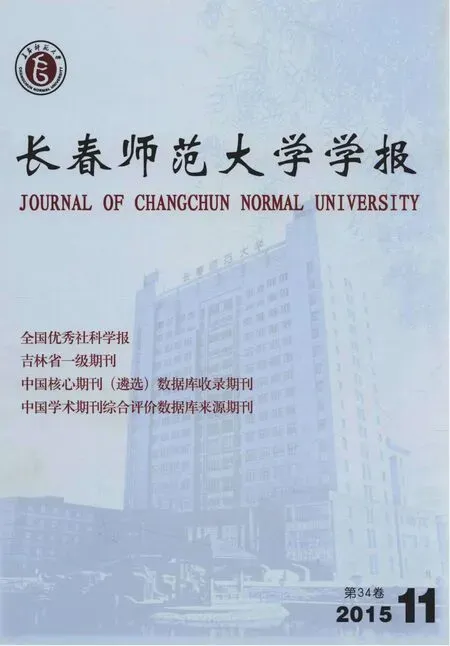直面現實的叩問,直擊時代的悲傷——論方方《涂自強的個人悲傷》
唐 宇
(濟寧學院中文系,山東 曲阜273155)
方方的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是一部具有強烈現實感的作品,發表之后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作品中的農家學子涂自強憑借自身的勤奮考入大學,得到有著“學而優則仕”觀念的鄉鄰們的極大認同。他雖一直努力奮斗,但生活始終辛酸艱難,最終因疾病走向死亡。現實的殘酷讓他產生了“原罪”意識,這“原罪”來源于他無金錢、無關系、無根底、無背景的農家兒子身份。作品透過涂自強的故事,暗含了有關“公平”的社會問題,指出社會如果沒有公平,將是時代最大的悲傷。
一、鄉鄰的認同與現實的殘酷
一個人存在的價值感、自信心、成就感、滿足感基本上都來源于認同。如果沒有認同,人的內心就會感覺到與世界、與他人的疏離,自我存在也會逐漸走向毀滅。沒有認同感的人是無法生存的,而認同感的滿足方式又分為公眾認同和自我認同。對于考上大學的農村窮學生涂自強而言,他得到的公眾認同在鄉村和城市這兩個不同的地域是截然相反的。
涂自強的家鄉在遙遠偏僻的深山之中,那里的人們孤陋寡聞、封閉保守,信奉傳統的“學而優則仕”觀念。當涂自強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后,他得到了鄉鄰、親戚的極大認同。首先是四爹爹,他認為即將去武漢上大學的涂自強就是人才,為在這個村子中人數不占優勢的整個涂氏大家族爭了光。其次是村長,村長的邏輯是“學好了得去縣衙當官!村里只要有一個人當官,吃不到虧。朝內有人,一村人都好過。”如果說四爹爹的認同更多地來自于家族榮譽,那么村長的認同則體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傳承的“學而優則仕”觀念。村長完全從官本位的思想出發,把讀書與當官統一起來,一廂情愿地認為上了大學就能當官,當了官就能惠及鄉鄰。這種認同感擴及全村,因此,所有涂姓人家都給涂自強湊了學費。在他離開家時,全村老少幾乎全趕來為他送行,并留下“要當個大官回來”的囑托。涂自強在步行去武漢的途中在建筑工地打工時,臨走之際,耳邊也聽到“好點學,早點當個大官回來,給咱山里造點福”的喊聲。
然而,不管鄉鄰們的愿望多么天真與美好,涂自強所要面對的依然是殘酷的現實。當他來到上大學的城市之后,這種公眾認同發生了巨大的逆轉。
涂自強所面臨的現實殘酷首先體現在報到的那一幕。繳費時,他當著眾人的面解下已經骯臟不堪的布腰帶,從中摳出里面被汗水濕透的零錢一一數給收費員時,他面臨的是驚訝、同情、鄙夷的目光。在這種目光中,他的信心瞬間消失,心里變得茫然而膽怯,不知道怎么迎接大學的新生活。隨后,涂自強所面臨的現實殘酷還體現在他尷尬的愛情上。他和同在廚房幫工的中文系女生的身份地位以及經歷非常相似,在相處中萌發了愛情。而當他約女生去看黃鶴樓卻舍不得買80元一張的門票時,純潔的愛情被赤裸的金錢所輕視。之后,兩人之間產生了消除不掉的距離感,女生不久被開著銀色小車的男子接走,傍上了大款,不再來廚房幫工。
報到的尷尬、愛情的失敗還只是現實給涂自強的小小的打擊,更加殘酷的現實還體現在就業上。一個沒有家庭背景、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濟實力、沒有名牌大學的頭銜、沒有高學歷的普通本科畢業生,想要留在大城市,他所要面臨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父親的突然亡故讓涂自強錯過了考研時間,不得已匯入就業的洪流中。找到第一份做電話營銷的工作,辛苦半年后,老板卻卷款逃跑。后來又陸續做過廣告公司策劃、保險公司推銷、房地產公司文宣、電器商場送貨員、空調安裝人員,在暖氣公司的工作也幾次三番因為母親的原因而受到影響,最終被迫辭職。每一份工作都得在上司面前如履薄冰,都得在顧客面前拼盡全力,但依然薪水低微、朝不保夕。涂自強極度艱難地維持著自己和母親在大城市里的生活,租最廉價的房子,生活開支儉省到極致,這和鄉鄰們認為的讀了書就可以當大官、過上好生活的愿望實在相差太大。“學而優則仕”對涂自強而言簡直是個巨大的諷刺。
現實的殘酷還不僅于此。涂自強得知自己已經是肺癌晚期,這無異于命運給了他最沉重也最致命的一擊。沒有錢,無法住院治療;沒有錢,無法修繕老家的房子安頓母親;沒有錢,無法為母親以后的生活提供經濟來源。金錢再一次嘲諷了像涂自強這樣處在社會底層的弱勢人群。由此可見,出身于農村的涂自強由于自身經濟地位的低下,他所能得到的僅僅是和他經濟條件相近的鄉鄰們的認同。而在城市之中,在處處都需要錢的殘酷現實環境里,他得到的只有諷刺與蔑視。雖然我們并不認同“金錢萬能”這樣的觀點,但是,涂自強的經歷又的確折射出“沒有金錢萬萬不能”這樣的殘酷真相。由此,我們應該反思這個社會,到底能夠給涂自強這樣的人提供一些什么?
二、美好的人際關系——刻意營造的理想化世界
在涂自強的生活歷程中,小說刻意營造了一個充滿人情味的溫暖世界。在步行去武漢上大學的途中,他在山上遇到了給他提供飯菜的砍柴大嫂,在鎮上得到了李哥及工友們熱情的招待,工地上的老板給他最高的工錢,鎮中學的老師借給他地圖,牛肉店的老板娘介紹他去洗車店打工,雨夜有好心的大爹收留他過夜,讓他覺得“這世道上的人十分善良”。到學校后,他遇到了為他在食堂找到工作的“戴眼鏡的老師”,食堂的師傅們給他幾乎免費的飯菜,宿舍里的同學也把自己的舊電腦、舊手機送給他,專業老師鼓勵他考研,讓他“真心覺得學校太好了,而同學們也太好了。”可以看到,涂自強的確是遇到了許多給他溫暖的人,這些溫暖的人情彰顯了美好的人性,也營造出了一個理想化的溫暖世界,這樣的世界能夠讓涂自強平靜而安穩地度過他的大學時光。但是,現實世界會一直這樣溫暖嗎?仔細分析便不難發現,在這些施予他溫暖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與他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陌生人,是同樣處在社會底層的人;還有一部分是發生在人際關系相對單純的校園之中,單純的校園環境給予了他單純的師生之愛和同學友愛。
這種溫暖在涂自強走向復雜的社會之后,很自然地沒有得以延續。他在廣告公司遇到了卷款逃跑的師兄老板,使得他辛苦工作大半年本該得到的提成加獎金五千多元化為泡影。他在暖氣公司工作時,因為中午吃飯時總是買最便宜的盒飯,受到的是同事的譏諷與嘲笑。他喜歡的那個細眉女孩,更是以他無房無車直截了當地拒絕了他。因他母親在飯店打工與顧客發生沖突和突然走失,他耽誤了公司的事情,卻得不到同情和理解,冷漠的老板反而強迫他辭職。和他同屋租房的舍友,先是嘲笑他儉樸的個人開支清單,接著以他渾身發出餿臭味要求他必須去澡堂洗澡。大學同學聚會時,他得去李同學住的賓館免費洗澡,因為不會開淋浴開關調不好水溫,不會堵上浴池,他受到以往同學放肆的狂笑。
由此可見,在涂自強的學生時代結束后,他面對的不是溫暖的幫助,恰恰相反,他面對更多的是欺騙,是因為貧窮而受到的輕視與嘲笑,他甚至沒有得到過同樣來自底層的其他人的關心和幫助。那種純粹而美好的人際關系是作者的一種向往與追求,是她刻意營造的一個理想化的世界。當涂自強走出淳樸閉塞的山鄉村落,離開單純美好的“象牙塔”校園,他所面對的就不再是類似“邊城”中的那種自然和諧、美好融洽的人際關系,一無所有的他必然在看重金錢、注重物質追求的現實社會中,在疏離冷漠的人際關系中舉步維艱。這樣的人文環境也促成了涂自強的悲劇,使他后來在艱辛的打拼中無所慰藉,使他在生活最艱難的時刻無所依傍。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選擇回到自己的故鄉,回到那種原初的簡單淳樸的環境中,這也是在另一個層面表達了涂自強在精神上的一種向往。
三、勤奮自強與“原罪”意識
涂自強學習勤奮刻苦,是全村唯一考上大學的;他工作踏實肯干,無論在哪里打工都能得到認可與好評;他生活節儉樸素,除了吃飽穿暖之外無任何多余開支,甚至對自己異常苛刻;他在大學里認真學習,從不缺課;他孝敬父母,父親亡故時犧牲考研機會匆忙回家,家中房子垮塌后毅然帶著母親去武漢同住,為了母親寧愿犧牲工作;他對人、對世界充滿感恩,總是覺得別人對他很好,盡可能用自己的勞動去回報他人;他樂觀堅強,能客觀冷靜地看待自己的出身。幾乎可以說涂自強是一個沒有缺點的青年。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種認命般的自我價值定位始終縈繞著他,他的思想里甚至出現了“原罪”意識。
上大學之后,涂自強逐漸認識到自己和其他同學在家庭背景和經濟實力上的巨大差距。在強烈的對照中,他時常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種既認命又樂觀的思想。父親亡故之后,涂自強通過考取學位改變命運的人生規劃成為泡影,這一次他深刻地覺得“這就是命。我的命!”在老家的房子被大雪壓塌、母親被壓傷后,涂自強第一次產生了“原罪”意識。“他很明白,除了這個逃掉的老板,這世界并沒有誰虧待于他,這世間的人也并沒有誰惡待過他。相反,那些來自無數人們的溫暖,就像是許多的手一直在撫摸他。而他享受這種撫摸之后,而對的仍然是陣陣痛感。這世界于自己是哪里不對呢?是哪里扭著了呢?莫不是,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我有原罪?這本就是我的原始創痛?”他去宜昌工作看山峽大壩時,看到地勢決定水的方向,此時再一次想到“原罪”,他想“他的命運同樣也是地勢所定,這幾乎就是他的原罪哩。”
“原罪”一詞來自《圣經》。基督教認為原罪指的是人類生而俱來的、洗脫不掉的罪行。當然,這種罪行不是實指,而是指人性中有犯罪、墮落、作惡的傾向或者源頭。原罪說法的重點不是叫人贖罪,而是讓人明白自身的不足。對于涂自強而言,他認識到的“原罪”就是地勢,就是每個人出生的起點,就是他的家庭背景。
涂自強出生在大山深處的溪南村,從村子里走到鎮上要大半天。他的父親沉默寡言,一輩子在山里打柴刨土豆地,母親也是個老實的普通婦女。他是家里存活的唯一兒子。他從來不記得自己吃飽過,上學時靠喝涼水撐飽肚子。涂自強的命運似乎是給定的,他的人生就像家鄉的那條河,“河并不寬,石頭遍布。”小說一開頭就已經為他的人生歷程定下了一個狹窄坎坷的基調,接著又以他在沙漠中獨自艱難爬行的夢境加強了這種意味和象征。涂自強帶著他的“原罪”去奮斗,而他的“原罪”,“就只是他來自鄉村,是一個無關系無根底無背景的農家兒子”[1]。所以,不管涂自強怎么努力、怎么自強,到最后都只能是徒勞一場。涂自強這個名字,本身就寓示了結局。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無法選擇的“原罪”,當真是涂自強們所應該背負的罪責嗎?我們的這個時代,為什么出身寒門就是“有罪”呢?像涂自強這樣背負“原罪”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又該如何進行自我救贖?小說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問題,但沒有給出答案。
四、去啟蒙化與社會公平
涂自強的形象,本來應該是個勵志的典型。他一直在努力奮斗,一直在試圖跟上城市人的步伐。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拼了命,但還是無法讓自己和母親過上好一些的生活。他也曾經有過在武漢安家立業的夢想,但都一次又一次地被現實的變故擊得粉碎。正如小說結尾所言:“他從未松懈,卻也從未得到。”作者沒有拿涂自強這個形象對當代青年進行一種教育、一種啟蒙,因為按照世俗的觀點來看,他的人生是失敗的。對于這樣一個青年,作者只能給他安排一個悲劇的結局,讓他得了癌癥,將不久于人世。如果他不得癌癥,在這個大城市中,他依然會碰得頭破血流,謀生艱難。如果涂自強活著,他的未來會好嗎?他的未來怎么樣才能好呢?這是作者也給不出答案的問題。
涂自強的故事是沉重的,讓人扼腕嘆息,讓人如芒在背,讓我們深深體味到個體生命的微小和悲涼。小說起名為《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表面上把悲傷都賦予了個人,其實是把悲傷指向了整個時代。在創作談中,作者方方明確地說到:“任何個人的奮斗,都得仰仗一個有可能讓你的個人奮斗得以成功的時代。……一個時代,如果不能給如涂自強這樣的青年以希望,或者說讓他們左突右沖還是找不到生路,那它的前景是令人擔憂的。”[1]命運明顯對涂自強是不公平的,他自己也說:“我也從沒指望這世上有一個公平的社會。”不公平如此顯而易見,正是這個社會的悲哀所在。涂自強需要一個可以公平競爭、公平奮斗的時代和社會,“在一個沒有公平的社會里,他的悲傷注定不只是個人悲傷。”[1]
我們的這個時代,所追求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就是社會的公平。社會公平所指向的是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它體現出來的是人與人之間一種平等的社會關系。社會公平包括生存公平、產權公平和發展公平。顯而易見,涂自強的生存與發展都存在著一種潛在的不公平。城市與鄉村,在小說中似乎被設置為一種二元對立的因素。城市意味著經濟發達、商品豐富、城市繁榮,而鄉村意味著經濟落后。巨大的城鄉差別,寓示了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公的殘酷現實。涂自強是一個來自鄉村的無關系、無根底、無背景的“三無”人員,他想要在城市中生存下來要付出比一般城市人多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他要再想在城市中獲得發展的機會,可能性更小。所以,生存公平、發展公平,體現在有著城市夢的涂自強身上,正是一種顯在的不公平。
涂自強的故事是普通的,他所經歷的都是常態之下的事情,但這個普通的故事讓人對整個時代產生深深的思考和憂慮,這種常態下的事情必有它不太正常的地方。小說是虛構的,它以這種典型化的方式,透過社會的表象,直擊時代的軟肋,把“公平”這個問題擺在所有人面前,讓所有人意識到社會如果沒有公平,將是時代最大的悲傷!而怎樣能盡快、盡好地解決這種不公平,是每個人都應該深深思考的。
[1]方方.這當然不只是個人悲傷[J].小說選刊,201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