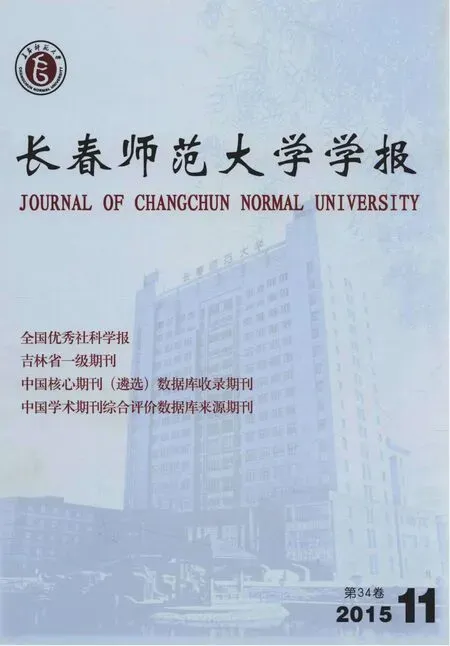19世紀中期美國女性小說暢銷原因探析
崔 娃
(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19世紀中期,美國文學市場空前繁榮,涌現出眾多為我們所熟知的經典作家,如霍桑、梅爾維爾、惠特曼。這一時期被評論家F·O·馬西森稱為“美國的文藝復興”。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文藝復興”不僅僅由以上那些男性作家所組成。許多女性作家創作的小說作品在19世紀中期的美國文壇也大放異彩,如蘇珊·沃納的代表作《廣闊、廣闊的世界》(1850年)是美國首部銷量過百萬的小說;瑪麗亞·康明斯的《燈夫》(1854年)在出版后的八周就銷售了4萬冊;哈里葉特·比徹·斯托的《湯姆叔叔的小屋》(1852年)是19世紀美國除《圣經》外最暢銷的文學作品。此外,還有范妮·費恩的《露絲·霍爾》(1855年)、E·D·E·N·索思沃斯的《隱藏的手》(1859年)、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小婦人》(1868年)等等。關于19世紀中期美國女性小說繁榮興盛的原因,我們大致可以從社會的流行思想、文學市場、女性作家和女性讀者三方面進行考察。
一、社會的流行思想
19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流行“真正女性崇拜”思想,主要針對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提出了一系列行為準則和倫理規范。歷史學家芭芭拉·韋爾特將之概括為四種女性美德,即虔誠、順從、貞潔、持家。當時的社會認為,女性只有具備了這四種美德,才能被稱為“真正女性”。
當時的社會認為“真正女性”首先應該具備的美德是虔誠。男性在尋找配偶時,會首先考慮對方是否虔誠。社會普遍認為,虔誠的宗教信仰對女性至關重要,宗教信仰會使女性忠于家庭,而沒有宗教信仰的女性是無法想象的。當時的社會還要求女性順從男性,認為男性是社會的推動者、主動的行動者,而女性則是被動的回應者,無論作為妻子、母親、女兒、姐妹都始終處于從屬地位,只有懂得服從,才能成為“真正女性”。對當時的年輕女性來說,貞潔是非常重要的。女性若抵擋了男性的侵犯,保護了自己的貞潔,則可以證明其強大的力量,并可以自豪地聲稱自己具有無價的女性美德。當時的女性雜志經常提及女性持家的美德。女性要盡力營造溫馨歡樂的家庭氣氛,使自己的丈夫不會去別的地方尋歡作樂。同時,女性應該經常鼓勵、寬慰自己的丈夫,做他們的心靈護士和道德導師。在家庭里,“女性的重要任務是把自己的丈夫召喚到上帝面前。女性不僅是家庭的道德標準,同時也要負責整個家庭的道德提升”[1]。
19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經歷了工業革命和西部大開發。這兩個重大事件為普通百姓改善生活和發財致富創造了大量的機會。在眾多的機會面前,許多人在欲望的誘惑下擁抱物質主義,放棄了精神追求,引發了諸如社會倫理道德滑坡、家庭觀念淡薄、忽視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這時,“真正女性崇拜”思想作為救世良方被提了出來,其目的就是想用女性的高尚道德影響力來緩解甚至消除這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用具有虔誠、順從、貞潔、持家四大美德的女性來“重新支撐起美利堅民族的道德脊梁”[2]。家庭是社會結構中最小的單位,對維護良好的社會道德秩序至關重要。家庭也是教育下一代的起點,子女的教育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因此,家庭和社會的道德守護者角色理所當然地落在了女性的肩上。19世紀中期美國女性作家創作的小說作品迎合了這種思想,塑造了一個又一個女性道德典范形象,深受讀者歡迎。
二、文學市場
19世紀上半葉,英國作家的作品在美國的廣泛發行為當地培養了眾多的讀者群體,而這些讀者群體也成為美國作家竭力吸引的對象。對英國圖書的印刷、宣傳、發行使美國的出版業逐步走向成熟,為美國文學的繁榮興盛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美國的文學中心主要集中在港埠城市,這些城市的出版商可以用低廉的費用將圖書發行到廣大內陸地區。隨著鐵路取代船運,圖書可以被更為快捷地發行到全國各地。圖書出版行業中的一些弊端和惡性競爭行為在19世紀40年代也得到了控制。至此,比較成熟穩定的圖書出版市場基本形成。
19世紀40年代,美國圖書出版業在全國主要城市的主要公司中得到鞏固,出版和發行的不斷資本化和高效化使美國本土作家獲得了不斷擴大的文學市場。與此同時,廣泛發行的文學雜志也培養了廣大的讀者群體。19世紀40年代末,這些文學雜志的讀者品味開始決定美國文學的模式。[3]
三、女性作家和女性讀者
19世紀上半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轉變,美國男性離開家庭,進入社會公共領域,女性則繼續留在家庭。家庭——由男性主宰卻又被社會定義為女性的領域——成為當時女性作家主要的寫作范圍。女性不像男性那樣可以在邊疆和海洋任意馳騁、在商界和政界發揮才干,只能在社會所規定的領域內進行活動。這些被限定在家庭領域內的女性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描寫了女性的困境與無奈、探索與追求,引起了女性讀者的共鳴,滿足了女性讀者的心理需求。這些女性作家實際上超越了家庭領域,試圖去影響社會公共領域。這些女性作家用親身經歷向世人證明,她們能夠把女性的家庭角色和作家的職業身份結合起來。
美國著名女性評論家尼娜·貝姆稱:“如果小說是19世紀人們眼中家庭伊甸園里的蘋果,那么女性就是蘋果的大吃家。”[4]19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圖書出版不斷發展,教育迅速普及,推動了巨大讀者群體的形成。當時流行的“真正女性崇拜”思想使社會認識到女性教育的必要性。到了18世紀60年代,大多數的美國白人女性具有了一定的文化程度,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都進入公立學校學習讀、寫、算等方面的基本知識。[5]眾多女性被女性作家創作的小說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深深地吸引,對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有強烈的興趣,可以從女主人公身上找到與自己相似的生活經歷,并從女主人公的奮斗歷程中獲得鼓舞和激勵。
四、結語
霍桑曾不無抱怨地跟他的出版商說:“美國現在完全被一群亂寫亂畫的女人占據了。”[6]霍桑的抱怨或許可以反證這樣一個事實:與同時代的男性作家相比,19世紀中期的美國女性作家“更受歡迎,更具影響力”[7]。也許正是由于“真正女性崇拜”的流行思想、成熟穩定的文學市場、龐大的女性讀者群體,19世紀中期的美國女性作家在小說中塑造了大量順應當時流行思想和讀者需求的女性道德典范形象,引起廣大女性讀者的強烈共鳴。這些女性小說牢牢占據了當時的美國文學市場,并廣泛參與了讀者的道德塑造。
[1]Barbara Welter: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 [J].American Quarterly,1966,18(2):163-164.
[2]王恩銘.20世紀美國婦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17.
[3]薩克文·伯克維奇.劍橋美國文學史:第二卷,1820-1865年[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78.
[4]Nina Baym.Novels,Reader,and Reviewers:Responser to Fic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54.
[5]金莉.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19世紀美國女性小說家及作品[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18.
[6]Sacvan Bercovitch,Cyrus R.K.Patell,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lume 2,Prose Writing 1820-1865[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89.
[7]James D.Wallace.Hawthorne and the Scribbling Women Reconsidered[J].American Literature,1990,62(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