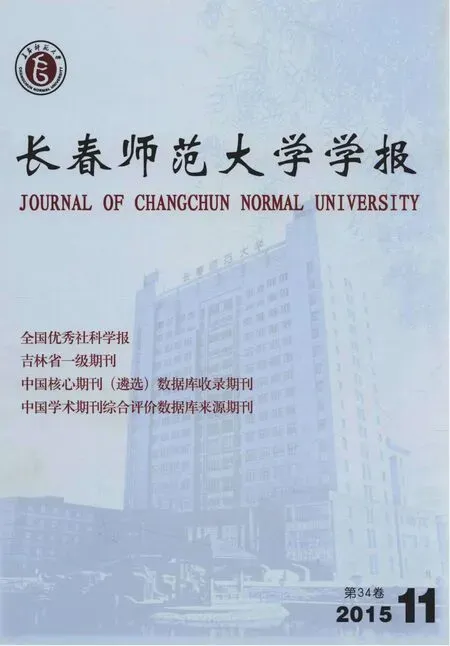坂口安吾作品中的男性本位思想解讀
馬碧誠
(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100081)
日本戰后無賴派作家坂口安吾在戰后發表的文學評論《墮落論》直指天皇制、武士道、婦女貞潔等傳統道德倫理,提出應以人性為武器、以墮落為途徑迎來社會和人類的新生,震動了日本文壇。同時,坂口小說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和其他作品中大量的關于女性問題的討論也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坂口安吾曾在多部作品中對戰爭時期及戰敗初期的女性處境進行細致描寫,如《白癡》《戰爭與一個女人》《續戰爭與一個女人》等。作品《白癡》描寫了住在破爛住宅區的女人們,她們有的未婚先孕卻不知道孩子父親是誰,有的有許多個情夫,有的是別人的小妾和賣淫女。女主人公白癡被定位為“一具女人的肉體”“會哭泣的狗”“豬”。作品《戰爭與一個女人》中的主人公野村認為既然戰爭會摧毀一切,也就沒有必要擁有愛情和家庭,于是在戰爭開始后與一名妓女如夫妻一般住在一起,過著有性無愛的生活。戰敗后,野村開始思考戰敗對日本的影響,并開始糾結是否要與女人分手,而女人卻再次在出軌與肉欲中沉淪,不會為生活的變化而憂慮和感傷。通過對小說作品的解析,可以看出坂口的作品中存在的男性本位思想和作家對女性問題的態度。本文以《白癡》為中心,從兩性社會角色的差異和男性尊嚴兩個方面對坂口的男性本位思想進行具體分析。
一、男性與女性的社會角色差異
《白癡》講述了戰爭期間文藝工作者伊澤收留了從鄰居家逃出來的白癡女人,二人悄悄同居并且在空襲中一起逃難的故事。在當時的日本社會,“為天皇效忠、為太陽旗感動、對士兵感謝”是主流。因此,伊澤的同事們雖然身為文藝工作者,喊著自我、人類、個性等口號,心里卻鄙夷對個性和自我的追求。在日常工作等級關系嚴格的環境中,堅持藝術獨創型和個性的伊澤受到同事排擠,漸漸對工作失去了熱情。伊澤收留了白癡女人后無時無刻都在恐懼著可能出現的麻煩,擔心白癡女跑出房間被人發現。甚至在空襲來臨時還拼盡全力保持理智,只怕白癡女被鄰居發現。他對鄰居說:“我是個文藝工作者,性命危機時就是審視自己的機會,在這種關頭必須做最后的較量。我想要逃走,卻不能逃。不能錯過這樣的機會。”在恐懼到極點時,伊澤還顧慮著事發影響到自己的聲譽。
這樣的形象安排映射出了社會對男性的角色要求,即要求其與國家一體,為天皇效忠并支持戰爭,必須遵守社會規則和道德,否則就會受到社會的排斥。但是,這顯然不符合人的本性。伊澤在這樣的生活中郁郁不得志,直到怪鄰居的白癡妻子闖入伊澤的生活。在伊澤下班回家發現白癡女躲在自己家中時,考慮了種種解決方案,最終“心里涌起一股奇妙的勇氣”而收留了她。通過對伊澤心理的透析可以看出,他冒險收留這個女人并非出于善良,而是出于好奇心和刺激感。他對自己說“收留白癡女一晚權當義務,沒有必要擔心害怕,也不必為自己慶幸這一突發事件感到羞恥”。但是,當伊澤得知白癡女對自己抱有好感時,內心深處仍然感到慶幸。他認為自己“在齷齪的世間被世俗染黑,追尋虛無的影子,已經十分疲憊”,只有白癡女沒有被這一切詛咒,與白癡女在一起,他似乎能夠擺脫現實的束縛。收留白癡女之后,他擔心事情敗露對自己造成不良影響,在內心深處卻認為這種不安是“低俗的”,自己與世俗一樣惡劣低下。由此可見,社會對男性的角色定位和道德標準是伊澤痛苦的根源之一。
文中兩位主人公的對比也是女性所代表的“本性人”與男人代表的“道德人”的對比。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是沒有道德概念的,有的只是對肉欲的渴望和對死亡的恐懼,代表著人類的本性和原始欲望。白癡女前來投奔時,伊澤感受到“白癡女行事意志和感受能力是非‘人’的”,這里的“人”顯然是指伊澤一類的道德人。關于白癡女給伊澤的生活帶來的變化僅僅是“家里多了一具女人的肉體而已”、“還不如桌子挪動了位置”。白癡女對肉欲的渴望和對死亡的恐懼沒有絲毫理智的克制和抵抗,意識不到別人的存在,帶著“盲目、無意識、絕對的孤獨”。她雖然在空襲時一度表現出了意志,但在空襲過后又恢復成一具肉體。
與白癡女形成對比的是伊澤所代表的“道德人”。他掙扎在現實的生活與藝術的夢想、肉體的渴望與世俗的目光、死亡的恐懼與理智的抵抗之中,唯恐因“墮落”而陷入“絕對的孤獨”。由此可見,社會環境和道德標準對兩性角色的要求是存在差別的。坂口在《續墮落論》中也提過這個觀點,主張“雖說處于黑暗中的女性是社會制度的缺陷,也許他們中很多人都覺得戰爭比起被征用、從事辛苦的體力勞動來得要有意思得多,強制女性穿上制服工作,根本無法斷言這是一種健全的生活”。
二、女性:襯托男性尊嚴的“他者”
男性尊嚴是另一個驅使伊澤收留白癡女人的原因。在職場、生活上失意的伊澤迫切需要滿足自己的優越感和虛榮心。在小說的逃難情節中,白癡女本能地想跟隨人流而去,伊澤卻根據對地形的分析選擇了另一條路線。他向白癡女解釋,那條路是死路一條,要求白癡女跟隨他一起逃向另一個方向。對于他的話,白癡女第一次表達出了自己的意志——用力點點頭。這讓伊澤十分震撼,使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擁抱的是一個“人”并為此感到驕傲。在這一情節中,伊澤在混亂中表現機智,在鄰居中樹立了“文藝工作者”的大無畏形象,又能在逃難中當機立斷,并且見證了白癡女第一次表現出自我意識。伊澤感對白癡女有意識的回應到十分震撼,為自己拯救和解放了這個女人而感到驕傲。
法國存在主義學者波伏娃認為,男性不能孤立地實現他自己,他的生活是一項艱巨的事業,因此他們需要占有、馴服女人作為“他者”,以證實自己的自由感和優越感。張京媛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指出:“男性的魅力似乎完全來自于他對女性所表現的力量以及他以武力對世界進行的統治,而不是源于他自身某種豐富的、極富生命力的東西。”[1]在生活中,伊澤是脆弱的,雖然在工作中無法施展十分痛苦,卻不愿辭去工作,因為“如果不去上班,就沒有煙抽了”。雖然心中有對藝術的理想,但是每月二百元的工資才是現實的幸福。伊澤的精神和靈魂都被這二百日元所束縛,使他感到作為人的卑微與可憐。但是,他卻在白癡女到來這一突發事件中感到了慶幸和感動。白癡女沒有名字,沒有思考能力,完全被伊澤所支配、領導和解放。在逃跑的過程中,白癡女第一次表現出了自我意識,但這種意識并非她自發產生的,而是對伊澤的肯定與服從。因此,伊澤不會拋棄白癡女,對白癡女的支配權是他在艱難、不自由的生活環境下唯一的成就和自由。
三、男性本位思想的根源
波伏娃認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即女性的形成取決于她所面臨的處境。通過對坂口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男性本位思想來源于“女性依附于男性而存在”這一社會普遍認識。坂口曾借歌舞表演的例子闡述了該觀點。受邀在東京帝國劇院觀看歌舞表演時,他認為跳起舞來的男演員看起來愚蠢無比,除了這樣一個特例:“這個男人一上臺,女人們就變得毫不引人注意。讓我想起了敲著木魚念經,舞臺上充滿了堂堂男人的威風,不僅男人的形象顯得更高大,女人們像蝴蝶一樣安心地依偎著他翩翩起舞,讓人看了心情愉悅。我沒有想到會在男演員身上看到可靠和威嚴……我不愿在舞臺上看到柔弱愚蠢的男演員,如果男演員像森川信那樣充滿威嚴,受到女演員們依賴和簇擁,女演員就是不漂亮,跳的差勁也沒關系。一樣很美,讓我感到愉快。”男人和女人,一個被威嚴,一個臣服,展示出了讓坂口贊嘆的美感。在他看來,女人理應依附于男人,作為男人的附屬品而存在。這樣的依附關系并非來源于二者的生理差異,而是他們所面對的社會處境。
首先,在經濟方面不平等。在生活中,坂口把夫妻關系歸結于經濟上的依附,在《安吾人生案內——その八安吾愛妻物語》中具體表述了自己的觀點:“從女性在經濟上處于從屬地位的意義上來說,可以是一種妻子為丈夫提供服務的營生,帶有商業性質。全面了解丈夫的性情,提供其他女人無法提供的周到服務……日本女性為了丈夫付出一切的獻身性,是處于從屬關系下最高級別的商品,在從屬性的夫妻關系中,沒有比這更珍貴的了。”坂口認為,女性在經濟上處于從屬地位,這就意味著女性必須依附于男性。這樣的關系近似于商業關系。于是,安吾對女性提出了具有“獻身精神”的要求,即妻子要為丈夫付出一切。相對的,男性享有著經濟主導帶來的特權。“就算是呼吁男女同權,只要在經濟上女人依附于男人,一切都是空談。男女同學也好,培養男人做好護花使者的習慣也好,無論男女在外的生活如何改變,只要在經濟上女人依附于男人,最終男人還是要求女人有獻身的美德……對外和氣,對內霸道,并不意味著男人不顧熱愛家庭。在妻子經濟上依附男人的情況下,甚至于可以說男人在家中霸道的態度是妥當的”。
其次,女性對男性的依附也來自于女性的心理依賴。坂口在《孤獨閑談》中描繪了一對十分不般配的夫婦。男人又老又丑,女人年輕且尚有姿色,女人公然與其他男人交好,但夫妻二人卻照常維持著婚姻。對此,坂口指出了女性對男性天然的依附心理:“對于老丑的恐懼如今清楚地展現在主婦面前,什么樣的男人都可以,老不死的也可以,必須有所依靠。對于瘋狂愛著自己的老板,就算是覺得厭煩無比,也必須依靠。那不是愛情的聲音,是衰敗的年齡或是肉體的聲音”。由此可見,女性沒有自我意識和超越意識是這種依附關系形成的另一個原因。
男性和女性截然不同的社會處境導致了男性在生理、經濟、心理等方面對女性的支配和領導,而女性也習慣于隱藏真實本性,迎合男性創造的文化環境來認識自我和進行選擇。筆者無意將男女置于二元對立的立場對其作品中的男性本位思想進行批判,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坂口的作品所表現的兩性社會角色差異、男性尊嚴和存在于兩性之間的依附關系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也是女性讀者在閱讀中應該思考的問題。
[1]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