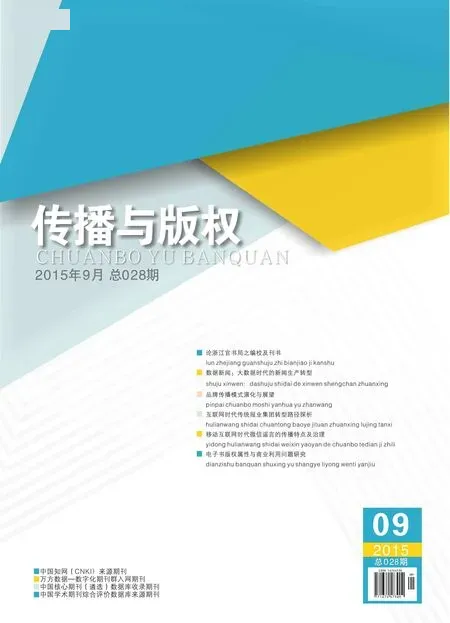微博動員:特性、偏差與治道
王 楊
微博動員:特性、偏差與治道
王 楊
區別于傳統社會動員,微博動員表現出動員主體祛魅化、動員客體節點化、動員時空脫域化的傳播特性。而處理好政府、網民和新媒體之間的三重關系,是保證微博動員有序發展的重要前提。面對微博動員在發揮作用過程中出現的信息偽化、情緒極化、道德矮化等傳播失范問題,政府部門應建立網絡輿情的監測和預警機制,拓展政府與新媒體間的互動對話機制,提升網民綜合素養,推進完善網絡立法,進一步規范和引導治理微博動員的健康發展。
微博;社會動員;政府;治理
[作 者]王楊,博士,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因為現實表達渠道不暢,社會代償機制不健全,網絡成為民眾利益訴求和意見表達的重要平臺,網絡動員成為規避現實風險、救濟現實缺失的有效選擇。這其中,微博因其獨特的媒體屬性和傳播方式成為公眾發起網絡動員的新載體和新手段。微博動員中的框架議題如微博救助、微博公益等事件表現了微博動員的正向功能,體現出微博可貴的民主協商精神。但同時也應看到,在涉及沖突事件和敏感問題的微博動員議題中,如把握不好引導和管理的尺度,極有可能發生集群暴力事件,對社會秩序造成極大破壞。因此,探究微博動員的傳播特性及效應偏差,并提出規范其健康發展的治理措施,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一、微博動員的差異化特性
區別于傳統的社會動員及網絡動員,微博因其即時互動、裂變式擴散的傳播特點和媒體屬性,使微博動員以其獨有的傳播優勢和傳播影響力,表現出不同于其他動員方式的差異化特征。
(一)動員主體“祛魅化”
傳統的社會動員中,政府作為無可爭議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具有無可比擬的領導力和號召力。進入互聯網時代,動員主體的權威性被消解。在微博動員中,動員主體的角色更多的由普通公民來承擔,即使是加V認證的意見領袖,也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組織者,作為普通個體中的精英人士,他們只是自覺不自覺地發揮著網上動員組織者的作用。觀察2011年至2013年的微博動員事件可以發現,不論是微博救助還是微博反腐,其發起者多為無官方背景的個體公民。在微博動員中,個體的傳播行為因微博高效低廉的傳播特性,完全可以隨時隨地地觸發一場全國互動的行動聯盟。微博動員主體的“祛魅”效應和能動作用,更多地激發了他者主體的積極呼應,使微博動員越來越多地演變為草根階層政治參與和利益訴求的重要手段。“而在網絡時代,一旦公共危機顯性化和媒介化,更多的社會行動者將會意識到,通過個人策略性的行動可能對現實政治產生一定的干預效果。”[1]
(二)動員客體“節點化”
微博動員中的參與客體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傳統社會動員客體的“群體”性面貌,但其本質也并非毫無聯系和疏離的“原子化”個體。網絡空間的最大特性是,它改變了公民個體的“原子化”狀態,使他們成為相互連接的節點,構建成相互交錯的復雜網絡,微博恰恰是這種復雜節點網絡的形象代言。微博中的每個用戶以自己為節點形成個體社會網絡,無數的個體社會網絡之間,依靠粉絲作為互連公共節點,使微博形成無界化的巨大社會網絡。微博通過“關注”和“轉發”功能,使信息發生多級流動和核裂變式的傳播,發揮輻射式影響,在極短時間內覆蓋無限范圍的網絡空間。這使得微博動員的參與客體在接收到動員信息后,可以相互轉發,交互影響,使微力量在交叉連接的關系網絡中,聚沙成塔,匯流成河,最后產生網絡的聚合效應,微能量轉變為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在輿論場不斷地釋放動能,從而促使現實行動的發生,實現社會目標。
(三)動員時空“脫域化”
“脫域”的概念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意為“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2]在微博中,它擺脫或弱化了與現實時空的關聯,信息傳播的無邊界和無限時空為動員主、客體發起動員和參與動員的“脫域”提供了技術支持,不同地域和不同時間內的網民可以通過微博在“近似的同一時空內進行言語、思想、情緒與行為上的互動”[3]。微博動員既打破了傳統動員中依托地緣關系或親緣關系的組織傳播形態,又創新了普通網絡動員中論壇、博客等傳播平臺的信息裂變和信息聚合的效能特點,以無限延伸和無限拓展的時空場域,“凝聚社會資源,發動社會運動,促使集體行動”[4]。這也使得微博動員可以通過主導性的框架性動員議題,引發動員客體的情緒共振和心理共鳴,在極短時間內發起跨越地域和脫離時空的表達參與和行為互動,以病毒傳播的速度幾何式倍增,在虛擬空間內形成主流輿論并對現實世界施壓,促使動員議題的進一步解決和動員目的的實現。
二、微博動員中的三重關系
在微博動員中,政府、網民和以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之間的三重關系構成了動員事件發生和演化的重要原因。它們在動員過程中扮演著獨有的角色,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對三者關系的正確處理和維護,有利于微博動員進程的健康、有序發展。
(一)新媒體提升網民在官民關系中的主動性
中國傳統的社會動員通常是政府主導型,政府在國家生活中掌握有較多的社會資源,往往容易在某一特定時期集中調動人力、物力來“辦大事”,在動員過程中,“全能型”政府可以對動員進程進行主動性干預,使社會動員有意識地按預期方向發展。而在微博代表的虛擬社會動員中,網民在動員進程中發揮了更多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動員事件的生成和演化過程中,從信息發布到輿論放大,從意見擴散到采取行動,網民自始至終扮演著發起者、組織者以及參與者的重要角色,使微博動員具有了更多的自發性和無意識性。
(二)新媒體促進政府與網民平等關系形成
傳統的社會動員多為政府發起的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動員,政府與民眾之間是以“命令”“指揮”等表征意義符號為特征的層級關系,不存在平等的概念。而在微博動員中,新媒體與生俱來的平民化氣質和平等的精神內涵拉近了政府與網民之間的層級,政府和網民之間可以通過意見協商來進行平等對話,網民通過微博發起的政治反腐和社會救助,通過新媒體放大輿論壓力,民意倒逼政府決策,迫使政府進行相應調整,形成新型的政治參與和有效監督。微博動員中,權力被消解,身份和地位的特征被弱化,政府和網民更多地被橫向流動的信息連接在一起,平等化的關系對接進一步得到加強。
(三)新媒體構建政府與網民互信關系
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要更好地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新媒體應在政府與網民之間更好地發揮溝通和橋梁的作用。作為草根階層意見表達的社會化媒介,微博在傳遞弱勢群體利益訴求的同時,也應及時傳遞政府積極、公信的聲音,搭建政府與網民之間良性互動、智慧溝通的平臺。微博一方面要有效地反映網民的意見和需求,聚合網民力量,實現微博動員功能在虛擬空間中地有效釋放;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做到全面、系統地發布政府信息,解釋政府行為,引導網絡輿論,贏得公眾對政府的理解與支持,構建政府與網民互信關系。
三、微博社會動員進程中的效應偏差
由于微博社會動員的低準入門檻,發起和參與微博動員的主、客體身份隱蔽又龐雜,這使得微博動員在發揮作用的進程中易出現信息偽化、情緒極化、道德矮化等非理性表現和傳播失范問題。
(一)“信息偽化”效應
在以微博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中,信息流通因為缺少“把關”和信息核實的責任意識,導致謠言和陰謀論加速傳播,信息“偽化”現象嚴重。在微博動員進程中,部分議題表現為緊跟熱點事件的虛假信息,在引發高關注度的同時,很多網民缺乏對信息來源和真實性的基本辨識能力,在恐慌壓力下盲目地成為網絡謠言的“搬運工”,致使謠言在快速傳播的過程中衍生出新的謠言,引發更大范圍的群體性恐慌。由于信源發布者的匿名身份和謠言信息的高速傳播,加大了政府研判和治理的難度,部分謠言如不能得到及時回應和適度引導,被別有用心的人士利用易導致煽動性動員,在“蝴蝶效應”的作用下,對社會秩序產生更大的破壞力。
(二)“情緒極化”效應
網絡群體的集體無意識心理導致網民情緒極易互相傳染和強化。而在群體中,“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5]因此,“群體極化傾向在網上發生的比率是現實生活中面對面的兩倍多”。[5]在微博動員中,動員主體和參與者在表達意見、立場、態度過程中所夾雜的負面情緒,因微博傳播的低成本和匿名傳播的無約束性,極易在網絡世界不受控制地蔓延,使群體情緒向負面極端化轉化。同時,在微博動員過程中,“協同過濾”現象和“信息繭房”的存在使動員參與者只能接近相似的觀點或自我主動選擇的觀點,進一步加劇了信息的“窄化”傳播,對立的觀點或不同的聲音被壓制,群體極化的風險進一步增大。此外,在情感動員中,“悲傷”和“憤怒”常被用來引發動員群體的情緒共振,如掌控不好動員的情感尺度,也易導致動員群體的情緒極化。
(三)“道德矮化”效應
在微博動員議題提出后,各方聲音匯聚進行意見協商,當主導性的議題框架激發參與群體的情感共鳴的同時,議題框架中的“不公正情節”也會激發公眾憤怒、失望的不滿情緒,諷刺、戲謔乃至攻擊、謾罵等非理性表達成為部分網民情緒宣泄的出口,人肉搜索、網絡審判等網絡暴力現象拷問社會道德觀念的滑坡,網絡給了人們肆無忌憚和眾聲喧嘩的理由和借口。在微博傳播的海量信息中,低俗、惡搞、暴力的負面信息淹沒了正面的價值觀點,網絡負能量的增長見證著社會價值觀念的淪陷。在充滿誘導的偏見框架議題中,網民對“問題”官員的幸災樂禍和對炫富行為的冷嘲熱諷,反映了“仇官”和“仇富”的集體社會心理,在一邊倒的尖刻批駁和謾罵攻擊中,道德矮化幾乎成為一種條件反射。
四、政府對微博動員的引導與治理
(一)建立網絡輿情的監測和預警機制,掌握網絡輿論動向
安全管理領域中的“海恩法則”告訴我們,任何一起重大事故的發生都是有征兆并且可預防的,只要我們及時發現征兆和苗頭并進行排查處理,就可以防患于未然。針對網絡輿情的發展動態,各地政府應該建立7×24小時的點、線、面的監測預警系統,形成多角度、全領域的輿情監測網絡,密切關注網絡輿論的動向。這樣,在微博動員初期,針對動員議題的提出,尤其是涉及社會沖突性質的動員議題,及時進行監測和預判。如果發現有異常變動,各部門在最短時間內調動和整合各種力量,發揮聯動的合力應對危機,從而預防群體性危機事件的發生,并減輕危機事件發生后的損失。
(二)完善和拓展政府與新媒體間的互動渠道和對話機制
因為現實社會表達渠道不暢,中國的互聯網承擔了超越常規意義的社會代償功能,微博尤為突出。要弱化微博動員功能的過度開發,在社會生活中,就要不斷拓寬社會各類群體意見表達、利益訴求、政治參與、輿論監督的現實渠道,及時疏導公眾的負面情緒;不斷增強政府與新媒體之間的互動與對話機制,如政府與微博意見領袖展開對話,設立面向新媒體領域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等,通過對話和引導,消除虛擬空間內可能發生轉化的不良社會運動。同時,在微博動員中,隨著主導性的意見信息不斷的裂變擴散,主導性的動員議題也對政府產生一定的輿論壓力,這要求政府必須在“第一時間”進行主動回應,爭分奪秒,及時發布權威信息,不斷公布事件最新進展,掌握輿論引導主動權,引導熱點事件走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三)加強網民自律意識,提升網民媒介素養
因為微博動員的參與者為數量龐大、身份隱蔽、沖動多變的網民群體,這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難度。因此,促使網民理性、有序地參與網上動員也成為政府能更好地引導和掌握網絡群體性事件發展走向的重要基礎。加強網民自律意識,應敦促微博意見領袖率先垂范,加強網絡傳播中的言論自律,引導網民培養責任意識,不信謠,不傳謠,堅守“七條底線”,客觀傳遞,理性表達,積極傳播社會正能量。同時,政府、媒體、學校等相關部門,應做好針對網民群體如何正確使用新媒體的宣傳和教育工作,培養網民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時,能夠正確選擇,準確辨識,合理評判,正確地使用微博傳播信息,表達觀點,明確新媒體的意義和價值,提升自己的判斷力和免疫力。
(四)制定并完善網絡空間的法律法規
在推行依法治國的當下,“依法治網”也成為題中之義。在國際社會,雖然各個國家在互聯網監管方面的具體規制各不相同,但立法治網已漸成世界趨勢。如美國自1995年以來先后出臺130多項法律法規來約束網絡犯罪,德國、瑞典已經有多起逮捕并審判網上新納粹主義者的案例,新加坡也出臺多項法律嚴厲打擊和制止任何個人、團體或國家利用網絡來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目前,中國也已出臺200多部規范網絡空間的法律法規,對于以發起暴力集群事件為目的的微博動員有一定的規制作用。但中國的網絡立法依然存在著立法滯后、法律層級低、部門立法明顯、重管理輕權利等問題。隨著依法治國的逐漸推進,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可以借鑒國外的最佳實踐經驗,進一步完善和提升網絡立法的有效性和科學性,營造健康、有序的網絡環境。[本文系2013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微博在地區事務中社會動員的演變與引導研究”(項目編號:L13DXW018)的研究成果;遼寧省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社交媒體環境下大學生的手機使用狀況調查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01410165000049)的相關成果]
[1]張盛.網絡政治參與的特征與治道變革[J].現代傳播,2014(9).
[2]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3]鄧希泉.網絡集群行為的主要特征及其發生機制研究[J].社會科學研究,2010(1).
[4]劉小燕.政治傳播中微博動員的作用機理[J].山東社會科學,2013(5).
[5]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M].黃維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