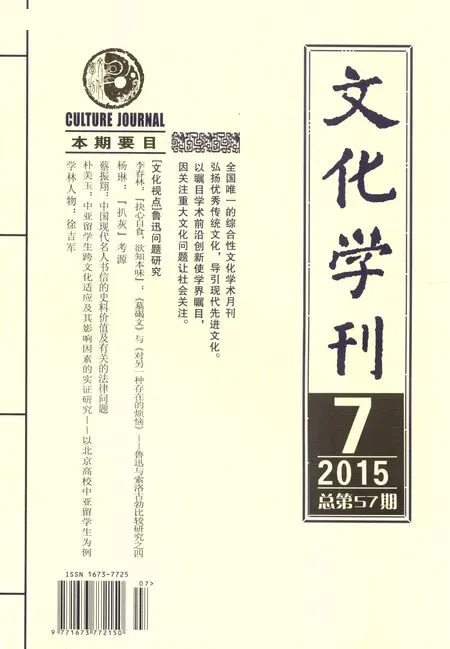民俗之美
——談鄂爾多斯青銅牌飾的裝飾規(guī)律
郝建斌王文靜
(燕山大學(xué)藝術(shù)與設(shè)計(jì)學(xué)院,河北秦皇島066004;
河北科技師范學(xué)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民俗之美
——談鄂爾多斯青銅牌飾的裝飾規(guī)律
郝建斌王文靜
(燕山大學(xué)藝術(shù)與設(shè)計(jì)學(xué)院,河北秦皇島066004;
河北科技師范學(xué)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鄂爾多斯青銅器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藝術(shù)形式,其中的青銅牌飾以其獨(dú)特的樣式、風(fēng)格特點(diǎn)形成動(dòng)物風(fēng)格的裝飾美。本文從以動(dòng)物風(fēng)格為主的表現(xiàn)主題,牌飾的輪廓變化精妙多樣,藝術(shù)表現(xiàn)語(yǔ)言韻律感強(qiáng),平行、并列的構(gòu)圖藝術(shù)形式,利用透雕的藝術(shù)形式拓展空間表現(xiàn)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鄂爾多斯青銅牌飾的裝飾規(guī)律,旨在深入挖掘其裝飾藝術(shù)美形式,以期為當(dāng)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提供借鑒與參考。
鄂爾多斯;鄂爾多斯青銅器;青銅牌飾;裝飾美
如果說(shuō)蒙古高原是橫亙?cè)谥袊?guó)北方的巨龍,那么鄂爾多斯就是鑲嵌在高原上一顆璀璨的明珠,擁有悠久民族文化的鄂爾多斯為中華燦爛文明奉獻(xiàn)了頗具含金量的文化歷史。
在中華文明的發(fā)展進(jìn)程中,北方草原文明與漢文明的互融影響使中華文化顯示出多元的發(fā)展態(tài)勢(shì)。近些年,北方草原文化[1]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文化形態(tài),為眾多學(xué)者和專家重視,研究、探索成果頗豐,角度各異,可謂是草原文化在當(dāng)代文化研究中的春天。草原人民面對(duì)嚴(yán)酷的生活環(huán)境而產(chǎn)生浪漫想象力;對(duì)草原游牧、狩獵生活的細(xì)節(jié)觀察、體會(huì),也為眾多的藝術(shù)品創(chuàng)作提供不竭源泉,形成獨(dú)特的藝術(shù)發(fā)展形勢(shì)。被藝術(shù)、考古界廣泛關(guān)注的“鄂爾多斯青銅器”[2]就是以草原為背景創(chuàng)作的金屬藝術(shù)品。鄂爾多斯地區(qū)是北方草原文明的重要發(fā)展地,是鄂青銅器主要出土地,其地名也因此而來(lái)。除了鄂地區(qū),該類物品在我國(guó)長(zhǎng)城以北地區(qū)也廣泛分布,蒙古及俄羅斯的南西伯利亞地區(qū)也有類似作品。作為一個(gè)成熟的藝術(shù)形式,它們雖然出土地不同,但在藝術(shù)風(fēng)格、物理特征上都有較大相同性。
“鄂爾多斯青銅器”起始時(shí)間較早,大約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其發(fā)展經(jīng)歷的民族大概有東胡、匈奴、烏桓、鮮卑等,匈奴控制北方草原時(shí)達(dá)鼎盛期,即中原的秦漢帝國(guó)時(shí)代。在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漢化進(jìn)程中,鄂式青銅器藝術(shù)逐漸沒(méi)落,直至消亡,跨度為1 000年左右。它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造型樣式規(guī)律的來(lái)源,據(jù)專家研究分析,有的與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有著不解的淵源;有的有與南西伯利亞卡拉蘇克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跡;更多的認(rèn)為是我國(guó)北方民族文化發(fā)展的產(chǎn)物(鄂爾多斯起源說(shuō)),但不管其屬何種來(lái)源,都是古代中國(guó)北方悠久文化傳統(tǒng)與中原商周文化的強(qiáng)烈影響而促其發(fā)達(dá)與繁榮的。[3]
“鄂爾多斯青銅器”的樣式很多,其主要藝術(shù)形式是一種牌飾。這種青銅牌飾從功用上來(lái)講,是北方馬背民族的服裝與馬具上的裝飾物;從歷史意義上講,它是我國(guó)悠久青銅文化的多元成份;從審美上講,它所形成的審美規(guī)律是我國(guó)古代雕塑藝術(shù)的延伸與擴(kuò)展,它獨(dú)特的造型特征與裝飾語(yǔ)言,豐富了我國(guó)雕塑藝術(shù)的表現(xiàn)語(yǔ)言與表達(dá)技巧。大量精美遺物的出土為我國(guó)裝飾藝術(shù)的研究、發(fā)展提供重要資料,其獨(dú)特的裝飾美符號(hào)也為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提供借鑒與參照。基于此,對(duì)鄂爾多斯青銅牌飾的裝飾美進(jìn)行深入分析與闡述,旨在挖掘古代文明潛力,繼承歷史藝術(shù)傳統(tǒng),造福當(dāng)代藝術(shù)創(chuàng)作。
鄂爾多斯青銅牌飾(以下簡(jiǎn)稱鄂牌飾)的裝飾規(guī)律分析如下。
第一,動(dòng)物風(fēng)格為主的表現(xiàn)主題。鄂牌飾的主要內(nèi)容多為幾何形、人形、怪獸形、動(dòng)物形等,其中以表現(xiàn)動(dòng)物形的圖案(有雙羊、四馬或動(dòng)物搏斗等,幾乎囊括草原上的所有動(dòng)物形象)最多,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狩獵、生活場(chǎng)景的較少。因此,鄂牌飾也屬于歐亞草原動(dòng)物風(fēng)格藝術(shù)的一種,分布于鄂爾多斯的朱開(kāi)溝文化人群可能是這種文化的最早探索者。[4]
典型作品有內(nèi)蒙阿魯柴登的《四虎食羊金牌飾》、寧夏固原的《虎銜驢銅牌》以及烏蘭察布二蘭溝出土的《三鹿紋銅牌》等。這些以動(dòng)物形象為主要表達(dá)內(nèi)容的牌飾,經(jīng)過(guò)北方不同民族不同時(shí)期的多年經(jīng)營(yíng)、演變后,最終形成獨(dú)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從而在中國(guó)乃至世界上奠定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地位。
第二,牌飾的輪廓變化精妙多樣,對(duì)比性強(qiáng),適形性好。牌飾作為一種裝飾用的金屬制品,其實(shí)用的局限性已基本確定它的基本形狀為方形,易于佩戴、安裝。但聰明的草原先民卻在這個(gè)有限的空間內(nèi)變化出豐富、精彩的內(nèi)容來(lái)。首先,將牌飾的外形稍作變化,以方形為基礎(chǔ),演變出長(zhǎng)方形(有橫豎構(gòu)圖)、正方形、B形、P形,甚至有以夸張的動(dòng)物造型為輪廓、無(wú)規(guī)則外形的樣式,如內(nèi)蒙呼和浩特出土的《鹿形銅牌》;其次,在動(dòng)物造型安排上,體現(xiàn)強(qiáng)弱、動(dòng)靜對(duì)比的節(jié)奏美感。
以長(zhǎng)方形或正方形為輪廓的牌飾,外形表現(xiàn)基本為對(duì)稱式、排列式;B形、P形一般是以動(dòng)物的外輪廓進(jìn)行夸張、變形后適形到字母B或P,不脫離牌飾的基本形(方形)。這兩種形式的表達(dá)頗具技巧、匠心獨(dú)用。以《虎銜驢》為例進(jìn)行分析,該作品中老虎的形象十分威猛,虎虎生威,有力的虎爪堅(jiān)定地邁著大步,仿佛能聽(tīng)到落地有聲。為適合P形構(gòu)圖,作者在安排老虎的尾巴時(shí)沒(méi)有讓它同自然中真實(shí)景象一致,而是蜷曲內(nèi)收到老虎腹下,和后腿、腹部連結(jié),而虎尾也同虎背臀部形成一條優(yōu)美的下滑弧線。在處理驢的造型上更顯示出工匠的技藝精湛,驢被虎噬住脖子,又反身被甩到虎背上,驢的后腿、蹄自然地落在虎肩部,在胸、背處形成另一條弧線,既表現(xiàn)出驢無(wú)力掙扎的垂死狀態(tài),又為外輪廓的適形起到關(guān)鍵作用,可謂鬼斧神工。
第三,藝術(shù)表現(xiàn)語(yǔ)言以概括、抽象、夸張、變形為主,韻律感強(qiáng)。鄂牌飾的藝術(shù)表現(xiàn)語(yǔ)言完全符合裝飾造型規(guī)律。工匠在深入觀察自然的基礎(chǔ)上,以寫實(shí)為基礎(chǔ),進(jìn)行裝飾性語(yǔ)言處理,從而形成鄂牌飾的裝飾美。我們今天分析所有牌飾中的動(dòng)物或人物形象,尤其是匈奴時(shí)期的牌飾造型會(huì)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動(dòng)物、人物或景物,無(wú)不是在抓住對(duì)象最本質(zhì)的特征,概括抽象后進(jìn)行夸張、變形。如呼和浩特的《鹿形銅牌》,大角鹿昂首屈足,耳部后垂到腦后,大角形成四個(gè)相連的圓環(huán)形貼在肩背部,整體造型飽滿、有勁,張力十足,通過(guò)寫實(shí)與變形的巧妙結(jié)合,既照顧到外形輪廓的整體性,又使動(dòng)物形象生動(dòng)、鮮活。外廓的整體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產(chǎn)工藝的難度,可謂精妙至極。
第四,平行、并列的構(gòu)圖適合浮雕藝術(shù)形式的表現(xiàn)。在鄂牌飾中,很多作品都對(duì)造型進(jìn)行平行、并列式的安排,解決浮雕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缺憾,即因透視、形體遮擋而無(wú)法看全形象的全部。制作鄂牌飾的匠人和古埃及壁畫(huà)、浮雕的制作者有著一樣聰慧的頭腦,同樣把形象進(jìn)行平行式排列構(gòu)圖,使觀者能全面了解全部形象,如上文提到的《虎銜驢》中老虎四肢的表現(xiàn);再如遼寧西岔溝的《雙牛銅牌》中,作者在一方形回紋外框中對(duì)稱地并列著兩只雄健的牛,平行并列的構(gòu)圖形式,使牛的形象展露無(wú)疑,非常適合浮雕藝術(shù)的表現(xiàn)。
第五,利用透雕的藝術(shù)形式拓展空間表現(xiàn)。鄂牌飾作品都利用浮雕形式來(lái)表現(xiàn),實(shí)用功能限制浮雕起位高度,因此,聰明的匠人就利用鏤空透雕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來(lái)拓展空間,彌補(bǔ)起位低造成的立體感不強(qiáng)的缺憾。關(guān)于鏤空,著名的老雕塑家傅天仇曾說(shuō)過(guò)“鉆孔是人工找到深度和厚度的勞動(dòng),鉆孔沖破平面,它是三度空間的第三空間,是雕塑造型的基本因素,這是立體裝飾的開(kāi)始”。[5]因此,鏤空在雕塑發(fā)展中極為重要。
在鄂爾多斯地區(qū)出土的很多牌飾,利用鏤空技法,使薄薄的銅牌飾立體感增強(qiáng),有“小物件大乾坤”的藝術(shù)感受。如《群鹿紋銅牌飾》《盤羊紋銅牌飾》《人面紋銅牌飾》《四驢紋銅牌飾》等等,無(wú)不在浮雕的表現(xiàn)手法中加入鏤空技巧,使作品顯得精巧神奇。
鄂牌飾依托草原文明,在方寸之間綻開(kāi)艷麗的藝術(shù)花朵,取得令人矚目的藝術(shù)成就。作為北方草原文明的一部分,它的造型方式也影響到中原地區(qū)的動(dòng)物風(fēng)格形式,如漢代的某些動(dòng)物形象的雕刻作品。鄂牌飾以其精巧的造型方式、獨(dú)特的裝飾藝術(shù)形式,在中國(guó)古代雕塑藝術(shù)中獲得特殊席位。近些年,越來(lái)越多的人關(guān)注草原文化,關(guān)注草原文明的發(fā)展,鄂牌飾也以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魅力被更多的人所關(guān)注。它的裝飾風(fēng)格、樣式也為當(dāng)今藝術(shù)的發(fā)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本文意在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研究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透過(guò)牌飾這支獨(dú)放異彩的奇葩,促進(jìn)北方草原文化和民俗文化研究的深入,使人們對(duì)北方游牧民俗文明有更多了解,對(duì)古老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有更多感悟。
[1][2]陳兆復(fù).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美術(shù)[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91.29-30.
[3]阿木爾巴圖.蒙古族美術(shù)研究[M].沈陽(yáng):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115.
[4]郭物.馬背上的信仰——?dú)W亞草原動(dòng)物風(fēng)格藝術(shù)[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5.91.
[5]傅天仇.移情的藝術(shù)——中國(guó)雕塑初探[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6.82.
【責(zé)任編輯:王 崇】
K876.41
A
1673-7725(2015)07-0078-03
2015-05-20
郝建斌(1975-),男,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人,講師,主要從事雕塑藝術(sh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