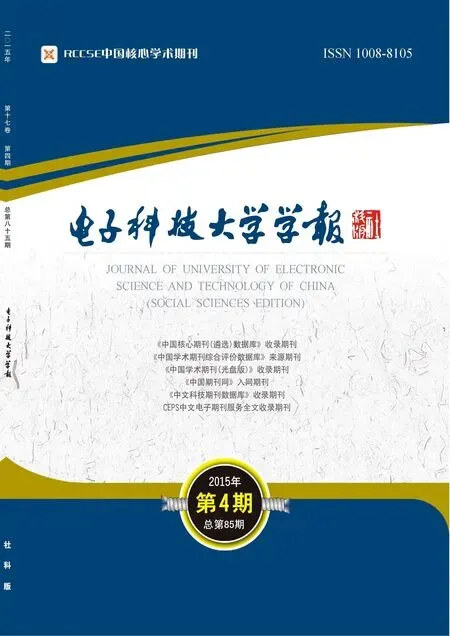中西文化詩學歷史意識比較論
[摘 要] 中國文化詩學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為指導,強調歷史的總體性和進步性發展原則;文學真實要求作者反映世界和生活的真諦與本質,準確把握事物發展邏輯和規律。西方文化詩學研究從考察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到關注歷史認識和對歷史的理解和闡釋,按照語言學模式重新審視歷史,弱化歷史的客觀規律性特點,強調歷史的共時性、互文性和建構性;真理的產生不再為人們所發現,而是在不斷建構和創造中。
[文獻標識碼]A
[DOI]10.14071/j.1008-8105(2015)04-0082-05
[收稿日期] 2014 ? 12 ? 11
[基金項目] 華南師范大學青年教師科研培育基金資助項目“新歷史主義文論的本土化實踐”(14SK10);武漢大學研究生自主科研項目“賽博空間的身份認同——基于文藝作品的批判性反思”(2014111010203).
[作者簡介] 盧絮(1979? )女,博士,華南師范大學南海校區講師;吳群濤(1982? )女,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引言
西方文化詩學拒絕把文學作品孤立于社會、生活、歷史之外。在反歷史的形式化潮流中重標歷史的維度,打破歷史和文學的二元對立,將文學看成是歷史、文化的一部分。格林布拉特強調“歷史與文學的相互疊加” [1]關系,認為“歷史首先是一種話語,但并不意味著這是否定歷史的真實性;個人無法超越自身的歷史,所以歷史就其建構的現時性變得因時因人而異。” [1]中國文化詩學抱著強烈的重振文學威力和干預現實的美好愿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探索文學理論新的出路。童慶炳指出:“文化詩學的意義就是力圖把所謂的‘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結合起來,把結構與歷史結合起來,把文本與文化結合起來,加強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歷史深度和文化意味,走出一條文學理論的新路來。” [2]這里的歷史深度即是指分析文學作品要進入歷史語境,同時文學作品是歷史的產物,是某種歷史語境下適應時代需要而產生的。中西文化詩學對于歷史的關注程度是相似的,但在關注的內容和方式,在看待歷史本身,以及歷史與文學關系的問題上卻大異其趣。
一、歷史記憶與文學記憶
人類發展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棄舊擇新的過程,但所謂的新和舊不是截然不同和猝然分裂的,兩者之間通過人類的記憶取得千絲萬縷的聯系。克羅齊對于歷史的記憶功能不曾懷疑,“歷史之有別于純粹的幻想,……就在于歷史是根據記憶的。”但他同時指出“歷史只能把拿破侖和查理大帝,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法國革命和意大利統一,當作具有個別面貌的個別事物再現出來” [3]。在這里,克羅齊客觀地評價了記憶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可歷史最終還是呈現出個體性、事件性和片段性的特征。就如歷史無法被完全無誤地記錄一樣,文學記憶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同樣值得懷疑。伊格爾頓說:“所有文學作品都是由閱讀它們的社會‘再創作’的(只是無意識地),事實上,沒有一部作品在閱讀時不是被‘再創作’的。” [4]這里說的雖然是讀者在閱讀中的‘再創作’過程,但恰恰體現了文學記憶的能動性和變異性,它根據具體情境的變化而變化。
西方文化詩學認為在文學研究中重新恢復文化、歷史和政治的視野,無疑是對于商業化和專業化越來越明顯的學術界以及整個西方社會對于歷史采取回避、忽略或者遺忘等趨勢的一種反撥。蒙特羅斯曾經強調人文學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去除學生認為歷史一去不復返的看法;要使學生們認識到他們自己就生活在歷史中。正是針對這種歷史意識的衰退,西方文化詩學重整歷史的大旗,主張通過回到過去找回已經失落的人文精神。必須注意的是,這里的歷史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數大寫的歷史(History),而是小寫復數的歷史(histories)。以前由重大歷史事件和君主、英雄排列組合的歷史開始轉向由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婚喪嫁娶、奇聞軼事組成的歷史。此時,呈現出來的歷史不是單一性、整體性和規律性的特征,這和個體記憶的豐富性、片段性和偶發性特點密切相關。小寫復數的歷史(histories)實際上成了由不同的個人、敘事者講述的故事(his-stories和her-stories)的組合,歷史成為個體記憶的集合體。格林布拉特的研究注重具體歷史時空中那些普通個體的日常生活,通過描繪生動的社會場景來闡釋各種文化力量、權力、意識形態等因素的交匯、互動、協商和往復循環,以完成對于當時復雜的社會系統及其內部各組成成分相互關系的還原,從而顛覆或重寫歷史。西方文化詩學認為“歷史是指過去發生了什么(事件的集合),同時也是對于這些事件的解釋(即故事)” [1]。所謂歷史的真實和客觀性來自于對這些故事的合理性的批判和反思。過去,即歷史不是一個客觀存在物,它與其文本重構不可分離,就如文學文本不可能與作家及讀者分離一樣 [1]。
中國文化詩學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作為指導,強調歷史的總體性和進步性發展原則,任何對于社會生活的理解都來源于對人類歷史的總體性思考;規律支配著歷史進程,并允許對于人類發展做出長遠的預測,深信共產主義社會是最理想的人類社會,且一定會實現。文學的屬性和對它的闡釋要置于歷史語境中,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重視文學的歷史差異性的同時,強調文學對于歷史的服從,用再現或反映論來界定文學的工具屬性。以上所述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反復強調的歷史與文學的觀念。實際上,我們容易忘記的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既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和確定性,也具有為現實服務和滿足當下需求的現時性和不確定性,而后一點往往被我們故意忽略,或避而不談。馬克思曾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5]。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之一本雅明更是認為過去能否成為歷史,是與現時密切相關的。不能被現在關注和認可的歷史都會不可避免地消失,而一切記錄下來的歷史都是統治階層和征服者的歷史。同時,本雅明認為歷史進步論也是值得懷疑的,很多的殘暴和戰爭行為就是在進步的名義下進行的。他說“應該把一個特定的時代從連續統一的歷史過程中爆破出來,把一個特定的人的生平事跡從一個時代中爆破出來,把一件特定的事情從他的整個生平事跡中爆破出來” [6]。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對于“歷史連續性”的爆破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已經相去甚遠,而和福柯的斷裂歷史觀、格林布拉特的懷疑、謹慎和批判地對待歷史的態度息息相通。西方文化詩學研究套路之一便是從歷史洪流中梳理出的個人日記、奇聞軼事、男女日常生活等歷史的邊角和碎片,以及它們與文學的關系,這無疑類似于本雅明所說的“爆破”方法。可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本身是發展變化的,有些中國的文化詩學研究者認為“歷史本身是一種客觀存在”,強調“歷史的必然性”,認為“具有強烈歷史記憶功能的文學向人們展示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的邏輯 [7]”等觀念似乎與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歷史發展觀本身是矛盾的,值得進一步思考和修正。
文學記憶和歷史記憶有極其相似性。如果承認歷史有其文本性,即如詹姆遜所說只有通過文本才能接近歷史的話,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歷史的當下呈現是極具主觀特性的。這不是要否定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客觀存在,而是提醒我們要對歷史記憶、歷史敘事時刻保持警惕,要通過自己的獨立觀察和思考理解歷史的真相。西方文化詩學在這一點上是有十分清晰認識的,格林布拉特主張從歷史記憶的模糊、隱秘處挖掘歷史新意,借以補充或顛覆已有的固定歷史敘事,就是這一歷史、文學觀念的體現。中國文化詩學理論建構的前提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在這種歷史觀的指導下,歷史記憶和文學記憶不是沒有個體性,而是通常被集體性、階級性記憶遮蔽。個體在強大歷史理性和集體意象面前顯得異常卑微,個體記憶要么被忽視,要么被替換,歷史時空中始終游蕩的是關于國家、民族和階級集體記憶幽靈。在這種情況下,個體不可能成為歷史的真正主體,只能扮演歷史中的配角和小丑的角色。
二、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
一成不變、一勞永逸的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方式并不存在,變動不居以適應當下語境才是其始終不變的特點。同時,文本作為語言能指游戲的場所,充滿了難以辨析的空白和縫隙,因此,對于文本的闡釋同樣變得不可確定,而現時需要最終成為人們試圖捕捉歷史真實的最后“一根稻草”。任何一位作家都局限于他自身的歷史階段,都只能闡述人類心靈在其發展的時代所達到的那種境地。歷史和文學的任何一種敘事對于現時的人們而言從來不是不確定的,因為理解和闡釋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他們手中。
西方文化詩學對于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觀點最好的表述體現在“歷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歷史化”。一方面,歷史是通過文本來敘事和顯現的,沒有文本就沒有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可文本不能成為歷史事實;另一方面,本身并不是客觀事實的文本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對于實際產生了影響和后果,成為了歷史事實構成的一部分。歷史和文本的這種互文關系同時也顯示了現在和過去、前人和后人的互文對話關系。格林布拉特非常重視想象對于歷史敘事的作用,甚至把它等同于想象在文學敘事中的作用。他提倡文學研究者們“把所有想象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8]。海登·懷特作為歷史學家,他的視野似乎超出了一般歷史學者學術眼光所能及的范圍,想象對于歷史敘事的重要性體現在海登·懷特的元歷史話語中。首先,他把歷史作品看做是敘事性散文結構的一種,他說“它們一般而言是詩學的,具體而言在本質上是語言學的。歷史話語和文學話語在修辭和比喻的層面取得溝通” [9]。其次,他識別出四種可能的歷史言說模式,即形式論、有機論、機械論和情境論,就情節化而言,它們是浪漫劇、戲劇、悲劇和諷刺劇四種原型。由此,他認為史學家表現出一種本質上是“詩性的行為”。在他看來,任何歷史都是一種修辭想象,歷史是被構建的,而且是被詩意地構建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歷史不過是作為修辭和文本的歷史,其敘事過程和模式取決于敘事者的修辭態度、方式、闡釋角度和價值立場。海登·懷特明顯受到結構主義語言論的影響,在歷史研究中采用文學研究方法,使得文學和歷史文本在元史學的理論框架下回歸敘事問題。由上可見,西方文化詩學所指的文學敘事和歷史敘事并沒有本質的不同,兩者同樣需要借助于語言、文本的強大支撐力量,也需要豐富想象力的潤色、補充。
中國文化詩學則強調文學的審美詩意屬性,堅持以審美體驗為中心。雖然呼吁文學“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結合起來,把結構與歷史結合起來,把文本和文化結合起來,加強文學研究的歷史深度和文化意味” [2],但是筆者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始終束縛著學者的思考方向和深度。一方面,把文學看作是歷史發展的暫時的產物,這意味著脫離了形式主義文本分析的窠臼,把文本置于一定的歷史語境中,通過歷史文化的視野來分析和闡釋文本,但歷史作為文學研究的參照系,繼續充當著文學研究的佐證和背景;另一方面,雖然強調歷史語境的具體性和進行文本細讀,但文學作為歷史的衍生物而存在,文學與歷史依舊赫然獨立于彼此,歷史的地位,其客觀性、確定性和進步性不容文學虛構的質疑和攪亂,而文學的作用僅限于反映和揭示這些特征。中國文化詩學的提倡者們有感于現實精神文化的缺失,對于社會中丑陋的、消極的和缺乏詩意的傾向深感擔憂,希望文學能承擔“介入”社會的功能,通過文學審美實現人類精神的某種救贖。實際上,就上文提到的他們對于文學與歷史的關系的理解來推論,文學不是歷史的參與者和創造者,無法影響和干預歷史的演變進程,使得這種期待頗具理想的烏托邦色彩。
敘事歷史主義已然成為西方當代歷史學主流,也不斷刷新當代人們的歷史觀念,“歷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換言之,我們只有通過預先的文本化才能接近歷史” [10]。說的是人們雖然可以通過具體器物接觸歷史,但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呈現只有通過敘事的方式進行。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以文本的方式在詩學層面相遇,歷史與文學的二元關系應被互動、多元關系所置換。西方文化詩學秉持的就是這樣一種敘事歷史主義的原則,也是由于這點引起了海登·懷特等其他人文學科領域的學者的強烈關注,同時也招致了許多批評。說到底,格林布拉特反對的就是對歷史和文學單方面的、宣稱唯一正確、權威的解釋,還有對所謂的宏偉的歷史演進模式的質疑。而中國文化詩學對這種敘事歷史主義的立場持有懷疑態度,很多學者反對新歷史主義理由便在此,即認為新歷史主義的歷史闡釋始終給人“一種歷史所指的感覺” [11]新歷史主義把“歷史等同于文本”,“把歷史文本的最終所指那個曾經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件’放逐了” [12]。對于新歷史主義的這種判斷至今還普遍存在,原因就在于中國學界始終把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截然區分開來。因此,筆者認為歷史與文學的二元對立觀念是中國文化詩學首先要解決的理論矛盾和困境。
三、歷史真實與文學真實
真實性問題自古以來就受到中西文論家的關注和探討。亞里士多德認為真實并非作品與其參照對象(即現實)的關系,而是與讀者信以為真的事物之間的關系。這關涉到作品與話語之間的關系,文學真實性不過是指話語與話語之間的關系,這與后現代文學理論的觀點不謀而合。話語在福柯看來是語言與言語結合起來的豐富而復雜的具體社會形態,是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中與社會權力關系相互纏繞的具體言語方式。在任何社會里,話語一旦產生,就立刻受到各種控制、篩選、組織和分配,這一過程使得某些知識取得權威,獲得“真理”般的地位和意義。然而,話語不是一個超越時空的結構,而被福柯賦予了歷史階段性的特征。話語在歷史中生成,也會在歷史中變化,在歷史某個時段成為真理的知識也許在另一個時段就為歷史所否定和淘汰。因此,對于歷史和文學的真實性問題的探討也終究會有其歷史的局限性。
西方文化詩學研究的典型方法,即通常由一則軼聞故事或真實存在的文物說起,引出對某個文學家或文學事件的描述。這種研究方法的目的就在于讓讀者相信研究者對歷史真實的客觀把握,那些看似研究者偶然間發現的原始素材,其實都是他們精心選擇用來描述和佐證自己判斷的有力證據。格林布拉特說:“我們要利用這些奇聞軼事,以一種精煉壓縮的形式,來展示活生生的經驗元素如何進入文學,平凡的日常生活和身體如何被記錄。”“我們想要發現過去真實存在的身體和聲音,如果這些身體早已腐朽,聲音早已沉寂,從而無從發現,那么我們至少要抓住那些與真實經驗息息相關的蛛絲馬跡。” [1]由此可見,西方文化詩學非常注重歷史存在的真實性,而文學的力量就是向后人顯示這種歷史真實性,顯示的方式則要回歸最普通個體的最普通日常生活,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那些關于真實的“蛛絲馬跡”如此難以追尋卻引人入勝,西方文化詩學研究者的興趣和重任之一便在此。
基于敘事歷史主義的立場,海登·懷特認為歷史事實在歷史學家的筆下不過是構思和講述故事的素材,他們的目的不是要鋪陳歷史的真相,而是表達和抒發歷史學家自身的人生觀和歷史觀。他在《元史學》的序言里說:“我想要強調的是,在我看來,歷史事實是構造出來的,固然,它是以對文獻和其他類型的歷史遺存的研究為基礎的,但盡管如此,它還是構造出來的。” [9]這種說法和上文所寫的西方文化詩學關于歷史真實的觀點還是有區別的,前者全然不顧歷史真實的存在,認為歷史事實完全是歷史學家想象和構造的結果,這樣的論斷自然不具備說服力,而后者雖然也同意想象力和敘事的重要性,但其目的就是對于歷史真實最可能的接近和最貼切把握,對歷史真實的觸摸應該說始終是西方文化詩學研究的重點。而海登·懷特所主張的歷史事實的構造等同于文學家的小說創作的觀念應該與之區分開來。
中國文化詩學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作為指導,強調歷史的真實性、總體性和進步性。歷史的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歷史學之所以成為一門學科,就其因為尊崇對歷史真實面目的還原,相信“隨著新物證、新資料、新視角和新方法的應用,人類正處于逐步接近真相、真實和真理的過程中。” [13]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詩學主張的是歷史真實是在辯證唯物論基礎上的歷史客觀性,歷史是一門依據史料,追求真實為目的科學。這和西方文化詩學所說的“觸摸真實”有根本的區別,因為前者認為歷史真實不容置疑、唯一正確、始終存在,因為歷史的科學性決定了它的真理性和無可爭辯性;而后者則質疑這種武斷的,實際上非科學的話語方式,進而站在邊緣化立場去發現另一種歷史真實。中國文化詩學高舉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旗幟,卻忽略這樣的話“凡是今天被承認是真理的東西,都有現時隱蔽著的而過些時候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同樣,凡現在被承認是謬誤的東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從前才被認作是真理” [14]。真理和謬誤只有放在有限的歷史階段內才能顯現出意義,一切有關絕對真理和人類絕對狀態的想法都是值得懷疑的。同樣,中國文化詩學研究者認為的文學真實要求作者反映世界和生活的真諦與本質,準確把握事物發展邏輯和規律也就顯得有些絕對化了,這違背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初衷。
史學家們一直在追尋歷史的真實,并以此來區分歷史和文學。近代科學的發展和普及也使歷史學家對于史料和證據的挖掘和判斷充滿自信,理性和科學主義觀點一直引領著近代以來傳統歷史學家的思考方向。強調歷史的客觀性、進步性和規律性,尋求歷史的真相是他們引以為豪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性主義的方法在瞬息萬變的當代世界顯得力不從心,他們也發現非理性因素時常干擾著他們的工作,我們非但不能發現歷史的真相,也無法預知歷史的走向。實際上,相對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歷史觀的更能使人信服,不要試圖真正客觀和真實地認識周圍的世界、過去的歷史和我們自身,沒有永恒不變的所謂規律和真理,一切都是話語的建構和宣揚。
結語
中西文化詩學在看待歷史和文學的功能,在處理歷史與文學關系問題上有著明顯的差別。中國文化詩學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強調歷史的客觀性和必然性,堅持歷史的總體性和進步性發展原則。歷史敘事的確定性與客觀性不容文學虛構的質疑與攪亂,文學真實要求作者反映世界和生活的本質,準確把握事物發展邏輯和規律。西方文化詩學研究從考察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到關注歷史認識和對歷史的理解和闡釋,按照語言學模式重新審視歷史的話語建構特征,弱化歷史的歷時性、客觀性和規律性,強調歷史的共時與互文。歷史話語和文學話語一樣,是在不斷建構和創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