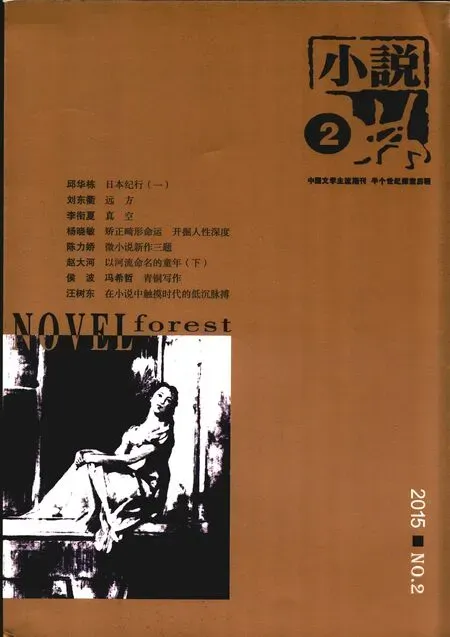小咖啡店靠窗子的餐桌
◎胡泓
小咖啡店靠窗子的餐桌
◎胡泓
在哈爾濱這個洋風盛行的城市里,這家小小的咖啡店可是不同尋常的。它除了有美味的咖啡和可口的俄羅斯傳統飲食,還死心塌地地守護著這座城市獨有的一段俄僑的歷史。
據國內外史學家考證,1903年7月1日東清鐵路全線通車后,就從世界各地向哈爾濱涌來幾萬外國人。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暗殺后,1923年那一年就有二十多萬擁戴皇帝的俄國貴族上流社會和了不起的藝術家逃亡到了哈爾濱。據日本的哈爾濱研究學者的論著稱:“哈爾濱在這一時期成了俄國沙皇貴族在全世界唯一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文化的實際所在地和避難地。”那么,這幾十年當中,在哈爾濱生活的俄羅斯僑民一定有它獨特的魅力和美妙的故事。正如當時歐洲對她的評價——東方小巴黎。
與中央大街交叉口的西頭道街上,有一幢華麗的俄國人建造的兩層樓。一樓稍稍靠里面的墻上、門旁、大窗子四周,爬滿了枝繁葉茂的山葡萄藤。夏天一過,闊大茂密的葉子也遮不住綴滿串串的黑色小葡萄。窗戶和牌匾上的葡萄藤每年夏天都要修剪幾次,以免被遮擋。窗前有十叢紫丁香樹,也是由女店主與葡萄藤同時埋下的小樹苗。轉眼十幾年了,兩米多高的丁香樹遮了大半個玻璃窗。當它們在四月底開出擁擠成團團束束紫色的小小十字花瓣時,這個城市也四處飄起又香甜又溫情的香氣了。
房子是1914年建的,粉刷著橘黃色的外墻。六年前對面建了一幢難看的高樓以后,在夏天只有早九點到十一點,下午一點半到四點,陽光才會照進大窗子里,落在靠窗的雙人座的小桌子上和赭石色地面上。大廳里也變得明晃晃的到處閃動光輝。墻壁上和高高的天棚上反射到了柔和的光暈,有一種身臨其境的神圣感不禁會把過分的不以為然和放松收斂起來。室內按照三十年代的俄僑家里的大客廳風格陳設的。家具都是更早年代的。墻壁上掛滿了1903年至1942年代在哈爾濱生活的俄國人的照片。另一面墻則是店主的母親(也是俄國人)的朋友,九十一歲才故去的哈爾濱俄僑妮娜和她家人的照片。那架1889年的黑漆立式鋼琴,是妮娜的妹妹——音樂教師年輕時的愛琴。她的一家人去了澳大利亞。鋼琴現在依舊能彈出一百多年前的好聲音。還有玻璃櫥柜,里面用心地擺置著許多古老的餐具和茶具,看起來可不是普通瓷器。窗臺及可能的地方都放著盆花,枝葉精神抖擻。總之,這間小咖啡店,從里到外再從外到里,都與四周的景象截然不同或者說格格不入。它很特別,很頑固,在這間小空間里精致地展示一個過去了的時代,虔誠地紀念著曾經在這個城市生活過的俄國僑民。
這個小咖啡店完全拿出了歐洲大城市中有名咖啡店的風度。因此,誰也學不像它。這里有個很客觀的原因:據說拘謹有禮的女店主是個不平常的雕塑藝術家,正在名聲大噪的時候退隱下來。她是1978年隨母親離開哈爾濱去了澳大利亞。丈夫去世后,一個人帶著孩子在國外生活了二十幾年。等女兒結婚了,她就放心地回到故鄉開了這么個小店。問她為什么一定要回哈爾濱呢?她回答說:“沒什么理由,就是想回來,就回來了。”每年都回悉尼的家住兩個月。女店主的母親就是個在哈爾濱出生的俄國人。至于她的祖上是不是沙皇俄國的什么人物,就無從考證了。熟人都認為女店主血統高貴,這也不算是玩笑話。因為對待女店主這樣的好人絕不會有人失禮取笑她,尊敬還來不及呢。這就是這家小店為什么如此與眾不同,既不做作,又清高又雍容華貴的原因了。
當然還要說明一下,小店的名氣可不小。很多國內和國外的客人,特意來吃上兩個油煎包,喝上一盤紅菜湯再品嘗一杯咖啡的人可不算少。今天的網絡時代,一切瞬間傳遍地球各個角落。有客人在網上看到有這樣一段描寫,并且抄寫在了放在鋼琴蓋上的客人留言簿里:

窗前的小桌子
“……上午和煦的陽光,像凡·高的畫一樣的陽光,柔情地緊緊貼在奶油黃色的墻壁上。像鐘表的分針那樣不易察覺地移動。這是一幢古老又美麗的俄國式的兩層樓房,高大厚重又有華麗的雕塑。僅看這一隅,誰都會忘記自己是在哈爾濱。墻面爬滿了青藤(其實是山葡萄藤,藤架粗壯,枝健葉闊)。推開古老沉重的綠色木格子門(其實門是新做的,剛十幾年),突然入耳的是清脆歡跳的門鈴聲。坐在靠窗的雙人桌旁,叫來一杯香熱的摩卡,打開手中為享受這時光而帶來的書,書名是《流動的盛宴》。
“陽光落在桌子上,我知道我的臉龐會被桌上的光涂上了一層圣潔。我愛這桌子上的陽光,愛從鼻子下面飄來的咖啡香氣,在這間如同三十年代的俄國人的咖啡店里,我完全失去了時間概念和忘記了俗塵四起的世界,恍惚中是在巴黎或圣彼得堡……”
沒錯,這像是一個青年女性寫的。要表現超脫又注意細節。現在的女青年或大學生們,也許就一時心血來潮,受了一本書的蠱惑或者怎么說呢,都存在著那些太容易多變的情緒。每天都掙扎在墮落的追求金利又無法脫身離開的污泥濁水里,偶然想起離群索居一下,進到咖啡館體味一次歐洲或從前的俄國僑民的咖啡與茶,也可能為了時尚中的某種心境吧。細心的店主的確看到過留言簿里有前面那么一段描寫。她情緒一閃,產生出了一陣冷風似的為他人的惋惜。她希望她的這間小店給更多喜歡它的人以更多的溫情。在另一種立場上說,這個小店又是一家哈爾濱“俄僑紀念館”(這也是店主自己做的一塊牌子)。在1960年前后俄國人都被驅趕似的離開這座城市。那時中蘇兩個政府如仇敵一般。自然,在哈爾濱的俄國人僑民只有提著簡單的行李趕緊滾蛋。這些人,實實在在可以這么說,他們是俄羅斯帝國歷史上羅曼諾夫王朝的最后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一漂貴族。眾多的高官顯貴,上流社會人士,還有一大批優秀的流亡藝術家們。這些人不是蘇聯公民,因為他們是1917年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后,幸免于被新政權屠殺而逃亡到這里的俄國人。女店主的曾外婆就是幾十萬逃亡到哈爾濱“難民”中的一家人。她只說自己是俄羅斯人而絕不承認是蘇聯人。

窗前丁香樹
再回來說這小咖啡店。也許是網上那一段的描述實在感人,這張靠窗子的桌子的確有很多人喜歡它。看得出來有時候急急忙忙闖進來的男人或女人都是為了這張桌子而來。當她推開門扭過頭這一刻,看見這張桌子空著,就會快步滑到它跟前拉開椅子立即坐下,露出慶幸的小小喜悅。如果扭頭看見了這張桌上已經有主落座了,手就會慢慢地松開了門拉手,臉上顯出失落和泄氣的神色。只好在別處選個位置,拿出書,要杯咖啡。不論在哪個位置,只要聞到了咖啡的香味,人們心情都是愉快的。再讀上十幾頁書,這段時光可真是再好不過了。在這間與世隔絕般的1930年氛圍的大廳里,還彌漫著面包的香味,奶油和草莓甜醬的香味。“叮鈴鈴鈴……”綠色沉重又高大的格子木門被推開,有人進來了。“叮鈴鈴鈴……”門又被拉開,有人出去了。鈴聲脆脆的,也提醒人們抬起眼睛輕松地看看窗外的風光和室內四周。
剛剛五月初的一天早上,天空雖然晴朗,可街道四周都像是覆蓋了灰塵一般。樹上的枝子已經鼓出細小的芽苞,又小又干,像快要枯掉了。店員們剛到店里就開始用塑膠管子把清水灑在地面上,噴在樹上、葡萄藤上,把布滿一夜灰塵的大玻璃也沖刷干凈了。接著開始整理室內。拿出去桌單抖掉上面的面包屑,加滿瓶罐里的糖、鹽、胡椒。擦干凈所有銀器,澆好盆花水和換好鮮花瓶子里的水。這時,會有人打開CD播放機,播放出合適的音量。所有的曲子都是店主從國外親自選的,她對音樂可不是一般程度的理解。從原版CD上刻錄下的音樂,音色完全夠這個小咖啡店享受的。

店內風景
這樣的小店,一個收款員兼咖啡師,一個廚師,一個店員。店主也就是老板,也和店員一樣,哪兒忙她就在哪兒。這點的確和其他餐廳的老板不大一樣。她做得最多的是擦地做清潔衛生這類的事,她把衛生間里擺上小瓶子鮮花,布置得又整潔又雅致香噴噴的。客人們也不知道這個個子不高、溫柔謙遜的中年女人是誰。現在她去市場買菜了,也快回來了。三個人都在做著各自熟悉的工作,準備迎接客人。綠色高大厚重的對開木門,每扇門的上半截有八個方格子玻璃,陽光把所有狹窄的菱形光斜著投在褐色瓷磚地面上,形成了四條連續的白光線段。一大塊由外面某個神秘地方反射進來的光,強度較弱投在了墻上,這塊亮光也粘在進小廚房的門口上方用水泥抹出來又描上色彩的玫瑰花和葉子上,使人想起陽光照耀的玫瑰花廊架。隨后不久,一窄條明晃晃的上午陽光斜著劃在了那張惹人喜愛的小方桌上。還不知道它等來什么樣的人坐在跟前。桌上剛換上了碎花滿布的白地桌單,擦亮了不銹鋼小托盤和里面晶瑩可愛的鹽瓶胡椒瓶和糖瓶。店員都在默契專注地忙于自己手頭的活兒。在這個安靜的時候,門鈴的一聲響就很令人心驚。通常這個時候還不進來客人。也許是送廣告宣傳雜志或報紙吧。不是,從推開的門背后慢吞吞地側身進來一個二十幾歲模樣的姑娘。她向大廳粗略地看了一遍,多少有點旁若無人地向右一轉臉,立刻從眼睛里露出好看的喜悅神色。徑直向那張有了寬寬一條陽光的桌子走去。女店員向她問好并送上了菜單。她獨自翻看,緊繃著臉頰,身體略略前傾坐得很直。和許多人那樣,要特意擺出清高傲慢的樣子。可有的人就繃不了多一會兒,剛開始還像那么回事,用不了多久就散架子了。其實這也不必多有指責。這個女孩子開始就對自己的樣子很沒自信。她不知道為什么自己要做著這種姿勢和表情,她是第一次故意要這么做的。她坐在這樣的一家令人緊張恐慌不知所措的咖啡店里,第一次走進這種具有某種精神威懾力的餐廳,很多人都會有這樣平靜不下來的慌亂,又要做出老練和很適應的樣子。她的衣服除了滿是皺褶沒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特點。肩后背著一只土黃色臟糊糊的背包。褲子和鞋也都沒有什么個性。還有亂蓬蓬的頭發和沒有洗過的臉,加上沉重沒有光澤的眼皮和不能給人留下些好記憶的眼睛和面孔。她衣著不整,而且肯定是多日沒洗過衣服。作為這樣年輕的人的確邋遢。可以斷定:她是乘火車或長途汽車,經過一段難耐的長時間旅途直接來到這里的。盡管是早上九點半鐘,她的臉上混合著疲倦困乏和新鮮的四周所帶給她的興奮和趣意。她理所當然地坐在了斜劃過一道明亮耀眼陽光的那張令人留戀的桌旁。她總是認為自己受到了注視,動作上表現出了缺少應有的自然流暢。而且,她還要努力拿住一種架子,她當然有理由想象把自己提到比店員還要高些的層次上。在我們的四周這是一個普遍的就餐者的消費心態。當下形成了這么一種社會風氣竟被當作時尚。很難看到有客人對店員恭敬有禮,尊重自謙。其實就是花些錢吃頓飯。花錢的交換條件是走進餐廳,坐在桌子旁,等待店員把所點的吃食送來也就為止了。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人們通常花了點錢就要當一回大老爺以至上帝。這些男人女人神氣闊現大聲喝喚:“服務員!”“把牙簽拿來!”“再拿一根來!”就是吃上四元錢的兩個包子,也要聲色俱厲地支使下人般地喝道:
“把醬油拿來!”
“醬油在您身后的桌上。”服務員收拾著碗碟,邊回應。
“你給我送來,你憑什么讓我去拿?”這種事在餐廳,特別是一些普通的小餐館,是平常事,沒人覺得有什么不妥。都是些底層人,也難得有機會擺擺威風。在中國就是這樣。而一般來西餐廳的人都還規矩,偶爾也有張牙舞爪、吹吹呼呼不可一世的。這家小咖啡店,進來的人還都很注意自己的舉止言行。他們說話聲音很小,與店員說話也能放下架子,表現出屈尊俯就,常常也能和顏悅色甚至有笑容。因為這是一家有名氣的小店,又有特別的俄僑歷史背景。還有從外到里的氛圍和歐洲的咖啡館一樣,氣質優雅的女店主又總是彬彬有禮,待人謙恭和氣熱心容忍,從不露不悅之色。客人心里有一種尊重,自然就安靜多了。畢竟有那么一些人也真是想要有一種文明社會正常的好氣氛。那么說到這個姑娘,她做的可真不過分。只是在眼皮掀上去看店員的一瞬間,或者把腰靠在椅背上,雙肘支在桌沿,手指蘸著舌尖過分用力翻動菜單的表情上,可以隱約看出她沾了一點點前面說的那種心態和風氣。但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去想它。也可以原諒她僅僅帶著那么一點點社會上的灰塵。因為她很安靜,語音也極弱小,店員沒聽清楚還要再問她一次。再次說出來的語音,仍然語弱氣虛。也不能再怪這姑娘了,現實的社會中下等心態像流溢四面八方的病毒,太臭太多。人們只要有機會就想要毫不顧忌地凌駕于別人之上(當然遇到另一種機會人們又像下賤的奴才不計丑態)。病毒怎么可能不落在這個窮鄉僻壤的姑娘身上呢?她也會感冒。但是她只是小小的沾了一點兒病毒。她其實很緊張,所以聲音很弱。人應該有畏懼心,一定場合里畏懼心是一種涵養。她第四遍說過之后,店員才聽懂是要“摩卡”咖啡加牛奶。可是姑娘已經臨近最后一口勇氣了。店員當然像對待每天眾多的顧客一樣,也不會去多想。轉身就到后面的小廚房把手寫單子交給咖啡師兼收銀員。然后等著把做好的咖啡放在托盤里送給顧客。店員把小勺子放在橢圓形的白瓷碟子邊緣,鼻子吸著早上第一杯咖啡的香味,覺得一陣恬靜。特別是正播放的這首曲子,是一首英國的老爵士曲,英國一代大牌爵士樂歌手正唱著:“……上午的陽光,照在我窗子外的小杉樹上,你從窗前走過,還是那件舊衣裳……”
店員把碟子和上面的一杯咖啡放在顧客的面前,又仔細地擺到最適合的位置。再把精巧的小玻璃奶盅放在咖啡杯左手邊,里面是半下濃牛奶。糖瓶就在桌子里側,半圓的鏡面不銹鋼瓶蓋正把一個極亮的光點反射在你的眼睛里,只要你看它,那個強光點就像電弧光那樣刺你的瞳孔。接下來,這個姑娘一開始就把她想象的整個喝咖啡的浪漫優雅給搞砸了,真是搞砸了。

店外風景
她讓人所看到的實在是不忍目睹。最初,這個姑娘從掛在椅子背上的背包里抽出一本書放在桌子上咖啡杯的旁邊,她的手油膩膩的。她真應該先去化妝間洗洗手再擦擦臉,然后坐下等咖啡。明擺著她是一個偏遠的農村女孩子。開始看像是個學生,然而更像是偏遠山村的初中教師(我們暫且認為她是初中的老師更合適。那股子執著勁,她實在是太像老師)。指甲早幾天就該剪了。每個指甲前端都有一條彎曲的黑邊。她好像兩天沒洗臉了,耳朵后面和脖子上有一層不均勻淺色的污漬。仔細看看,她整個人長得挺瘦,皮膚灰黑色。兩側的顴骨稍稍突出,也沒有紅暈。眼睛很普通,眉毛很淡。這是第一個如此與眾不同的女孩子,十幾年來這家小店里從未進來過這般邋遢的青年女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不僅要一杯摩卡咖啡,還擺在桌上一本書,一小盅牛奶。她只是不在意地瞥了一眼牛奶卻連碰也不碰它。她用明顯不清潔的手,從咖啡碟上捏起了晶亮亮,形狀乖巧秀麗的半搪瓷柄壓花銀色小糖匙。她也要像別人那樣從水晶糖罐里舀出一小匙糖,順著咖啡杯邊緣繞一周,把又細又白的砂糖撒進杯子里。不,她搞砸了。她把漂亮的小匙子直接伸進了咖啡里,連一兩圈也沒繞就舀出了那么淺淺的僅僅幾滴淚水一般多的摩卡,送進嘴唇之間立刻緊緊抿起了嘴唇,臉色變得奇怪像是要哭出來。接下來,這個姑娘打開了書。翻到目錄那頁看了一小會兒,就翻到正文,開始讀書了。女店員依舊背著身忙碌自己每天必做的工作,好在并沒注意到她的所有舉動。姑娘仍舊用可愛的小匙舀起那么少的一匙咖啡含進嘴里,把炒糊了豆粒般的苦味不情愿地咽下喉嚨。她急速地瞭起眼睛向四周掃了一眼,目光膽怯又害羞。剛才還有一點小小的超脫感,微弱得像一顆被冷風抽得緊抓住蠟燭絨芯閃動的小火星。就是這么小小的高傲的虛榮心也一下子熄滅掉了,變成了一縷細微白煙,那么快,那么徹底。桌上的陽光正是通亮反光的時刻,半張桌子,斜著像對角線那樣,半邊暗半邊耀眼。然而反射映照在姑娘的臉上的光暈,卻一點不美妙,毫無詩意,沒有任何想象力。因為她的臉色很糟,像是在孤島上遭到了幽禁。仿佛那陽光是從一米乘以兩米的牢墻上方的小洞口里透過來的,她煩這個和她沒任何關系的強光,這個讓她出丑的光芒。她沒洗過的面孔,稍稍突出像新石器蒙古人的顴骨,粗糙的灰色皮膚,黑邊的指甲。這些,在這公平又千百萬年如一不變的陽光中,在桌布上反射的光暈中,不僅變丑,而且表情漸漸開始變得無助、驚慌。這時,門鈴響起來,姑娘立刻抬起頭。女店主推開門走了進來,她一眼就看見了這屋子里唯一的顧客。她正好看見姑娘用小糖匙舀出咖啡送進嘴里,女店主向客人瞇起眼睛微笑著問早安。見顧客只是看了她一眼而別無表示,便帶著微笑走進后面的吧臺和小廚房去了。她知道一定不要對她喝咖啡的方式表現出一星半點驚異,更不能被對方察覺。她步伐輕松和店員們愉快地打招呼,減少這個姑娘對外界的不適感。她想讓姑娘輕松自若。咖啡怎么喝都行,當然可以用糖匙喝。也可以用大匙子更可以用吸管。這都沒什么,都沒任何關系。只要姑娘不察覺,只要你知道這里的店員什么也沒在意什么也沒看到,只要你愉快地讀書,就著咖啡。你開心,你對整個世界的冷言碎語都聽不見就行!本來對一個人來說,她可以看不見任何人,聽不見任何聲音,這全由你自己做主。再說誰都有第一次。
“只要你能夠開心就好,不要在意別人。”女店主默默重復著。
這時候,姑娘擺了一下手,叫服務員。她的聲音很弱很不容易聽到。
她要付款了。她一共只咽下了四小匙咖啡,從上衣口袋里她抓出了十八元錢,兩張五元,八張一元的,紙幣揉在一起。很皺,很黏,很值錢,又十分可惜。
收款員伸手接了她的錢,兩張五元,八張一元。平平常常,沒有什么不同。收了錢,回應了一句“謝謝”。完了。姑娘把書合起來快速地塞進背包里。拉上拉鎖時又往里推了一下子。看得出來她還是在那種在被人注視的心態下做著各種動作。她要快快逃離這里!她盡量想把背包整得平整些,把衣服向地下的方向拍打幾下,把塵屑拍打到地上,只顧衣服干凈。女店主看到了這些,這是平平常常司空見慣的舉動。姑娘不會想到這種動作是給別人造成了不便或困擾。其實能有什么東西掉落在地上呢,每個人都會帶進來浮灰。她做這個舉動是說明她愛清潔,是個文明的愛干凈的人。反過來卻表示出從未被察覺的自私和不善于考慮對別人有什么弊端。沒錯,人人都會這么做,在飛機上也一樣。進過餐,把掉落在身上的東西撣拂在機艙干凈的地毯上。沒人覺得不對。這個坐在陽光灑滿餐桌旁的女孩子當然沒有什么不安,沒有多想。店主全都看到了,她發自內心地原諒這個姑娘。第一眼看見她就要滿心善意地維護這個勇敢的姑娘。她想象得出來,這個姑娘平時根本沒有這么細心清理自己的習慣或者時間。她是在時時作祟的被注視的錯覺下,自然就做出了這種只清理自己,不顧周圍環境的舉動。這不該怪她,一點也不要責怪她。她很快整理好自己的行裝背在了肩上。大步走到門前,又在伸出手拉門把手的時候不合時宜地掂了兩下肩后的背包。門鈴“叮鈴鈴鈴”地響了一串脆脆的聲音。她又推開外面的門,然后完全走出了這間小咖啡店。女店主在她站起來的時候,想替她弄平扭了勁的背包帶,但是她放棄了這個打算。女店主看見滿滿的咖啡如同沒動過一樣,她唐突地伸出手幫這么個小忙,反而更讓姑娘心中不坦然。姑娘是要拿出那么一個喝咖啡老手的派頭來,可是她不是老手也沒辦法做好。看得出這是她人生第一次嘗了如此苦澀難咽的湯水。她萬沒料到人們在電影、電視、書籍、雜志上描寫的咖啡……那種特別香味的濃咖啡,那種普通農民從未想象過,從未沾過一滴的美味,喝起來就變得又高貴優雅又時尚超脫。喝咖啡的人就不是不喝咖啡的人。喝咖啡的人是一種藝術人、文明人、高貴人、時尚人、洋氣人,有上等品位的人。一個高級層次的人,走起路來可以仰起頭,有一種特別的風雅派頭,隨時都可以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尖叫道:啊,真想找個地方坐下喝杯咖啡呀!
喝咖啡可很不一般。而且,有時間的話一定喝杯香熱的咖啡,讀上幾頁名著。
這個衣著臟舊不整的姑娘,懷著什么樣的想象從大老遠的地方乘車來到哈爾濱,就為了走進這間小咖啡館呢?她背著一個雙肩背的行囊,做好了全部準備當中最重要的準備,借來一本應該是很潮流的書裝進了行囊里,決心來這張小桌前坐一個上午,喝一杯所謂的香得妙不可言的摩卡,邊借著神圣的光暈讀書。原來她喝不下那苦澀的濃湯。書雖然雙手捧在眼前,實際上連一個字都沒讀進去。
一個遙遠農村來的女孩子,心里總在竄動著一個向往,打算讓自己向另一個生活情景中邁去一步,卻沒邁出去反而絆了一跤。還有那些皺巴巴數了幾遍卷在一起的黏糊糊的紙幣,都是為了今天上午坐在陽光下臨窗的桌上,喝著咖啡,讀上幾頁書。
現在,一切都終結了,結束了,完了,再見了。
女店主站在她坐過的椅子旁,一只手按在椅子靠背上,低著頭看著空座位。也許在想象著剛才那個女孩子還坐在這里。這里還彌留著姑娘身上帶來的車廂里卷煙的臭味和酸哄哄的怪味道。女店主曾經想要坐在對面和她說幾句輕松又得體的話,沒有這個時機。或許早些想到她會像逃脫似的離開這里,再送給她一大杯橙子汁或者可樂這樣的飲料,誰都喝得慣。
女店主站在那足有十分鐘。
她帶著一種過失般虛弱的口吻說:“剛才這個姑娘是第一次喝咖啡,你們看到她根本不習慣就應該再送給她一杯果汁飲料。真可憐這個女孩子,她拿出那么多的小額紙幣,真不該收下。她是為了體會一種好感覺,可是她太失望了。也許她一輩子也不想再進咖啡店了。真希望她會再來這里,也許她不想再來了。”
那個言語不多表情倨傲的女店員,大學畢業還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她沒在意女店主惋惜的表情和傷感的語調。她把收拾下來剛用過的咖啡杯放在后面的吧臺上,回過身對女店主說:
“我倒覺得沒什么,不是那種人為什么偏要做個樣子,還拿出一本書來。這叫人怎么說呢,還不如不進來好。”
“你這么說不好。誰都會有不知所措的時候。這個女孩子是有一個好動機。她在嘗試一個追求,她以后也許會很習慣的。喝咖啡是非常好的事,全世界到處都有咖啡店。但是她的家鄉沒有,這是她第一次嘗試。人絕不該去譏笑別人無辜的偶然出丑。我們應該幫助她,有時候發生過的一件小事會一生忘不掉,不經意想起來都為自己所做的傻事羞愧。”
以后幾年,至今,那個女孩子也沒來過這家小咖啡館。店員換了又換,可是每來新店員,女店主一定要講起這個故事給他們聽,讓她們懂得尊重別人的虛榮心。
可是,再沒有類似的人出現,也沒有類似的情形發生
這是一個讓人想起來就有點苦澀又有些酸溜溜的故事,夾雜著一縷令人感動的淳樸。很像一杯“摩卡”咖啡的味道。
女店主總在盼望:那個姑娘會來的。我要親自給她做一杯咖啡,坐在她對面,再送給她一本她肯定會喜歡的書(當天她就買了一本薩岡的書《你好,憂愁》,還夾進了女店主做的書簽。至今還放在咖啡店的五屜柜里)。
和她聊一些她愿意聽的奇聞軼事或者國外的中學是怎么上課學習的。
想做她的好朋友,是的。
胡泓,確是1951年出生于哈爾濱,四歲開始學習音樂,后來師從于日本老師佐藤康正學習小提琴。1968年去“北大荒”生產建設兵團,開始油畫、雕刻、雕塑、建筑設計。1971年考入蘭州空政文工團,開始寫作。1976年復員在醫院工作。1984年創建裝飾公司。1987年去日本TERRAPIN株式會社任建筑設計師。2000年回故鄉哈爾濱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