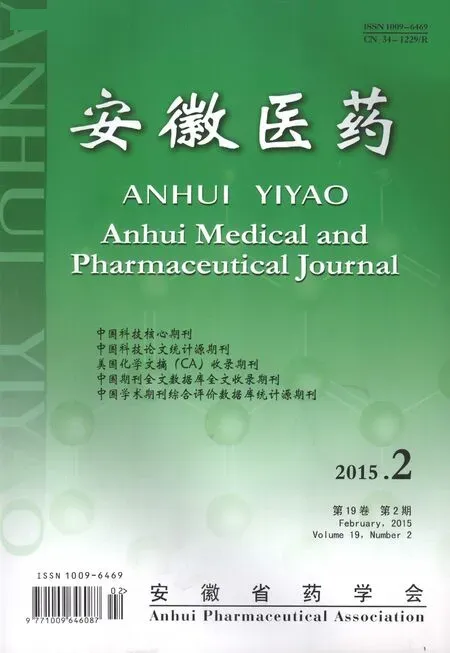18 F-FDG PET-CT顯像在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術后局部復發及轉移監測中的應用
劉 飛,汪世存,潘 博,展鳳鱗,倪 明,劉 昕
(安徽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PET-CT中心,安徽合肥 230001)
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是一種分化方向不明的未分化多形性肉瘤,1964年由O’Brien和Stout首先發現并提出[1]。該病好發于40~60歲中老年人,男多于女,以四肢多見,其次為腹膜后,原發于陰莖及脾臟亦均有報道[2-4]。臨床多以局部腫塊疼痛腫脹就診,病程長短不一,易局部復發和遠處轉移。本研究回顧性分析10例經手術病理證實的MFH術后患者18F-FDG PET-CT顯像資料,總結后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4月至2014年4月在本中心行18F-FDG PET-CT顯像的11例經手術病理證實的MFH術后患者,男9例,女2例,年齡31~80歲,平均55.1歲。近期1例接受放療及射頻治療肺轉移患者肺轉移灶殘存的確診依據由臨床隨訪和臨床診治經過等情況綜合判斷得出,余局部腫瘤殘存、復發及遠處轉移灶的診斷均經臨床隨訪證實,隨訪時間均>6個月,失訪1例。
1.2 儀器及顯像劑 采用德國Siemens公司 BiographSensation16型PET-CT顯像儀,18F-脫氧葡萄糖(18F-fluorodeoxyglucose,FDG)由本中心 eclipse RD型回旋加速器(美國CTI公司)及正電子藥物生產線(ExploraFDG4)自行合成,放化純度>95%。
1.3 檢查方法 患者檢查前禁食4~6 h,平靜狀態下按體質量 5.55 ~7.4 MBq·kg-1靜脈注射18FFDG顯像劑。注射后患者靜坐或安靜平臥,休息40~60 min后,排尿后分別行體部及顱腦PET-CT掃描。體部CT掃描條件:電壓120 kV,有效 mAs100,螺距5.0,層厚5 mm。PET圖像采用三維采集模式,一般6~7個床位,每個床位采集2~3 min。掃描范圍從腹股溝至顱底層面,檢查過程中患者保持平靜呼吸。采集完成后利用CT數據對PET圖像進行衰減校正,采用有序子集最大期望值法(ordered subsets expectation maximum,OSEM)迭代重建,獲得橫斷面、矢狀面、冠狀面的PET與CT圖像及PETCT融合圖像。腦部圖像應用3D模式采集。必要時為明確診斷可行局部延遲顯像。
1.4 圖像分析 所有 PET、CT及 PET-CT融合圖像都進行幀對幀對比分析,PET-CT和單獨CT圖像分別由3位有影像醫學和核醫學診斷經驗的高年資醫師獨立閱片完成。定性分析中PET圖像見非對稱性局灶性放射性攝取增高灶,同機CT上相應部位見密度或形態異常及其他多發轉移征象,可擬診復發或轉移;半定量分析釆用感興趣區(ROI)技術,由計算機自動計算得到最大標準攝取值(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SUVmax> 2.5且越大提示惡性可能性大。結合病史,在除外炎癥病變、生理性攝取及術后改變等情況后得出綜合診斷。
2 結果
按各組織器官病灶數目計算診斷效能(1例重復檢查病人累計),原發灶共11處,肩胛骨、大腿、小腿各2例,下頜骨、上臂、腘窩及左側髂骨與腹股溝各1例;局部殘存與復發灶5處,其中1例手術后局部殘存假陽性(圖1);轉移灶14處,肺3例,腋窩、腹股溝及大腿各2例,上肢、胰腺、腎上腺、腹膜后淋巴結及盆壁各1例,其中1例膀胱轉移假陰性(圖2);分析可得18F-FDGPET-CT顯像在MFH術后局部腫瘤殘存、復發及轉移監測的靈敏度為94.7%(18/19)、特異性 90.9%(10/11)、準確性96.6%(28/29)、陽性預測值 94.7%(18/19)、陰性預測值100%(10/10)。
3 討論
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MFH)是常見的軟組織惡性腫瘤之一,臨床表現多無特異性,本組研究對象術前多以局部腫塊疼痛腫脹就診,一般檢查無特異征象,與常規報道相符。MFH組織學上表現為顯著的細胞多形性,以成纖維細胞和組織細胞為主要成分,富含血管的膠原纖維是瘤體間質主要組成部分[5]。腫瘤無明確分化方向,病理性核分裂象多見,常局灶性出現席紋狀或輪輻狀結構[6]。目前報道主要有3種起源學說:纖維細胞起源、纖維與組織細胞雙重起源、原始間葉細胞起源[7]。新版WHO軟組織腫瘤分類重新定義MFH的本質是組織學來源及分化方向仍不明確的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ndifferentiated polymorphic sarcoma,UPS)。重新定義的MFH含3種組織學亞型:席紋狀-多形性MFH(高級別UPS)、巨細胞性MFH(UPS伴巨細胞)和炎性 MFH(UPS伴明顯炎癥)。血管瘤樣MFH被納入軟組織未確定分化方向類腫瘤,新命名為血管瘤樣纖維組織細胞瘤。黏液性MFH被納入成纖維細胞性/成肌纖維細胞性腫瘤,新命名為黏液纖維肉瘤[8]。
MFH多位于深部軟組織,可沿筋膜及肌纖維浸潤性生長,局部復發和遠處轉移率高。本研究10例術后患者,單純局部復發1例,單純遠處轉移4例,局部復發伴轉移2例,復發與轉移率高達70%,另有1例右上臂MFH多次復發,5次手術,PET-CT檢查提示右側腋窩淋巴結轉移(圖3)。影響MFH術后預后的重要因素有:病灶大小及浸潤深度、腫瘤組織學分級、手術方式等。因具體手術及相關治療經過欠詳,加之病例數較少,故本研究對MFH術后局部復發與轉移的影響因素不做詳細分析。
發生在軟組織內的病灶,CT平掃及增強無明顯特征,因CT空間分辨率不高,對MFH診斷及術后復發與轉移監測的臨床價值有限。本組研究中部分患者攜帶CT資料多顯示局部腫塊,病灶形態多樣,密度不均,不易鑒別良惡性。MRI可多參數、多層面、多方位成像,對軟組織分辨率高,是軟組織MFH檢查的首選影像學方法,因MFH細胞多形性明顯,組織學及形態學差異大,其信號變化較大,容易誤診,需結合臨床表現、影像學及病理學結果綜合判斷。另MRI檢查禁忌證相對較多,部分患者缺乏檢查適應證。常規影像學檢查掃描范圍有限,且多關注于解剖學變化,對于早期的復發、轉移灶及遠處病變易造成假陰性。如單純以短徑是否大于1 cm判斷腫瘤淋巴結轉移與否具有一定假陰性及假陽性,PET-CT代謝顯像結合CT密度及形態學變化綜合判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誤診率。全身18FFDG PET-CT顯像可以在表現局部腫瘤活性的同時顯示患者淋巴結轉移及遠處轉移的情況[9]。PETCT掃描范圍廣,一次完成全身顯像,對于惡性腫瘤術后復發、轉移監測具有明顯優勢,特別是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等術后局部復發與遠處轉移率高且廣泛的患者顯像極具臨床應用價值。PET-CT不同于普通的影像學檢查,可在同機CT解剖學診斷基礎上,提供分子學水平代謝顯像,可于明顯器質性變化前發現功能異常,進而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明顯改善惡性腫瘤預后。
早期根治性手術治療輔助術前或術后放化療的綜合治療已成為現行主要的治療手段。本組研究明確手術時間9例,術后1月以上7例,其中4例未行放化療,術后不同時間均出現轉移。臨床研究發現術后輔助放化療有利于控制局部復發及轉移,提高生存率[10]。對于沒有術前放化療指針的不可切除巨大MFH患者,高強度聚焦超聲療法可作為促進保肢手術的額外選擇[11]。對于治療后局部組織結構及病灶形態、成分的改變,常規影像學缺乏特異性,PET-CT代謝顯像可明顯優于常規影像檢查判斷術前腫瘤活性及術后腫瘤局部殘留或術后瘢痕形成,對于手術方式選擇及預后判斷提供依據。因而本研究中有兩例術后1月內患者,檢查目的首要是判斷術后是否殘留,觀察手術效果,研究下一步治療方案。此外,PET-CT檢查可用于指導放療計劃及術后再分期,PET-CT顯像清楚顯示腫瘤活性部分,可為放療患者適形放療計劃提供可靠依據;因腫瘤對治療有效的早期反應為病灶活性降低,PET-CT檢查可在常規影像學顯示形態學變化前預知療效,可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免除不必要的治療,減少藥物損害及經濟損失。
因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術后全身轉移范圍廣泛,必要時需加掃雙下肢,以確保無明顯漏診,在本組研究過程中,所有患者均在常規全身掃描基礎上加掃雙下肢,并在體部掃描中要求患者將雙側上肢放于身體兩旁,實現無一病灶漏診。同時,因放化療可明顯降低細胞活性,減少活性組織放射性藥物攝取,需掌握PET-CT檢查指針,放療三月內、化療三周內慎檢,以免造成假陰性。空腔臟器必要時需充盈滿意后觀察,本組1例假陰性(圖1),因患者病情較重,膀胱充盈欠佳,壁稍厚,與鄰近組織分界不清,未能發現局部腫瘤浸潤,誤診陰性。另有1例假陽性(圖1),左大腿脛骨外側多形性MFH術后16 d,PET-CT顯像示術區FDG代謝輕度增高,隨訪證實為術后炎性攝取。
本研究不足之處在于:病例數相對較少,統計學誤差偏大;廣泛轉移病例難以逐一病理證實,臨床隨訪可能存在一定誤差;另18F-FDG作為一種腫瘤非特異性顯像劑,在急慢性炎癥、肉芽腫性病變及淋巴結反應性增生等良性病變中均可有不同程度攝取,對于MFH術后轉移與復發固然存在一定的假陰性和假陽性。但18F-FDG PET-CT顯像在MFH術后局部腫瘤殘存、復發與轉移監測中仍具有一定的臨床應用價值,可作為MFH術后復查的有效檢測方法。
[1] O’Brien JE,Stout P.Malignant fibrous xanthomas[J].Cancer,1964,17(11):1445-1455.
[2] Suqiura S,Tatenum T,Sakata R,et al.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undifferentiated pleomorphic sarcoma of the penis:a case report[J].Nihon Hinyokika Gakkai Zasshi,2013,104(6):706-711.
[3] 何 輝,陳丹丹,王 磊.超聲檢查發現脾臟原發性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一例[J].解放軍醫藥雜志,2013,25(7):70-71.
[4] Rakic'M,Pogorelic'Z,Lambasa S,et al.Primary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 of the spleen:recurrence eight years after splenectomy-- report of a case and literature review[J].Coll Antropol,2013,37(3):1007 -1010.
[5] 李惠明,李 偉,于靜紅,等.MR在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診斷中的應用[J].疑難病雜志,2014,13(2):172-174.
[6] 王 東,陳 韻,劉文慈,等.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的CT表現及病理特征[J].中國介入影像與治療學,2013,10(1):45-48.
[7] Matushansky I,Hernando E,Socci ND,et al.Derivation of sarcomas from mesenchymal stem cells via inactivation of the Wnt pathway[J].J Clin Invest,2007,117(11):3248 -3257.
[8] Fletcher CDM,Coindre JM,Molenaar WM,et al.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of tumors.Pathology and genetics of tumors of soft tissue and bone[M].Lyon:IARC Press,2002:109-126.
[9] 李 遠,牛曉輝,鄧志平.18F-FDG PET-CT顯像在軟組織腫瘤診斷中的應用[J].山東醫藥,2011,51(8):68-70.
[10]王 姿.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治療及預后的研究現狀[J].臨床腫瘤學雜志,2011,16(1):82-85.
[11] Zhou MQ,Hu XY,He HF,et al.Neoadjuvant HIFU treatment for 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report of a case[J].Journal of Medical Ultrasonics,2012,39(4):259 -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