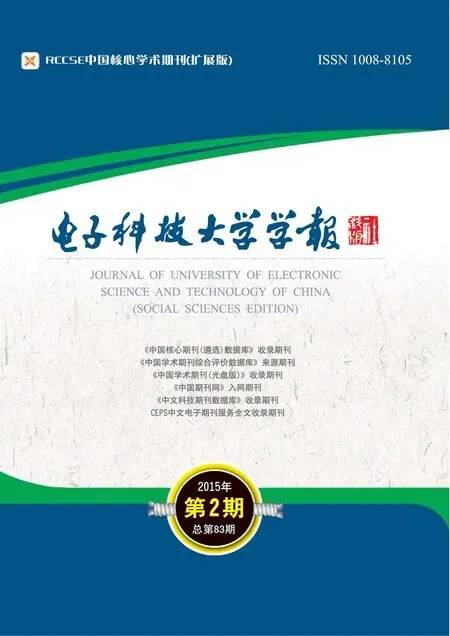黑社會性質組織財產刑的適用
□張志鋼
[北京大學 北京 100871]
1997年刑法修改時,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并無設置財產刑,隨著司法實踐的需要和理論的呼吁[1],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對本罪增設了財產刑,修改后的第294條第1款規定:“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以并處罰金。”由此形成了對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財產的三種處置措施:罰金、沒收財產與刑事沒收。這三種財產處置措施的正確運用,是有效摧毀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經濟基礎,也是實現立法目的的重要內容。
一、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財產刑的適用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在內容上包含兩種情況,一是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實施的其他一般犯罪;二是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自身的犯罪,即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本身。相應地,黑社會犯罪組織財產刑適用的內容也包括這兩個方面,一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其他一般犯罪時財產刑的適用;二是因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對黑社會性質組織以及其組織成員財產刑的適用。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財產處理應當遵循財產刑適用的一般原則。由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自身的特殊性決定,黑社會性質組織財產的處理必然會遇到一些特殊的問題需要具體分析與檢討。
(一)財產刑適用的一般原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指出,對于邪教組織犯罪、恐怖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等犯罪依法嚴懲的同時,也要分清情況,區別對待:“對犯罪組織或集團中的為首組織、指揮、策劃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從嚴懲處,該判處重刑或死刑的要堅決判處重刑或死刑;對受欺騙、脅迫參加犯罪組織、犯罪集團或只是一般參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的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符合緩刑條件的,可以適用緩刑。”對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所適用的財產刑,與其所適用的主刑(主要是有期徒刑)一樣都是刑罰的方法,兩者(之和)應當與其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無疑,在對于懲治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財產刑的適用上應當貫徹這一思想,即對于財產刑的適用以及數額的裁量在總體從嚴的基礎上,也要區別對待。
(二)財產刑的具體適用——對組織成員區別對待
依據刑法第294條第1款之規定,對于組織者、領導者必須并處沒收財產刑,對于積極參加者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或者罰金,對于其他一般參加者可以并處罰金。
1.對于組織者、領導者必須并處沒收財產
黑社會性質組織一般都具有明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作為組織的核心和首要人物一般不難認定。司法者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在判處財產刑時,可以裁量是沒收一部份財產還是沒收全部財產。本文認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通常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具有很強的持續性與再生性,即使作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首要分子的組織者或者領導者被判處相應刑罰并沒收一部份財產后,如果該組織的經濟基礎尚未被徹底根除,該首要分子可能在服刑期間或者刑罰執行完畢之后繼續利用其尚存的經濟能力招募成員、購置犯罪工具繼續實施犯罪活動,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要么繼續存續,要么在沉寂一段時間后死灰復燃。因此,對于組織者、領導者一般應當沒收全部財產,徹底剝奪其再犯罪能力。
2.對于積極參加者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或者罰金
對于積極參加者,司法者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裁量是附加適用財產刑還是僅適用主刑附加適用;在決定附加適用財產刑時,可以選擇是適用沒收財產刑還是適用罰金刑;決定適用沒收財產刑時,可以選擇是一部份沒收(包括沒收的數額)還是全部沒收;決定適用罰金刑時可以裁量罰金的數額。自由裁量應當在綜合考慮、分析這些積極參加者在所參與的具體犯罪中的地位與作用(包括犯罪情節、主觀惡性程度)、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違法所得的數額(包括從組織違法所得中的分配)以及自身的經濟能力的基礎上做出裁定,既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也要有利于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3.對于其他一般參加者可以并處罰金
在司法實踐中其他一般參加者,主要是指受蒙騙、脅迫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在組織犯罪中處于次要、從屬地位的犯罪分子。對于這類犯罪分子應當綜合考慮其參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個人的再犯可能性以及個人的經濟能力,確定是否適用罰金刑以及罰金刑的數額。
(三)財產刑適用的合理界限——與刑事沒收的區分
對于涉黑財物及其收益以及犯罪工具,應按照刑法第64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7條的規定予以追繳、沒收。《解釋》實際上是對刑法總則第64條有關刑事沒收在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領域上的具體化。《解釋》指出,對黑社會性質組織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分子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工具等,應當依法追繳、沒收。
問題是,刑法第64條規定沒收的對象是“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是指犯罪分子因實施違法犯罪活動而取得的全部財物,包括金錢和財物[2]。“違法所得”當然包括因犯罪直接獲取的收益,但是否包括因犯罪而間接獲取的收益則存在爭議。
從司法實踐來看,間接收益也在沒收的范圍之內。如2007年廣東省公安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印發的《關于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七條解釋如下:“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全部財產及其收益,既包括組織成員為了該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投入的資金,也包括組織成員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經濟利益,還包括利用非法利益再投資獲取的全部經濟利益和孽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也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通過犯罪活動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是指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形成、發展過程中,該組織及組織成員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其他不正當手段聚斂的全部財物、財產性利益及其孳息。”[3]
(四)財產刑適用的競合——數罪并罰
依據刑法第294 條第3 款的規定,犯本罪同時又有其他犯罪的,應當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也就是說,行為人只要實施了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就構成犯罪,獨立于其他為實現犯罪組織的目的而實施的任何具體犯罪;如果行為人還實施了諸如故意殺人、敲詐勒索、聚眾斗毆、尋釁滋事、非法經營等犯罪,應數罪并罰。如果在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實施其他具體犯罪中也涉及到財產刑的適用時,則也會出現數罪并罰時財產刑適用的問題。數罪并罰時財產刑的適用與其他一般犯罪相同,視具體情形或并科適用或吸收適用。
二、對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財產的認定
如何合理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的財產與財產的性質,是對黑社會性質組織財產進行處理的前提和保障。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財產的處理的首要問題是區分合法財產與非法財產:非法所得及其收益、用于犯罪的工具等是刑事沒收的對象,與具體案件無關的合法財產則可能成為適用財產刑的對象。
(一)對黑社會性質組織財產的認定
作為一種有組織的犯罪現象,現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結構呈現“金字塔”狀,其組織成員是“職業化”的,組織的運作是“企業化”的。換句話說,現代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結構往往呈現出一個經濟實體中的工作關系,或者說與現代企業具有很大的重合性與相似性。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往往是某個企業的老板,他們不僅對企業的發展有決策權,而且還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指使下屬職員從事合法的或違法犯罪活動;企業往往雇有一批企業的中層干部,他們對老板負責,并按照老板的指令帶領下屬職員從事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活動;另外,則有一些普通的職員,他們聽命于老板或者中層干部,參與具體實施了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活動。”[4]問題是如果這種公司型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以單位名義,為了單位利益而實施犯罪的,是否以單位犯罪論處?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2 條明確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該規定實際上規定了為單位利益以單位名義而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應當以個人犯罪論處的兩種情況及其認定標準:一是“犯罪分子為規避法律的嚴厲制裁,在實施犯罪行為以前,采用欺騙手段設立公司、企業,而后以該公司、企業的名義實施犯罪活動,其犯罪心理是即使案發被追究刑事責任,所受到的刑罰處罰也不重”[5]的情況,簡言之,是設立專門從事犯罪活動的企事業單位;二是設立企事業單位,在從事合法經營活動以后,才產生了以單位為幌子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意圖,同時進行“黑白經營”,以“黑”為主的情況,即“以公司、企業成立后實施的正當經營行為與犯罪行為的比例作為單位犯罪的劃分標準”[6]。具體到黑社會性質組織以企事業單位為掩護而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也可分為兩種:一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之后,為了攫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而設立專門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公司企業,即,其成立自始便是“黑”的;二是原來從事合法經營活動的公司、企業逐步蛻變為專門從事犯罪活動的公司、企業,逐步蛻變形成了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即“由白變黑”。
對于第一種情況,涉黑單位的經營所得與資產一律是涉黑財產。單位徒具公司、企業的空殼,實質上是以單位之名行自然人犯罪之實。此時單位經營所得、資產及其孳息,均屬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收益及其孳息,或者是用于犯罪投入的資金,都應當予以沒收或者追繳;在單位存續期間,單位將經營所得分配給組成人員的,也在沒收之列,是黑社會性質組成人員的違法所得,也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
對于第二種情況則比較復雜。以一定的經濟實力為支撐,通過違法犯罪活動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是現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一種主流方式。如果以動態的過程來看,可以分為3個階段:(1)公司、企業設立之初的合法經營階段,與一般的經濟實體并無區別,因而不屬于刑法評價范圍之內;(2)向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過渡階段,在此期間實施一些為單位利益以單位名義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可能構成單位犯罪,依據涉嫌的單位犯罪判處財產刑;(3)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之后,為單位(組織)利益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適用上述第一種情況的規定。當然,在單位存續期間也可能同時進行合法經營活動。必須注意的是,上述三個階段不是截然分開的,這就需要非常審慎地把握和確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的時點問題。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的時點的把握,需要綜合某一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依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法律特征來進行確定。時點的認定對涉案財物的處置影響巨大。因為一旦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之后,其所實施的一切犯罪活動,均應當被視為違法犯罪活動。因而對該組織形成之后所聚斂的一切財物及其收益,均在沒收之列。而在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之前,該組織及其成員的合法收入及其收益則不能沒收,只有違法犯罪活動所獲得的財產及其收益才可以予以追繳或者沒收。同時,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時點的合理確定,也有助于正確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形成過程中資金的來龍去脈,為企業、事業單位財產的正確處理做好準備;黑社會性質組織內部違法所得的分配方式也是認定組織成員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地位和作用的依據之一。
(二)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財產的認定
1.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非法所得的認定
涉黑組織成員的非法所得是指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通過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所獲取的經濟利益。從司法實踐來看,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滿足自己的貪欲,往往不擇手段,包括實施賭博、走私、販毒、敲詐勒索、詐騙、搶劫、綁架等違法犯罪活動。當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自身具有合法的收入來源,或者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在加入黑社會性質組織之前,或者在其退出黑社會性質組織之后的合法收入,都應當作為合法財產。
2.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投資財產的認定
在實踐中,涉黑人員為了掩飾、隱瞞其攫取的非法收益,常常以合伙、入股、并購等方式投資,將不法收益與其他單位、個人的合法財產混為一體。罪犯為了逃避罪責,減少被沒收的損失,往往將屬于本人所有的財產進行轉移、隱匿或者說成是其他成員所有的財產。如何區分罪犯本人與其他投資人的財產已經成為司法人員所面臨的棘手問題。此時,司法機關應當審查涉案財產的來源及其性質,在懲治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同時,也要確保企業、事業單位財產以及其他投資人的合法的財產權益。
3.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個人合法財產的認定
在將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的不法財產及其收益以及用于犯罪的財物剔除出去之后,剩余的財產在性質上為合法財產。由財產刑的懲罰性本質所決定,只有這些屬于個人所有的合法財產則才有可能成為財產刑的適用對象。
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很難想象個人有權占有的財產完全等同于個人合法所有的財產。一般情況下,個人有權占有的財產可能屬于他人所有,自身具有所有權的財產也可能處在他人的占有之下,或者與他人共同擁有財產的所有權。簡言之,財產權屬具有流動性和復雜性,個人所有的合法財產及其范圍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同時,家庭成員共同生活時,財產一般并不分開;罪犯的財產(不論合法與否)還有可能用于投資,與他人的合法財產混為一體。
所有這些特征導致司法實踐中財產刑適用的困難,調查難與分割難[6]。在財產共同共有中,涉黑成員個人所有或者應有的財產的性質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在對涉黑人員適用財產刑以及對其涉案財產做出刑事沒收處理時,都涉及財產分割問題。如果罪犯與他人共有的財產是不動產或者其他不宜分割的財產,問題就更為復雜。當涉黑財產的分割在執行時也需要罪犯的家屬和其他財產的共有人協助,這無疑也會增加執行的難度。涉黑組織成員個人財產的分割應當遵循的原則是,依照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在有效地懲治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同時,盡量不影響家庭其他成員的正常生活,盡量不影響企業的正常運營以及當地正常的就業狀況。
三、對“灰色”財產的認定與處理
上述財產的認定與處理的前提是財產及財產的性質能夠區分。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財產性質“黑白”難分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即存在“灰色”財產的情形。所謂“灰色”財產,是指司法機關無法認定財物是否是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當事人也沒證據證明其財產的來源是正當的。
“灰色”財產應當如何處理?我國刑事法律并無明確規定。實務中的做法通常是:不對財產的性質進行區分籠統地以罰金刑或沒收財產刑剝奪犯罪分子的財產。這就不可避免使得財產刑的適用范圍擴大至非法財產。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財產刑不需要這個要件,比較便捷。這雖然省去了查證財產非法性的麻煩,但不正當、不合法。”因為“不甄別財產的性質以財產刑取代刑事沒收,會使判決罰沒財產的數量不能正確反映處罰的輕重。”[7]也有學者不無擔憂地指出:“要維護罰金刑的刑罰性質,就要在立法上和司法上真正將其作為刑事責任的實現方式,而不是將其作為置于刑事責任之外的為了實現某種特殊的政策性目的而適用的犯罪對策。因此,以剝奪犯罪人的合法所得為內容,就是罰金刑本來的意義。否則必然導致罰金刑的異化,而與罪刑法定原則發生沖突。”[8]
對“灰色財產”的處置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為了加強對有組織犯罪的打擊,近年來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強化了有關刑事沒收的規定。比如1992年意大利頒布第306號特別法令還規定,“黑手黨人一經判刑,若無法說明所獲得金錢、物品、資產之來源,或其對于財產之支配顯與其個人合法收入不成比例的,應予沒收。”再如1992年德國公布《有組織犯罪法》(全稱《防治非法毒品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有組織犯罪法》)增加了“擴大追繳條款”(Erweiterter Verfall),“如果將由行為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告發為‘有組織犯罪’,(擴大之)追繳應當延伸至所發現的所有財物”[9],這使剝奪犯罪人的全部違法所得成為可能;同時,對犯罪人占有犯罪所得物的證明要求被降低:“只要有較大可能性表明財產來源于犯罪,法院即可命令將團伙犯罪或職業犯罪的正犯或共犯的財產予以追繳。”[10]
就價值取向而言,我國學者對財產刑適用時異化的擔憂與德國、臺灣地區學者對于“擴大沒收”制度的批評是一致的:司法機關在懲治有組織犯罪、保護社會法益的同時,也應當兼顧對犯罪人人權(包括合法財產權益)的保護。不同的是,后者討論的焦點是在立法選擇上法益保護與人權保障孰先孰后的問題,而我國關注的焦點是司法權是否越位的問題,因為司法實踐的做法(即財產刑的異化)實質上是在立法缺位的情況下懲治犯罪的政策性選擇——選擇了法益保護。從憲政維度而言,對公民生命、自由、財產權益的剝奪,只能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依據法定程序通過的法律來規定。因此,這一問題亟待我國立法對“灰色”財產的處理做出明確的表態。
本文認為,從打擊當前日益猖獗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需要來看,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灰色財產”的處置應當吸收國外的立法精神:或者對于財產來源的合法性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由犯罪嫌疑人承擔),或者降低司法機關的證明標準。正如有學者所主張的,在“公司型”黑社會性質組織“黑白財產”混合時,不宜采取傳統的由公訴人舉證的做法,而是應當特別設置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即由犯罪分子自己舉證證明哪些財產屬于免于追繳或沒收的合法財產;否則,視為舉證不能,其財產將被推定為非法財產而予以沒收[11]。
[1]羅錦桂,迮銀軍.黑社會性質組織應增設財產刑[J].人民檢察,2002(7):52-53;盧建平,郭理蓉.有組織犯罪刑罰之比較研究——兼論我國刑法關于有組織犯罪刑罰規定的完善[J].政治與法律,2004年(2):83-87; 姚毅奇.論黑社會性質組織附加刑完善——以“反黑司法”實踐為視角[J].犯罪研究,2009(5):33-46; 莫曉宇,劉暢: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增設財產刑之研究[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76-80.
[2]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81-82.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節錄)[M]//刑事審判參考(2010年第3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6.
[4]阮方民,王曉.有組織犯罪新論——中國黑社會性質組織防治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154.
[5]張軍.解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刑事·行政卷)1997~2001年[D].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13.
[6]謝望原,肖怡.中國刑法中的“沒收”及其缺陷與完善[J].法學論壇,2006(4):5-12.
[7]阮齊林.再論財產刑的正當理由及其改革[J].法學家,2006(1):24-29.
[8]李潔.罰金刑之數額規定研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1):64-73.
[9]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維特根.德國刑法教科書[D].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956,2-14.
[10]彭文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若干問題研究[J].法商研究,2010(4):13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