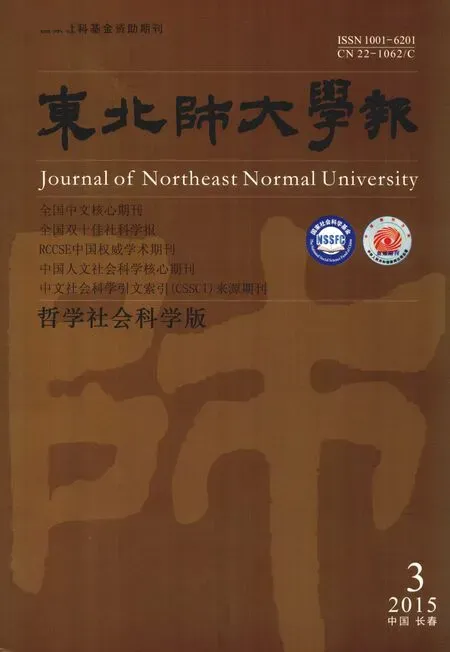再論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
韓秋紅,楊赫姣
(東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部,吉林 長春 130024)
?
再論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
韓秋紅,楊赫姣
(東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部,吉林 長春 130024)
西方哲學中國化體現出中國學者在新的歷史時期所應具備的文化自覺與理論自信。這一文化自覺與理論自信從西學傳入之初就已經形成,并為一些具有民族性意識和世界性眼光的學者所論及。西方哲學的中國化已經不僅局限于探討中學和西學何為體用的問題,而是西學如何助力于中國社會建設以及中學如何在納入多元視野以走向世界的問題。面對這一問題,不妨將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所呈現的特征加以明晰,即不是西方哲學的理論自覺,而是西方哲學研究的理論自覺;不是西方哲學在中國的簡單進化,而是西方哲學在中國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自覺發展。這樣的認識方式有助于在哲學視閾中實現中國當代哲學理論的理論自信,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助力。
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覺
西方哲學中國化在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有著較深的話語背景,這不僅體現為其貫穿于西方哲學(文化)探討的全部過程中,更體現為其深伏于中華文化發展的根脈中。發掘其思想資源和思想基礎,把握西方哲學中國化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的具體意義,發掘其在時代發展中的現實依據,延展出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價值及使命是研究西方哲學中國化論題、繼續深化其所實現的理論自覺的重要內容。
一、“中國化”表述方式的歷史根據
對于西方哲學“中國化”思想資源的開掘與整個西學東漸史有著時代背景的重疊。自西學(特別是西方哲學)以文化的形態傳入中國之后,就已經有學者以敏銳的觸覺把握這一變化,并開始思考如何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問題。在處理這一關系時,所期望實現得并非是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對立與矛盾,也并非二者孰優孰劣,而是在確定二者之間的邏輯界限和思想交界的基礎上來實現西方哲學脫離開其固有的“西方”母體。一些典型的時間點、學者、文化事件和觀點的連線能夠大體勾勒出這一圖景。
梁漱溟與“東西方文化論戰”。20世紀初的“東西文化論戰”是中國人第一次集中的、正面地表現出在面對西方哲學之重大背景——西方文化深入中國文化領域時的應對態度,這其中不乏能夠提供一些重要的線索,可為繼續探討西方哲學中國化之話題梳理前提性的理據。在東西文化問題的探討中,梁漱溟是一位典型的人物,他曾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專門提到了兩個概念,“西方化”以及“東方化”,梁漱溟試圖解讀兩個概念時指出:“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或說: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塞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兩大異采文化。”[1]33西方化的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兩種“新”的精神,而對于“如何是東方化?”這一問題的回答方面,自覺的植入與西方文化的對比視角,梁漱溟認為:“我對這兩樣東西完全承認,所以我的提倡東方化與舊頭腦的拒絕西方化不同。”[1]29不是簡單的拒絕“西方化”是論述“東方化”的意欲,是在“東方化”未來中加入的新的認識。然而這樣的觀點不等同于“全盤西化”,因為梁漱溟同時指出“東方化”與“西方化”的一個共同的論域,即“你且看文化史什么東西呢?不過是那以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1]32歸根到底,梁漱溟將“東方化”放在與“西方化”的比較視閾中加以生成,承認“東方化”在中國文化保持傳統方式的意義,另外也試圖在“西方化”的解讀中啟示“東方化”的發展路向。當時許多學者也都意欲到了中國文化轉型的問題,張申府(張崧年)也曾認為:“中國舊有的文明(或文化),誠然許多是應該反對的。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見得就全不該反對,就已達到了文明的極境,就完全能滿足人人的欲望。但反對有兩個意思,一為反動的,一為革命的。我以為囫圇地維護或頌揚西洋近代文明,與反動地反對西洋近代文明,其值實在差不多。我以為現代人對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種革命的相對的反對態度。”[2]對于西方文化的“革命”帶來了一種新的啟迪,而這種啟迪在中國文化中得到了持續的醞釀。
賀麟與“西洋文化華化”。20世紀40年代,賀麟先生以西洋文化之“華化”用度作為思考的進路,進一步具體地提出了儒家思想能否具有新展開的探討。賀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展開》一文中指出,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能否在西洋文化大量輸入的考驗下取得新展開,“成為儒家思想是否能夠翻身、能夠復興的問題,也就是中國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復興的問題。儒家思想是否復興的問題,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中國文化能否復興的問題,亦即華化、中國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3]6賀麟先生從文化的論域中所強調的儒家思想的“華化”問題也就是強調:一方面“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圍里,現代決不可與古代脫節。任何一個現代的新思想,如果與過去的文化完全沒有關系,便有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絕不能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文化或歷史雖然不免經外族的入侵和內部的分崩瓦解,但也總必有或應有其連續性。”[3]3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就其為中國過去的傳統思想而言,乃是自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來最古最舊的思想;就其在現代及今后的新發展而言,就其在變遷中,發展中,改造中以適應新的精神需要與文化環境的有機體而言,也可以說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里,我們可以得到現代與古代的交融,最新與最舊的統一。”[3]4可以看出,文化論域中的“華化”當然包括對傳統連續性的發展視角以及對新思想融合的視角。如今,西方哲學中國化也正是在這兩個維度上具有了再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當代學者與西方哲學中國化。西方哲學中國化是在非“西方”的意義上,在傳續西學東漸的文化進路,尤其是西方哲學東漸的歷史事實與邏輯上具有合理性的理論特征;與此同時西方哲學中國化又是在不斷開創主動自覺的文化意識中成為一種顯現的創新式理論形態。當代已有諸多學者提出了“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多種角度:趙敦華于21世紀初提出了“用中國人的眼光解讀西方哲學”,所謂“中國人的眼光”同樣吻合在兩種維度上自覺理解的西方哲學中國化,即“用中國人的眼光解讀西方哲學,是基于‘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而提出的。”[4]代前言1用中國人的眼光解讀西方哲學意味著尊重傳統的重要維度。“我們不僅要在西方哲學的研究領域和西方學者競爭,更重要的是促進中西文化的互相理解。”[4]代前言4“運用中國人的眼光是中國文化意識的自覺,用中國人的眼光解讀西方哲學,更是我們在文化建設中面臨的新任務。”[4]代前言11用中國人的眼光解讀西方哲學意味著文化發展中的創新自覺,也就是發展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形態的自覺認識。李景源在《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一書中也提出觀點,即將西方哲學中國化視為一種探討中國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潮流”形態,認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西學東漸、中西方哲學文化由沖突走向融合、中國人努力將西方哲學中國化成為潮流這樣一種哲學文化歷史大背景下產生的,是西方哲學中國化潮流的一部分,同時更是一種超越、一種創新發展。”[5]認為西方哲學中國化作為一種在西學東漸中形成的思想潮流構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鋪墊和重要論域,這實際上說明了西方哲學中國化所具有的接續文化發展使命的合理維度,表達了一種在連續性的文化生成史中解讀包括中國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理論形態的方式。另則,陳衛平也對西方哲學中國化進行了闡釋,認為“西方哲學的中國化是指它們在中國取得了新的理論形態,有著與其在西方不盡相同的貌。……西方哲學在中國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態,是因為中國傳統哲學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資源。所以,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建構始終貫穿著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三個互相聯系的普遍性的環節:變革、融合、制約。”[6]如何在傳統文化論域中走出自我道路是深化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重要向度。正是在這兩個意義的認識基礎上,即西方哲學中國化在文化生成史中具有的與西學東漸相同的歷史邏輯以及在理論形態的自覺發展中凸顯的創造性、融合性本質的理論實質的雙重理解中,西方哲學中國化具有了再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具有了我們通過這兩個維度開出更多合理啟示的關鍵契機。
回顧以往幾代學者對西方哲學中國化相關論題的探討可以發現,西方哲學中國化首要實現的是使西方哲學走出“西學”的固有域境,使之能夠在中國學者的自覺意識支配下融入中國社會現狀,并在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實現其自覺的“中國化”。他們對問題的探討已經將西方哲學中國化上升到文化和理論自覺的高度,對其內涵、特征和實現方式等做出基礎性說明。他們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一方面應繼續夯實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身的生成史,在“西學東漸”的歷史論域中結合西方哲學中國化面對的現實問題回答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形態的自覺前提;另一方面注重在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發展的突出表達中揭示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自覺,即自覺探索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形態發展中的可能方案。這些都是在努力推動西方哲學中國化之“走出西方”的重要步驟,也是在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問題探討的同時開展實踐研究的基礎。
二、“中國化”實踐經驗的歷史演進
哲學產生、發展、融通從最深層次上說都是時代要求的結果。可以說,中國理論界對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關系的理解從來都不是將其作為簡單的文化交融問題,而是在不同時代對其在中國社會的特殊語境中形成的對中國社會哲學形態理解過程彰顯出的時代自覺。正如馬克思所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學者們在論及西方哲學中國化將其作為理論問題加以探討的過程中,同樣將其作為時代問題加以破解。這樣的破解方式就是將西方哲學中國化這一理論問題轉變為時代問題,使其能夠體現哲學發展的應有之意。
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文化殖民產生了“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初級形態。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通過耶穌會組織,帶著他們的科學著作進入中國,在那時主要傳播的科學著作與哲學是分不開的,傳教士們信奉托馬斯,因此其著作大都將基督教、天主教神諭與亞里士多德哲學結合起來,也可以說,西方哲學最早通過傳教的方式進入中國。然而不難看出,西方哲學的初期傳播并非按照中國自身的國情發展需要而主動尋求和選擇的,而是西方殖民主義者通過教會力量向海外擴張勢力的一種手段。利瑪竇自己就曾宣稱:“中國偶像崇拜這個三首巨怪較之萊恩納湖的蟒怪更為恐怖……而我們耶穌會本著自身的宗旨,奮起與之戰斗,跨越千山萬水,穿過許多王國,從遙遠的國度來此拯救不幸的靈魂,使之免遭永恒的天譴。”[7]在西方傳教士傳播“人文主義”福音的外表下隱藏著以在西方哲學為基本形態侵略中國人文化以及思想的動機,可這在當時恰好適應了中國社會出現的現實問題: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環境對于神圣文化的需求。在歷史背景下顯示出的文化進程之邏輯與現實問題凸顯中構成的共同合力致使西方哲學的中國化最初淹沒在侵略與統治的野心之中。隨著中國社會發展現實問題的轉變,對西方哲學的這種淹沒并沒有得到實質的改變,所謂的洋務運動之后迎來的西學東漸的真正高潮只是從另一個歷史事實中表明了西方哲學在中國被動發展的初級階段。
中國社會救亡圖存運動催生了“西方哲學中國化”論題的出現。建立在民族精神刺激之下的西方哲學的廣泛開展只是反映了對西學思潮接納的廣度上取得了進展,即西方哲學作為洋務運動的器物之變、制度之變之后對中國文化觀念、哲學理念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化分支,在一次次國家危難和歷史選擇面前被推向了前臺。經過鴉片戰爭的慘痛洗禮,中國人清晰地意識到西方列強通過科學技術改造的堅船利炮的軍事優勢,因此中國人抱著“中體西用”的原則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態度尋找一條救亡圖存的發展之路。然而此時的中國面對外敵入侵、國難當頭之際,首先選擇了學習西方的器物之理及制度之綱,19世紀60年代一場洋務運動便適時地開展了。在這場廣泛地汲取西學之用的運動中,中國學者實際上已經具備了較為主動地思考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學在內的資源儲備和主體動機。洋務運動中,在中國南、北方的上海和北京分別成立江南制造局譯書館和京師同文館,陸續翻譯出版了大量的西學著作,其中包括大部分的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也有少部分人文科學方面的著作。民國之后隨著引進西方哲學逐漸加溫,19世紀初在西學著作的翻譯中自然科學類書籍數目出現了下降,哲學、社科類開始上升,“五四運動”之后西方哲學的翻譯著作便受到了更加明顯的重視。而就學習西方哲學的主體動機來說,中國人學習西方哲學的主動動機受到了社會現實問題的啟發,從長時間受困于外憂的現實問題轉向同時解決內患的社會變革、維新的現實問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在歷史邏輯的延續以及現實問題的契合中初步展現了中國化的特征。
不同于戰爭時期,對西方社會和西方文化的深化認識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實現由以往的制度層面學習向精神文化層面學習的轉變。誠如梁啟超所言:“求文明而從形式入,如行死港,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求文明而從精神入,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真瀉,沛然莫之能御也。”[8]陳獨秀在《吾人之最后覺悟》中也講到:“最初促吾人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流離之景。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9]因此在西方哲學領域中出現了一批最早挖掘此精神文化之覺悟的有識之士。嚴復、王國維、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都意識到要想使植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的中國本土哲學表現出新的狀態,就要“運用西方哲學來解讀中國哲學的概念與觀點,或者吸收西方哲學的某些思想與原理融會到中國哲學中來,從而使中國傳統哲學走上了變革和轉型的階段。”[10]6正是在這種契機之下,西方哲學中國化成為促使中國哲學走上轉型之路的動力之一。新文化運動中試圖以西方科學與民主精神填充中國文化的意圖使得宣揚西方哲學成為一條合理的途徑。
20世紀30、40年代,與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的社會局勢密切相關,中國該向何處去的探討也達到了空前的熱潮,藉此出現了眾多的現實問題的探索和爭論,許多學者關注到了在特殊歷史背景和社會發展時期哲學、文化演進本身的特殊需要,并基于對當時中國現代化發展方向的思慮調整了方向。就廣大學者的認識來說,在馬克思主義視域下展開的理論探索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蘊含了豐富的革命理論,但與此同時人們也開始注意到西方哲學對于開拓中國文化思想的新領域以及在理論自覺的層面上提升常理性認識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就為這一時期的西方哲學中國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把西方哲學家的重要著作及其學說系統地輸入進來,經過深入的研究把取得的理論成果在社會中廣泛傳播開來,使它們在繼續開展的思想啟蒙,進一步喚醒民族精神覺醒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10]501事實正是如此,中國思想界在不斷地推進西方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展示了在思想認識中發生的明顯轉變。以賀麟先生為例,他饒有興趣地從事著德國古典哲學開疆辟地的研究工作,但可以從他的研究軌跡看出,個人興趣與對時代的敏感認知相結合是賀麟先生開展哲學研究的重要初衷。1939年賀麟先生寫作出版的《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引證了其研究西方哲學的基本態度。1941年,賀麟先生繼續秉持著傳播西方哲學重要思想的目標,成立了“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開始組織系統地翻譯西方哲學著作的工作。“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第一集便出版了四本書,包括賀麟自己翻譯的斯賓諾莎的《致知篇》;陳康翻譯的柏拉圖的《巴門尼德篇》;賀麟的學生翻譯的羅伊斯《忠的哲學》與《近代哲學的精神》。對西方哲學著作的占有日益豐富的同時,賀麟先生還在中西哲學融通的層面上進一步提出了“新心學”思想體系的建構思路,即從中國哲學中的心學出發,寫作了《近代唯心論簡釋》,同時在自我的學術經歷以及學習背景的支撐下,通過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潛心鉆研提出可以通過德國唯心論論證陸王心學與胡適實用主義唯心論不同的新穎論點。從這樣的歷史事實更加明顯地看出,西方哲學正在通過一種與時代節奏、理論建構相關聯的發展方式彰顯著“中國化”的理論內涵。
中國社會發展要求哲學思想引領創設了“西方哲學中國化”的不同情境。新中國成立之后,西方哲學的研究更加在曲折發展中體現了中國化的具體特征。建國后,西方哲學的發展及研究首先出現了向蘇聯哲學“一邊倒”的特征,新的國家體系以及社會制度的建立,亟須思想領域做出規范和解釋,因此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哲學界開展了以日丹諾夫在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成為著名標志的研究方向的轉變。1950年初,中國學術界多次在北京大學舉行關于學習日丹諾夫發言的討論會。馬特曾指出:“照日丹諾夫的意見,哲學史的定義很重要,它就是對哲學史的基本看法。假如沒有給哲學史下正確的定義,對哲學史上的各種問題,就不能有正確的理解。”[11]至此意味著我國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史的性質進行全新的認識和詮釋。以蘇聯模式為樣板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西方哲學研究,符合我國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要求,也有利于解釋建國初期很多重大的和根本性的社會問題。正如鄭昕所言,“舊的被否定了,新的尚未能掌握,頗有茫茫然之感。”[12]新的哲學原則和標準的建立在當時起到了統一思想的積極作用。而此時中國學者研究西方哲學,也已經逐漸超越傳統的方式,從出于革命斗爭的需要轉移到建設國家,樹立民族獨立精神的層面上來。因此,西方哲學研究所呈現出的特征盡管不甚符合西方哲學的學術邏輯,但卻是符合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內在邏輯的,即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研究一方面是西方哲學的研究,但更體現的是中國人研究的西方哲學。而在西方哲學的這種研究中體現中國階段性的發展現實情況,以中國人的政治立場、價值選擇和利益訴求為旨趣也是無可厚非的。經過文化大革命一段低迷期后,西方哲學的中國化研究進入了自我反思的重要階段。以1978年蕪湖“西方哲學討論會”的召開和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重要標志,我國西方哲學在真正的思想解放理念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具有了更為符合時代要求的合理性特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同樣灌注在西方哲學的研究當中,以西方哲學本真的面向理論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帶來了西方哲學中國化的新一輪繁榮。即哲學研究不能只是被動單純的照搬照抄,而應該尊重研究者自身的思想立場、主觀需求和價值取向,甚至將研究主體特有的歷史性、能動性和創造性有個性地表達出來。西方哲學的思想理論探討應逐漸摒棄蘇聯模式的禁錮,不再以是否符合蘇聯哲學的模式為判斷標準,逐漸從教條、僵死、二元對立的“本本主義”中解脫出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確立,為一切思想理論研究掃清了障礙。加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在思想觀念上為新思想、新觀念的進入和傳播奠定了現實基礎,也催逼新的理論形態的出現。因此,在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研究領域,積極地開展的廣角度研究是基本的趨勢,古希臘、中世紀、經驗派與唯理派、德國古典哲學、現當代西方哲學等不同歷史時期的西方哲學,以及各個時期代表人物、流派、著作、思想的專門研究紛紛成為西方哲學注重多元視角研究的現實表現。在這種多元化、創新意識的推動下,西方哲學的研究在基于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情本身”的層面上開始進行“中國化”的反思,正如高清海先生所指出的:“學習西方先進的哲學理論,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創建屬于我們自己的當代中國哲學。別人的理論終究無法代替我們的哲學思考。”[13]中國人開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創造性地發展西方哲學,對西方哲學能夠做出自覺的解釋與自我的說明,特別是自覺的運用。如對西方哲學史上其他流派和觀點的闡釋中,越來越帶上中國人的思維特點和解釋原則,使得西方哲學在中國越來越本土化、中國化。這樣的西方哲學研究,是研究者主體性逐漸彰顯的過程,也是主動追求、甚至是主動催化西方哲學向“中國的西方哲學”轉變的過程。西方哲學的中國化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得出的自覺認識。
西方哲學在中國的演進與發展以深刻的融入中華民族社會發展形勢的歷史邏輯以及鮮明的彰顯現實問題凸顯了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重要前提[14]。也正是由于西方哲學在中國的最初發展所呈現的受制于歷史與現實的雙重特征,才使得這一時期西方哲學在無意識狀態下呈現的被動融入的形態促成了后來中國人主動、自覺學習、研究西方哲學更加長久的歷史與更加突出的“中國化”的現實意味。如果說西方哲學中國化在建國前尚未全然自覺,那么這種空白在建國之后西方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中得到了填補,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關鍵機制也在對這種空白的補缺過程中實現了真正的合理化。
三、西方哲學“中國化”的思想成果
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是民族化的理論自覺,這一“是”民族化理論自覺的過程經歷了以下幾個步驟,即還原——識質——建構。在當下,西方哲學中國化所形成的成果,體現了對西方哲學的不同態度轉變過程,也體現了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層次和程度。此“是”的過程也是西方哲學中國化中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呈現的過程,是從最深層次挖掘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歷程。從研究成果看,中國人在引進西方哲學時,體現了從摘選到全面引介再到自覺創造的整體過程;對西方哲學的自覺主動甄別也就是建構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機制,表達學者們對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覺的主動建構。
建國之前我國理論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總體上體現了還原和介紹的思路。從西學引進之初,進化論的熱潮以眾多著述的翻譯與引進為現象,屹立于中國思想史的重要轉折階段。中國人主動的選取那些集中展現西方文化之進化向度的文獻,作為迎合國家危機的現實局勢以及抒發救亡圖存的民族心理的途徑。19世紀末嚴復選取了赫胥黎《天演論》進行翻譯,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據統計,自1898年以后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論》就發行過30多種不同版本,廣泛流傳,風行海內,這是當時任何其他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15]進化論迅速成為代表中國引進西方文化轉變思想主流的成功案例。在人們熱衷于進化論之際,中國學者開始積極的摘選符合這種文化思潮的思想資源,如1902—1903年,馬君武翻譯了達爾文的巨著《物種起源》中的“生存競爭”、“自然選擇”兩章,并以《達爾文物競篇》、《達爾文天擇篇》為題,出版了單行本。1903年,李郁翻譯了《達爾文自傳》第3卷。直至五四運動之后,對進化論相關書籍的選取翻譯與引進仍然被視為中國思想發展的重要陣地。1920年,馬君武全面譯出達爾文進化論巨著《物種起源》,“1922年以后,又有許多進化論的經典著作如達爾文的《人類原始及類擇》、黑格爾的《生命之不可思議》、《自然創造史》以及進化論通俗讀物如《進化論十二講》、《進化論發展史》等書先后在國內出版發行,推動了進化論的普及。”[16]最初中國人對于西方哲學的摘選是在主動迎合變革需求的前提下進行的精神改良,雖有主動但并不是在自覺建構的意義上對西方哲學的慎重思忖。實際上在這一時期,任何符合救助民族危亡的思想資源都是受到歡迎的,因此除了進化論,西學思潮中的國家發展、社會制度等理念也被摘選出來,填充到中國文化的新進展之中。如嚴復繼《天演論》之后后又譯出了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疑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等著作,從嚴復甄選、翻譯的西方著述來看,其共同之處就在于這些西方文化成果大都能夠在與中國社會情況結合之下加以改造,為解決當時的現實問題提供啟蒙。這就造成了西方哲學最初的引入也必然受制于這樣的社會現實,對于西方哲學的甄選中也呈現出了貼合進化論的趨勢,如康有為所著的《諸天講》,其中對于康德星云學說的引進便符合了這一時期在世界觀方面發生轉變的中國人的需求。又如梁啟超在西方哲學中總結、反思的文明發展根源以及西方的政治學說等等,也通過自我主動的發展與傳播成為了能夠被中國人即用的思想資源,他曾通過廣泛的閱讀西方哲學著作,開始思考中國社會落后的根源,試圖通過認真的研究近代西方哲學的主要著作總結西方國家進步的根源,由此寫作了《培根學說》、《笛卡兒學說》、《霍布士學案》、《斯片挪莎學案》、《進化論革命者劼德之學說》、《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等等基于西方哲學名篇研究的學術成果,同時還特別關注西方哲學家思想中的政治理念,發表了《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法理學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等多篇介紹西方政治哲學家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國長期所處的動蕩局勢,使得中國人一方面在文化發展中不得不注重社會現實,另一方面又在動蕩中初嘗了文化之對流,具有了不一樣的眼界,因此,西方哲學翻譯成果在中國人集中精力救亡圖存的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傳播,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40年代左右。然而不同的是,在相對政治環境寬松的30、40年代,西方哲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全面引進西方哲學階段。中國學者開始以整個西方哲學史為對象進行較為全面的翻譯和引介工作,比如在古希臘哲學方面,有楊伯愷譯出的《赫拉克利特哲學思想集》、《德謨克利特哲學道德集》以及《學說與格言》;1944年陳康翻譯《巴曼尼德斯篇》等等。近代西方哲學方面,有關其桐翻譯的培根《新工具》;巴克萊《人類知識原理》;休謨《人類理解研究》;笛卡兒《方法論》、《哲學原理》、《沉思集》等等。德國古典哲學方面,有胡仁源翻譯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張銘鼎翻譯的康德《實踐理性批判》、黑格爾《論理學》;王造時翻譯的黑格爾《歷史哲學》等等。對現代哲學著作翻譯也取得了較為全面的進展,其中叔本華、尼采、詹姆士、杜威以及羅素等現代哲學家的著作都成為中國人全面促成西方哲學中國化發展的前提資源。
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理論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總體上體現了性質界定的思路。1948年至1954年由我國學者李立三翻譯出版的《日丹諾夫同志關于西方哲學史的發言》、《論哲學史諸問題及目前哲學戰線的任務》以及《日丹諾夫在關于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三本譯作中都曾提及日丹諾夫代表的蘇聯學者在研究西方哲學史方面的主要立場,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立場,由此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走上了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立場下的建構階段。日丹諾夫指出:“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底胚胎、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唯物主義派別斗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末,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的歷史。”[117]建國后在新的國家和社會制度剛剛建立的初期,在思想領域做出規范和解釋具有必要性。也正是在此時,日丹諾夫在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被引入國內,他指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必須以蘇聯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為指導,還要以此為樣板撰寫和編纂整個西方哲學史。馬特就曾指出:“照日丹諾夫的意見,哲學史的定義很重要,它就是對哲學史的基本看法。假如沒有給哲學史下正確的定義,對哲學史上的各種問題,就不能有正確的理解。”[11]也正是在這種對哲學史的基本認識之下,我國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西方哲學史)性質進行全新的認識和詮釋。一段時期內,西方哲學的建構發生了向蘇聯模式的哲學建設“一邊倒”的轉變,但這段歷史無疑是符合中國國情以及現實問題的,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段時期的西方哲學研究視為錯誤的,只能說正是由于我們經歷了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哲學的辯證發展階段,才進而擁有了更加清晰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哲學的思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積極地走向建構型的中國化理論的同時,西方哲學也在不斷地起承轉合的研究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化視角。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一種主流的方式詮釋了中國人主動自覺的容納新的思想理論的一種轉變,西方哲學就是在不斷的以批判性認識的方式推助這種主流轉變的另一種中國化力量。然而西方哲學中國化最終還是在自我的建構機制中真正凸顯了其不同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獨特之處以及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契合之點。
改革開放后我國理論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總體上體現了建構的思路。1978年蕪湖“西方哲學討論會”的召開和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意味著我國西方哲學建構時期的到來。以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論研究,特別是哲學理論體系中主體性思想的當代發展和引入建構西方哲學成為新時代的重要主題。西方哲學的中國化需要建立真正的理論自覺認識,需要在歷史邏輯和現實問題的視域之外形成新的自覺性認識。反思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發展中的局限性,努力彰顯以“建構”為實質內容的一大批優秀成果在70年代之后紛紛涌現。如在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中,朱德生、李真所著的《簡明歐洲哲學史》,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所著的《西方哲學原著選讀》,陳修齋、楊祖陶所著的《歐洲哲學史稿》,全增嘏所著的《西方哲學史》,冒從虎、王勤田、張慶榮所著的《歐洲哲學通史》,高清海所著的《歐洲哲學史綱》等都力圖立足于“還歷史本來面目、還哲學本來面目”的真切目的,積極地建構著西方哲學中國化的新樣貌。如葉秀山在八卷本的《西方哲學史》(學術版)的前言中所說:“‘創造性’的‘歷史’是一部‘自由史’。哲學史也就是這種‘自由史’的理論的表達。對于‘創造—自由’的歷史,我們也是要‘學習—研究’的。‘學習—研究’他人,特別是學習那些歷史上的哲學大師們如何創造性—自由地思想,舍此之外,沒有什么捷徑可以使我們的思想真正成為‘創造性’的。編寫這部多卷本的西方哲學史,目的也在于把西方歷史上那些載入史冊的哲學大家們如何創造性—自由地‘思想’哲學問題真正客觀地介紹給大家,而要做到這一點,沒有我們自身的創造性,是不可能的。只有‘自由者’能夠理解自由。”[17]中國學者對待西方哲學態度的轉變從強調西方哲學的外在的“應激反應”式的“為我所用”過渡到從西方哲學的真實研究出發的內在建構的“為我所用”,西方哲學實際上真正進入了中國化、現代化的廣泛發展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哲學中國化在進一步發揮主體自覺性上呈現了知識建構過程中的多樣性特征。正如孫正聿先生所總結的:“從哲學的最基本的理論框架去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哲學狀況,大體可以劃分為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教科書哲學、80年代以反思教科書為主要內容的哲學改革和90年代以來以現代性的反省為主要內容的后教科書哲學。”[18]中國學者在逐漸意識到哲學研究中的反思意義以及以現代性的視角建構哲學體系的重要性的前提下開展了對西方哲學中國化的新探討。在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方面,從以往注重從宏觀的角度出發的研究轉向對西方哲學中的具體思潮、流派、人物等微觀視角的把握,這一變化不僅僅帶來了西方哲學史方法論意義上的變革,同時意味著中國學者在研究西方哲學的同時已經開始努力地探索哲學史中展現的思維發展的規律性總結。例如趙敦華先生所編寫的《西方哲學通史》以及后來推出的《西方哲學簡史》、《現代西方哲學新編》都極力在微觀的視域下融合了西方哲學的自身歷史的真實性與中國人解讀西方哲學產生的主觀自覺。趙敦華先生通過對西方哲學史資料的充分占有和整理,突出哲學觀點、把握思維線索的表述目的,展現了現代西方哲學中國化研究中的重要立足點,即“史論結合”地闡釋西方哲學。可以說,就西方哲學史研究方式的變革來說,我國學者已經具備了自覺實現西方哲學中國化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與此同時,中國學者還在自覺擴充西方哲學研究的現代視域上實現了理論自覺。除了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之外,現代西方哲學的引介與研究越來越在成為潮流。現象學思潮、分析哲學、后現代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極具特色的現代西方哲學流派在中國人尋求更多地展現理論自覺性的實踐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這些無疑都構成了我國研究西方哲學的新視角、新內容,同時充實著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現代發展的合理性內涵。
對西方哲學中國化理論自覺地再挖掘,不僅是一個辨識、融合西方哲學于中國的理論研究,更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把握理解文化沖突、把握時代問題和解決現實實踐問題的重要步驟。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所彰顯的既有中國學者之于西方哲學研究的主體自覺意識和價值需求,更有中國社會實踐基礎之于中國大“哲學”的客觀反映[19]。中國哲學在所處的時代境遇和現代性問題的前提下,對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自覺的充分認識和重視,既能推動西方哲學中國化發揮融通維度下哲學創新的積極意義,又能深化中國學者之于“西學”等外來思想的主體自覺意識。這無疑將有利于推動借鑒、吸收“西學”的有益成分,實現中國哲學自身民族化根基的夯實,推動中國哲學變革創新的目的。
[1]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 張申府.張申府學術論文集[M].濟南:齊魯書社,1985:11.
[3] 賀麟.文化與人生[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4] 趙敦華.西方哲學的中國式解讀[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5] 李景源.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92.
[6] 陳衛平.西方哲學的中國化與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J].學術月刊,2004(7):9.
[7] 裴化行.利瑪竇評傳:上冊[M].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9.
[8] 梁啟超.國民十大元氣論[M]//飲冰室合集(1),1989:飲冰室文集之三六二.
[9] 陳獨秀.吾人之最后覺悟[J].新青年:第1卷,1916-02(6).
[10] 黃見德.西方哲學東漸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 馬特.討論日丹諾夫關于亞歷山大洛夫《西歐哲學史》的發言[J].新建設,1950(1).
[12] 鄭昕.送車思科洛夫、阿斯凱洛夫兩教授南下講學[J].新建設:第2卷,1950(5).
[13] 樓宇烈,張西平.中外哲學交流史[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364.
[14] 韓秋紅.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研究范式[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1-5.
[15] 王曉明.西方進化論與近代中國社會[J].教學與研究,2005(10):70-75.
[16] 日丹諾夫.日丹諾夫在關于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M].李立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4.
[17] 葉秀山,王樹人.西方哲學史(學術版):第一卷,總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前言3.
[18] 孫正聿.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1978—2008.哲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3.
[19] 史巍.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基本規律[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6-10.
A Re-examination on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 Siniciaz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HAN Qiu-hong,YANG He-jiao
(School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e sinciz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reflects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which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possess.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were form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China,and have been discussed by some scholars wi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world-wide sight. The siniciz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is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the question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use or western culture in Chinese use,but also with the way to help Chines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way for Chinese philosophy to absorb visions of pluralism to reach the world. To address this issue,it is feasible for us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siniciz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It is not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western philosophy-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eastern consciousness-it is the national 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By this way,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can accomplish its theoretical confidence in philosophical vision and increase the self-confidence of road,theory and system of Chinese socialism.
Siniciaz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Theoretical Self-consciousness
2015-03-20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2&ZD121)。
韓秋紅(1956-),女,吉林吉林市人,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楊赫姣(1985-),女,吉林吉林市人,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博士研究生。
B5
A
1001-6201(2015)03-0007-08
[責任編輯:秦衛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