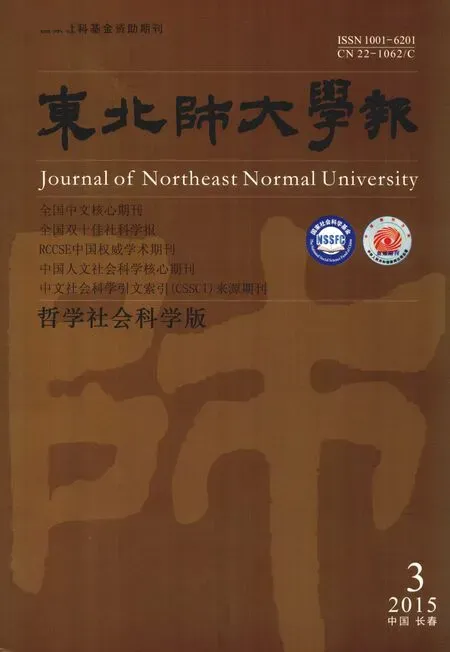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價值自覺與文明憧憬
龐 立 生
(東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部,吉林 長春 130024)
?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價值自覺與文明憧憬
龐 立 生
(東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部,吉林 長春 130024)
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應當具有怎樣的思想擔當和價值自覺?筆者認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需要立足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和文明成就,深入領會和體認馬克思主義哲學蘊含的文明教養和思想張力;需要把握中國道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踐,所蘊含的強大的哲學轉化和創新能力。在世界歷史的重構與文明轉換的關節點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正日益體現為民族復興的價值自覺,并昭示出一種有別于西方現代性文明形態的新氣象。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實踐哲學;文明類型
哲學本質上是對一定時代人民最深層渴望和生活理想的思想領會和理論表達,是對一個民族乃至人類生存狀態的前提反思和價值澄明。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現代中國人反思和改變自己生活命運的思想武器,一直在思想和現實的雙重向度中展開著自身艱難的中國化歷程。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創新不僅取決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精神實質的深刻洞見,而且取決于我們對時代狀況和自身經驗的直觀能力和把握水平。世界歷史時代,各種不同的世界觀將會把我們的生活引向不同的視軌和方向,世界歷史的開放性也將使各種世界觀在相互交流、交匯和交鋒的歷史實踐中來伸張和確證自己的真理性。那么,在此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應當具有怎樣的思想擔當和價值自覺?如果說,哲學是文明的活的靈魂,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否蘊含著一種新的文明類型的可能性?顯然,這些問題是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重大根本性問題。
一、深入領會馬克思主義哲學蘊含的文明教養與思想張力
在當代紛繁復雜的哲學思想景觀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在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那里得到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繼承和發展,也在當代更為廣闊的思想理論視域中激起綿延不斷的思想震蕩,產生著深刻復雜的思想效應。隨著時代生活的延展,我們會越來越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種深刻影響現時代的卓越思想,其所具有的理論開放性和復雜性越來越被彰顯出來。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基深深地植根于現代文明所能達到的思想成就之中。對于這一點應予更加深刻的領會與認知。如果割斷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塑造現代文明的各種思想成就之間的內在關聯,就會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失去其文明的根基,從而淪為沒有血脈來源的抽象僵死的形上教條。以馬克思的實踐觀點為例,這一觀點的確立其實具有豐富的思想史與文明史基礎。馬克思的實踐觀點與對古希臘實踐哲學傳統的批判性改造內在相關,它既揚棄了古希臘人出于對自由、不朽和崇高的追求所表達的對物質生產勞動的蔑視,反過來賦予勞動以普遍而深刻的人性意蘊,同時還在實踐概念中保留了古希臘人對生命理解所具有的藝術向度和自由旨趣。馬克思的實踐觀點與近代產業革命的發展以及近代政治經濟學也具有密切的聯系。近代產業革命以來,勞動作為物質文明的支柱,其對人類生存發展所具有的基礎性意義日益凸顯,人們對勞動的時代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斯密等政治經濟學家將勞動視為財富和價值的源泉,將勞動上升為社會生活的決定性形式。馬克思一方面吸收了政治經濟學家對勞動積極意義的理解,另一方面又從中看到了政治經濟學家把勞動工具化的歷史局限。勞動也是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主題。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黑格爾精神勞動的辯證法所表達的人經由勞動而實現自我生成和自我確證的合理內核,又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沒有看到勞動的特殊形態所導致的異化現象展開哲學批判。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的實踐觀點中,汲取了從古代到近現代且包含西方哲學、經濟學等在內的思想文化精華,積淀和負載著西方時代精神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的實踐觀點,才不僅上升為一種理解人的自我產生、自我創造和自我發展的新的思維方式,而且蘊含著對作為實踐主體的人民群眾通過自覺的實踐活動實現自身解放的價值要求。實踐哲學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于西方傳統思辨哲學的根本特質。從根本上說,實踐觀點就是徹底的辯證法觀點,它奠基于對人的生命活動所具有的辯證本性的理論洞見,也在本質上與社會的觀點、歷史的觀點內在相通。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真理性是歷史地生成和獲得的,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真理性當然也就必然地是歷史的。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哲學才有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離開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史和文明史理解,就不會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我們需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為人類理論認識和文明發展的歷史性成果。
作為歷史性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蘊含的文明教養需要持續不斷地去體認和領會。一方面,這需要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常識、科學、宗教、藝術等諸種時代性的文化樣式以及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人類學等不斷發展的學科思想的關聯中,去把握其理解世界的獨特方式和獨到思想。畢竟,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初就是作為區別于學院派哲學的世界觀理論而產生的,它并不是懸隔現代文明教養的孤寂的沉思默想,而是把現代西方文明發展的優秀成果作為必然性環節包含于自身之內的“文明的活的靈魂”。離開了對兩千年來西方哲學和文化發展的真切理解和自覺意識,也就難以掌握吸取了兩千年來西方哲學和文化積極成果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精華。如果缺乏必要的文化教養和文明胸襟,自然就難以真正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方式和價值態度的理論自覺,也無法真正抵達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具有的歷史性本質和文明底蘊。另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也需要我們深入到時代生活的根底處,準確地把捉特定時代人們的生存狀態及其中心課題,領會時代精神的根本關切與深層渴望。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影響世界的世界觀,究其原因,在于它從根本上觸及了人們這一時代人民大眾最為鮮活的生命感受和存在經驗,提示著人民大眾改變自身命運的文明方向。海德格爾就曾經稱贊馬克思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道出了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基本經驗。因此,面向時代的根本矛盾,把握時代的普遍情緒狀態和深層的精神脈動,是理解和領會馬克思主義哲學最為基本的生活基礎。
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具有的文明教養,在思維方式上體現為對這一時代所彌漫的知性思維的揚棄。立足人的生活實踐,分析和批判事實與價值、理論與實踐、理性與信仰、個體與社會、物質與精神、歷史與現實等諸多二元對立得以存在的現實生活基礎,使其在人類自我解放和發展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從宰制生活世界的各種虛假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逐步獲得辯證的和解和從容的精神棲息之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思維方式的要義。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具有的思想張力,常常在更加根深蒂固的知性思維的理解中遭到肢解。以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為例,我們看到,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對社會歷史的理解上,一方面把社會歷史建基于物質生產的基礎之上,看到了物質生活條件對社會歷史發展所具有的奠基性意義,揭示了使人類歷史得以可能的物質生活條件。另一方面,他又沒有僅僅停留于物的意義和層面上去理解社會歷史發展的物質因素,而是洞察到了物質生產所具有的主體意義,從中將社會歷史看作是通過能動的實踐活動被自覺地建構起來的產物和過程,由此把人理解為社會發展的主體、動力和目的,從而使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僅區別于黑格爾式的主觀任性的精神自由,也同時區別于缺乏價值目標和抹去主體向度的實證主義。這表明,歷史唯物主義是在實踐觀點的基礎上,超越了抽象的實證主義與觀念唯心論的視野,實現了主體性向度與客體性向度、科學性向度與目的性向度的辯證統一。這一雙重向度使歷史唯物主義呈現為特別的思想張力與彈性。“我們習慣于過分強調唯物史觀對歷史的科學性理解,忽視其目的論和信仰的一面,但這恰恰是一種抽象的片面的解讀,導致把唯物史觀看成是經濟史觀和經濟決定論,損害了馬克思歷史地理解的人性內涵、學術品味和思想力量。超越這種抽象的純粹科學理解,我們可以看到,革命的歷史目的論是馬克思歷史學說的高度理想特征和信仰維度的實現形式,只有當歷史的科學理解和目的論理解結合到一起,才能解釋馬克思學說經久不衰的思想力量。”[1]我們發現,無論是出于科學主義的價值追求,還是出于實用主義的現實考量,抑或受到日常知性思維的支配,我們常常單向度或實體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蘊含的文明教養和思想張力遭到損害,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也就喪失了必要的思想基礎和可能性空間。至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體化理解,依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阻礙性因素。因此,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需要我們進一步立足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能達到的思想高度和文明成就,深刻領會和體認其所蘊含的文明教養和思想張力。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道路的價值自覺
正像馬克思所言:“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竭力體現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2]思想與現實的相互作用及其相互轉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實踐的哲學所具有的內在張力。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傳播到中國并被被迫進入現代性起點的中國所選擇和接受,本質上還是由于它具有滿足現代中國改變自身命運的客觀需要的實踐性力量。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實踐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日益與中國的現實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相互作用。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既充分確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實踐的哲學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實踐性品格,也表征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實踐生成和具體實現。
實踐的哲學與哲學的實踐,始終是近百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懈追求。毛澤東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3]。毛澤東對于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給予了不遺余力的批評,并親自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樣的經典著作,以此指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應當說,這樣的哲學著作,絕非是學院派哲學家在書齋里主觀構想的產物,而是凝結了中國革命十分沉痛的經驗教訓。教條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先在本質決定論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以虛假的主觀意識來規范和裁剪生活的偏執粗暴的理論生活態度。事實證明,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片面性傾向的克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項需要不斷與之斗爭的艱難任務。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通過實踐標準的重新確立而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而得以實現的。在此過程中,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觸及的是我們多年來一直固守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教條。它超越了在兩極對立思維模式下對社會主義僅僅從所有制關系方面進行實體化理解的誤區,轉變為從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的角度,去規定和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理解的思維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是對社會主義認知概念框架的重新改造和理解范式的實質性轉換。以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思考為前提,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所成就的中國道路,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實踐。馬克思曾言:“感覺在自己的實踐中直接成為了理論家”[4]。在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實踐探索中,凝結著深沉的理論智慧。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哲學,是指導中國道路具體實踐的哲學理念,那么中國道路就是哲學的實踐,它所實現的巨大的哲學轉化和創新能力,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實踐模式,成就并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新境界。
中國道路所體現的哲學洞見,在以下關系中得到集中體現:一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的理解,不僅是一個具有基礎性和總體性的理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實踐問題。對于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而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以唯物辯證的態度處理和對待這一關系。在此意義上,中國道路的要義就在于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圍繞發展這一主題,用“建設的邏輯”代替“革命的邏輯”,通過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充分占有和辯證否定來實現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其中,重要的是,中國道路既對資本主義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沒有采取漠視態度,同時又對資本主義文明所具有的歷史限度具有清醒而冷靜的認知。歷史事實表明,對資本主義文明采取掩耳盜鈴般的無視態度,也就無法從中汲取文明的成分使其充實、轉化并提升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環節,社會主義的發展就會喪失了必要的文明基礎;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限度缺乏深刻的把握,就會使社會主義的發展喪失應有的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從而偏離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應當說,中國道路在對待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上,在諸如計劃和市場關系等諸多方面的認識和實踐上,超越了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教條化、主觀化的知性理解,真正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觀點,體現出實事求是、內在超越的實踐哲學態度。
二是政黨、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領導全體人民開展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創造性實踐。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傳統厚重、民族多元一體、人口規模龐大且發展不均衡的國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保持國家穩定、凝聚民族精神、實現社會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必要基礎。中國道路的價值自覺就在于把黨的先進性建設與現代性社會的建構內在統一起來[5]。始終葆有社會主義的價值關懷,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具有的思想品格和文明素養。通過黨的先進性建設,引領和推進依法治國和現代性社會的建構,從而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這是中國道路不斷彰顯的價值選擇。如果說,資本主義所奉行的是物化的“資本的邏輯”,那么,社會主義所遵循的則應是人本化的“社會的邏輯”。社會與個人不是抽象對立的。在創造日益發達的物質文明的基礎上,使物質文明的發展服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價值理想,使社會的發展成為每個個人發展的內在環節和必要條件,從而把社會的發展與個人的發展辯證統一起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蘊含的社會主義關懷。中國道路的主體性力量就在于政黨、國家、社會、個人的整合與凝聚,它所形成的不是分散的離心力,而是統一的向心力。把黨的先進性建設、依法治國與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統一起來,這是中國道路實踐哲學的應有之義,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創造性成果。
三是中國文化、西方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文化三大精神資源之間的關系。以何種思想資源來支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以便為之注入先進的文化精神與文明動力,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頗費周折的價值選擇。現代中國在眾多的思想資源的辨析與取舍中,最終選擇了符合時代精神趨向的馬克思主義,由此開啟了重構世界歷史和民族命運的中國道路。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言,并不是一種先驗的可以拿過來就套用的抽象普遍性,它需要以中國化的方式重新獲得自己的現實性。唯有一種思想文化被充分地消化吸收并取得了自身的現實性內容之后,這種思想文化才能真正深入到社會現實的內在處境中并成為現實道路的內在支撐。“中國的發展道路必須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6]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在必然地蘊含著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性轉化與對西方文明的批判性吸收。中國道路的展開,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文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結合點上找到了自身新的生長點。海德格爾曾言:“一切本質的和偉大的東西都只有從人有個家并且在一個傳統中生了根中產生出來。”[7]從自身的文化傳統中汲取優秀基因,從中開顯出文化傳統的當代意義,實現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會通,從而共同融匯于中國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中國道路的文化智慧。對西方文化及其文明成果的批判性的積極占有,則使中國道路獲得了必要的思想滋養和世界性的內容。可以說,三大精神資源的相互營養與視域融合,使中國道路獲得了充盈的精神活力和辯證的思想張力,創造、生成并體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哲學智慧。
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敞開一種新的文明類型的哲學實踐
當代世界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世界歷史的重構與文明轉換的關節點上。我們看到,在世界歷史時代,現代性的全球化擴展使現代性與傳統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東方與西方、全球性與本土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矛盾關系更加緊密、更加復雜。反思世界歷史時代的根本問題,我們會發現,如今的世界歷史時代,雖然社會主義特別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修訂了資本主義的價值邏輯并頑強地彰顯了自身的存在,但是不可否認,世界歷史在總體上依然頑固地體現為全球資本主義時代。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限度由于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震蕩而日益顯現出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全球擴張,進一步放大和凸顯了西方現代性的問題與弊端。
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展開根本性批判的思想理論,它敞開了一種通向新型現代性文明類型的內在必然性。無論是當代資本主義歷經何種形式的自我調整和自我修復,都不能掩蓋其資本邏輯宰制和擴張的本質,也不能取消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走向沒落的根本性趨勢。在此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中國道路與中國智慧,逐漸顯露出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另一種現代性文明形態的新端倪。這種現代性文明形態的端倪之所以可能在當代中國產生,從根本上看,首先是中國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龐大的人口規模以及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得中國不可能也根本無法在對西方殖民體系的依附中獲得理想的發展。在今天,我們如何既能享有西方現代文明的物質生活,而又不丟掉中國文化的精神生活?一百多年的探索使我們認識到,中華文化所固有的內在整體性使得我們很難將西方文化的某一層面簡單機械地嫁接到我們的文化母體上。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叛,以及蘇聯模式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危害,使得當代社會主義中國不得不自覺地在理論建構與道路設計上,尋求和探索自主性的特色道路。此外,中國文化傳統在基因上所具有的中庸之道、辯證轉化的思想智慧,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生命精神以及協和萬邦、和而不同的價值追求,使得它具有經由傳統的再生而孕育出新的文明形態的文化底蘊[8]。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和文明碰撞中站穩腳跟并能有所創造的根基。
進入新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開啟的中國道路,正在日益實現著對自身精神基礎的文化自覺。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到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再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夢等思想話語,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表述的更新,而且在更深的層次上體現為對民族復興和文明走向的文化自覺。中國夢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之夢。實現中國夢不僅僅意味著政治、經濟、軍事的崛起與強大,更意味著在文化自覺基礎上的文明復興。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是建基于原子化的個人基礎上,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并在發展中體現出支配性、擴張性的本質和普遍主義、中心主義的傾向,那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提示的新的文明形態,則是建基于群體性自我意識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向內用力”和實現內在超越,更加關注社會共同體的共同理想,體現出整體性、和諧性的特質以及文化天下、道德世界的價值情懷。體悟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我們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展開和深化,越來越激起對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傳統的文化自覺,喚醒我們對自己民族文化遺產的自我意識和文化自信,并在時代的理解方式中重新表達和復活了我們的傳統。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在中國經過百年來的實踐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新傳統,并越來越與中華文化傳統的活的本土性元素內在地結合在一起。近年來,習近平倡導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強調的“親、誠、惠、容”理念,將實現民族振興的戰略構想與世界其他國家共同繁榮聯系起來的“一帶一路”構想等等,無不浸潤并透溢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文化智慧,昭示出一種有別于西方現代性文明的新氣象。
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世界秩序和文明圖式深度調整的世界。正如戴維·施韋卡特所言,“中國需要處理的問題有多龐雜,它取得的成就就有多偉大”[9]。在越來越復雜的世界歷史情勢下,馬克思主義哲學依然被認為是能夠有效思考當代世界根本問題的思想方式。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將引領中國新型現代性社會的建構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相信并憧憬,一種新的文明類型正日益開顯并終將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仍需更加深沉的責任擔當,需要觸及人類生存經驗和中國發展中最為緊迫、最為迷茫的根本性問題,更為準確、更加深刻地表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精神要求,在此基礎上,思辨、反思地給出民族生活的基本價值和文明發展的最高尺度,從而為民族復興進行新的存在論奠基,提供更加堅固的本體論支撐。我想,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中國化的當代使命和價值期許。
在現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具有文明重構意義的既偉大又艱巨的歷史性實踐。我們唯有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堅持不懈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成為我們有效思考當代問題的世界觀,成為我們深層的生活依據和深刻的精神支撐,成為一種新的文明類型的思維方式的基礎,才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必要的思想力量和理論信念。可以說,直至今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真正內涵和普遍意義仍然有待清晰地提煉出來。人類歷史的經驗是,生存的問題越是艱難和復雜,生存的動能和勢能越是突出和強烈,生存的碰撞越是激越和深刻,它所掀起的精神浪花也就越加壯觀和驚艷。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漫漫征途上,“在這青春化和強有力的實體性基礎上培養起哲學的發展”[10],在這發展階段的行程中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覺,這是我們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文明憧憬,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文明的活的靈魂”賦予自身現實性內容的必然要求。
[1] 張盾.“歷史的終結”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命運[J].中國社會科學,2009(1):27.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3] 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6.
[5] 鄒詩鵬.當下中國道路的三重邏輯[J].探索與爭鳴,2013(12):15.
[6] 吳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怎樣的國際視野[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11-26(2).
[7] [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下卷[M].孫周興,選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1305.
[8] 盛海英,李秀華.從趨古到創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趨古思維模式的創造性轉換[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249-251.
[9] [美]戴維·施韋卡特.反對資本主義[M].李智,陳志明,等,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88.
[10] [德]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33.
Value Consciousness and Civalization’s Vis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NG Li-sheng
(School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In current times,what kind of ideal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Consciousness should Marxism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seek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ivalization literacy and thingking tens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based on the height of thinking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need seize the strong ability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as the practice of Marxism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is time of reconstucting world hist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Marxism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more and more achieving the valu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howing the new climat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
Marxism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ractical Philosophy;Type of Civilization
2015-03-20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4ZDA009);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NCET-12-0817)。
龐立生(1971-),男,山東郯城人,東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
B15
A
1001-6201(2015)03-0015-06
[責任編輯:秦衛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