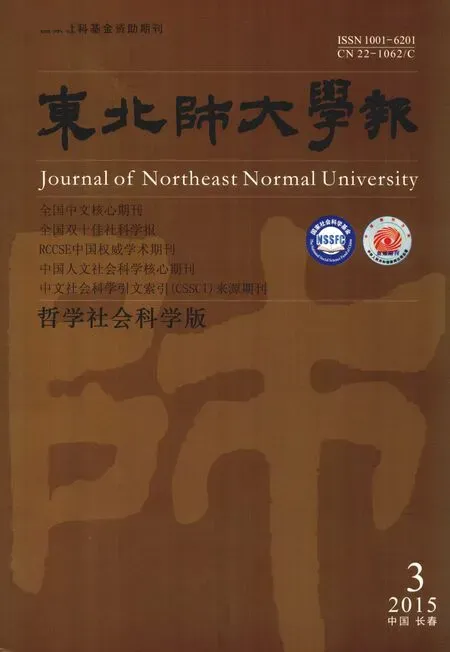被害人承諾在中國刑法中的地位分析
張 旭,蘇 忻
(吉林大學 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
被害人承諾在中國刑法中的地位分析
張旭,蘇忻
(吉林大學 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被害人承諾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通常作為損害行為的違法阻卻事由之一,它因法益的欠缺而使其獲得了存在的根據。近年來,將被害人承諾的效力從阻卻違法層次提前到阻卻構成要件該當層次的“一元論”在大陸法系國家盛行。從中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和刑法分則三個角度考察,被害人承諾在中國刑法中難以找到存在的根據。對此,應當在體系性評價的基礎上,改良或變革我國刑法中的犯罪構成理論。
被害人承諾;犯罪構成;違法阻卻事由;正當化事由
被害人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其當事人地位的回歸逐漸獲得更多人的支持,近年在我國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備受關注的刑事和解制度不僅反映了法律對犯罪人的人文關懷,也反映了對被害人作用的重視。事實上,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不僅體現在被害人對犯罪人的諒解上,在犯罪構成體系內,被害人承諾也顯現出被害人因素對犯罪成立與否的影響。被害人承諾在部分國家那里被直接規定于刑法之中,即便立法未作規定,被害人承諾在國外刑法、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中都是一個重要的內容。但被害人承諾在我國刑法中不僅沒有立法規定,在理論探討上其深度與廣度也難與大陸法系國家相比較。我國刑法的犯罪構成具有本國的特點,這樣的特點是否適合在實踐中適用被害人承諾是個必須回答的問題。
一、被害人承諾的本體展開
被害人承諾,又稱被害人同意*被害人同意與被害人承諾其實并非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是我國理論界對二者的研究其范圍大致相當。因此,在我國特定的理論背景下,二者不存在太大的差別。,在國外刑法中多有涉及。行為人在獲得權益人的承諾后實行的對權益人的危害行為,稱作被害人承諾的損害,它是指“得到有權處分某種權益的人的同意而實施的損害其權益的行為”[1]。
(一)被害人承諾在國外刑法中的地位
被害人承諾在國外刑法中被當作違法阻卻事由之一,它來源于“得承諾的行為不違法”(Volenti non fit injuria)這一羅馬法的格言。目前,被害人承諾在大陸法系國家中受到的關注更多,部分國家甚至直接在立法中規定了被害人承諾的條款,例如,意大利在其刑法典第50條作了如下規定:“經可以有效處置權利的人之同意,對該項權利造成損害或使之面臨危險的,不受刑事處罰。”而在德國、日本兩國的刑法典中雖未明確規定類似于意大利刑法典第50條的內容,但兩國的多數學者都支持將被害人承諾作為違法阻卻事由。但同樣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國,其學者卻多反對將被害人承諾作為違法阻卻事由。法國有學者認為:現代刑法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保護私人的利益,它只是通過維持社會秩序來達到保護私人利益的效果。所以,即使有被害人的承諾,如果一個行為危害了社會秩序,這種行為仍然應構成犯罪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2]。實際上,反對在法律中規定被害人承諾的學者僅僅是因為沒有認識到被害人承諾能夠阻卻行為違法性的合理范圍,被害人承諾其實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阻卻違法。“受害人的同意只排除法秩序規定法益享有人所具有的處置權以內的傷害行為的違法性。”[3]筆者認為,在劃定范圍的基礎上,將被害人承諾作為違法阻卻事由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二)被害人承諾阻卻違法的理論根據
被害人承諾因何能夠作為違法阻卻事由?對于這一問題,理論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以大陸法系兩個典型的國家——德國、日本為例,兩國學者在被害人承諾阻卻違法的理論根據方面,存在著諸多觀點。
在德國,說明被害人承諾的正當化根據大致存在三種觀點。其一,法律行為說。該說認為,被害人承諾是一種刑法意義上的法律行為,可以承認行為人能夠取消承諾者的權利,作為一種法律行為,承諾者是在行使自己的權利,該行為并不具有違法性,因此被害人承諾對于刑法而言成為正當化事由。可以說,此觀點受民法的影響較大。民法中的法律行為理論在德國極為發達,即便在今日,繁瑣的處分行為和負擔行為的二分之法仍在德國盛行。刑法借鑒民法理論彰顯了德國人的哲學思維,符合德國法學的一貫特色。其二,放棄利益說。該說認為,被害人承諾應當看作是承諾者放棄了原本屬于自己的利益,而承諾者的利益在放棄之前是受到法律所保護的法益。其三,放棄法的保護說。該說是對放棄利益說的一種延續,該說認為,被害人承諾雖然在形式上是承諾者放棄了屬于自己的利益——即法益,但在實際效果上,其實是放棄了法律對損害行為人的懲處,這就意味著放棄了法律對自己的保護[4]410。
在日本,關于被害人承諾能夠阻卻違法的根據,不同的學者同樣是有不同的觀點。大谷實教授對此進行了總結,大致存在以下三種觀點:其一,基于被害人承諾的行為,在社會上是相當的。其二,因為法益的主體同意放棄了可能處分的利益,應當保護的法益已不存在。其三,將自己決定的價值與被害法益的價值進行充分的權衡,結果是前者優于后者,因此而肯定承諾的效力。大谷實教授也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因為承諾的主體可以處分的法益是親自同意行為人對其進行侵害的,所以應當保護的法益實際上已不存在,而根據刑法理論的法益不可欠缺原則,應當認為被害人的承諾能夠阻卻損害行為的違法性,因此,上述第二種觀點是妥當的[4]410-411。
山口厚教授的看法與大谷實教授大體相同,他認為:“被害人的同意(承諾),是由于法益主體的有效同意而致法益失去其要保護性,由此犯罪的成立被否定的場合,是以‘法益性的欠缺’為理由的違法阻卻事由。”[5]151筆者認為,因為法益的欠缺而使被害人承諾阻卻損害行為的違法性的認識是比較合理的,但是我國刑法理論通說并不承認法益的概念,在我國,與法益類似的概念是犯罪客體。盡管有學者指出,犯罪客體與法益的內涵大體相當,但至少在被害人承諾阻卻違法的根據問題上,二者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區別。當行為人實行損害被害人利益的行為時,犯罪客體所認為的其背后遭到破壞的社會關系不會因被害人的同意侵害而修復。因此,被害人承諾在中國刑法中,首先在犯罪概念*雖然犯罪客體在我國刑法理論通說中不屬于犯罪概念的范疇,但它的性質卻對犯罪概念的確定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失去了能夠阻卻違法*在我國刑法中是指排除犯罪可能性或正當化事由。的基本根據。
二、被害人承諾的時代命運
如前所述,被害人承諾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的作用主要是阻卻違法。在大陸法系國家的犯罪構成結構中,被害人承諾的作用表現在第二個階段,即違法性評價階段,其是作為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外的其他違法阻卻事由而存在的。然而,目前這一現狀發生了一定的改變,主要是在刑法理論界出現了新的認識。
事實上,被害人承諾在德國的情況更為復雜。在德國,被害人承諾還可以具體區分為承諾(Einwilligung)和合意(Einverstaendis),前者與我國刑法所探討的被害人承諾的范圍大體相當。在犯罪構成體系內,被害人與行為人的合意適用于第一階段,即該當性評價階段。當被害人與行為人達成合意后,行為人的損害行為不該當刑法分則所規定的具體犯罪,即合意阻卻的是構成要件符合性,而非阻卻違法性。真正阻卻違法性的是具體意義上的承諾,這種承諾才是違法阻卻事由。承諾和合意的區分,被稱作被害人承諾的“二元論”。
被害人承諾的“二元論”不僅在德國,在大陸法系其他國家情況也大致如此。然而近年來,一種新的認識逐漸有取代“二元論”的趨勢。部分學者主張,被害人的承諾并無必要區分為承諾和合意,因為被害人承諾僅在構成要件符合性的層次才有意義。質言之,被害人承諾并不是違法阻卻事由,也不是一部分為違法阻卻事由、另一部分為構成要件該當阻卻事由,而是應當統一作為構成要件該當阻卻事由。“若是認為由于法益主體的有效的同意使法益失去了其要保護性的話,已然是法益侵害的存在本身被否定,構成要件該當性本身也被否定,這樣被害人同意就成了構成要件不該當事由。在這個意義上,被害人的同意作為關系到作為構成要件要素的結果是否存在的問題,在構成要件論中予以討論,也可以認為在理論上是更為適宜的。”[5]151這種被害人承諾的一體化適用,被稱作被害人承諾的“一元論”。可以說,“二元論”和“一元論”區別的產生,是建立在大陸法系國家三階段犯罪構成體系基礎上的,在此體系下,構成要件符合性和違法性的內涵隨著司法實踐和理論探討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才產生了將被害人承諾提前到該當性階段探討的主張。“二元論”與“一元論”究竟哪個更合理,這不是本文探討的問題。在大陸法系國家內部,二者的爭論一直持續著,不少“二元論”的支持者又針對“一元論”的批評而發表了批評,這一問題至今未形成統一的看法。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刑法中卻并不存在,這是由中國刑法犯罪構成體系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三、被害人承諾的中國境遇
前文談及被害人承諾在中國刑法中,首先在犯罪概念中失去了能夠阻卻違法的基本根據。當然,犯罪概念畢竟不是立法所強行規定的內容,下面本文還將通過三個方面的內容來分析被害人承諾在中國刑法中的地位。
(一)罪刑法定視域下的被害人承諾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最重要的原則,是現代刑法的理論基礎之一。“在我們今天,罪刑法定原則已深入人心,成為刑法的鐵則。”[6]目前,幾乎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都在本國法律中規定有罪刑法定原則*在英美法系國家,罪刑法定原則主要體現在程序法之中。,在我國自然也不例外,我國將罪刑法定原則規定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之一。眾所周知的是,罪刑法定原則最經典的表述方式為“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從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則體現了一定的人文關懷,更多地在于實現刑法的保障機能。我國刑法對于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與經典表述相近的部分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而與經典表述不同的是,我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還多了一層含義,首先強調“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對此,我國刑法理論通說的解釋為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是積極的罪刑法定,不僅實現了刑法的保障機能,也兼顧了刑法的保護機能。事實上,我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已改變了罪刑法定的最初含義,至于這種改變是否合理,這并非本文探討的問題。
在中國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背景下,被害人承諾在刑法中得不到足夠的認可。因為,刑法首先強調在法律有明文規定時,必須依照法律定罪處罰,在法律沒有規定特殊情況的前提下,行為人是無法脫離刑事制裁的。在我國刑法中,排除犯罪性的事由(或稱正當化事由)只規定了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換言之,行為人只有在符合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險的條件時,才可能阻卻犯罪的成立。當然,刑法理論中包含超法規的正當化事由,在司法實踐中也承認超法規正當化事由的存在。“刑法不可能將正當化的所有事由都規定下來,在刑法規定之外必然存在事實上被公認的正當化事由。”[7]盡管如此,超法規正當化事由的范圍依然繞不過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只有在符合刑法第101條的規定,即在其他法律中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超法規的正當化事由才能在我國得到適用的根據。基于此,一些常見的超法規正當化事由都在相關法律中找到了適用的根據,例如,法令行為和業務行為在特定的職業法律中有所規定。而作為超法規正當化事由之一的被害人承諾,卻難在其他法律中找到根據。可見,我國現行刑法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是不允許、至少是不易適用被害人承諾的規定*確切來說,是不易將被害人承諾作為正當化事由來適用。事實上,被害人承諾的作用不僅體現在這一方面,具體情況將在下文中予以闡釋。。
(二)犯罪構成視域下的被害人承諾
與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不同,我國刑法的犯罪構成體系采取四要件模式,是一種源自前蘇聯的犯罪構成體系。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犯罪的成立先經形式性的判斷,再經實質性的判斷。在我國刑法中,由于“耦合性”犯罪構成的存在,犯罪的成立在犯罪構成體系內形式性判斷和實質性判斷是同步進行的。即我國對于犯罪的認定采取一次性的判斷,由犯罪構成作為唯一的標準來認定犯罪。上文所言的“二元論”與“一元論”的區別在我國刑法的犯罪構成中并不存在,我國的犯罪構成不區分形式判斷和實質判斷,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的階段特點無法在不區分評價階段、僅是平面化形式的犯罪構成體系中體現出來。因此,被害人承諾成為犯罪構成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即它是作為認定犯罪的一個要素而存在的。
然而,問題卻遠沒有這樣簡單。即使在罪刑法定原則靈活適用的基礎上,被害人承諾在我國犯罪構成中的地位仍然是比較尷尬的,這種尷尬并非僅體現在被害人承諾這里,而是體現在我國的犯罪構成之外還有一個正當化事由的存在。根據我國刑法典的規定,即使在實踐中有限地承認了被害人承諾的合理性,被害人承諾也僅能是在法律明確規定的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之外、當作一個超法規的正當化事由來適用。言下之意,被害人承諾屬于正當化事由的范疇,而并不屬于犯罪構成的范疇。這樣一來,被害人承諾“二元論”與“一元論”的區分在我國犯罪構成中的確無意義,這不僅是因為我國犯罪構成是平面化、不區分形式和實質判斷的犯罪構成,也是因為被害人承諾在性質上根本就不屬于犯罪構成的內容。在認為犯罪構成是認定犯罪唯一標準的前提下,又在犯罪構成之外獨立設定一個正當化事由,即在完成犯罪構成的認定后,還要考察是否存在正當化事由。這與“唯一標準”的看法顯然是自相矛盾的,這種矛盾也是近年來我國學者主張變革犯罪構成理論的主要理由之一。由此可見,被害人承諾在我國的犯罪構成中并不能發揮實質性的作用,而作為超法規的正當化事由,也因為上文提及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特色性規定,使其欠缺存在的堅實根據。綜上,被害人承諾在中國刑法犯罪構成的視域下,其地位仍十分尷尬。
(三)刑法分則視域下的被害人承諾
在大陸法系國家中,被害人承諾的“一元論”主張將承諾的效力由阻卻違法變為阻卻構成要件該當,這樣的變化體現在犯罪構成體系內部各個階段涵義的改變。而實際上,單純考察刑法分則的個別罪名,被害人承諾的效力已經能夠阻卻行為的該當性。例如,在盜竊罪的場合便是如此。“在所有者的承諾之下拿去其占有下的財物的行為本來就很難說是刑法第235條*此處指日本刑法。的‘竊取’,應該解釋為不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8]仔細觀察便可看出,此時被害人承諾阻卻行為該當性與“一元論”所主張的內容并不完全相同。其實,此時的被害人承諾阻卻構成要件該當僅反映了盜竊罪作為個罪而需具備的基本要件——違反財物所有者的意愿。質言之,被害人承諾在個罪方面也并無存在的必要,因為被害人的意愿問題是由個罪成立的基本要件來解決的。
事實上,被害人承諾在國外刑法的分則中是有存在根據的。具體表現為,被害人的承諾是構成刑法分則某種具體犯罪的必備條件。例如日本刑法中規定有“承諾殺人罪”(日本刑法第202條),區別于普通的故意殺人罪。在刑法的視野內,人的生命權是無價的,因此各國的刑法理論通常認為人是不能夠輕易對自己的生命做出不負責任的承諾的。所以,在被害人承諾某行為人可以殺害自己時,該行為人依舊成立犯罪。只是獲得承諾的殺人行為其危害性要輕于未獲承諾的殺人行為,所以在日本,為區分二者不同的刑事責任,特意在普通的故意殺人罪之外,特別規定一個承諾殺人罪。承諾殺人罪的構成要件之一,便是需要得到被害人的承諾。而這樣的罪名在中國刑法中并不存在,所以,將被害人承諾作為刑法分則規定的某個具體犯罪的成立條件在我國也是難以實現的,至少當下如此。
四、結 論
通過從中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體系、刑法分則個罪三個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害人承諾的適用在我國尚存在種種的困境。但是,從世界范圍看,被害人承諾的效力無論是阻卻行為的違法性還是阻卻行為的構成要件該當性,被害人承諾對于有承諾事實的損害行為最終能否成立犯罪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基于此,我國刑法應尋求正當適用被害人承諾的路徑。這樣一種目標的實現是一個整體性的工程,不僅需要在刑法基本原則方面做出觀念性的變革,也應注重犯罪構成體系的合理性,還應注重刑法分則個罪的設定。特別是犯罪構成體系的合理性問題,因為被害人承諾畢竟最終還是作為認定犯罪的因素,而認定犯罪只有在犯罪構成體系內才是正當、合理的。一個有利于我國刑法體系的情況是,被害人承諾的“二元論”與“一元論”之爭并不會影響到我國刑法的犯罪構成。在主張保留“四要件”的前提下,將正當化事由納入犯罪構成體系內,可以保證被害人承諾在犯罪構成框架下的有效適用。而事實上,我國也有學者指出,中國刑法典中規定的正當化事由其實并非是游離于犯罪構成之外的,只是由于刑法典的編排讓人產生了誤讀。在以犯罪構成作為認定犯罪標準的基礎上,認定犯罪的過程實際已經充分考慮了行為是否具有正當化事由,即正當化事由的考察實質也是處于犯罪構成體系內的[9]。而在主張全面變革我國犯罪構成的學者眼里,被害人承諾也并不存在所處地位難以確定的困境。考察我國學者變革犯罪構成的觀點,主要有張明楷教授的“違法構成要件——責任要件”體系[10]、陳興良教授的“罪體——罪責——罪量”體系[11]、周光權教授的“客觀要件——主觀要件——排除要件”體系[12]。這些基于我國刑法特點而建立的新犯罪構成體系,對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的區分并不像大陸法系國家三階段犯罪構成那樣明顯。當然,無論是進行改良還是發起變革,啟發我們的是,對于刑法的完善,必須進行體系性的評價。例如,被害人承諾這個看似微小的要素,在犯罪構成的體系中,其地位如何是考驗該犯罪構成合理性與否的一個標準,它關系到認定犯罪的過程是否符合邏輯規律以及是否實現正義。犯罪構成的改良或變革并不僅僅是設定一個粗略的框架,更重要的是框架之下各個要素的評價順序、作用設定和思維引導。
[1] 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826.
[2] [法]卡·斯特法尼,等.法國刑法總論精義[M].羅結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371.
[3] [德]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46.
[4] 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5] [日]山口厚.刑法總論[M].付立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6] 陳興良.刑法的啟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23.
[7] 王駿.刑法中的正當化事由基本問題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2:79.
[8] [日]大塚仁.犯罪論的基本問題[M].馮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57.
[9] 車浩.論被害人同意的體系性地位[J].中國法學,2008(4):113-114.
[10] 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7.
[11] 陳興良.規范刑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11.
[12] 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04.
On the Position of Consent of the Victim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ZHANG XU,SU Xin
(School of Law,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It is usually recognized by the civil law countries that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is one of the reasons to remove illegality.The legitimacy of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comes from the lack of interests of criminal law.In the recent years,there is a mainstream view that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was regarded as elements of a crime which used to consider as one of the reasons to remove illega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nciple of legality,constitution of a crime and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we find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does not exist in our criminal law.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we should improve or change our theory of constitution of a crime.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Constitution of a Crime;One of the Reasons to Remove Illegality;the Justified Actions
2014-12-10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009JJD820004)。
張旭(1962-),女,遼寧黑山人,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忻(1983-),男,吉林撫松人,吉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D914
A
1001-6201(2015)03-0021-05
[責任編輯:秦衛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