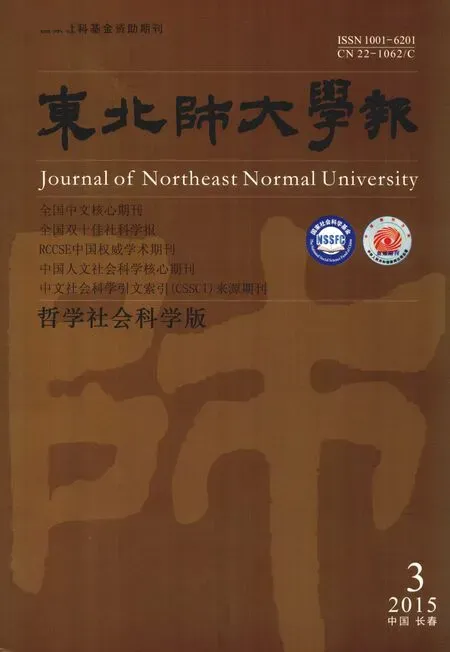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論
錢宇丹,尹奎杰
(東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
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論
錢宇丹,尹奎杰
(東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當代中國權利發展面臨著雙重文化語境,即傳統社會中自然主義的親倫文化語境和個性自由、平等法治的現實文化語境。這種雙重文化語境締造了中國權利發展話語表達的特殊方式和特殊邏輯,構成了當代中國權利發展的獨特語境。構建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的路徑是,建立穩定明確的權利發展規范體系語境,建立理性、有序、和諧的權利發展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語境,增強深化權利發展的法治參與的現實程序語境和推進完善權利發展的救濟制度保障語境。
權利發展語境;親倫文化;內在邏輯;路徑構建
權利發展,是中國當代政治發展與法治發展的主題。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的權利發展語境,理解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更好地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為權利發展創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是當前中國政治建設和法治建設的重點所在。
一、當代中國權利發展的雙重語境
(一)自然孕育的集體文化和親倫文化是當代中國權利發展面臨的傳統文化語境
從客觀上看,自遠古時代開始,中國人為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集體地開始了與自然力量的抗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集體文化,形成了以集體方式對抗自然,謀求全民族集體生存與發展的文化發展方式,形成了中華民族集體奮斗的權利斗爭方式。在這樣的文化中,某個個體的權利意識和權利訴求往往被忽視或者否定,只重視群體的、集體的訴求和意志,個人淹沒在集體之中,造就了個人與代表集體的權力中心的距離感和秩序意識,形成了長幼尊卑、等級有序的“家國”一體的政治文化秩序。在這樣的文化秩序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政治文化制度中的“宗法制度”。作為一項根本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家長在群體中,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和國家,都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成為關鍵的要素。權利不是這個社會格局中的因子,人與人之間講的不是平等,而是“長幼尊卑”和“親疏遠近”。在社會中需要促進的不是個體的權利與利益,而是集體或者整個群體的“榮辱”和“進退”。“禮”“法”是維系這種群體等級、“親疏”秩序的關鍵所在。社會上強調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講“親”、“情”、“義”、“分”。因而社會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個體權利發展的重視的文化基礎上的,相反,是對整體的禮義名節的重視的基礎之上的。例如,我國古代西周的宗法制度被視為政治、經濟、法律以及家族制度的綜合體,處于全部社會制度的核心地位[1]。這種傳統思想深刻影響和塑造中國人的個體意識和個體文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權利發展的進程。
從本質上看,集體文化和親倫文化社會呈現出差序格局的特點。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一個人可以為己犧牲家,為家犧牲族,一切價值點都以自我為中心。但是,他對族的放棄和犧牲有可能是為家庭利益,家在他看來即為‘公’,這樣的行為也不再是‘私’,從而拒絕被視為‘自我’的表現。這種道德范圍依需要而擴大或縮小的現象即為‘差序格局’,這種格局同西方世界的‘團體格局’不同,致使集體主義和親倫關系范疇內的個體在不同的場合下有著不同程度的結合[2],不可籠統地進行道德判斷,還需要運用邏輯進行梳理。
應當說,盡管中國傳統的集體文化和親倫文化對于權利發展來說是消極的,但其中也蘊含著一定的積極因素。例如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中庸思想、無為思想、泛愛思想等,均為可以發展的積極因素。
(二)個性自由、平等法治的現代權利文化是當代中國權利發展面臨的現實文化語境
權利發展的現實文化語境中,最重要的是對個體價值的重視與尊重。近些年來,中國黨和政府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權”、“以人為本”等主張和做法,為在實質上推動中國的權利發展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和制度環境。經濟體制改革同時促動了個別化利益的增長和利益的個別化,將相當活躍的利益基礎賦予原本缺乏獨立主體的法定權利;對個體資格、利益、主張給予肯定的社會評價和道德評價因思想的解放而成為可能;為謀求超越實在法制度和權利正義,人權受到更多的重視,且為以個人為中心的正義提供了動力;為使更多的權利得以真正被享有,立法盡可能將合理的愿望和利益轉變為權利,由司法機制和法律職業進行保護和實現[3]。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高度警惕西方某些國家打著“人權”旗幟,干涉他國內政的政治伎倆,應當重視從中國現實的國情出發來認識和發展中國的權利問題。把尊重個體價值、尊重個性自由、尊重個人貢獻融入社會主義集體文化之中,使集體與個人、國家與社會得到充分和諧的發展,承認個人權利實現對于整體權利發展的重要意義,這就需要締造平等、自由、公平、正義、法治、和諧的局面。
二、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的內在邏輯
(一)以人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中權利話語的獨特表達方式
這里的“人”,在政治上首先指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尊重和保障人權,就是尊重和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利和選擇,尊重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需要。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既是傳統文化語境中“民為邦本”的現代回應,更是把保障人權的實際需要轉化為執政理念的歷史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因為人權保障的主體是“人”,目標也是“人”,“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在執政之前,它是我們革命的根本理念;在執政之后,則是我們執政的根本理念。”[4]這在實質上構成了當代權利發展真實的政治基礎和話語場域,也就是說,實現權利發展和保障人權是黨執政興國的必然邏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要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實現作為中國人權的本質要求和最終體現,這也是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的基本根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促成權利發展的真實語境,實際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結果,是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從黨的執政意志上升為法律意志的必然結果,是全體中國人民意志要求的必然反映。
(二)生存權的發展是中國權利發展語境中的首要問題
沒有生存權*對生存權的理解目前已形成三種釋義:廣義的生存權,指包括生命在內的諸權利總稱;中義的生存權,指解決豐衣足食問題,即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而狹義的生存權,指社會弱者的請求權,即那些不能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穩定生活來源而向政府提出物質請求,政府有義務來滿足其請求從而保障其生存尊嚴的權利。參見徐顯明:《人權研究(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的發展,就沒有真正的權利發展。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現實的權利發展首先是人民生存權的發展。現實的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人均資源相對貧乏,曾經長期遭受外國侵略、掠奪和壓迫的國家。享有生存權,就歷史性地成為我國人民最迫切的要求。
在中國人的生存權利發展問題上,應當破除兩個認識上的誤區。一是認為只有犧牲政治上的各種權利,才能發展社會經濟權利和生存權。這種觀點的錯誤在于,它把政治權利發展與社會經濟權利發展對立起來,過分強調政治權利發展的能動作用,忽視社會經濟權利發展的重要性。事實上,經濟社會權利發展是政治權利發展的前提,人民政治權利發展是社會經濟權利的保障。只有首先實現經濟社會權利的發展,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的生活條件,“衣食足而知榮辱”,才能進一步推動政治上的權利發展。另一個誤區是,把生存權作為社會經濟權利的一種,認為只有在經濟發展一定程度以后才發展人們的生存權。盡管從生存權產生的歷史過程中,我們把它作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之外的“第二代人權”,是現代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產物,但是,在社會高度發展的今天,生存權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一個社會經濟問題,而是與政治生態、政治發展與政治文明緊密相關的權利范疇。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環境不好,人們的生存權也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生存權的發展,既是經濟社會權利發展的題中之義,也是政治權利發展的要義所在。
(三)重視集體人權、強調權利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是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中的主體邏輯
中國的權利發展,植根于當下的中國語境,不是發展“孤立的”個體權利,而是要實現全體中國人的集體人權,實現權利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強調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中的“集體人權”,就是要強調權利主體的“集體性質”、權利內容的“普遍性質”和權利本質的社會性質。對這種權利發展的強調,既是對權利主體的人格尊重的需要,也是權利發展語境所決定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社會雙重語境下的中國人格,是一種“集體人格”,是一種“類”人格,對權利主體的尊重和保護,就是對這種“集體人格”和“類”人格的尊重,這既不是簡單地對“差序格局”下緊密的人倫關系的現代改造,更不是對“原子式”個體人格的直接嫁接,而是對現代社會的中國“人”的發展的真實寫照。因為現代的中國人,已經不再是某種特殊意義上的“某些人”,其已經發展為具有“普遍的”生物意義上的“每個人”,是從“孤立的”個人,發展成為“集體的”人;已經“從生命主體發展到人格主體”[5]。
與西方文化不同,中國文化語境更容易生長出集體人權的邏輯。在差序格局的文化語境中,人們更為注重人與人之間的義務聯系,個體能否得到實在的承認和接納,取決于這個個體在集體中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義務。“人人各司其職之為正義”的一種基本含義即為個體對于集體所盡到義務的程度。中國文化語境中集體人權發展的源頭是個體對于集體所盡的義務,相對于每一個對集體主體應盡義務的個體而言,集體人權的主體有權力要求集體中的每個個體都要盡到服從集體的義務,否則個體就無法在這個集體中生存下去。
(四)強調和諧與穩定、重視權利發展的國內性與國際性的統一是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中的現實表達
和諧與穩定是中國發展的大局。在權利發展的語境上,影響和諧與穩定的因素既有來自國內的,也有來自國際的。權利發展的國內性和國際性的統一,就是要在權利發展中,從強調和諧和維護穩定的發展大局出發,正視和確認影響權利發展的各種因素,使國內社會成員和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能夠理解、認可和接受權利發展的客觀條件,推動和促進權利的主觀要求與客觀進步的統一。
中國權利發展語境中,當現實的社會條件尚不具備時,就亟須發展現實的社會生產條件,推動社會進步,帶動權利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把權利的發展與國內法律完善和國際法律接軌相聯系,高度重視權利發展的國際形象,重視國內公民與外國人、外國企業的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權利,實現中國人與外國人在國際法律地位上的同步的權利發展,重視權利發展的國內性與國際性的統一,應當是未來中國權利發展的基本方向。
(五)強調人權在法律上的權利性與義務性的統一是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的要害所系
權利發展語境中,人權的要害在于法律。也就是說,權利發展的根本在于人權在法律上獲得了多少的認可和尊重。一方面,作為法律規范層面(實然)上權利義務的統一體,人權獲得多少法律上“權利化”的資格,也就意味著有多少的義務被規范和確定下來,權利的發展也就意味著法律上義務的發展,否則就談不上人權的任何進步。
另一方面,權利發展語境中人權的進步,所體現的價值層面(應然)的意蘊是,法律應當“以權利為本位”。盡管我們在現實的法律中強調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性、等值性,是法律上權利發展的要害所在,但是我們強調人權在法律上的這種聯系,并不妨礙法律在人權保障和權利發展語境中的價值表達。這種表達恰恰是,法律應當以“權利”為核心,否則現代法律就無法體現出人權的精神和價值,就無法構筑出理想的法律圖景。
在權利發展語境中,人權法律化問題上堅持權利義務的統一性,意味著人權這個“權利要素”,“其中包括人身人格權利、政治權利和自由,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等。人權有多種形態,例如,應有權利、法定權利、習慣權利和現實權利等。”人權問題上對權利要素的堅持,仍然要堅持與義務性要素的平衡,“不能就人權論人權,不能用某類某種人權排除其他人權,不能只主張主體的權利和自由,而忽略主體的義務和責任”[6]。因此,強調人權問題上權利性與義務性的統一,才是權利發展語境中的要害,它既構成了法律上權利發展的內容性要素,也是權利本位價值觀念的必然反映。
三、構建當代中國權利發展語境的路徑選擇
(一)建立穩定明確的權利發展規范體系語境
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是國家權力的功能和義務這一基本原則既是基本權利固有內涵的內在規律又是憲法規范發揮作用的邏輯原點和基本目標。憲法權利運行塑造的憲法權利文化,構成了憲法權利價值體系的現實基礎[7],而民主政治理念逐步深化,借助公權力建立平等、自由、人民主權的沖突管理機制和社會秩序已經成為公民普遍的認知和訴求,尤其在對自身合法權益的保障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局限于普通法律保護的范疇,更應重視憲法在權利保護方面可以且應當起到的重要作用,通過憲法對各項基本權利進行確認,進而使公民基本權利和“憲法是權利的憲法”理念同時得以充分實現。
當然,強調憲法的重要意義并非對部門法的功能加以否定或取代。和部門法相比,憲法對于公民權利的規定具有一定的指導性和框架性,并不涉及具體的規定。反之,部門法也無法代替憲法在權利保障方面起到的作用,但由于部門法本身在基本權利保障方面的具體內容尚不完善,導致已然經過憲法確認的公民基本權利并沒有完整體現在部門法的具體規定中,在司法實踐中自然無法實現部門法的保護作用,形成基本權利的虛置狀態。
(二)建立理性、有序、和諧的權利發展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語境
權利的發展有賴于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與政治法治發展的同步推進和全面提升。當前,盡管我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和相對完善的社會主義文化,但是在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法治文化、特別是權利文化方面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尤其是把權利發展置身于這樣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之中的語境和條件尚未完全具備,亟需在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中融入權利發展的基本要求,使得法治建設過程中權利發展與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同步[8]。因此,在當前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完善過程中,首先應當把保障人們享有相當數量和質量的權利列入法治建設的整體規劃和制度設計之中,通過憲法和相關法律的完善來逐步實現人們在權利發展上的制度保障,并在現實的執法、司法和法制監督過程中賦予人們更多的權利救濟和權利實現機會,建立和健全一個保護和保障既有權利的社會環境和法律機制,使權利發展能夠在公平、合理、和諧、公正的社會文化氛圍中得以充分實現。
(三)增強深化權利發展的法治參與的現實程序語境
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深入,“開門立法”*強調“開門立法”,不僅應當充分傾訴公民的意見,還應設定民意汲取的法定程序,使公民表達中的合理部分最終得以體現在法律中,才能為法律的順利實施消除潛在障礙,同時提升公民對法治的信任和信心。的概念逐步確立,公民的參與權日益得到重視,為立法過程中的民主化實現提供了條件。以參與領域進行區分,目前我國公民立法參與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同民生息息相關的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從醫療條件的提升、教育資源的公平享有、食品和藥品安全的保障、住房問題的改善、霧霾治理和整體生存環境質量的提高、社會秩序的法制維護、新型犯罪的法律規制等方面延伸到對整個民生問題的關注,既是社會發展的熱點問題,也是公民法治觀念中需要借由法律手段加以解決的難點問題。事實上,在當代法治社會,公民具備規則制定的參與者和規則的遵守者雙重身份,強調公民的法治參與既是權利平等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公正的體現方式之一,能夠保證法律規則更加符合理性、公平的內在規律以及人權和社會發展的訴求[9]。反之,如果法治參與權利長期遭受冷遇將引發公民對政府的認同危機,認為自身的正當權利被立法機關邊緣化,進而出現逆反心理并采取一定的手段表達異議,而公民的表達通常以非制度化、沖突化的方式體現,不但無法理性地解決問題,還會造成社會多方利益的損失,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同樣置于民主性和理性之間關系的視域內,同行政環節更為強調理性的正當性相比,立法環節更為強調民主的正當性,政府負有保證在形成民主的過程中各種理性因素得以實現的責任[10]。因此,公民基本權利的發展問題體現了政府、公民以及所有社會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互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公民本身應當是法治建設的主體之一,同時也應當受到法定程序的指導和約束。
(四)推進完善權利發展的救濟制度保障語境
從立憲主義的精神來看,對抗公權力是公民基本權利的重要功能,防止公權力對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進行不合理的侵犯,維護公民的利益免受政府的恣意干涉[11]。我國憲法關于基本權利原則和內容的規定同樣對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影響,這意味著如果憲法的政治性被過度強調,其法律性仍然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無法成為案件審理的依據,將導致公民受到侵害的、尚無具體部門法條款進行規制的部分基本權利形成無法可依的局面。另外,較為完備的違憲審查制度及相應的救濟機制依然從缺的現狀也導致公民很難在上述情況發生時獲取有效的訴訟和維權途徑,或將導致侵權損害進一步擴大。換言之,憲法有關規定無法在司法領域得以貫徹直接導致了憲法權威的減損及憲法直接約束力的降低。憲法的直接約束力能夠保證國家機關能夠直接適用該法的具體內容,并作為裁判公權力是否合憲的重要依據,旨在調整國家機關之間或公民與國家機關之間的關系,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違反憲法的行為均為無效。但是,最高法律效力原理并未推動我國違憲審查制度的構建,仍需以憲法的司法實用性為前提,以憲法的直接法律效力為依據,方可將違憲審查機制引入法律體制之內[12]。綜上所述,現行的司法制度在憲法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和救濟方面依然存在較大的調整空間,探尋司法審查機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賦予公民憲法層面的救濟方式,同時兼備現實意義和必要性,只有通過司法權力對公民的憲法權利進行保障,方為真正意義的保障。
[1] 王占通.論宗法制度是適用于西周全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J].社會科學戰線,2009(9):180.
[2] 費孝通.鄉土中國[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2-41.
[3] 夏勇,主編.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公民權利發展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38.
[4] 陳淅閩.馬克思主義執政理論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78.
[5] 徐顯明.人權主體之爭引出的幾個理論問題[J].中國法學,1992(5):36.
[6] 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408.
[7] 劉茂林,秦小建.論憲法權利體系及其構成[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1):40.
[8] 陳紅巖,尹奎杰.論權利法定化[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77-81.
[9] 陳金釗.詮釋“法治方式”[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1-7.
[10] 楊利敏.論現代政府體系的理性[J].學習與探索,2012(10):47.
[11] 張翔.論基本權利的防御權功能[J].法學家,2005(2):65.
[12] 朱福惠.違憲審查制度的法理基礎——論憲法對立法權的限制和約束[J].廈門大學法律評論,2003(1):269.
The Contextualis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ights Development
QIAN Yu-dan,YIN Kui-ji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117,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rights is faced with double contexts,that is,the context of the traditional naturalistic household-ethic culture and the realistic cultural context of freedom,equality and legality. These double cultural contexts create the particular pattern and logic of the expression in Chinese rights development and constitute the particular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rights. The routes to construct Chinese rights development context are as follows: establish a stable and specific context of a standardized rights development system,build a rational,ordered and harmonious context of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rights development,improve the context of standardized system of rights development that law participates in and completes the context of rights development of relief system security.
Rights Development Context;Household-ethic Culture;Internal Logic;Route Construction
2014-11-10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4BFX030);吉林省科技發展計劃項目(20140418038FG);東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13QN048)。
錢宇丹(1984-),女,吉林長春人,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尹奎杰(1972-),男,吉林東豐人,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
D920.0
A
1001-6201(2015)03-0026-05
[責任編輯:秦衛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