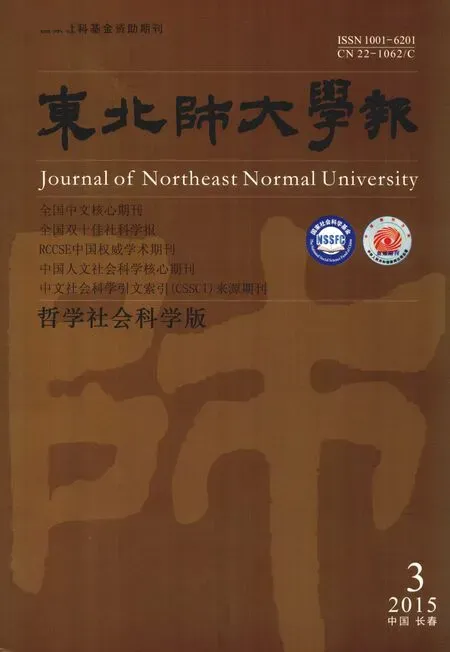論“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出場形態
孫 全 勝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
?
論“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出場形態
孫 全 勝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是在對蘇東劇變后的當代社會現象及其倫理意識的批判、審思中出場的,其中蘊含著德里達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的致敬和復歸,對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現象的批判和對理想生活情景的建構。它作為貼近現實生活的批判理論,有著自身特定的出場形態: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復歸決定了其生成邏輯;對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現實及其倫理意識的批判表征了其批判維度;批判倫理追求理想生活的本性彰顯了其倫理主張。“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我們學會更好地生活有真切的現實價值。
德里達;批判倫理;出場形態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就是德里達處于蘇東劇變后的時代背景中,用解構的策略對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現象及其倫理意識進行批判、審思的學說。它的考察對象是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的不合理現象,它的出場宗旨是倡導人們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以創建關切、親和、寬恕的理想生活。德里達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反教條、反封閉的倫理意識形態。這不僅對于瓦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有推動意義,對于實現理想生活,也起著重要作用。
一、“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生成邏輯:為何向馬克思批判精神致敬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生成邏輯就是“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本身的歷史生成過程。“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的演化遵循著特定的出場軌跡。它作為一種反映蘇東劇變及其后時代的后馬克思思潮,其生成邏輯既呈現了蘇東劇變及其后思想潮流對解構主義的影響,又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和解構內在批判邏輯的契合,還蘊含了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由“回避”轉向“致敬”的自身思想演變。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生成深受蘇東劇變及其后思想潮流的影響。隨著蘇東劇變的發生,國內外學者掀起了一股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潮流,德里達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的解讀也深受這股潮流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前,德里達對馬克思及其共產主義思想始終采取回避的策略。然而,蘇東劇變讓德里達的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他非但不再避開斯大林和共產主義的話題,而且公開論證馬克思批判精神的時代價值。“我們也許會問,為什么德里達這個本質上疑心重重的思想家會關注馬克思,因為馬克思的著作在整個20世紀幾乎快變成不容侵犯的教條。”[1]德里達選取在“共產主義運動退場”之后,竭力論證馬克思批判精神的價值,亦是解構邏輯的進一步展開。因為解構的策略之一就是要在歷史的遮蔽處尋找價值。
自身內在的批判邏輯也讓德里達最終走向了馬克思批判精神。“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既是德里達解構策略的應有之義,也是他在共產主義運動受挫之后向馬克思批判精神致敬的必然產物。這無疑是德里達解構思想的重要轉折。德里達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為何由回避轉向致敬?“德里達之所以從解構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這是由解構主義的內在邏輯,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功能以及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似的政治學維度決定的。”[2]解構本身是一種批判傳統思維模式的思潮。德里達的批判不是無病呻吟,也沒有所謂的“德里達達主義(Derridadaism)”。[3]因此,解構也具有政治意識形態作用。總之,德里達的解構思想就是在對傳統思維模式的批判中出場的。
德里達自己察覺到了解構缺少實踐的維度,這讓他走向馬克思主義。他聲稱,“馬克思的修辭學或教學法遠不是一種便利的表達方法,在那里,性命攸關的東西似乎是——從一方面說——幽靈的不可簡約的特殊特征。”[4]142這一點與解構的策略具有同質性,但它們在理論宗旨上是天差地別的。解構更多的是一種批判二元對立思維的策略,而馬克思主義的宗旨卻是毀滅現存的一切不合理制度,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美國學者麥柯·瑞安指出:“解構理論是對一些主要的哲學概念和實踐的哲學質疑。馬克思主義恰恰相反,它不是一種哲學。”[5]因此,他反復提醒人們要重視馬克思的實踐精神,“只要對馬克思的指令保持沉默,不要去譯解,而是去行動,使那譯解[闡釋]變成一場‘改變世界’的變革,人民就會樂意接受馬克思的返回或返回到馬克思。”[4]14這可能是德里達面向馬克思實踐精神的真誠審思,在共產主義“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他看到了解構的乏善可陳之處。
馬克思批判精神蘊含的解構元素如同強大的磁極,牽引著德里達向馬克思批判精神致敬。馬克思解構了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思辨性,并聲稱思辨哲學與唯物主義勢不兩立,“我的辨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6]馬克思抓住了實踐這一環節,把哲學改造為變革現實的科學理論。海德格爾認為,馬克思通過對傳統邏各斯中心主義中存在和意識關系的顛倒,終結了形而上學哲學的發展軌跡,“隨著這一已經由卡爾·馬克思完成了的對形而上學的顛倒,哲學達到了最極端的可能性。哲學進入其終結階段了。”[7]伊格爾頓亦聲稱,馬克思政治學說對德里達有強大的吸引力,“馬克思主義不僅以它的邊緣位置吸引著德里達,而且由于替代它的那些政治學說淡而無味,所以對德里達的吸引力就更大了。”[8]因此,是解構的內在批判邏輯和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功能使二者在后現代工業社會“傾心相交”,激勵德里達決心要庇護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的生成還蘊涵了德里達自身思想演變邏輯。德里達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始終未像同時代的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那樣癡迷于“左”派思想和“文化革命”,更沒有像阿爾都塞和列斐伏爾那樣一度與法國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他始終注意保持著對馬克思及其共產主義運動的疏離。抱有這樣的態度,德里達此階段沒有走進馬克思的文本,他對馬克思存有偏見。在他的印象中,馬克思批判思想繼承于黑格爾,仍然局限于傳統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藩籬。而解構主義的主要立場就是反對傳統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思維模式,因此,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遲早也要接受解構的洗禮。于是,德里達有意或無意地避開馬克思及共產主義話題。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德里達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由回避轉為親近,由拒斥轉為接受。在此期間,他關心時事政治,頻繁在媒體露面。他開始發現馬克思批判精神在諸多方面與解構主義的策略能夠交融,他在不同場合也屢次提及馬克思及其文本。蘇聯解體之后,德里達直接走進馬克思批判精神,與馬克思開始了正面交鋒和對話。他用解構的策略闡釋馬克思批判精神,提出了所謂“共產主義運動退場”后,如何繼承馬克思批判精神的“題目”。這在一定意義上表明了解構主義向馬克思批判精神的復歸。因此,“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為時已晚的整合”[4]84,而是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的致敬和推進。
二、“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維度:何以批判發達工業社會
在德里達看來,蘇東劇變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悄然開始。這個新的時代與馬克思當年所處的時代究竟有何變化?“這是一個脫節的時代。這個世界出毛病了。”[4]76德里達借用哈姆雷特的內心獨白,給蘇東劇變后的脫節時代下了斷語。在德里達看來,人類社會并沒有實現完全的正義和公平,當代發達工業社會更沒有勝利,而是處于全面危機之中。各種衰敗使這個時代完全喪失了原則,偏離了正常的軌道。為此,他批判了發達工業社會的不合理現象及倫理意識。
德里達批判了單調、貧乏和封閉的日常生活秩序及倫理意識。蘇東劇變及其后的時間,社會主義國家紛紛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在經濟上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在政治上則建立起民主政治體制,而發達工業社會不但克服了金融危機而且憑借著全球化運動向整個世界闊步前行。聲稱要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無產階級運動遭受重創,而高舉自由和尊嚴、“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的革命的作用”[9]的發達工業社會卻欣欣向榮。對此,德里達清醒地指出:發達工業社會的繁榮只是表面現象,它內部隱藏著深刻危機。人類并沒有隨著工業社會的全球化運動而實現理想社會,資本引發的各種危機和災難仍舊普遍存在;社會陣營的冷戰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發達工業社會卻產生了新的矛盾和對立。發達工業社會把生產力的發展、財富的增長當作目的,而把人的需求當作手段。資本使人從屬于物,成為物的附屬品。因此,發達工業社會非但沒有實現普遍繁榮,而是處于全面危機當中。
德里達講述了蘇東劇變后日常生活被資本控制,造成新的思想奴役的故事。蘇東劇變標示了冷戰的結束,但沒有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時代衰敗的背后推動力量是資本利益。受利益驅動的虛假宣傳鋪天蓋地地向人們涌來,讓人們目不暇接。發達工業社會拒斥多元,掩飾真相,熱衷操控,試圖用利益迷惑人們的內心,這讓良知沉默、欲望膨脹。發達工業社會利用媒介傳播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而解構就是要揭露這種偽意識形態存在的真面目。由于生產技術的進步,資本的運行在不斷擴大空間范圍,形成資本的全球化運動。資本的全球化運作,縮短了商品生產和流通過程,形成了統一市場。資本的高速運行,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正當需求,而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引起了地區的不平衡發展,不僅破壞了環境,而且導致了社會混亂,“這一不平衡的新自由主義化的復雜歷史中,一個持續的事實就是普遍存在一種趨勢:擴大社會不平等,并使社會中最不幸的成員越來越受邊緣化的悲慘命運。”[10]
因此,發達工業社會正處于深刻的危機當中,暴力斗爭和種族歧視仍然普遍存在。
德里達倡導自由、開放和多彩的日常生活狀態,號召人們勇敢正視現實,謀求真實幸福。他認為,要消除發達工業社會的異化狀況,必須讓日常生活回歸真實。在他看來,揚棄工業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除物質生產與生活的壁壘,讓自由多元的能量成為改造生活的動力。他主張,喪失主體自由選擇意志的個人必須重啟想象力,化被動的支配地位為主動的批判行為。因此,解構的使命已經不是打碎資本加在人們頭上的枷鎖,而是直接摧毀迷人的資本景象。解構就是要揭露歷史的遮蔽處,關注不在場的在場者,“要正義,我們的原則就必須尊重不再或尚未存在的他者。”[11]解構就是要擊碎日常生活布展的凝固性,顛倒資本意識形態的頭尾倒置,建構真實的日常生活情景。解構是日常生活開出的思想之花,如果日常生活敗壞,那解構也必定失敗。因此,德里達從日常生活尋找未來理想的源頭,他要求精心地建構符合生活的情景,創造具有差異的情景性。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是馬克思社會批判倫理在當代的出場,它的目的是喚起人們對暴力、專制的抵制和對公正、自由的期望。德里達認為,在發達工業社會,以往主體對客體的操控那種狀況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人們面對的是一個已經完成的世界,剩下的只是已有事件的重復。發達工業社會讓人們尋求即刻的欲望滿足,整天處于欲壑難填的境地。資本摧毀了傳統的倫理道德,人們要求的是欲望的即時實現。“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盛行著一種舒適、平穩、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現象,這是技術進步的標志。”[12]資本造就了邪惡、混亂而低能的生活地獄。個體自主的選擇被大眾盲目的跟風取代。發達工業社會培訓出無理性的機器人,讓人們喪失良知,失去判斷真假的能力。德里達認為,資本生產導致了人的迷失,人們必須拒斥資本,回歸真實。德里達期望通過回歸真實生活解放麻木的人群。
總之,德里達聽從正義和內心良知的引領,用超現實的倫理夢境批判現實日常生活,大聲控訴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奴役。由于共產主義運動的退場,德里達——這位激進而高尚的哲人,走出書齋,參與政治,為處于社會邊緣位置的馬克思思想做起了辯護。盡管明白傳統倫理思維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可他不會放棄批判的腳步,狂熱地解構一切。“解構實踐著一種自我毀滅的模式,這種模式使得解構如同一張空白頁那樣無懈可擊。”[13]在德里達看來,我們處于一個狂躁不安的時代,各種“幽靈”糾纏不清,各種鬼怪混戰不已,使它完全偏離了正常軌道、混亂不堪,這就是他論證馬克思批判精神具有時代價值的主要圖景。
三、“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倫理主張:如何學會更好地生活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出場形態還體現于其倫理主張:學會更好地生活。“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并非一種僵化的立場,它的寬恕精神和給予原則,讓它帶有悲世情懷和救世愿景,處處彰顯著對平等、自由、人權、尊嚴、良知、寬恕等的渴求。在生存的目的達到后,生活得更好就成了進一步追求的目標。德里達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展示了“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倫理主張:如何更好地貼近社會實踐,以便指導人們實現理想生活。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彰顯著清晰的倫理氣質。它秉持人道主義精神原則,探討了向馬克思“幽靈”中正義學會理想生活的路徑。“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強調倫理學和政治的緊密結合。德里達晚年愈來愈關切現實政治的災難,他不僅用寬恕思想,號召消除專制暴力和種族歧視,而且直接用行動表達對“新國際”的渴望。德里達聲稱,“喚起記憶即喚起責任”[14],他在此時走進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喚起人們對正義和良知的渴望。在他看來,盡管馬克思“幽靈”借以在場的蘇聯共產主義制度已經消解,但是“幽靈”的靈魂——正義精神卻將繼續指導人們建構理想生活。德里達指出,通過與死亡對話理解生存的價值是我們現實必經的道路。只要生命還在繼續,就應該向死亡學習。追求美好未來,從希望開始,“某個人,您或者我,走上前來說:‘最終,我當然希望學會生活’”[4]1接著,德里達就開始了對這個人生命題的解析與論證,他將目光聚焦于這個命題的時間限定:“但為什么是最終?”[4]1單借人類的力量無法理解生存的全部意義。也就是說,人類有認識局限,無法感知生命的一切,必須向“他者”且是憑借記憶才能通達生命的真諦。
德里達在一系列的追問后,做出論斷:要學會更好地生活,只能進入生與死之間,與游蕩在生死之間的鬼魂展開對話。“因此,在生與死之間,實際上就是常常假裝公平地言說的警句指令之所在。”[4]2而且只有與鬼魂交流才能理解生存的意義。我們務必遵循鬼魂的指令。幽靈如同具有靈性的意志一樣,我們務必遵循它的運行軌跡,并視需要,或對其尊重,或對其抵制,或與之和解。經過思考與探尋,德里達聲稱,我們要與之交流的鬼魂其實早已退場。我們不禁詫異:這個沒有出場就退場的鬼魂,它究竟“在哪里?”“明日在哪里?”“向何處去?”[4]3悖論產生了,這個悖論就是:什么東西過去沒有出場過,但將來必定出現?而這個東西之所以在將來會出場,是因為過去和現在的時空斷裂。正義就是將來必定出場的東西。正義的到來,不需要特定的的時空,它只有形式。因此,德里達所謂的那些“既不在場又無生命”的幽靈,其實是正義等價值法則。我們要實現美好生活,就必須接受這些價值法則的指引。
在德里達看來,實現美好生活必須依靠榜樣的指引。經過反復思考,他指出了我們學會更好地生活的參照對象:馬克思的“幽靈”。因此,德里達與“幽靈”的對話與交流,也就轉化為“在生死之間怎樣生活”的思索,而思索的直接指向就是學會更好地生活。在日漸衰敗的時代,德里達以沉重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決心承擔起教化人心的重任。他要承擔的倫理義務就是:在馬克思批判精神的引導下,呼吁人們秉持正義和良知[15]。馬克思的“幽靈”是諸多倫理精神的集合產物,也就是說,馬克思的“幽靈”展現著倫理精神,分有著倫理精神,它借助倫理精神構成其骨架。所以,馬克思“幽靈”是倫理精神的肉體形式,是倫理精神表現自己的媒介和工具。在這個混亂不堪的時代,以馬克思“幽靈”中的正義為倫理法則,才能保持內心的寧靜。馬克思“幽靈”中的正義具有“彌賽亞”色彩,體現著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德里達看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不僅不是空洞乏力的理論假說,而且還深入了歷史和現實,“沒有什么看起來能比位于《馬克思的幽靈》核心處的彌賽亞性和幽靈性離烏托邦或烏托邦主義更遠的了。”[16]因此,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將繼續指引人們批判傳統和現實。
“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倫理主張絕不是無關痛癢的,也不是消極無用的,而是基于責任意識的積極思考。德里達啟發我們要擺脫僵化的倫理判斷,掙脫偏執和誹謗,達到真正的理解和對話。通過批判發達工業社會,德里達的批判倫理思想彰顯出了橫跨當代生活的積極價值,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反權威、反封閉的價值法則。德里達的批判倫理雖然沿襲了其解構的基本方法與策略,但兩者還是有很大異質性的,并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只是一種詭辯式的胡言亂語。他的批判倫理很注重思想的實踐性、應用性,而其解構理論更多體現了思想的批判性、多元性。“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既不屬于哲學門類,也不屬于文學學科,但實際上,“無論在哲學界還是文學界,現在沒有一個思想家可以忽略雅克·德里達的作品。”[17]而“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倫理主張就“體現于其兩歧性的文本和多重性的思想語境。”[18]
概而言之,“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倫理主張就是要打破傳統倫理形態對日常生活的禁錮。德里達既撕下了傳統倫理形態的偽善面紗,又暴露出發達工業社會的頹敗趨勢,從而在批判傳統和現實的基礎上,把倫理形態的發展邏輯指向未來。德里達啟示我們要打破專制和暴力,激發內心的激情與良知。“解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開辟了新的思維空間,開啟了人們思考當代政治問題的一個新的視角。”[19]因此,“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是具有積極價值的,它的價值就是消解傳統倫理形態,回歸本真的生活。“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僅開啟了一種馬克思主義新的解讀范式,而且為我們實現理想生活指明了道路。
[1] [英]斯圖亞特·西姆.德里達與歷史的終結[M].王昆,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73.
[2] 岳梁.幽靈學方法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
[3] Heinz Hartmann.Saving the Text: Literature/Derrida/Philosoph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33.
[4] [法]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M] 何一,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5] M.Ryan.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M].Baltimore and London,1982:1.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12.
[7] [德]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M].陳小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59-60.
[8] [英]特里·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M].馬海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122.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10] 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16.
[11] [英]克里斯蒂娜·豪維爾斯.德里達[M] 張穎,等,譯.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187.
[12] [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張峰,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3.
[13] [英]特里·伊格爾頓.沃爾特·本雅明[M].郭國良,陸漢臻,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5:180.
[14] [法]雅克·德里達.多義的記憶——為保羅·德曼而作[M]. 蔣梓驊,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1.
[15] 宋曉杰.政治的馬克思何以可能?——自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58-65.
[16] [法]雅克·德里達.友愛政治學及其他[M].胡繼華,譯.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38.
[17] Jim Powell.Derrida for Beginners[M].New York: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1997:89.
[18] 孫全勝.兩歧性與多重性:德里達解構思想的出場形態[J].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43-52.
[19] 荀泉.德里達“解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述評[J].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27-32.
The Appearance Pattern of “Deconstruction Marxism”
SUN Quan-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89,China)
The theoretical formation of “Deconstruction Marxism” was produced in th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phenomenon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tremendous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in which contains Derrida’s salute and recurrence to the critical spirit of Marxism,the criticism to the phenomenon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in indus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life. As a critical theory close to life,it has its particular configuration: the recurrence of classic Marxism critical spirit determines its generative logic;the criticism to the reality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developed industry characterize its critical dimension;the natural character of critical ethics to pursue an ideal life manifests its ethical proposition. “Deconstruction Marxism” has a distinct realistic value for us to move in a better life.
Derrida;Critical Ethic;Appearance Pattern
2013-12-15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2BZX078);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8JA720004)。
孫全勝(1985-),男,山東臨沂人,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A811
A
1001-6201(2015)03-0044-05
[責任編輯:秦衛波]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