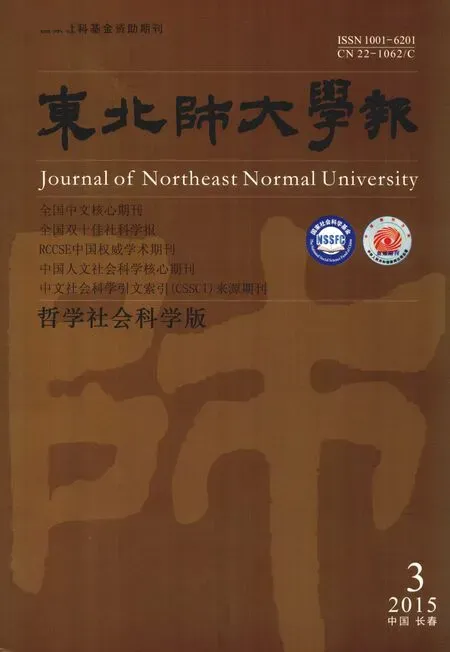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協(xié)和運動》的刊行歷程與“滿洲帝國協(xié)和會”的輿論導向
王紫薇,陳秀武
(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
《協(xié)和運動》的刊行歷程與“滿洲帝國協(xié)和會”的輿論導向
王紫薇,陳秀武
(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協(xié)和運動》作為“滿洲帝國協(xié)和會”的機關雜志,在思想教化領域發(fā)揮輿論導向作用,為殖民政治服務。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刊的輿論導向追隨政治風向標而發(fā)生偏轉。《協(xié)和運動》輿論導向的前后變化,標記了協(xié)和會運動的變遷和日本殖民政策的演變。
《協(xié)和運動》;協(xié)和會;輿論導向
協(xié)和會成立伊始便試圖在東北地區(qū)普及其建國理念,1936年變身為“滿洲帝國協(xié)和會”(下文簡稱協(xié)和會)后,作為“滿洲國”唯一的思想、教化、政治的實踐組織體,它強化了從意識層面對東北民眾的統(tǒng)治。其機關刊物《協(xié)和運動》成了為殖民當局張目的工具。在二者的關系中,殖民當局將自身的思想體系輸出至教育對象,即“滿洲國國民”,使其全盤接受殖民思想。《協(xié)和運動》作為思想教化的重要媒介,從內容、形式到發(fā)行渠道被殖民者牢牢掌控。本文擬以《協(xié)和運動》雜志為中心,從其不同時期的特點入手,探討日本殖民者在“滿洲國”推行的政策以及太平洋戰(zhàn)爭前后宣傳方針的變化等。
一、《協(xié)和運動》的發(fā)行與分期
作為機關雜志,《協(xié)和運動》并不是從協(xié)和會誕生之始就創(chuàng)刊的。《工作月報》和《協(xié)和會志》是《協(xié)和運動》的前身。《工作月報》創(chuàng)刊于1935年12月,共發(fā)行7冊,1936年6月因協(xié)和會改組的關系停刊。待于1936年8月重新印發(fā)之際,《工作月報》更名為《協(xié)和會志》,由當?shù)毓ぷ魅藛T執(zhí)筆。后來《協(xié)和會志》也經歷了休刊[1],再次發(fā)刊時以《協(xié)和運動》一名刊出。
《協(xié)和運動》1939年9月創(chuàng)刊,1945年7月停刊,共發(fā)行7卷73號。戰(zhàn)后經由綠蔭書房采用現(xiàn)行古舊文獻的基本整理方式,于1994年陸續(xù)發(fā)行復刻版。即在現(xiàn)有資料基礎上重新編卷,根據(jù)原版大小按比例縮印,一般采用單色印刷,同時編著別冊,收錄解題、總目錄和執(zhí)筆者姓名索引等。復刻版由20卷構成,另加別冊。受時局影響真正保存下來的僅有68號。復刻版整體文字量粗略估算830萬字左右。
《協(xié)和運動》歷經6位編輯兼發(fā)行人,他們分別是半田敏治(1939年9月—1940年2月第1號~第6號)、柏原清喜(1940年3月—1941年9月第7號~25號)、櫻井信義(1941年10月—1942年1月第26號~29號)、阪本政治(1942年2月—1943年6月第30號~第47號)、坂野龜一(1943年7月—1944年5月第48號~第(誤)49號)、佐藤巖之進(1944年6月—1945年4月第(誤)50號~第(誤)60號)。
作為月刊,《協(xié)和運動》的印刷時間基本為當月5日,發(fā)行時間為當月10日。印刷工作在不同時期分別由村上印刷所、中央印刷社、杉田印刷社、東亞印書局4家完成。《協(xié)和運動》每期頁數(shù)通常在140—180頁之間,其中頁數(shù)最多的分別是1940年第1號和1943年第8號,均為236頁。從1944年開始,每期雜志頁數(shù)銳減,均未超過百頁,頁數(shù)最少的是1944年第2號,僅有72頁,并且由該期始雜志開本也由“菊判”轉變?yōu)椤八牧杜小?“菊判”和“四六倍判”均為日本書籍開本規(guī)格,分別約為150 mm×220 mm,188 mm×254 mm。[2],價格也一路飆升,從創(chuàng)辦之始的30錢,提升至50錢,到1945年1月上漲為80錢[3]。
協(xié)和會在1939年的工作中,提出“中央指導機關雜志發(fā)行計劃方案”,規(guī)定《協(xié)和運動》的基本任務是“加強各級本部工作人員和會員之間建立在會務運動基礎之上的同志情誼,提高其人格、見識和技能,同時對于在這些同志的指導下所開展的協(xié)和會運動應該能從思想、認識、行動方面保證統(tǒng)一性”[4]。根據(jù)刊物登載的內容、執(zhí)筆者以及國際局勢變幻與協(xié)和會輿論導向變化等實際情況,將《協(xié)和運動》的發(fā)展脈絡劃分為三個時期:
(1)第一卷第一號(1939.9)到第二卷十二號(1940.12)為第一期。協(xié)和會自身處于精銳主義和大眾組織相互沖突、矛盾、糾結的狀態(tài)。
(2)第三卷第一號(1941.1)到第四卷第十二號(1942.12)為第二期。協(xié)和會經歷戰(zhàn)時體制改革,完成與政府的一體化進程,進入全方位配合階段。
(3)第五卷第一號(1943.1)至第七卷第四號(1945.4)為第三期。戰(zhàn)爭頹勢已現(xiàn),協(xié)和會開始探索獨立發(fā)展的道路,再次強化其思想教化作用。
對《協(xié)和運動》的分期參考前人研究成果,以基本歷史時間為區(qū)分點[5],同時在每一階段內依據(jù)代表性的歷史事件進行細致劃分。以下筆者將按照上述三個時期,來考察《協(xié)和運動》的輿論特點及所發(fā)揮的作用。
二、《協(xié)和運動》的矛盾整理期
所謂矛盾整理期,是指與協(xié)和會自身的狀態(tài)相對應的初創(chuàng)期。這一時期的協(xié)和會一方面以“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為基礎,宣揚“民族協(xié)和”理論;另一方面對現(xiàn)行政策,如“滿洲國”施政綱領以及政府主導協(xié)和會活動的方針、中央本部的工作方法抱有不滿。因此協(xié)和會將既想“尋求依靠”,又想“謀求獨立”的糾結矛盾展示在《協(xié)和運動》的載文中,希望引起相關人士的關注,在混亂的狀態(tài)中對矛盾和對立進行整理,探尋解決問題的路徑。
“矛盾整理期”的文章以聲援和批判為主,代表人物有協(xié)和會創(chuàng)立時期“民族協(xié)和”思想堅定的追隨者山口重次、小山貞知以及青田武重等人。在他們的領導下,《協(xié)和運動》在配合“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同時,試圖以特有的方式解決協(xié)和會內外矛盾。
《協(xié)和運動》創(chuàng)刊之際,日軍在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中慘遭失敗,加快了戰(zhàn)略的調整。時任首相的近衛(wèi)文麿為混淆視聽,于1938年11月3日發(fā)表了“建設東亞新秩序”聲明,1940年發(fā)起“新體制運動”,同年8月又提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這一構想與《協(xié)和運動》的主要執(zhí)筆者小山貞知、山口重次等人的想法產生共鳴,因此在鼓噪“大東亞共榮圈”的聲浪中,《協(xié)和運動》刊載了大量聲援“東亞新秩序”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文章。
例如,山口重次撰文強調“東亞的年輕人,在完成艱難事業(yè)的道路上,應該共同肩負著三個重要的使命。一是本民族或國家的革新運動;二是各民族、各國家的協(xié)同體運動,即東亞聯(lián)盟結成運動;三是世界大戰(zhàn)前夕,精神上、物質上的必勝準備運動”[6]。根據(jù)世界局勢的變化,他認為在世界大戰(zhàn)來臨前夕,協(xié)和運動的主調應該在于結成東亞聯(lián)盟,永遠維護東洋文化和東亞各民族。從整合東亞各民族的實際效用看,可以說“東亞聯(lián)盟”、“協(xié)和運動”與“大東亞共榮圈”是異名同體的存在。
幾于同期,小山貞知認為,近衛(wèi)新體制的目標是消解“南守北進”與“北守南進”之間的矛盾,統(tǒng)合南北亞細亞。原本以民族協(xié)和為出發(fā)點的協(xié)和會已經將運動發(fā)展到經濟和政治領域,因此“協(xié)和運動”在某種意義上為新體制建設提供了范本。他還指出,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應該在民族、政治、經濟問題上分別采取民族協(xié)和、眾議統(tǒng)裁、確立自給自足圈的對策[7]。
山口和小山二人大力倡導的“民族協(xié)和”運動,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東亞新秩序”論調的一種配合。除此之外無論是橋本虎之助的創(chuàng)刊詞,還是皆川豐治所作的卷首語,都體現(xiàn)了協(xié)和會中堅分子對“東亞新秩序”的熱衷和追捧。
與此同時,面對協(xié)和會的內外矛盾,《協(xié)和運動》刊載加強溝通、呈現(xiàn)矛盾、引發(fā)思考、促其解決的文章,以監(jiān)督與提醒協(xié)和會的領導者們。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廣開言論,《協(xié)和運動》在“投稿須知”中寫道,“歡迎各個領域各種形式的稿件,稿件一旦刊載,文責由編輯承擔,可以匿名”[8]。
其二從第1卷第3號開始增設“地方意見和建議”欄目,因此對政府、政策、中央本部的本位思想進行評論的稿件增加,呈現(xiàn)出尖銳的批判態(tài)勢。此類文章成為雜志另一主要論調。以青田武重和鈴鹿山人為代表。
來自地方分會的青田武重對干部官吏的工作態(tài)度以及協(xié)和會工作的華而不實進行了批評。“在參加省聯(lián)時官吏缺席、遲到的情況并不罕見,即便出席,對于需要說明的事項避而不答”,青田把這樣的情況批評為“不是沒有認識到省聯(lián)的重大意義,就是玩忽職守、敷衍了事”[9]。同時,他還揭露了協(xié)和會工作輕視或無視民眾性格的本質,指出“協(xié)和會民眾工作只是抽象地宣傳‘建國精神’,沒有深入到社會底層中去”[10]。
與青田武重不同的是,鈴鹿山人以《滿洲新聞》記者的身份對協(xié)和會運動進行批判時指出:“協(xié)和會是會務職員的協(xié)和會,協(xié)和會運動已經是機械化、事務化、閉塞的運動,走上了團體運動所最忌諱的官僚獨善的歧途”,即是說,協(xié)和會已經淪為權力機構的附屬品,協(xié)和會對報紙和記者的作用認識不夠充分,因不能深入?yún)f(xié)和會內部,導致記者對協(xié)和會認識也不夠徹底[11]。
《協(xié)和運動》借助民眾的口吻一邊為協(xié)和會唱贊歌,一邊將輿論的矛頭指向政府。有民眾發(fā)出了“統(tǒng)制經濟究竟統(tǒng)制了誰,歸根結底,受到統(tǒng)制的都是平民百姓。百姓做牛做馬的勞作,卻處處受損,政府和特殊會社限制我們,自己卻不遵守約定,不說謊話的只有協(xié)和會了”[12]的感慨。這無形中揭示了政府與協(xié)和會的矛盾。“協(xié)和會雖然是政府的精神母體,但實際二者卻是對立的關系”[13]。
另在矛盾整理期內,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協(xié)和運動》編輯部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不僅作者來源多樣化,言論所受限制甚少。在第1卷第4號的“編輯后記”中甚至出現(xiàn)了馬克思的名句“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異類的存在。之后“滿洲國”的言論統(tǒng)制政策逐漸收緊,即便是機關雜志,政論批評性的文章數(shù)量也隨之減少,直至銷聲匿跡。
簡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協(xié)和運動》一方面抨擊政府,評論時政,試圖打造協(xié)和會獨立自主的形象,希望借助輿論監(jiān)督,讓民眾看到協(xié)和會切實的行動力;另一方面為了在殖民體系內站穩(wěn)腳跟,不得不攀附權貴,為殖民言論搖旗吶喊。雖然協(xié)和會左右為難的矛盾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呈現(xiàn),但機關雜志的定位決定了其局限性,在解決矛盾方面并沒有發(fā)揮預期的作用。
三、《協(xié)和運動》的合作期
進入1941年,協(xié)和會和“滿洲國”政府的關系逐漸趨向平和、目的一致,協(xié)和會成為政府統(tǒng)治民眾與殖民者進行侵略的工具。相對矛盾整理期而言,協(xié)和會所發(fā)生的轉變使《協(xié)和運動》進入其發(fā)展歷程的第二階段——合作期。
這一時期,在《協(xié)和運動》的靈魂人物伊地知則彥、櫻井信義、菅原達郎、三宅光治等人主持下,《協(xié)和運動》作為機關雜志的特征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形式也日趨完善。因協(xié)和會在此期處于追隨和配合政府的地位,所以伴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和戰(zhàn)況不斷發(fā)生變化,《協(xié)和運動》所展現(xiàn)出的輿論導向也有所差異。以珍珠港事件、中途島海戰(zhàn)為分界點,合作期的《協(xié)和運動》又可被細化分為三個小的分期:戰(zhàn)爭準備期、戰(zhàn)果擴大期、戰(zhàn)爭轉折期。
(一)戰(zhàn)爭準備期
1941年日本通過與他國簽訂系列合約,加強與法西斯國家合作的同時,逐步逼近印度支那南部。東條內閣通過的《帝國國策遂行要領》,實際是日本企圖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的動員令。在中國東北,為了強化政府的統(tǒng)帥力,保證政府在戰(zhàn)時能夠全力配合日本,協(xié)和會內部進行了“二位一體”改革。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情勢下,戰(zhàn)爭準備期內的《協(xié)和運動》輿論出現(xiàn)兩種傾向:
第一種傾向表現(xiàn)為對“二位一體”制的順利推行做思想鋪墊和政策宣傳,并監(jiān)督后續(xù)執(zhí)行情況,進行整改。
《協(xié)和運動》1941年第1、2號,登載了協(xié)和會該年度的工作方針。其主要內容有:強化國民鄰保組織;訓練青少年;提倡民族協(xié)和;改革機構與調整人事。其中,工作的兩大重心是青少年的指導訓練和國民鄰保組織的強化[14]。工作重點的調整,預示了“二位一體”的機構改革已成為協(xié)和會迫在眉睫的任務。
與此同時,為化解中央本部與分會之間的矛盾、便于實行總力戰(zhàn)體制,強化會務機構、推行人事交流也成為《協(xié)和運動》的宣傳重點。1941年第3號刊載的有關機構改革、人事調動的文章竟然達到7篇之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央本部長三宅光治的《關于人事變動的訓示》、《告轉出和殘留職員》、《劃時期的人事異動和協(xié)和會的新起點——輸出者一千二百余名》,以及對其指示進行總結的《關于三宅中央本部長的指示要旨》等文章。三宅在文中解釋道,“這是非常時局下的非常處置。雖然經過這樣的改革,但是協(xié)和會的本質卻是沒有發(fā)生改變的,他并不是政府的從屬機構,不要在意流言蜚語,而是應該高瞻遠矚,克服眼下的困難。對于余下的工作要進行很好的交接,避免協(xié)和會內部工作發(fā)生混亂”[15]。通過1941年的整改,協(xié)和會、政府、特殊會社彼此之間的對立意識逐漸統(tǒng)合為整體國家意識。
第二種傾向則以宣揚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優(yōu)越性為核心。
為了宣揚戰(zhàn)爭的正義性、必然性以及被迫性,《協(xié)和運動》開始強調日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使命、“滿洲事變”的歷史意義、“滿洲建國”的世界意義。以“大東亞共榮圈”這一所謂的“理想”蒙蔽民眾,煽動國民盲目的愛國熱情,同時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曲解,試圖用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泯滅民族意識、麻痹民眾,為其侵略辯護,穩(wěn)固殖民統(tǒng)治。
日高輝忠的《日本的世界文化史使命》一文從1941年第1號開始連載三期,為大東亞戰(zhàn)爭做戰(zhàn)前宣傳,試圖從理論、現(xiàn)實兩個角度證明日本統(tǒng)治世界的必然性。“將東西方文化相融合,展現(xiàn)所謂的‘新世界文明’是歷史賦予日本的使命,如果脫離了日本這塊苗圃,東西方文化的融合終將成為空談。因為在東洋諸多民族中間,只有日本逃脫了亡國或成為殖民地的命運。究其原因,當與異文化接觸時,原有文化都會因外來文化產生沖擊,甚至被異文化同化,但日本文化卻可以將相對的文化融為一體”[16]。日高表面宣揚只有日本這樣的“天才”民族才能最終實現(xiàn)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間接表達要想完成這一歷史進程戰(zhàn)爭是必然的途徑。
松浦嘉三郎在《滿洲文化的特質》一文中宣揚“滿洲建國”的重要性,指出“滿洲是世界新秩序的母胎,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根據(jù)地”,實際上是在培養(yǎng)殖民地民眾畸形的國家榮譽感和自豪感,使其淡漠被侵略奴役的事實。另外他還將滿洲文化從中華文化中剝離出來,鼓吹滿洲文化和日本文化形態(tài)上的接近,認為忠孝是滿洲文化的精髓,同樣也是東洋道德的根本,以便打造文化或是心理上的親近感,并進而張揚“隨著滿洲國的強大,滿洲文化終將成為民族國家的精神中心”的這一觀點[17],意在蠱惑殖民地民眾為“滿洲國”盡忠。
《協(xié)和運動》所提倡的“東亞永為東亞人之東亞”,實則表露出東亞是日本人領導下的東亞的實質。由于日本民族和文化的優(yōu)越性,日本理所應當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領導者,占據(jù)核心位置。
(二)戰(zhàn)果擴大期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協(xié)和運動》的輿論完全轉為與戰(zhàn)爭相關。1942年第1號到第4號的《協(xié)和運動》開設了“大東亞戰(zhàn)爭”特輯,基本由政府供稿,包括各種公告和會議記錄,會員投稿數(shù)量銳減,甚至創(chuàng)刊以來體現(xiàn)編撰者意圖的《編輯后記》也一度被取消,一直到1942年第6號才恢復正常。可以說這一時期,由于二位一體的改革,政府和協(xié)和會之間形成人事交叉,政府對協(xié)和會的控制加強,弱化了《協(xié)和運動》原本的辦刊宗旨,稿件多以強化政府對協(xié)和會的領導,宣揚戰(zhàn)果為主,幾乎淪為殖民者的“揚聲器”,對殖民意圖、殖民思想進行原封不動的轉述。
在初期戰(zhàn)事順利推進之際,《協(xié)和運動》對戰(zhàn)果極盡渲染之能事。“日本陸海軍驍勇善戰(zhàn)取得赫赫戰(zhàn)果,鐵袖一揮,英美戰(zhàn)營寂靜無聲”[18];“日本國力以及軍備的強大,一旦交火如英美、荷蘭、澳大利亞都不是日本的對手。日本強大的海軍和空軍足以保證制海權和制空權。對于日本來說也不懼怕持久戰(zhàn)”[19]。類似的描述充斥著整本雜志。在1942年第2號登載的《陸海兩相的戰(zhàn)況報告》和《大東亞戰(zhàn)爭周報》中,有對日軍初期勝利的炫耀,有對日軍侵略行為的美化,也有對英美失利的渲染,還有對日軍在戰(zhàn)爭中的損失以及當?shù)孛癖娝転碾y的遮掩。譬如占領香港的侵略戰(zhàn)爭甚至被描繪成日軍的無奈之舉,“占領九龍,人道主義的日軍不愿帶來無謂的犧牲,所以勸其投降,卻遭到了拒絕”[20]。此外,《協(xié)和運動》傾力宣傳“圣戰(zhàn)”與“王道之戰(zhàn)”。鼓吹“因為是圣戰(zhàn),所以失敗的例子前所未聞,因此戰(zhàn)爭的結果已經明曉。”[21]
(三)戰(zhàn)爭轉折期
中途島海戰(zhàn)后,日軍原有優(yōu)勢逐漸消退,太平洋戰(zhàn)爭進入轉折期。《協(xié)和運動》從1942年第6號起做了相應的調整,輿論指向確立戰(zhàn)時體制和強化新時期協(xié)和會的任務。
從執(zhí)筆者身份來看,多半來自中央本部,已經沒有會外成員,也就是說來自會外的稿件銷聲匿跡。但也是從這一號開始恢復原有框架,即重開“編輯后記”、“匯報”等欄目。1942年第7號是協(xié)和會成立十周年紀念號,所以格外受到重視,集中刊載了菅原達郎、半田敏治、小山貞知、板垣征四郎、于靜遠、甘粕正彥、本莊繁、阮振鐸、山口重次等人的文章。可以認為十周年紀念號是官方意志最完整的體現(xiàn)。
戰(zhàn)事逐漸走向敗退之際,思想教化作用的重要性開始凸顯。因此協(xié)和會開始討論其本身肩負的“新使命”。菅原達郎認為“國民運動開展的會務運動缺少感染力和精彩。各級本部委員會和聯(lián)合協(xié)議會都走向形式化,協(xié)和會存在的意義已經喪失了大半。我們必須對二者的使命進行反省,然后認真探討其構成和運營”[22]。協(xié)和會的新使命在于強化組織機構,同時提高精銳會員的素質。而在半田敏治看來,“未來會務運動的目標應該有以下幾點:(一)快速整備強化會務組織,特別是分會組織;(二)將建國精神提高到國民信念;(三)由國民信念而發(fā)出的感情融和,據(jù)此來實現(xiàn)民族協(xié)和;(四)這一信念要立足于感情,實現(xiàn)思想上的統(tǒng)一和浸透;(五)通過科學技術部會的活躍,促進在政治、經濟、交通運動等方面的建設;(六)開展作為國民訓練,同時也是物質建設原動力的勤勞奉公運動;(七)對作為勤勞奉公運動源泉的青少年運動進行強化,整備擴充其組織;(八)對作為國民政治力集結的精華——聯(lián)合協(xié)議會(特別是全聯(lián))的運營進行刷新與強化”[23]。
雖然表述重點各有差異,但是強化會務運動是二者的共識。之所以會達成這樣的共識,是因為無論是北部邊境的鎮(zhèn)守,還是向日軍提供物資,都直接依賴于協(xié)和會具體工作的展開。協(xié)和會運動在“宣揚建國精神、提高民眾對時局的認識,張揚重要國策的真正意義,保證有關國策執(zhí)行過程中民意的順達,真正地做到群策群力”[24]等方面釋放能量。殖民者充分認識到會務運動的開展直接決定著戰(zhàn)時體制確立的穩(wěn)定性。
此外,雖然也出現(xiàn)了批判性的文章,但因《協(xié)和運動》整體上配合政府言論和政策,所以同矛盾整合期批判性的文章相比,語氣相對溫和,措辭也顯得謹慎了許多。因而,批判性的文章并沒有沖淡《協(xié)和運動》的宣傳主題。
四、《協(xié)和運動》的回歸期
進入1943年,協(xié)和會的領導人認識到日本僅憑武力取得勝利的希望渺茫,所以轉而在“民族協(xié)和”上大做文章。他們認為,若能因此而加速戰(zhàn)爭的進程更好,即便事與愿違,至少也能為軍方提供穩(wěn)定的后方保證。因此,協(xié)和會主張?zhí)剿鳘毩⒌陌l(fā)展道路。相應地,《協(xié)和運動》的主辦者們開始反省在前一時期與政府的合作。他們在擺脫政府控制、找回最初的獨立風格、宣揚自己主張的強烈愿望下,引導雜志走向回歸。因此,《協(xié)和運動》進入了所謂的回歸期。
雖然《協(xié)和運動》最終回歸到提倡“民族協(xié)和”上來,但與第一階段所倡導的“民族協(xié)和”運動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即第一階段強調的是與偽滿政府的同體異身,而回歸期的“民族協(xié)和”則暗含著與政府分離而獨立發(fā)展的無限可能。能夠代表《協(xié)和運動》這一時期輿論走向的主要是大村次信、坂野龜一、高橋勝治、富永理等人。與矛盾整理期重視分會稿件相比,回歸期的投稿人大多來自中央本部。
在戰(zhàn)時體制下,協(xié)和會肩負的主要任務有:彰顯國體本性;徹底推行民族協(xié)和;強化政治力量;徹底推行戰(zhàn)時國民訓練;指導戰(zhàn)時國民生活等[25]。據(jù)此回歸期的《協(xié)和運動》將輿論重點調整為關注農村問題,它涉及農產品的征收、自興村育成、興農合作社建設等內容。
1943年2月10日,“推進增產全國會員大會”在新京市協(xié)和會館召開,會議現(xiàn)場懸掛印有“增產決戰(zhàn),足食足兵、完遂圣戰(zhàn)大東亞共榮”、“增產報國荷雙肩、奉戴圣旨齊向前”等內容的條幅。大會決議,“我們要貫徹必勝的信念,向舉國一體農業(yè)增產邁進,立誓實現(xiàn)一戶增產一成,開拓團增產七成的目標”[26]。之后《協(xié)和運動》刊載了“農業(yè)增產對策座談會”會議記錄,提出擴大耕地,振奮農民精神、機械作業(yè),充分利用“北支”零散勞力等建議[27]。根據(jù)地域的特殊條件,可以采取特定政策。譬如對入縣勞動者的手續(xù)進行簡化,或是在必要的時候強制婦女和學童進行勞動,推動城鎮(zhèn)內剩余人口進行歸農運動[28]。此外還發(fā)表文章《關于促進農產品征收的政策》、《納粹的糧食政策和增產戰(zhàn)》,對政策、方針、措施進行解說。通過系列宣傳以及各分會的實踐運動,1943年、1944年順利完成農產品征收任務。
東北民眾因此陷入更加窮困潦倒的生活,這一時期的《協(xié)和運動》刊載了較為罕見的關于民不聊生的文章。如西三道河子農作物總出荷量1943年為53噸,1944年劇增至230余噸,完成任務存在很大困難。當?shù)孛癖姴坏貌粚⒈蛔又械拿藁ㄓ脕砑彶伎p制衣服[29]。因為實行特殊物資配給制,物資嚴重缺乏,導致女主人因為家中只有一條褲子而無法起身招待客人[30]。由此可見,《協(xié)和運動》在追隨政府和軍隊腳步的同時,試圖用自己的力量改變現(xiàn)實,在協(xié)和會員中也有部分是具有同情心,顧及百姓生活的人士,但這樣的努力和改變在當時的大環(huán)境下不是很快被淹沒在“大東亞戰(zhàn)爭”、“大東亞共榮圈”的呼聲中,就是被重新詮釋,而為殖民者所用。譬如“拆被制衣”的故事就被宣傳為雖然條件艱苦,但民眾對出荷還是有相當?shù)恼J識和熱情的,用以迷惑更多的民眾。
日軍在太平洋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敗退時,正值東條英機和小磯國昭內閣統(tǒng)治時期。隨著《協(xié)和運動》的政策論和方法論已經很難繼續(xù)蠱惑民心,加之協(xié)和會成立之初,小磯國昭就是輕協(xié)和會而重關東軍的主要代表,所以協(xié)和會為穩(wěn)定民心,為戰(zhàn)爭的合理性重新尋找出路,調整《協(xié)和運動》的宣傳內容轉入“思想戰(zhàn)”,倡導建國精神。因此,這一時期稿件的另一內容以“思想戰(zhàn)”為中心,以“民族協(xié)和”為內核。
1944年第9號明確了在“思想戰(zhàn)”中協(xié)和會的地位。“戰(zhàn)時協(xié)和會運動要以思想戰(zhàn)為中心。協(xié)和會本部就是思想防衛(wèi)戰(zhàn)的司令部。同時在會務運動方面,以分會為中心,是動員指揮鄰組義勇奉公隊、青年團、國防婦人會的總指揮部”[31]。1945年第1號則規(guī)定了思想戰(zhàn)的具體內容、思想戰(zhàn)的正面攻擊法以及在不同時期不同區(qū)域對宣傳媒體機能的識別等[32]。同年第3號中將思想戰(zhàn)分為攻守兩類。“防御型的思想戰(zhàn)就是保證不被敵人迷惑,攪亂思想,削弱戰(zhàn)斗意識,也就是說要讓國民對自己國家進行的戰(zhàn)爭目的有充分的正義感,而且堅信正義的戰(zhàn)爭必然會勝利。攻擊型的思想戰(zhàn)就是主動出擊,擾亂對方軍心,讓敵人在不知不覺中和自身產生共鳴,認為繼續(xù)戰(zhàn)爭是愚蠢的、徒勞的。”[33]對宣傳的方針進行解釋,宣傳要通俗化、大眾化;宣傳應該適應不同的環(huán)境;強化動員工作,實際比理論更重要;強化慰勞安撫工作;推動被宣傳者進行宣傳,擴大宣傳[34]。為了減少農民的抵觸情緒,謊稱“出荷意味著為農村建設做出了多少貢獻”[35],錯誤地引導民眾,刻意營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氛圍。
通過思想戰(zhàn)的開展,協(xié)和會也逐漸深化對自身的認識,在軍事方面出現(xiàn)敗勢的時候,協(xié)和會中央本部認為“在戰(zhàn)時體制下,官制政治能夠發(fā)揮的作用已經到達了極限”,協(xié)和會應該根據(jù)自己的方針進行思想政治的教化工作。“樹立政治性的綱領,如果沒有積極的政治力,那么協(xié)和會就會淪為官僚組織或者是輔助機構”[36]。因此提出在運動中出現(xiàn)的問題自行消化和解決,并制定協(xié)議,也就是說要發(fā)展到政治實踐的層面。聯(lián)協(xié)要進行開展運動要領的協(xié)議,分會之間要互相合作,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37]。雖然在這里對協(xié)和會、聯(lián)合協(xié)議會提出政治性的要求,希望對其進行回歸性的改革,使二者都能夠取得更大發(fā)展,但是隨著戰(zhàn)爭的結束,這一切都成為泡影,所謂的回歸振興僅僅停留在了假設階段。雖然協(xié)和會中央本部還在努力為戰(zhàn)爭搖旗吶喊,但一線的協(xié)和會運動已然呈現(xiàn)無可挽回的敗勢。聲勢再浩大的思想戰(zhàn)攻勢,在日益覺醒的殖民地民眾面前,在大勢已去的戰(zhàn)爭形勢面前都顯得蒼白軟弱。
綜上所述,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滿洲帝國協(xié)和會”不時地調整方針政策與輿論導向,通過機關刊物《協(xié)和運動》進行輿論造勢。
正如協(xié)和會與政府的關系一樣,《協(xié)和運動》的輿論導向與殖民政策保持了亦步亦趨的關系。雖然經歷了矛盾整理期、合作期及回歸期等階段,但作為軍國主義控制下的主要教化工具,以“民族協(xié)和”、“大東亞共榮圈”為宣傳核心,以完成殖民思想教化為根本目的的辦刊方針貫穿雜志始終,其殖民者代言人的地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說《協(xié)和運動》站在“滿洲國”殖民宣傳的前沿陣地,不遺余力為殖民統(tǒng)治搖旗吶喊,通過粉飾殖民政策、趨利避害地介紹殖民地現(xiàn)狀,在蒙蔽認知、混淆視聽方面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38]。
殖民者通過侵華戰(zhàn)爭和太平洋戰(zhàn)爭,將“滿洲國”強行納入了日本的戰(zhàn)時體制,使其淪落為支持日本的最大軍事基地。殖民者也通過《協(xié)和運動》宣傳自身的殖民理論,試圖從思想上和文化上加強對“滿洲國”的占領。但是非正義戰(zhàn)爭,無論如何美化其卑劣行徑,最終都將會走向末路,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1]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東北淪陷十四年史吉林編寫組譯.滿洲國史(分論)[M].1990:186.
[2] [日]編輯後記[J].協(xié)和運動,1944(2):72.
[3] [日]謹告[J].協(xié)和運動,1945(1):19.
[4] [日]「協(xié)和運動」発刊に就て[J].協(xié)和運動,1939(1):1.
[5] [日]風間秀人.協(xié)和運動(別冊) [M]. 東京:緑陰書房,1995:13.
[6] [日]山口重次.協(xié)和運動の世界観[J].協(xié)和運動,1939(2):5.
[7] [日]小山貞知.新體制と協(xié)和會運動[J].協(xié)和運動,1940(8):94-97.
[8] [日]次の項を御熟読の上御投稿ください[J].協(xié)和運動,1939(1):1.
[9] [日]青田武重.龍江省聯(lián)所感雑記[J].協(xié)和運動,1939(1):121-122.
[10] [日]青田武重.協(xié)和會と農事合作社関係[J].協(xié)和運動,1939(2):85-87.
[11] [日]鈴鹿山人.協(xié)和會運動と新聞記者[J].協(xié)和運動,1940(7):32.
[12] [日]大津誠助.北安で拾った話[J].協(xié)和運動,1940(8):84.
[13] [日]新井清吉.如何にせば協(xié)和運動は徹底するか[J].協(xié)和運動,1940(8):110-111.
[14] [日]編輯後記[J].協(xié)和運動,1941(1):182; 編輯後記[J].協(xié)和運動,1941(2):130.
[15] [日]三宅光治.人事異動に関する訓示[J].協(xié)和運動,1941(3):8.
[16] [日]日高輝忠.日本の世界文化史的使命(一)(二)(三)[J].協(xié)和運動,1941(1):93-97,1941(2):70-76,1941(3):56-62.
[17] [日]松浦嘉三郎.満州文化の特質[J].協(xié)和運動,1941(7):66-74.
[18] [日]巻頭言[J].協(xié)和運動,1942(1):1.
[19] [日]三宅光治.盟邦日本の南方聖戦に際して全國には二百萬の會員に告ぐ[J].協(xié)和運動,1942(1):71.
[20] [日]陸海両相の戦況報告[J].協(xié)和運動,1942(2):10.
[21] [日]三宅光治.盟邦日本の南方聖戦に際して全國には二百萬の會員に告ぐ[J].協(xié)和運動,1942(1):71.
[22] [日]菅原達郎.協(xié)和會十年を顧み新たなる使命を惟ふ[J].協(xié)和運動,1942(7):2.
[23] [日]半田敏治.大東亜戦下における?yún)f(xié)和會の新使命[J].協(xié)和運動,1942(7):17.
[24] [日]巻頭言[J].協(xié)和運動,1942(9):2.
[25] [日]坂田修一.協(xié)和會運動基本要綱覚書[J].協(xié)和運動,1943(6):4.
[26] [日]三宅光治.中央本部長協(xié)和會増産運動方針説明[J].協(xié)和運動,1943(3):51.
[27] [日]農村増産対策座談會[J].協(xié)和運動,1943(3):100-143.
[28] [日]山田博.特別地帯における増産方案[J].協(xié)和運動,1943(4):14-15.
[29] [日]都盛男.現(xiàn)地工作報告[J].協(xié)和運動,1943(12):21.
[30] [日]根津義明.出荷工作雑感[J].協(xié)和運動,1943(12):24-25.
[31] [日]巻頭言[J].協(xié)和運動,1944(9):1.
[32] [日]佐藤巖之進.國內宣伝への覚書[J].協(xié)和運動,1945(1):46-53.
[33] [日]松浦嘉三郎.思想戦における?yún)f(xié)和會運動之再認識[J].協(xié)和運動,1945(3):19-26.
[34] [日]英賀重雄.宣伝と技術[J].協(xié)和運動,1945(1):57.
[35] [日]二上政治.出荷運動之思想的展開[J].協(xié)和運動,1944(9):28.
[36] [日]松浦嘉三郎.思想戦における?yún)f(xié)和會運動之再認識[J].協(xié)和運動,1945(3):19-26.
[37] [日]高橋勝治.県聯(lián)を観て省聯(lián)に斯く望む[J].協(xié)和運動,1945(4):38-41.
[38] 謝忠宇.“九一八”事變前滿鐵附屬地日本語職業(yè)教育述評[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6):121-124.
The Development of “Consonance Movement”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Consonance Union in the Manchu Empire
WANG Zi-wei,CHEN Xiu-w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s the official magazine of the consonance union in the Manchu Empire,“consonance movement” provide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ideology,which served colonial politics.As the result of timing,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this magazine shift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political direction.The change of the magazine reflected the transition of colonial politics and the consonance union movement.
“Consonance Movement”;the Consonance Union;Public Opinion Guidance
2014-12-1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2JJD770003)。
王紫薇(1977-),女,黑龍江哈爾濱人,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建筑大學城建學院外語系講師;陳秀武(1970-),男,吉林農安人,東北師范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K265.61
A
1001-6201(2015)03-0095-07
[責任編輯:王亞范]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