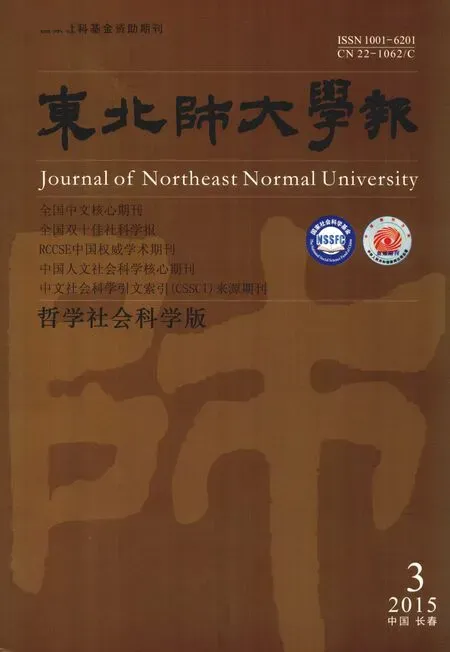異邦的法眼:莎士比亞戲劇的法律闡釋
馮 偉
(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
異邦的法眼:莎士比亞戲劇的法律闡釋
馮偉
(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莎士比亞戲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律文獻,劇中也鮮有早期現代英國的法律、法令,但劇作家卻在更深層面上思考了法律與自然、理性、自由、權利,乃至民主與道德等重大命題。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主人公如勃魯托斯、安哲魯、夏洛克、鮑西婭等無不面臨著西方法律文明至今仍無法完美解決的兩難困境,他們的迷茫和困惑既帶有鮮明的歷史特征,也是人類共同命運的最佳詮釋。
莎士比亞;法律;早期現代英國
法律對于莎士比亞時代的人們來說絕不是一個陌生的事物。從當時人們的衣著質地,到餐桌飲食,都存在著今人看來似乎是匪夷所思的各種各樣的法律規定[1]30-31。也許是驗證了中國老子的一句話,“法令滋彰,盜賊多有”[2]。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也曾有類似的表述:“一旦放縱與疾病在城邦內泛濫橫溢,豈不要法庭藥鋪到處皆是,訟師醫生趾高氣揚,雖多數自由人也將不得不對他們鞠躬敬禮了。”[3]113早期現代英國的倫敦街頭混跡著形形色色的盜竊犯罪分子,我們從該時期對于有關不法分子的五花八門的專有名詞中即可管窺一二[1]55。街頭爭吵、身體沖突甚至決斗也是司空見慣之事。著名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這樣形容伊麗莎白時代的人:“在16和17世紀,人們脾性暴躁不安,武器也唾手可得。……缺少管制使事情更加嚴重,因為在16世紀時,人們是如此極端暴躁。……此外,一個紳士總是隨時攜帶武器,而且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器。”[4]109盡管在隨后的幾十年里,英國的治安狀況逐漸得以改善,但在身體對抗減少以后隨之而來的是人們訴訟熱情的高漲。根據勞倫斯·斯通的統計,在此期間英國普通法法庭的訴訟卷宗數量表明,普通訴訟法庭的訴訟增長了6倍,王座法庭的訴訟增長了2倍[4]117。
莎士比亞戲劇中有大量的法律名句和經典判例,例如《亨利六世》(中篇)中屠夫狄克喊出了一句流傳至今的口號“第一件該做的事,是把所有的律師全都殺光。”(4.2.68)*本文莎士比亞原文引文均取自朱生豪譯本,行數標注則以諾頓版《莎士比亞全集》(1997)為準。;《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對整個威尼斯法律的蔑視:“你們的法律去見鬼吧!”(4.1.100)《一報還一報》中安哲魯說的“法律雖然暫時昏睡,它并沒有死去”(2.2.92);《哈姆雷特》中對律師的揶揄(5.1.90-94)等等。除了這些現代研究者耳熟能詳的法律名言,莎劇中還上演了大量的“法庭戲”,如《威尼斯商人》、《冬天的故事》、《一報還一報》,以及《李爾王》(其中“戲諷式審判”一場戲僅存于1608年的第一四開本)等。甚至《裘力斯·愷撒》中“愷撒的葬禮”也常常讓美國的法律專業人士聯想到今天的陪審團制度[5]。莎士比亞歷史劇(約占莎士比亞創作的1/4)[6]對于王權合法性問題的關注,《裘力斯·愷撒》對于古羅馬自然法思想和羅馬共和體國垮臺的反思,《威尼斯商人》中對于高利貸問題(莎士比亞與其父親都曾經從事過類似夏洛克那樣的高息放貸行為)、法律與經濟問題,乃至法律的正當性問題的表現,無不說明莎士比亞戲劇與早期現代英國法律之間存在著若干紛繁復雜的關聯。
《裘力斯·愷撒》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律文獻,劇中也沒有記載任何有關羅馬的法律、法令,但該劇卻在更深的層面上思考了自然法與善、法律與自由、法律與民主,乃至法律與政治的若干重大命題。該劇中,當羅馬民主制處于行將就木的危急時刻,勃魯托斯即處于這樣一個倫理困境:是否要殺掉尚未稱帝的愷撒才能保住羅馬共和制?在這個艱難的抉擇背后,實際上還同時潛伏著一系列的政治危機:內戰與獨裁、對私人的友誼與對城邦的忠誠、民主的形式還是共和的精神之間重重矛盾。勃魯托斯生性高貴、篤信美德和自由,崇尚自然法,是斯多葛學派的典型代表。最了解勃魯托斯的人,恰恰是勃魯托斯的最大敵手—安東尼。后者在其死于戰場時的感嘆可謂其蓋棺定論之語:“在他們那一群中間,他是一個最高貴的羅馬人;除了他一個人以外,所有的叛徒們都是因為妒嫉愷撒而下毒手的;只有他才是激于正義的思想,為了大眾的利益,而去參加他們的陣線。他一生善良,交織在他身上的各種美德,可以使造物肅然起立,向全世界宣告:“這是一個漢子!”(5.5.67-74)安東尼之所以認為勃魯托斯是“一個最高貴的羅馬人”,正是由于在愷撒的刺殺者當中,除了勃魯托斯其他所有的反叛者都是因為嫉妒愷撒而下毒手,只有勃魯托斯是為了大眾的利益而刺殺愷撒。然而勃魯托斯雖然免于嫉妒的寬饒,其動機也是為了大眾的利益,但卻無法超越他那典型的斯多葛主義者的道德精英主義,并最終喪失了斯多葛主義者珍視的自由,淪為榮譽和聲望的犧牲品[7]。其次,勃魯托斯刺殺愷撒固然是激于正義的思想,然而刺殺愷撒事件的正義性本身,時至今日仍是人們爭論不休的話題。作為斯多葛主義者,勃魯托斯的正義觀注定與古羅馬的自然法思想保持著無法割舍的親緣關系。著名法學家梅因認為:“從整體上講,羅馬法在改進方面,當受到自然法理論的刺激時,就發生了驚人的進步。”[8]33莎士比亞本人是否熟悉古羅馬的自然法思想,我們已經無從考證,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莎士比亞戲劇對于羅馬自然法思想之理論困境有著洞察秋毫的描寫。從法理學的角度來看,如何將抽象的自然法轉化為具體的法律條文,使得自然法在社會生活中成為法律現實,既有賴于人們的理性和知識,同時還取決于人們的意志。此中困難,正如著名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所言:“如果雙方當事人直接具有必要的知識和意愿,并從而避免任何爭端的話,那么,建立一個在爭端當事人之上以個別規范解決爭端的專門機關,也會是多余的。這是一個明顯的烏托邦的推定。……鑒于人的知識和意愿的不充分,自然法(始終推定它是存在的)的這樣一種實現,到底能實現到何種程度,那是另一個問題。”[9]434
無論從戲劇樣式,還是從語言風格、主題內容來看,《裘力斯·愷撒》與《威尼斯商人》都是兩部迥乎不同的作品。如果說解讀前者的關鍵詞是:羅馬人、榮譽、美德、自由、暴力、共和制和廣場,那么相對應地解讀后者的關鍵詞則是:商人、利潤、契約、平等、權利、愛情和法庭。即便如此,僅從法理學的角度理解莎士比亞,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兩部作品的確存在若干的契合之處。首先,兩部作品都格外關注法律“文本”的闡釋難題。其次,兩部作品都討論了法律的起源問題。第三,兩部作品都對法律的合法性或正當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第四,無論是羅馬還是威尼斯,都帶有鮮明的想象和建構特征。在《裘力斯·愷撒》中,劇中“文本”的闡釋困難在于何為自然和自然法,而在《威尼斯商人》中,文本的闡釋分歧則在于“一磅肉”的契約。在《裘力斯·愷撒》中,法律更多是一種自然正義,來自于亙古不變的超驗世界,而在《威尼斯商人》中,法律則表現為一種契約,是締約雙方的“合意”;契約既是對合同雙方權利和義務的明確規定,同時還是城邦或國家的經濟基礎和保障。在《裘力斯·愷撒》中,勃魯托斯所珍視的理性和自然法最終未能挽救瀕死的羅馬共和國,而在《威尼斯商人》中,一磅肉契約本身的不正當性既為“猶太佬”夏洛克贏得了眾多現代讀者的同情,也為劇中的基督徒鮑西婭和安東尼奧等人招來了許多不公正的惡名。在《裘力斯·愷撒》中,愷撒之死只是羅馬共和制滅亡的導火索,共和精神蛻變為黨派之爭才是整場悲劇的真正原因;而在《威尼斯商人》中,法律沖突的背后其實也未嘗不是政治的對抗。劇中的安東尼奧毫無理由地仇視夏洛克,而夏洛克一旦在法庭上占據主動權,則斷然放棄了巴薩尼奧提出的雙倍甚至更多的違約金。如果夏洛克只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吝嗇鬼,那么他大可以利用手里的一磅肉契約大敲竹杠,獲得一筆巨額的賠償金。然而夏洛克卻拒絕巨額的賠償,堅持要求按約執行,這令威尼斯人都感到十分吃驚。有理由相信,如果安東尼奧與夏洛克之間的仇恨可以通過經濟或法律(理性)的方式得以解決,那么《威尼斯商人》是否能夠流傳至今,都尚且存疑。“一磅肉”契約,乃至法律闡釋方式的分歧,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政治的對抗,法律只是復仇的工具而已。鮑西婭有關“仁慈”的著名演說可謂婦孺皆知,但是這一名段實則還涉及了另外一個重要主題——正義。首先,鮑西婭不但沒有否認夏洛克的契約符合正義原則,而且極力“維持”該契約的尊嚴和威信,“在威尼斯誰也沒有權力變更既成的法律”(4.1.213-214),甚至總督也無權改變合約本身。換句話說,嚴格執行一磅肉契約是正義的要求。然而鮑西婭這樣做無形中將正義與仁慈原則對立起來,其中的邏輯似乎是人們要么選擇正義,要么選擇仁慈,二者無法兼得。此種做法的一個惡果在于,威尼斯的法律被等同于抽象的正義原則,正義原則也被等同為強權本身。
如果說《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是為了保障威尼斯的商業繁榮和海外貿易的順通,那么《一報還一報》中維也納的法律則除了維護城邦秩序以外,還肩負著改善道德風尚、拯救犯罪者靈魂的更高使命。正如在《威尼斯商人》中,問題不在于鮑西婭的審判,而在于自由而不平等的威尼斯共和國,在于商人共和制中的法律理念[10];在《一報還一報》中,“問題”的癥結亦不在公爵,而在于維也納的法律。頗為有趣的是,在《威尼斯商人》中,無論是安東尼奧、巴薩尼奧,還是鮑西婭或夏洛克(后者稱之為“游戲的契約”)(1.3.169)都意識到“一磅肉”的離奇和反常,但劇中人物幾乎都異口同聲地維護威尼斯的法律尊嚴,強調法律的神圣不可更改。同樣,在《一報還一報》中,劇中人物上至公爵文森修,下至皮條客龐貝,也無不強調法律的至上地位。維也納公爵文森修一面坦然承認維也納法律過于嚴厲,另一方面卻任命具有無比執法激情的安哲魯為代理公爵“重整法紀”。盡管兩個劇本中的“法律”之具體內涵幾乎沒有任何共性,但威尼斯與維也納的臣民都在有意無意地維護和建構一個法律的共同體。人們既無法建立一個類似于烏托邦式的完美的法律機制,也無法停止對于法律烏托邦的向往和想象,或者至少無法從本體論上擺脫人類對于“法律”本身的信仰,這也未嘗不是西方近現代法律文明的一個兩難處境。
在《威尼斯商人》中,當夏洛克被問及割肉究竟對他有什么益處的時候,夏洛克的回答是:“拿來釣魚也好;即使他的肉不中吃,至少也可以出出我這一口氣。”(3.1.45-46)法律固然可以確保威尼斯貿易的發達,但卻無法消除夏洛克心中的仇恨,一個根本原因在于:仇恨也許有時是起源于利益沖突的,但一旦形成,則會蛻變為一種非理性的對抗,而這種對抗則遠非物質利益所能夠簡單化解的。同樣,法律也難以成為一門純粹的“科學”,關鍵原因之一在于,法律面對的是人類個體的“沉重的肉身”。啟蒙主義運動以來,西方文明的一個主線即是試圖用理性來解釋和規劃個體和社會行為,但人類的歷史卻一再表明:理性對于人類文明的發展有時候往往是軟弱無力,因而作用甚微的。在《一報還一報》中,殺人犯巴那丁則成為這個難以馴服之肉體的最大象征。
為了挽救克勞狄奧,公爵原本設計用巴那丁頂替,后者則是一個在監獄中已經被關押了9年,卻仍然能夠“視死如歸”,毫無懺悔之心的重犯。在被處決的前夜,克勞狄奧體驗著死亡前的種種精神折磨,而巴那丁卻能夠高枕無憂,“他睡得好好的,像一個跋涉長途的疲倦的旅人一樣,叫都叫不醒。”(4.2.55-57)頗為反諷的是,有關監獄與自由的意象,在其后創作的《李爾王》中也曾再次出現過,而李爾王竟與巴那丁一樣期待在監獄中找到自由和超然的快樂生活。難怪著名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說把整個維也納看作一個無比巨大和壓抑的“政府”,巴那丁則是該劇中人類僅存的希望[11]。巴那丁與考狄利婭和李爾王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巴那丁拒絕懺悔的精神姿態的確對以文森修公爵為象征的法律和秩序構成了嚴峻的挑戰。與巴那丁形成鮮明對比的,無疑是與其關押在同處的克勞狄奧。當路西奧看到好友克勞狄奧與其未婚妻朱麗葉同被游街示眾時,路西奧問克勞狄奧為何“戴起鐐銬來啦”。克勞狄奧回答說:“因為我從前太自由了,我的路西奧。過度的飽食有傷胃口,毫無節制的放縱,結果會使人失去了自由。正像饑不擇食的餓鼠吞咽毒餌一樣,人為了滿足他的天性中的欲念,也會飲鴆止渴,送了自己的性命。”(1.2.105-110)克勞狄奧無法節制“天性中的欲念”,文森修公爵同樣無法說服克勞狄奧擺脫對于死亡的恐懼。在一段冗長的布道之后,克勞狄奧貌似已經欣然接受了必死的判決。然而就在片刻之后,當他知道自己仍然還有一線生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選擇用依莎貝拉的貞操來換取他的性命。可以說,無論是克勞狄奧為了“茍延殘喘”,不惜讓“姊姊蒙污受辱”,還是巴那丁在臨刑前夜沒有睡好,而拒絕當日就死,二者的法律和政治寓意實際并無二致:人類理性始終要面對的是難以馴服的肉體和意志。柏拉圖認為,對于欲望的非理性的渴望,以及對于死亡的非理性的恐懼都是一種認識論上的錯誤,或者誤將假象當作真理,然而使徒保羅所說,欲望往往并非只是知識的問題,而是人犯罪的傾向:“我也知道在我里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惡,我倒去作。”(《羅馬書》第7章第18-24節)
守法作為一種美德,乃是理性的要求使然;但同時美德又不同于理性或知識,而是一種道德誡命,是一種愛的意志行為。因此在守法問題上,“知識”與“意志”的內在張力是理解《一報還一報》中法律難題的關鍵。總之,在《一報還一報》中,維也納法律所起的作用可謂捉襟見肘、舉步維艱,這不能不說是見證了人類“規訓與懲罰”之路的艱難和漫長[12]。然而與其說《一報還一報》表現的是法律的性質或淵源問題,不如說它表現的是執法者的美德問題。該劇劇名直接取自于圣經《路加福音》,其主題宣揚的恰恰也是“愛鄰如己”的基督教倫理思想。劇中文森修公爵可謂是一個披著神父外衣的哲學家,其宣講的教義也不是基督教神學而是柏拉圖哲學。由于兼有基督教和希臘哲學的雙重影響,該劇中的若干重大問題時至今日仍有待反思和解決,這未嘗不是西方兩大思想源泉在融合過程中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全劇開場時,公爵在正式任命安哲魯為代理公爵之前,對后者進行了一次意味深長的說教:“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來貢獻于人世,僅僅一個人獨善其身,那實在是一種浪費。上天生下我們,是要把我們當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造物是一個工于算計的女神,她所給予世人的每一分才智,都要受賜的人知恩感激,加倍報答。”(1.1.29-40)在上面這段“布道文”中,公爵使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比喻:擁有美德的人應當成為火炬。火炬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普照世界”,因此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不應該獨善其身,而應該兼濟天下。然而除了美德在于實踐這一層意思以外,此處的火炬還包含另一層更重要的意蘊:正如火炬本身需要人來點亮,美德也是上天所賦予的。既然美德是一種“天賦”,它就不應該是個人沾沾自喜的資本,否則美德注定滋生更大的惡—“驕傲”,而驕傲則是墮落的根源。上面這段美德的著名比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路加福音》(8:16-17)中耶穌的“燈臺”講道:“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盡管二者存在諸多重合之處,但與原劇文字不同,該段經文引文后半句卻是“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發人深思的是,這里的后一段經文是否暗示公爵早已懷疑安哲魯的外表與內心存在強烈反差?上面這段“美德”的論說是否也是話外有音呢?這也許又是該劇的另一不解之謎。按照基督教的教義倫理,基督徒行善不是為了榮耀自我,而是要讓上帝的榮光在信徒身上顯明,并最終將榮耀歸于上帝。
無論是《馬太福音》的5章14節,還是與耶穌的“山上寶訓”,都在于強調世人的一切善行和美德都出自于上帝神的恩典(grace)。該劇中使用的另一比喻,“自然是一個女神”,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如里士滿·諾布爾(Richmond Noble)指出,《一報還一報》與新約“塔蘭特幣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alents)一樣,兩個故事都講述了一位統治者由于某種隱晦的原因外出遠行,臨行前都賦予仆人以“塔蘭特幣”,而且都最終返回“審判”被授以銀幣的仆人。邪惡的仆人將銀幣埋藏起來最終受到主人的懲罰,而利用銀幣與人為善的仆人則得到主人更大的褒獎。劇中,安哲魯被公爵委以重任(talents),卻未能盡職盡責,受到了公爵的“審判”[13]。同樣,貫穿該劇始終,劇作家都在以各種方式表明:安哲魯的權力來自于公爵,他不是維也納權力的源泉,而是代替公爵的攝政或代理。換句話說,安哲魯代表維也納的最高權力,但其本身并非權力的正當性所在,拿依莎貝拉的話說,安哲魯只有“暫時的權力,卻會忘記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來面目”(2.2.121-122)
總之,莎士比亞戲劇通過展現劇中人物的極限情景,深刻揭示著人類永恒的道德和法律宿命。勃魯托斯、安哲魯、夏洛克、鮑西婭等無不面臨著人類至今仍無法完美解決的兩難困境,他們的迷茫和困惑既帶有鮮明的歷史特征,也是人類共同命運的最佳詮釋。莎士比亞本人到底知道多少法律?這是個眾說紛紜、言人人殊的問題。大量的法律專業人士曾信誓旦旦地斷言:莎士比亞一定受過法律訓練,或從事過法律行業,否則就不可能造就今天的莎士比亞[14]。甚至有人認為,如果斯特拉幅特小鎮的莎士比亞不可能具有任何法律經驗,那么莎士比亞戲劇則很可能出自他人之手。(莎士比亞本人對于法律的諳熟有時竟使得某些研究者臆測莎士比亞是否曾經做過律師,甚至“莎士比亞”是否就是莎士比亞創作的。)[15]莎士比亞本人是否曾經做過律師,或者到底具有多少法律知識,其實都無關宏旨。如康斯坦絲·喬丹(Constance Jordan)等人指出:“20世紀以來的莎士比亞與法律研究正是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本認識之上,即莎士比亞戲劇再現和重塑了早期現代英國的法律思想”[16]。誠哉斯言。
[1] Bryson,Bill.Shakespeare [M].London:Harper Press,2009.
[2] 李零.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179.
[3] 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4] 勞倫斯·斯通.英國貴族史,1558—1641年[M].于民,王俊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 Posner,Richard.Law and Literature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454.
[6]Kermode,Frank.The Age of Shakespeare [M].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4:11.
[7] 馮偉.曲高和寡的西塞羅:《裘力斯·愷撒》中的美德與自然法思想[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3):92-97.
[8] 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9] 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M].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10] 馮偉.《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與權利哲學[J].國外文學,2013(1):125-132.
[11] Bloom,Harold.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M].New York:Riverhead Books,1998:380.
[12] 馮偉.《一報還一報》與早期現代英國的德政思想[J].外國文學研究,2014(4):101-106.
[13] J.Gless,Darryl.Measure for Measure,the Law and the Convent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27.
[14] Michell,John.Who Wrote Shakespeare?[M].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6:1-14.
[15] Shapiro,James.Contested Will:Who Wrote Shakespeare?[M].New York: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2010:130-139.
[16] Jordan,Constance and Karen Cunningham.The Law in Shakespeare [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1.
A Prophet from the Distant Land: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
FENG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Shakespeare’s plays are not legal documents in a strict sense,neither are there many legal rules or regulations mentioned in them.However,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a big variety of personalities in various kinds of political and legal crisis,Shakespeare’s works provokes their audience into further thinking about those eternal themes of law and nature,reason,liberty,right and even democracy and morality.
Shakespeare;Law;Early Modern England
2015-01-16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2CWW030)。
馮偉(1976-),男,吉林松原人,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J809
A
1001-6201(2015)03-0127-05
[責任編輯:張樹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5.03.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