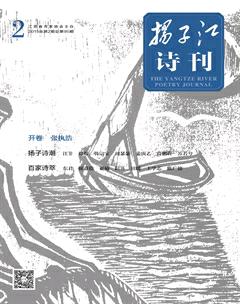文學的終極目的是什么
黑陶
“池水”已否“盡墨”
“池水盡墨”。池中洗筆,日積月累,竟致滿池之水,盡染墨色。
無論何種藝術領域,要想真正有所進步,必須時時自問:你的“池水”,“盡墨”已否?
李商隱的又一形象
李商隱(約813—858)敢于反抗權威,抒發己見。他聞聽前人所謂“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便“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
他在另外的場合更明確地表達過這個觀點:“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想起義山之前的王充和之后的李贄曾經說過的類似聲音。這是李商隱在其迷愛情詩專家的身份之外,展示給我們的又一形象。
每一本書都有其自足的氣血周流
那么多書籍堆壘。每一本書,都凝聚有某一生命個體思想與情感的能量。所以,每一本書都有其自足的氣血周流。而那么多的書籍在周圍,更是形成了一種似乎無睹卻強勁回旋的精神之氣場。你不去閱讀的書,就像你暫不聯系的朋友,但它們的存在,就足夠在靜默中給你借鑒、激勵和影響;你翻開了某一本書,就是和一位朋友相約坐下,開始了一段對談的時光。
卡佛的話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家、詩人)喜歡在寫字臺正面的墻上貼一些“三乘五英寸”的卡片,上面抄一些他極其認同的他人有關寫作的話,其中有:
每天寫一點。不為所喜,不為所憂。
準確的陳述是寫作的第一要素。
沒有什么能比一個放在恰當位置上的句號更能打動你的心。
“在這個國家里,選擇當一個短篇小說家或一個詩人,基本就等于讓自己生活在陰影里,不會有人注意。”卡佛自己的話。不甘?還是自知之明?
樹枝·漢字
窗外,小扇形的銀杏樹葉驟雨般紛落。日顯疏朗的樹枝,在冬天的書頁間,像我熟悉的古老象形漢字。
幾乎是兩位作家
翻讀意大利作家翁貝托·埃科的隨筆集《密涅瓦火柴盒》(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感覺很難進入,書中那種浮躁的、光怪陸離的炫耀式筆觸,讓我產生一種天然的拒斥。深究原因,發現這些文字,其實就是“不擁有時間”的文字(作家劉燁園先生的獨特理論)。埃科在寫作它們時,是即時的、喧噪的、走馬觀花的心態——書中所收,均為其人替一家周刊所寫的專欄文章;而缺乏一種“寧靜和專注、空寂和凝視、慢和停駐的時間心態”(劉燁園語)。因為寫作時是“現在進行時的當下心態”,所以,《密涅瓦火柴盒》就無法“擁有時間”。而不“擁有時間”的文字,盡管“妙趣橫生、古怪精靈”,盡管“慧黠機巧、天馬行空”,終究是不具備價值的泡沫。擁有什么樣的“時間心態”,就會寫出什么樣的作品,差異是如此明顯——在我看來,寫出《密涅瓦火柴盒》的埃科,和寫出《玫瑰之名》的埃科,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兩位作家。
郁達夫及其他
郁達夫和王映霞1928年2月在杭州成婚,時郁32歲,王20歲。1940年,兩人離異。1942年,王映霞和時任重慶華中航運局經理的鐘賢道結為連理,婚后育有兩女一子(其中一女夭折)。郁達夫1949年在蘇門答臘島被日本憲兵殺害,終年49歲;鐘賢道1980年病逝于上海,終年72歲;王映霞2000年病逝于杭州,終年92歲。
有訪者晤談鐘、王之女鐘嘉利女士(1945年生于重慶萬州,從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的教職退休),談及郁達夫,她只評以淡淡一句:“他的面相孤薄,一看就是少福之人。”
“云門舞集”林懷民
“中國傳統之博大精深,體系之完整,都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我們不清楚,是因為我們以前沒有去打開這扇門。”臺灣“云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先生,是進入了這扇“門”,并且淋漓地化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功者。
萬物兼為我所備,這句話適用于所有人,但是,面對“為我所備”的“萬物”,真實的情況是,絕大多數人都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百丈懷海叢林要則
百丈懷海禪師(750—814)曾述叢林要則二十條。其中,越出佛界,具普遍意義的要則有(我印象深刻者):
煩惱以忍辱為菩提。
是非以不辨為解脫。
疾病以減食為湯藥。
語言以減少為直截。
學問以勤習為入門。
待客以至誠為供養。
凡事以預立為不勞。
處眾以謙恭為有理。
遇險以不亂為定力。
濟物以慈悲為根本。
覺悟者
真正的覺悟者,對于優秀的同行都有由衷的推崇。像林懷民對邁克爾·杰克遜:“對我來講,他是第一名的。他沒有學過任何東西,他也沒有學過音樂,可他那個節奏感、那個身體的動作,沒話講,沒話講。他真是好!”
真正的覺悟者,在內心深處都對自身有一基本的自信。像楊麗萍評述自己:“我覺得我是一棵草,沒什么魅力。但一粒塵埃也有它的價值。塵埃集合起來才有土地,然后萬物才有生長的可能。”
謙遜。尊重。自信。行動。人的品質。
卓然特立之吾
《焚書》,《藏書》,以剃刀自刎的福建人李贄自取的書名,中國文化中罕見的直接呈現的決絕勇氣。李卓吾,“卓然特立之吾”。“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盲,既中痼疾,則必欲殺我矣,故欲焚之。”這是他的《焚書》。“與世不入”,“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這是他的《藏書》。
錯 ?覺
藝術需要“錯覺”,甚至需要去刻意尋找“錯覺”。“錯覺”是藝術之源,是美之源。“錯覺”能夠超越呆板固執的客觀,使作品進入主觀華美的另一空間,創造性的空間。
私人詞匯庫
一個作家的風格,既指思想、氣質,也指行文與用詞。后者在形式上體現:往往某一作家有他自己固定的句式或慣用的詞語。一座獨特鮮明的私人詞匯庫,讓我們能夠清楚地辨認出一個作家的面目,也是其成熟的真正標志。
兩句話
梵高的話:“在現行社會里,藝術家職業只不過是一只破飯碗。只有忍受面對著的嚴酷現實,你才是好樣的!”
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的話:“美是一種美妙、奇異的東西,藝術家只有通過靈魂的痛苦折磨,才能從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來。”
三種時間
在中醫領域,存在三種時間。
“順時間”:顯示為生老病死。
“無時間”:顯示為長生不老。
“逆時間”:顯示為返老還童。
這三種時間,幾乎涵括了文學作品中所有的時間形態。
寒夜窯火
寒冷深冬,想念昔年遍布故鄉的窯火。
燒制陶器的窯火,用青翠松枝作燃料的窯火。
遍布的、躍動方言俗語的火焰,映紅河流和夜晚,給孤寂清貧的童年以溫暖。
火 ?焰
火焰,私認的圖騰。
火焰,個人血液的組成部分。
蘇軾與博爾赫斯的同一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這是蘇軾在《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杜撰的典故,曾引起歐陽修的驚奇。
卡爾維諾說博爾赫斯:“他的每一個文本都通過援引另一些屬于某個真實或想象的圖書館的書籍,而加倍或多倍地擴大其空間。這些被援引的書籍,要么是古典的,要么是不為人知的,要么根本就是杜撰的。”“他用這一方法寫的第一篇非凡的故事《接近阿爾莫塔辛》于一九四零年在《南方》雜志發表時,讀者竟真的相信這是一篇關于某位印度作者的書評。”
——十一世紀亞洲的蘇軾與二十世紀美洲的博爾赫斯的同一。
兩本書
恰在手旁的兩本書,分別由香港人和上海人所著。港人,是詞人林夕的《我所愛的香港》;滬人,是易學家潘雨廷(1925—1991)的《易與佛教·易與老莊》。林之書,所記為現在進行時的斑斕色相;潘之書,文字與思想則直抵時空的深處。同為漢字書籍,同為誕生于東方大都市的漢字書籍,氣場殊異。
八 ?字
素樸生活,銳意書寫。
語言和情緒也具有能量
臺灣統一企業集團總裁林蒼生,應該算一位獨具個性的企業家。他甚至要求“統一”在生產面包時,須全程播放莫扎特音樂。他如是介紹“統一”的面包生產:“除了原材料不可殘存農藥,生產過程亦不添加防腐劑及人工色素等,這些是‘身的部分。統一的生產線人員都保持快樂的心情與面包對話,這便做到‘心的部分。而在生產面包的過程中,還要全程播放莫扎特的音樂,這已經進入產品‘靈的部分了。科學研究證實,‘在音樂中發酵的面包其酒石酸多了11倍、蘋果酸多了5倍,可提升波動值并增進健康。所以說相同的原材料及設備,由不同的公司來生產,其產品的‘波動值是不同的,這就是‘企業心靈不同而產生的差異。”
由此,想到小時候,老家過年蒸團子時,大人們總要特別叮囑孩子,要說好話,說吉利的話,這樣團子就會蒸得好,蒸出來的團子就會好吃。看來,語言和情緒也具有能量,那些貌似無知無覺的客觀物質——譬如團子和面包——也會接受此類的能量而改變自身。
念
冬日。筆尖應匯聚有強大的生命力。
李安綱論儒釋道
主編“三教九經”叢書的李安綱先生,對儒、釋、道三教的闡釋介紹,通俗而富于己見,茲轉述如下。
儒教之儒,從人,從需,塑造的乃是社會需要之人。
道教之道,從走,從首,是指運思玄想,探求奧秘。
佛教之佛,從人,從弗,弗字即是勿、不,不是人,超越了人,也就是佛了。
概括而言,儒家是現實的,空間的,要求秩序;道教是理想的,時間的,希冀永恒;而佛家是既在現實又在理想,既在時空又超時空。仿佛人之一生,少年充滿幻想近于道;中年講求實際,入于儒;老年虛實參半,喜于佛。
江南團子的柔與剛
江南習俗,冬至日吃團子。江南團子,花色繁多:色分青、白、粉;餡有菜肉、蘿卜絲肉、豆沙、芝麻、花生紅棗等等。甫從蒸籠里蒸熟,熱氣騰騰,晶瑩圓潤——此種食物的陰柔之美,于斯呈現。然而,正是這種外形精致細膩的吃食,較之粥、飯,它又是最為耐饑的——團子內在的剛性,讓人,特別是勞作者,有深刻的體驗。相柔性剛,柔剛一體,江南品質之顯現。
中和之美
中,中和之美,中國傳統的文化理想。中,無不及、無過度之謂。中,即和諧。想到中國、中醫。
掙 ?拔
無論再多的書籍,人和文字,仍應時時不忘掙拔出來,呼吸野氣。
無畏無媚、勇往獨行的野,謹記。
文學的終極目的是什么
文學的終極目的是什么?歲末之問。
在庸常人世、匆匆生命中,尋找到真實的自我?
證明自己活過,存在過?
探究并展示一個孤獨生命的內在宇宙?
發出自己的聲音,尋找到這個星球上的同類?
為人類留存一份特殊個體的感官與思想檔案?
抵抗時間的方式之一?
揭示人世、社會、生活的動人秘密?
孤寂生命的慰藉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