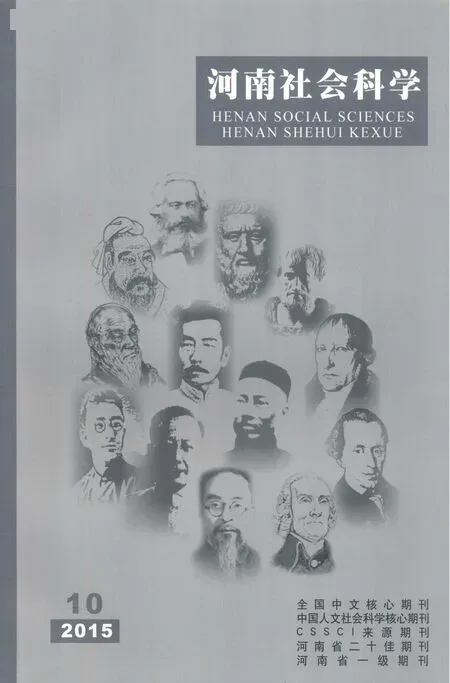葉燮詩性智慧的立論依據與精神旨歸
李鐵青
(曲阜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詩性智慧在中西方的文化傳統中是重要的精神內核和思想根基之一,對于中西文化比較與會通具有重要價值。作為一個重要范疇,詩性智慧由意大利著名學者維柯在《新科學》中首次明確提出。維柯以科學的態度一一探析了“用詩性文字來說話的詩人”[1]所創造的詩性玄學、詩性邏輯、詩性倫理、詩性經濟、詩性政治等“要費大力氣才能懂得”的詩性智慧,并對詩、詩人、詩性、哲學、哲學家、智慧等范疇都進行了闡述。由此,結合中國文化寶庫中豐富的詩性智慧資源以及詩與哲學、詩性與智慧和思想密不可分的歷史傳統,筆者對詩性智慧的內涵界定為:一是詩性智慧是詩與哲學以及智慧的統一,是詩與思的統一,即以“詩”的方式表達“思”的意蘊,將智慧之“思”與詩之“詩性”有機結合,力求實現詩化的智慧與智慧化的詩的完美呈現;二是詩性智慧是天人合一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有機統一,關注人的生命存在價值和意義。
葉燮(1627—1703)作為一名集詩性、智慧、德行于一體的清代文論家,以“詩”的方式表現哲學、智慧之思的深度,身體力行詩化的人生,力求詩與思的統一,不但詩文創作頗豐,而且寫成了系統嚴謹的詩論大著——《原詩》等,展示出了一種積淀與突破貫通的詩性智慧,啟人深思。本文就試著穿越歷史,還原文化情境,以積淀與突破為基點來探析葉燮詩性智慧的立論依據與精神旨歸。
一、對積淀與突破的思考
關于積淀與突破,學界曾進行過深入研究,在對各家的探索與爭鳴加以分析和思考之后,筆者認為,積淀與突破孕育著巨大的文化價值。“文化謂‘積’,由環境、傳統、教育而來,或強迫,或自愿,或自覺,或不自覺。這個文化堆積沉沒在各個不同的先天(生理)和后天(環境、時空、條件)的個體身上,形成各個并不相同甚至迥然有異的‘淀’。于是,‘積淀’的文化心理結構(Cultural-Psychological Formation)既是人類的,又是文化的,從根本上說,它更是個體的。”[2]但僅有積淀,文化不足以傳承、接續和創新。如果文化積淀通過各種方式的積累、吸收、深化,只是停留在量變的基礎上,那就有可能是一種無超越意義的復古或歷史的倒退。因而,文化的突破也就勢在必行,突破是量變基礎上有超越價值的質變,是推動文化發展和繁榮的歷史原動力,是對傳統的創新和復古的批判,是一種思想啟蒙和解放。“因此,文化的突破必須是在深沉厚積基礎上的突破,積淀應該是在不斷變革求新的過程中的積淀……文化的積淀與突破,是人類文化自身的矛盾運動,是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3]
由此,積淀與突破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研究路徑和有益的啟示,即以此來理解一個人、一種理論或范疇的立論依據與精神旨歸。正如陳炎所說:“‘積淀’與‘突破’之最重要的意義……說到底,它涉及人在個體與群體、感性與理性、歷史與未來、創造與享受等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對于自身存在及其意義的理解問題,即涉及所謂‘價值之源’的問題。”[4]從這個意義上講,葉燮作為一個文化個體,面對豐富歷史文化資源與時代、現實的激發,將積淀與突破合理貫通來審視、思考,既是其實現個體價值的途徑,也是其融入人類整體文化寶庫的必由之路。其詩性智慧既是積淀前人研究的“照著講”,也是有所突破創新的“接著講”,其中孕育著巨大的文化價值。
二、積淀與突破:葉燮詩性智慧的立論依據與精神旨歸
(一)價值論與方法論相統一的積淀:葉燮詩性智慧的立論依據
1.對《詩經》等文學經典的積淀
文學經典的學習和繼承是任何從事創作和研究的人所繞不過的一個“存在”。經典不僅可以提供豐富資源的支撐,顯示巨大的價值之用,具有價值論的意義,而且本身就可以成為立論的依據,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由于文學“名著中包含了人的心智賴以獲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好材料”[5],葉燮通過對歷代文學經典的積淀,諸如對歷代作品中所蘊含的風格特征、語言形式、結構等豐厚養分的不斷累積,為其詩文創作和理論建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例如,《原詩》開篇即引《詩經》作為其論述詩歌正變盛衰的依據,如“詩始于《三百篇》……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等。更重要的是,《詩經》作為文學經典,體現了詩性之美與哲思之美的有機統一,其中既有語言精妙、引人想象、意象豐富、怡情悅性、比興并用的詩性之美,也有關注生命體驗、文化意蘊豐富、憂患意識濃郁、雅正中和與可觀、可群、可怨的哲思之美。除《詩經》外,葉燮詩文、詩論中所引用的《離騷》《論語》《孟子》《古詩十九首》《史記》以及杜甫、蘇軾等的文學經典中都有大量的詩性與哲思統一的詩性智慧,這些都為葉燮詩性智慧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立論依據。
2.對古代哲學、文論范疇、命題的積淀
葉燮非常注重對古代哲學、文論的學習積淀,通過對以往諸多范疇、命題的吸納,賦予其新的內涵和意蘊,形成了豐富的詩性智慧。在葉燮的詩文、詩論中,如意、道、變、理、情、言、象、性、法、性情等哲學范疇,形神、虛實、有無、體用、本末等哲學命題,都為其建構理論、展示詩性智慧提供了依據。例如,《易經》中的變、天人合一、仰觀俯察、觀物取象等哲學范疇、命題都給葉燮以巨大影響,為其論述提供了有力支撐。正如有論者指出,“在哲學上,葉燮思想更為復雜。他以儒為主,又綜貫佛老,兼及諸子百家,可說是包羅萬象……在方法論上,葉燮受到儒家的《易經》,道家《老》《莊》,特別是佛家思辨方式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辯證因素”[6]。就其文論思想來說,他對歷代文論范疇、命題基本上都進行了有所創新的繼承。如詩言志、文質觀、溫柔敦厚、成一家之言、作詩者在抒寫性情、三不朽、陳言之務去、詩窮而后工、詩中有畫與畫中有詩等。以“詩言志”為例,葉燮說:“《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為‘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雖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于筆墨之外。”正是有了對“志”的分析、繼承,葉燮才進而提出富有新意的“才、識、膽、力”說來豐富其理論闡述。
此外,他還通過對歷代文論的系統分析,在積淀和揚棄歷代文論的基礎上,“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豐富其詩性智慧。雖然他認為“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如鐘嶸、如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最厭于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但可貴的是,他在對劉勰、嚴羽等文論批判的基礎上進行了積極的繼承和借鑒,取其精華而為其所用。在其詩文、詩論中,葉燮一再引用鐘嶸、劉勰、嚴羽等的理論思想、觀點、詞句,或作為立論的依據,或作為批駁的依據。由于所持的立場、言說方式等不同,評述雖然說有些過激,但從詩道不振的現實弊病和憂患意識出發,他還是對鐘嶸、劉勰、嚴羽等文論中優秀的思想進行了有益的吸納,為其理論體系的構建和詩性智慧的拓展提供了啟迪。例如,劉勰文論的系統性、理論性等對葉燮創建詩論體系的啟發,嚴羽的“以識為主”“妙悟”“本色”“極致”“入神”等對葉燮的影響。又如,葉燮就強調“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后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為其所搖”,主張在文學創作中要“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夫惟神,乃能變化”等。
3.對歷代文藝家偉大人格的積淀
人格與文藝創作關系密切,對創作者詩性才情的形成和哲學思維能力的提升等有巨大影響。葉燮在《南游集序》中說:“然余歷觀古今數千百年來所傳之詩與文,與其人未有不同出于一者,得其一,即可以知其二矣。”接著他通過對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蘇軾等詩文的分析,認為他們“無不文如其詩,詩如其文,詩與文如其人。蓋是其人,斯能為其言;為其言,斯能有其品……近代間有巨子與人判若為二者,然亦僅見,非恒理耳。余嘗操此以求友,得其友,及觀其詩與文,無不合也。又嘗操此以稱其詩與文,誦其詩與文,及驗其人其品,無不合也”[7]。通過對歷代文藝家偉大人格的積淀,葉燮將人格與詩文之品統一、“詩以人見,人以詩見”的創作見識融入其詩性智慧,以此為立論依據,推出了大量與人格相近的范疇,如《原詩》中提到的“胸襟”“品量”“面目”以及“性情”“才、膽、識、力”等,豐富了對于人格、人品與詩文之道的理解,將人格與遠見卓識、性情、才學、膽識、胸懷等統一起來,重視偉大人格的生成和內在涵養的提升,力求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來審視世界萬物。
4.對自然之道的積淀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8]人處于天地之間,在認識、改造自然的同時,自我在自然中得以復觀。中國古代先哲們很早就認識到自然的重要性,在俯仰之間,在遠取與近取中,人與自然得以合一。如孔子所說的“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以及劉勰提出的“江山之助”等。詩文是有限與無限的統一,自然、宇宙中的日月、山川乃至一草一木等都無不蘊藏著濃濃的詩情畫意,給詩人以創作靈思。
僅在《原詩》中,葉燮使用“自然”“天地”二詞就有十多次,如“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克肖其自然”“天地間自然之文”“自然之法立”“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等。葉燮通過對自然、宇宙之道的認識,不僅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胸襟,還以此立論,生發出對于“理、事、情”、詩文之“法”等的創見。此外,葉燮還十分注重在親身實踐的游歷中對自然之道的體悟,他遍游名山大川,其詩文中如黃山、泰山等曾出現過多次,許多理論的闡述就以對山川之體悟立論。葉燮通過游歷對自然之道和“江山之助”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在仰觀俯察中對自然之道加以把握,體悟自然之道所孕育的詩性智慧。恰如《原詩》中所說的“托意于仰觀俯察,宇宙萬匯,系之感憶,而極于死生之痛”“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于筆墨之外”。
5.對深厚家學的積淀
葉燮家學積淀深厚,曾有葉氏一門“七葉成進士”的佳話。其父葉紹袁不僅“處世接物,坦易樂與,而是非必以直。凡地方公事不便者,力言之當事,不市恩,不避怨”[9],而且對儒道釋等思想都有較深研究,編著有《午夢堂集》。其母沈宜修也工詩善文,家學傳承甚好,著有《鸝吹集》,是明代吳江派代表人物沈璟的侄女。根據相關研究,“葉紹袁具有較高的佛學修養……其妻沈宜修也‘究心內典,竺乾秘函,無不披覿;楞伽維摩,朗晰大旨,雖未直印密義,固已不至河漢’。在他們夫妻二人的帶動下,這個家庭‘精心禪悅,庭闈頗似蓮邦’,‘兒女扶床學語,即知以放生為樂’”[10],而且“葉紹袁對蘇軾特別崇慕……甚至夢寐之中都企盼能與蘇軾一見……葉紹袁對杜甫詩中家國深憂的境界也感同身受”[11],這可從葉燮的思想根源于儒道釋及論詩以杜甫、韓愈、蘇軾為宗得到印證。并且,“吳江沈、葉二大家族于明末清初世代聯姻……這種累世婚姻,將家族間的文化、教育方式打通融合,從而影響到文學創作,形成相近的文學創作模式及創作風格。沈、葉二氏才媛中創作成就較高的是沈宜修及其三女——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其中葉小紈創作有雜劇《鴛鴦夢》,“算是中國戲曲史上第一位有作品傳世的女作家”[11]。無疑,世代重視讀書、修身、心懷家國的深厚家學積淀及父母、兄弟姐妹博學有識、皆能賦詩善文的良好家庭氛圍對葉燮日后的思想和人格的形成等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通古今之變與成一家之言相統一的突破:葉燮詩性智慧的精神旨歸
在深厚積淀的基礎上,通古今之變與成一家之言相統一,力求創新和突破,就成為葉燮詩性智慧的精神旨歸。
1.通古今之變的歷史意識和救弊意識合一的突破基點
葉燮通過對歷代經典的積淀,面對現實中存在的是非不辨、蠱惑人心的“虛妄”之學和“遁于考訂證據之學”的弊處,對俗儒、盲目復古者、隨波逐流者等流弊諸多的近代之人進行了無情揭露,顯示出他對于中國古代優良文學傳統的深切呼喚和對于流弊的深惡痛絕。例如,葉燮在《原詩》中不無憂慮地說:“后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嘆于風雅之日衰也!”“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于中心,而時發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為害烈也。”一方面,葉燮的通古(這里的通古一是繼承前人的精華,一是對前人的錯誤觀點進行批判)都是為了解決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針對近代論詩者的流弊而展開的。另一方面,葉燮清醒地認識到其時論詩者與詩人的種種流弊,指出不但“乃近代論詩者……徒自詡矜張,為郛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于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剿獵成說”,而且“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其一好為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腳”。因此,他通過對古今詩歌發展的觀照和對當時詩壇現實的批判,將宏闊的歷史意識與強烈的救弊意識有機統一,構成其詩性智慧的突破基點。
2.成一家之言的突破意識
身處集大成的清代,面對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又親睹清初詩壇的流弊與紛爭,葉燮在深厚積淀的基礎上大膽創新,以強烈的成一家之言的突破意識完成了對詩性智慧的建構。一是重視創作主體或審美主體之“神明”。葉燮在詩文論述中,曾多次使用“神明”。例如,《原詩》中論述創作之法時指出,“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論述創作主體的才、膽、識、力時說“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論及鑒賞詩歌及作詩時說“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在《集唐詩序》中論及審美客體與審美主體之關系時說,“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間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見”,以說明審美客體的美有待于審美主體的創造性發現。綜合起來,葉燮所論述的“神明”實際上就是主體的一種突破意識、創新精神。二是大力標舉“成一家之言”并要求辯證對待。在《原詩》中,葉燮大力標舉“成一家之言”,期望“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提倡“立言者,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等。此外,葉燮還要求辯證對待“成一家之言”,而不能盲從和不加分辨地承襲。在《與友人論文書》中,他主張“謂文章一道不可以一律論,要各成一家之言而止”,反對“用其私智,而能成一家之言,以自鳴于古今者”,認為“仆嘗論古今作者,其作一文,必為古今不可不作之文,其言有關于天下古今者,雖欲不作而不得不作,或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后人不知言之而我能開發言之,故貴乎其有是言也;若前人已言之而我模仿言之,今人皆能言之而我隨聲附和言之,則不如不言之為愈也”[7]。葉燮認為要“成一家之言”,就必須在通古今之變和進行深厚積淀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和發現,具有強烈的自我突破意識,而不是無所依據地機械承襲前人、不知與時俱進和妄言獨辟一家。
3.對至文、至境不懈追求的突破目標
在《原詩》中,有多處對于“至”的表述。例如,“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為至文以立極”“自當求其至極者”“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等。在《原詩》中,有人對葉燮加以發問(此處也可認為是葉燮的自我發問):“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若夫詩,則理尚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征之實事者乎?’。”何謂“詩之至處”以及如何實現,那就需要通過對天地自然間的“‘意象’以及由它所形成的‘境界’的有無互立、虛實相生,一句話,賴其為可能性的言說方式;此不可言說者之被領會,又端賴領會者入于意象之境,結合自身的存在體認,而因有見無,由實至虛”[12]。需要審美主體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感悟能力以感性、詩性思維去帶動邏輯思維,共同參與到認識事物的活動中來,如“詩人”那樣來把握“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去開拓創新,而非如“人人”一般去“一一征之實事”。例如,他對于杜甫詩歌《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中“碧瓦初寒外”的解讀,“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于象,感于目,會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這種審美性解讀充分強調主體“當時之境會”的審美體驗,給了讀者以想象的空間,使讀者對于審美意象經由了一個“呈于象,感于目”而達到“會于心”的過程,領會到不可言說但已心領神會的藝術至境。
4.理論思維與形象思維并舉、理性思辨與詩性語言統一的突破方法
“詩歌是寓于形象的思維”“詩是直觀形式中的真理……因此,詩歌就是同樣的哲學,同樣的思維,因為它具有同樣的內容——絕對真理,不過不是表現在觀念從自身出發的辯證法的發展形式中,而是在觀念直接體現為形象的形式中”[13]。葉燮通過“立象以盡意”,在對大量具體、生動、可觀、可感的形象進行感知的基礎上,以具有豐富、無限意蘊的象征、審美意象來實現對思、道的言說可能性,運用比喻、象征等方法將他的理性思辨寓于詩性的語言之中,實現理論思維與形象思維并舉,使其作品和論述中既有哲性之思,又富有詩性和詩意。葉燮認為,“我今與子以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例如,在論述詩歌本源時,以河流、江海為喻:“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為九河。”在論述唐代詩歌時,以春秋為喻:“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晚唐之詩,秋花也。”在論述詩歌創作時,以建造“大宅”為喻,并細分為基礎、取材、善用、設色、變化五個步驟。可以說,運用這種形象性的比喻使得人們能夠直接獲取感性的信息,調動起了主體在具體語境下的想象力和感悟力,把詩性與哲性、靈性連接了起來。著名學者葉維廉就曾說,“疑問句的分析方法,與兇巴巴而來的權威性的肯定句的分析是不同的;疑問句有待讀者的點頭,葉燮把心感活動非常技巧地還給讀者”“葉燮給了我們非常有效的說明性的批評而無礙于美感經驗呈示之完整,這正是由于他了解到詩的‘機心’”[14]。
三、結語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九章中曾說過“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15]的著名論斷,指明了詩更注重表現帶有普遍性的事情。別林斯基也說過:“一切感情和一切思想都必須形象地表現出來,才能夠是富有詩意的。”[13]歷史總是有驚人的相似,他們對詩歌與哲學、形象、想象與思維等的闡述,或許對于我們理解詩與哲學、智慧以及詩性智慧都不無裨益,這或許是一個新的課題,自不在本文論述范圍之內。回歸到對葉燮詩性智慧立論依據與精神旨歸的分析、解讀,不難看出,葉燮總是在積淀與突破之間詩意地呈現他對萬事萬物以及文藝創作的深刻闡述,總是力求詩與思的統一,探析詩歌與哲學、智慧的合理融合。
今天,面對如此豐富、深厚的古代詩性智慧,我們在認知、理解、現代轉換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將積淀與突破統一起來。依然引用葉燮的話來說,那就是既要明確地認識到“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原詩》),也要學會“能因時而善變,如風雨陰晴寒暑,故日新而不病”(葉燮《黃葉村莊詩序》),更要做到“后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后人,何以竟其引申乎”(《原詩》),努力實現“端緒”與“引申”的統一,盡力克服不知積淀、一味創新突破的“執其源而遺其流”和“得其流而遺其源”的錯誤觀念,在根基深厚的積淀中突破,在有益的突破中積淀。
[1][意]維柯.新科學[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36.
[2]李澤厚.歷史本體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130.
[3]侯傳文.積淀與突破——論上古東方文化的轉型[J].青島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1):79.
[4]陳炎.再論“積淀說”與“突破說”——兼答朱立元、陳引馳先生[J].學術月刊,1995,(1):88.
[5][美]羅伯特·M.赫欽斯.美國高等教育 [M].汪利兵,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4.
[6]蔣凡.葉燮和原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17.
[7]吳宏一,葉慶炳.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C].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267,271—273.
[8]周易[M].郭彧,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304.
[9]叢書集成續編(第124冊)[G].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770.
[10]蔡靜平.明清之際汾湖葉氏文學世家研究[M].長沙:岳麓書社,2008.105.
[11]劉延乾.江蘇明代作家研究[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422—423.
[12]曹順慶,李清良,傅勇林,等.中國古代文論話語[M].成都:巴蜀書社,2001.153—154.
[13]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外國理論家作家論形象思維[Z].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56—58.
[14]葉維廉.中國詩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8.
[15][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M].陳中梅,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