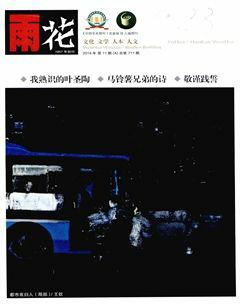我熟識(shí)的葉圣陶
吳泰昌
編者的話:今年是葉圣陶誕辰120周年,紀(jì)念葉老的書(shū)和文章不勝枚舉,但作者的這篇《我熟識(shí)的葉圣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評(píng)傳,不是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評(píng)說(shuō)葉圣陶,而是從自己與晚年葉圣陶近距離交往的獨(dú)特角度,紀(jì)實(shí)、樸實(shí)式地寫(xiě),從一個(gè)側(cè)面具體、真實(shí)地勾勒葉老的人生軌跡,細(xì)節(jié)生動(dòng),有血有肉,幾段往事,若干片斷,就把大師的風(fēng)采描繪得惟妙惟肖,可親可感。
葉圣陶是我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長(zhǎng)期活躍于文壇,因?yàn)楣ぷ麝P(guān)系,我與晚年的葉圣陶老人多有過(guò)從,茲將與其交往的一些片斷錄下,付諸版牘,以饗讀者。
飄浮在眼前的那片白云
拜讀葉圣陶先生的作品,是許多年前的事了,中學(xué)課本上幾乎年年都有他的散文或童話。可親眼見(jiàn)到這位慈祥的老人,卻很晚。1975年年底,我曾在《人民文學(xué)》雜志社工作過(guò)一段時(shí)間,辦公室正在他家的對(duì)面。每天清晨推開(kāi)窗戶,便能見(jiàn)到他家那幢深邃的四合院,看不見(jiàn)什么,庭院中幾棵樹(shù)梢老是那么挺立著,有時(shí)光禿,有時(shí)覆蓋著各種顏色。
記不清頭一次推開(kāi)這扇黝黑沉重的大門(mén)是誰(shuí)介紹的,反正我一直朝院子的里層走,那時(shí)他家還沒(méi)有那只獅子狗,一切都靜悄悄的。
本來(lái)我可以早幾年踏進(jìn)葉家大院,一個(gè)突然的電話,推遲了。那還是在北大上學(xué)時(shí),我們中文系1955級(jí)同學(xué)合伙在編著一部中國(guó)小說(shuō)史。我負(fù)責(zé)撰寫(xiě)清末民初部分,想求教于葉老,冒昧地給他寫(xiě)了信。一封潦草簡(jiǎn)約的信,卻得到了他老人家一封工整的親筆回信,他滿足了我的請(qǐng)求,答應(yīng)約我談?wù)劇<s定的那天中午,我胡亂地吃了飯,打算提前進(jìn)城。想不到,我剛要?jiǎng)由頃r(shí),傳來(lái)系里的電話,是葉老秘書(shū)打來(lái)的,說(shuō)葉老臨時(shí)有會(huì),今天下午沒(méi)有時(shí)間談了,以后再約。當(dāng)時(shí)我想不到再寫(xiě)信或打電話催問(wèn),只于等著“另約”,直至以后再?zèng)]有下文。
我坐在北屋客廳的沙發(fā)上,懇請(qǐng)葉老賜稿。他聽(tīng)我講,不時(shí)地點(diǎn)頭。滿子大嫂及時(shí)地遞了一杯熱茶。葉老先不回答寫(xiě)文章的事,喜歡問(wèn)問(wèn)這,問(wèn)問(wèn)那。至善在家,有時(shí)也從他的臥室出來(lái)一同聊聊,氣氛是親切隨意的。往往在我告辭時(shí),葉老會(huì)問(wèn)我稿子最晚幾號(hào)要。看著他那副認(rèn)真勁,我不好意思虛著說(shuō)了。葉老答應(yīng)了的稿子總會(huì)提前寫(xiě)好,信封裝著,或由家人送給我,或我自己來(lái)取。每次稿子里,幾乎都夾有一封短信,客氣地說(shuō)有不妥處請(qǐng)貴刊酌處,還有葉老對(duì)版面格式的要求。當(dāng)然也有約不到的時(shí)候,他說(shuō)這個(gè)內(nèi)容剛給某家報(bào)紙寫(xiě)了,重復(fù)再寫(xiě)沒(méi)有必要,答應(yīng)有合適的題目另給我們寫(xiě)。接著又是親切隨意地閑談,我手中同樣能得到一杯熱騰騰的青茶。去葉家次數(shù)多了,有時(shí)竟忘了面對(duì)的是一位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壇德高望重的大作家。有公事沒(méi)公事,只要是時(shí)間合適,不影響老人休息,我就愛(ài)進(jìn)去坐坐。
那些年,說(shuō)不上去過(guò)葉老家多少次,和這座大四合院以及大四合院里的主人漸漸熟悉起來(lái),可我卻沒(méi)有認(rèn)真地參觀過(guò)庭院里的東房、西房,前院、后院。直到有次我猛然見(jiàn)到大門(mén)墻上掛有文物保護(hù)單位的牌子,才知道葉家大院是座有來(lái)歷、保存完好并頗具北京古色古香風(fēng)韻的四合院。我去后進(jìn)照顧葉老的阿姨住處看了看,那幽靜的氛圍,使我強(qiáng)烈地感到阿姨和葉老全家的和諧融洽。阿姨照料葉老已幾十年了,葉家大院就像她自己的家。她能做出葉老愛(ài)吃的多種下酒菜,葉家大院里流淌的就是這人與人之間純真的情意。
有一次去看望冰心老太太。家里人告訴我,老太太知道葉老去世后很傷心,提醒我千萬(wàn)別同老人提起葉老。冰心躺在床上,我坐在旁邊,同她談天。她卻主動(dòng)談起了葉老。她說(shuō):在她熟悉的作家中,葉老做事是最認(rèn)真的,為人是最可信賴(lài)的。她這種印象我是從心底里贊同的。1984年我為《文匯報(bào)》開(kāi)了“書(shū)山偶涉”專(zhuān)欄,頭一篇《最早評(píng)論<子夜)的文字》,介紹1933年1月出版的《中學(xué)生》雜志上關(guān)于茅盾長(zhǎng)篇小說(shuō)《子夜》的一則提要。我在文中說(shuō)提要“很可能出自開(kāi)明書(shū)店的主要編輯,也是當(dāng)時(shí)《中學(xué)生》雜志的主要編輯葉圣陶之手”。這篇短文發(fā)表后家里人念給葉老聽(tīng)了,有次我去看他,還沒(méi)坐定,他從臥室里走出來(lái),頭一句話就對(duì)我說(shuō):“我想了想,關(guān)于《子夜》的介紹,不一定是我寫(xiě)的,很可能是徐調(diào)孚先生寫(xiě)的。徐先生已過(guò)世,你下次寫(xiě)文章說(shuō)明一下。”
葉老那些年數(shù)次住院,時(shí)間最長(zhǎng)的一次有三、四個(gè)月。怕打擾他,我很少去看他。聽(tīng)說(shuō)他那時(shí)心情煩躁,視力聽(tīng)覺(jué)均不好,我急忙從崇文門(mén)花店買(mǎi)了一束鮮花前往。他明顯消瘦疲倦,但聲音仍洪亮,問(wèn)我這花是誰(shuí)送的?我說(shuō)是我送的,他說(shuō)謝謝。我知道他問(wèn)這話的意思,因?yàn)檫h(yuǎn)在上海的巴金先生,有次聽(tīng)說(shuō)他住院了,曾囑我代他送過(guò)一束鮮花。葉老說(shuō)巴金自己身體也不好,還惦念他,高興得當(dāng)日寫(xiě)詩(shī)“巴金兄托泰昌攜花問(wèn)疾作此奉酬”。1987年,葉老青年時(shí)執(zhí)教過(guò)的江蘇吳縣角直鎮(zhèn)小學(xué)要為他建立一個(gè)紀(jì)念室,他不同意,說(shuō)當(dāng)初的事是和幾位朋友一起做的,成績(jī)不能全歸到他身上。我記得至善曾給我葉老寫(xiě)的一份聲明,說(shuō)如果紀(jì)念室真建立了,就發(fā)表。
我為葉老拍過(guò)好些照片,最后一張是1987年5月28日我訪問(wèn)港澳回來(lái),恰巧至誠(chéng)從南京來(lái)了,我們?cè)谠鹤永锱牧怂摹⑽鍙垺N业臄z影技術(shù)不高,但每次都能將給我印象最深的葉老那一雙濃重的眉毛清晰地拍下來(lái)。我特別喜愛(ài)老人眉梢上雪白的兩片,靠近他時(shí)常久久地盯住那潔白如云的兩片。
1988年2月16日上午,我得悉葉老謝世的噩耗趕到葉家大院,一切都靜悄悄的。我坐在往常坐慣了的沙發(fā)上,手中依然有一杯熱騰騰的青茶。我忘了該向至善等說(shuō)些安慰的話,我在回想,回想,眼前飄浮著那片白云。
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起葉老,眼前還會(huì)飄浮起那片白云……
葉圣陶閑談五四文壇前后
忘記是誰(shuí)說(shuō)過(guò),有的人的經(jīng)歷,本身就是一頁(yè)真實(shí)可貴的歷史資料。也許正是受這種說(shuō)法的影響,1979年,五四運(yùn)動(dòng)六十周年前夕,我特意兩次走訪大病初愈的葉老,文藝界尊敬的葉圣陶老人。
葉老已是近八十五歲高齡的人了。他比郭沫若小兩歲,比茅盾大兩歲,是當(dāng)時(shí)健在的我國(guó)現(xiàn)代有重要成就和影響的作家中最年長(zhǎng)的一位。他有長(zhǎng)久的創(chuàng)作歷史。五四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初期,他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員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發(fā)起人之一。上世紀(jì)2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說(shuō)集《隔膜》(1919—1921年)、《火災(zāi)》(1921—1923年)、《線下》(1923—1924年)、《城中》(1923—1926年),長(zhǎng)篇小說(shuō)《倪煥之》(1928年)等。葉圣陶開(kāi)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涉及的門(mén)類(lèi)多,除小說(shuō)外,還寫(xiě)新詩(shī)、散文、兒童文學(xué)、文藝雜論等,但初期以小說(shuō)為主。可以說(shuō),他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上的突出成就,是五四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最初收獲的一部分。
是一個(gè)暖得要人脫下棉衣的北京的春日,雖然已是下午四點(diǎn)多了,當(dāng)踏進(jìn)葉老住宅的大門(mén)時(shí),我還是遲疑了一下。一個(gè)多月前,在我江南之行的前一天,也是這個(gè)時(shí)辰,我去看望過(guò)他。葉老身體、精神一向很好,自1978年7月因病住院手術(shù)后,雖然療養(yǎng)得不錯(cuò),也很難與從前相比了。他告訴我,精神還好,只是視力愈來(lái)愈差了。那天恰好一位老朋友來(lái)看他剛走,他有點(diǎn)疲倦。我只匆匆將來(lái)意說(shuō)明,不忍心再打擾他,約定返京后來(lái)談。今天,雖然已事先約好,我比預(yù)定的時(shí)間還是晚到了,我想讓他多休息一會(huì)兒,使他更有精神來(lái)回憶一些有意義的往事。我進(jìn)門(mén)時(shí),葉老已端坐在沙發(fā)上,他急切地問(wèn)我這次在滬、寧、杭一帶見(jiàn)到的那些他的老朋友,他們的近況怎樣。當(dāng)談起郭紹虞時(shí),他笑著說(shuō),“‘五四那年,我同他都不在北京……”我們的談話,就這樣開(kāi)始了。
葉老說(shuō),五四運(yùn)動(dòng)發(fā)生的時(shí)候,他在蘇州角直鎮(zhèn)任吳縣第五高等小學(xué)教員。甪直是水鄉(xiāng),在蘇州東南,距離三十六里,只有水路可通,遇到逆風(fēng),船要?jiǎng)澮惶臁I虾5膱?bào)紙,要第二天晚上才能看到。教師們從報(bào)紙上看到了北京和各地集會(huì)游行和罷課罷市的情形,當(dāng)然很激奮,大家說(shuō)應(yīng)該喚起民眾,于是在學(xué)校門(mén)前開(kāi)了一個(gè)會(huì)。這樣的事在角直還是第一次,鎮(zhèn)上的人來(lái)得不少。后來(lái)下了一場(chǎng)雨,大家就散了。這一段經(jīng)過(guò),他寫(xiě)在《倪煥之》第十九節(jié)里,不過(guò)不是記實(shí)。說(shuō)到這里,葉老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寫(xiě)小說(shuō)不是寫(xiě)日記,不是寫(xiě)新聞報(bào)道,如果說(shuō)小說(shuō)中的某人就是誰(shuí),小說(shuō)中的細(xì)節(jié)都跟當(dāng)時(shí)的情景一模一樣,那就不對(duì)了。葉老這幾句話是有所感而發(fā)的。《倪煥之》是我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的一部名著。1928年在《教育雜志》上連載,1929年8月出單行本。不及一年,就印了三版,可見(jiàn)當(dāng)時(shí)影響之大。最近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又重印了這本書(shū)。有的研究者認(rèn)為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shuō),葉老不同意這種意見(jiàn)。我不止一次聽(tīng)他說(shuō)過(guò),《倪煥之》描寫(xiě)的內(nèi)容是有生活依據(jù)的,但決不是他個(gè)人生活經(jīng)歷的實(shí)錄,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而不是日記。葉老接著說(shuō),當(dāng)時(shí)大家沒(méi)有做宣傳工作的經(jīng)驗(yàn),雖然講得激昂慷慨,可是在角直這樣一個(gè)鎮(zhèn)上,群眾的反應(yīng)不會(huì)怎么大是可想而知的。
關(guān)于五四運(yùn)動(dòng)的影響,葉老說(shuō),“五四”提出了外御強(qiáng)權(quán)、內(nèi)除國(guó)賊的口號(hào),提出了要民主、要科學(xué)的口號(hào),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知識(shí)青年來(lái)說(shuō),影響是很大的,他肯定也受到影響,但是說(shuō)不清具體是什么樣的影響,那影響有多大。他說(shuō),關(guān)于這類(lèi)問(wèn)題,有的人能自覺(jué),有的人卻不自覺(jué)或不太自覺(jué),他是屬于不太自覺(jué)的一類(lèi),這只好讓研究的人從他當(dāng)時(shí)的言行和文章中去考察了。
葉老對(duì)“五四”前后的文藝期刊是很熟悉的。他說(shuō),民國(guó)初年的期刊,消遣性質(zhì)的多于政治性質(zhì)的,所以小說(shuō)期刊居多,出版幾乎集中在上海。“五四”前夕,全國(guó)各地出版期刊成為風(fēng)氣,大多討論政治問(wèn)題、思想問(wèn)題、社會(huì)問(wèn)題。“五四”以后,各地的期刊就更多了。在1958年和1959年,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研究室出版過(guò)《五四時(shí)期期刊介紹》三厚冊(cè),真可謂洋洋大觀。這些期刊大多是青年學(xué)生主辦的,還有比較進(jìn)步的教員。這表示中國(guó)的青年覺(jué)醒了,開(kāi)始登上思想政治舞臺(tái)了,這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有關(guān),跟十月社會(huì)主義革命的勝利有關(guān)。
談到新潮社,葉老說(shuō),新潮社成立于“五四”前夕,是北京大學(xué)的學(xué)生組織,1919年1月開(kāi)始出版《新潮》月刊。他的幼年同學(xué)顧頡剛當(dāng)時(shí)在北大上學(xué),是新潮社的社員,寫(xiě)信到角直約他給《新潮》寫(xiě)些小說(shuō),還邀他參加新潮社。葉老先后寄去了幾篇小說(shuō),第一篇刊登在《新潮》第1卷第3期上,篇名是《這也是一個(gè)人!》,后來(lái)編入集子,改為《一生》。在《新潮》上,葉老還發(fā)表過(guò)幾篇關(guān)于小學(xué)教育和語(yǔ)文教學(xué)的論文。葉老說(shuō):“大概是在《新潮》上刊登了文章的緣故,就有不相識(shí)的人寫(xiě)信到角直來(lái)了,振鐸就是其中的一位。這種尋求朋友的風(fēng)氣,在當(dāng)時(shí)是很盛行的。后來(lái)振鐸和朋友們?cè)诒本┗I備組織文學(xué)研究會(huì),寫(xiě)信邀我列名為發(fā)起人。”
葉老說(shuō),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宣言刊登在《小說(shuō)月報(bào)》第12卷第1期上,其時(shí)是1921年年初。發(fā)起人一共十二個(gè),只有郭紹虞是他小時(shí)候的朋友,其他八位是后來(lái)才見(jiàn)面的,還有蔣百里和朱希祖,根本沒(méi)見(jiàn)過(guò)。葉老說(shuō):“文學(xué)研究會(huì)標(biāo)榜‘為人生的文學(xué),似乎很不錯(cuò)。但是‘為人生三個(gè)字是個(gè)抽象的概念,大家只是籠統(tǒng)地想著,彼此又極少共同討論,因而寫(xiě)東西,發(fā)議論,大家各想各的,不可能一致。”
《小說(shuō)月報(bào)》始刊于1910年7月,是民國(guó)初年和五四運(yùn)動(dòng)以后影響很大的文學(xué)刊物。葉老說(shuō),“五四”之后,原來(lái)的《小說(shuō)月報(bào)》受到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沖擊,不大受歡迎了。商務(wù)印書(shū)館要跟上潮流,從1921年的第12卷開(kāi)始,改由沈雁冰主編。葉老回憶說(shuō):“也是振鐸來(lái)信,說(shuō)《小說(shuō)月報(bào)》將要改弦更張,約我寫(xiě)稿。我在1920年10月寫(xiě)了一篇《母》寄去。這篇小說(shuō)署名是葉紹鈞,發(fā)出來(lái)的時(shí)候,雁冰加上了簡(jiǎn)短的贊美的話,怎么說(shuō)的,現(xiàn)在記不清了。”
葉老在“五四”之前就寫(xiě)小說(shuō)了。據(jù)他自己回憶,大約始于1914年,其時(shí)他二十歲。上海有一種周刊叫《禮拜六》,他先后投稿有十篇光景,第一篇是《窮愁》,后來(lái)收在《葉圣陶文集》第三卷里。《禮拜六》的編者是王鈍根,他并不相識(shí),稿子寄去總登出來(lái),彼此也不寫(xiě)什么信。《禮拜六》的封面往往畫(huà)一個(gè)時(shí)裝美女,作者是畫(huà)家丁聰?shù)母赣H丁悚。
葉老說(shuō),當(dāng)時(shí)的各種小說(shuō)期刊,多數(shù)篇用文言,少數(shù)篇用白話。他記得給《禮拜六》的小說(shuō)除了用文言寫(xiě)的,也有一兩篇用白話寫(xiě)的。最近有人查到上海出版的《小說(shuō)叢報(bào)》上有葉老在1914年寫(xiě)的兩篇小說(shuō),也是文言寫(xiě)的,篇名是《玻璃窗內(nèi)之畫(huà)像》和《貧女淚》。葉老完全忘了這兩篇了。他只記得《小說(shuō)叢報(bào)》的主編是徐枕亞。徐枕亞是后來(lái)被稱(chēng)為鴛鴦蝴蝶派的主要角色。
葉老記得上海出版的《小說(shuō)海》也刊登過(guò)他的兩篇小說(shuō),可是忘了篇名。最近有人查到了,是《倚閭之思》和《旅窗心影》。葉老說(shuō),《旅窗心影》原來(lái)是投給《小說(shuō)月報(bào)》的。當(dāng)時(shí)主編《小說(shuō)月報(bào)》的是惲鐵樵。惲鐵樵喜歡古文,有鑒賞眼光,他認(rèn)為這一篇有可取之處,可是刊登在《小說(shuō)月報(bào)》還不夠格,就收在也是他主編的《小說(shuō)海》里。他還寫(xiě)了一封長(zhǎng)信給葉老,談?wù)撨@篇小說(shuō)的道德內(nèi)容。葉老說(shuō),魯迅先生的文言小說(shuō)《懷舊》就是發(fā)表在《小說(shuō)月報(bào)》上的,署名周逴。惲鐵樵對(duì)這篇小說(shuō)極為欣賞,加上了好些評(píng)語(yǔ),指出他所見(jiàn)到的妙處。如果現(xiàn)在能找到這一期《小說(shuō)月報(bào)》來(lái)看看,葉老認(rèn)為是蠻有意思的。葉老跟惲鐵樵通過(guò)信,沒(méi)見(jiàn)過(guò)面。惲鐵樵后來(lái)離開(kāi)商務(wù)印書(shū)館去行醫(yī)了,很有點(diǎn)名氣,診費(fèi)相當(dāng)高。我曾查找到惲鐵樵對(duì)魯迅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shuō)《懷舊》的評(píng)語(yǔ),并用大字抄錄,送給葉老和葉至善看,編者焦森(即惲鐵樵——引者)在篇末附志:“實(shí)處可致力、空處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誤、靈機(jī)人所固有、非難事也。曾見(jiàn)青年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饾訂、無(wú)有是處、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原標(biāo)點(diǎn)未改——引者)。葉老說(shuō)惲鐵樵的這段文字他以前看過(guò)。辛亥革命時(shí)魯迅年僅三十一,留傳下來(lái)的這一時(shí)問(wèn)的文學(xué)作品極少。客觀地說(shuō),《懷舊》在當(dāng)時(shí)的影響不太大,但對(duì)魯迅來(lái)說(shuō)這是一次良好的訓(xùn)練,對(duì)他1918年創(chuàng)作白話短篇小說(shuō)《狂人日記》有重要幫助。對(duì)惲鐵樵編輯改革前的《小說(shuō)月報(bào)》,葉老說(shuō)“惲鐵樵對(duì)于小說(shuō)創(chuàng)作,態(tài)度嚴(yán)肅,主張下筆必須鄭重考慮”。據(jù)說(shuō)有人和他開(kāi)玩笑:“這不是小說(shuō),簡(jiǎn)直成為大說(shuō)了。”惲鐵樵對(duì)來(lái)稿處理認(rèn)真。對(duì)青年投稿者也熱情。葉老最初向《小說(shuō)月報(bào)》投稿也得到他的鼓勵(lì)。葉圣陶認(rèn)為,惲鐵樵對(duì)我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發(fā)展,作過(guò)貢獻(xiàn)。
談?wù)劜挥X(jué)已近七時(shí),葉老的談興不減。葉老的長(zhǎng)子葉至善暗示我,談話該結(jié)束了。今天,還有以后多次,我隨著葉老從他熟悉的通道漫游了“五四”前后中國(guó)文壇的一角,大長(zhǎng)見(jiàn)識(shí)。葉老在我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園地里辛勤扎實(shí)地耕耘了半個(gè)多世紀(jì),他的豐富的記憶,是十分值得記錄下來(lái)的。這將是研究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葉圣陶瑣談《詩(shī)》
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伊始,全國(guó)各地期刊紛起,唯缺少一本專(zhuān)門(mén)刊載新詩(shī)的刊物。1922年元月,《詩(shī)》在上海誕生,《詩(shī)》月刊是我國(guó)第一份專(zhuān)載新詩(shī)、譯詩(shī)和詩(shī)評(píng)的雜志。
在《詩(shī)》即將創(chuàng)刊時(shí),葉圣陶和劉延陵商量在一些報(bào)刊上作些宣傳,為新詩(shī)吶喊,為《詩(shī)》創(chuàng)刊造勢(shì)。葉老曾談到,他用筆名在《文學(xué)旬刊》上連續(xù)發(fā)表了四篇短論。葉至善在《父親長(zhǎng)長(zhǎng)的一生》中介紹了這四篇短論,“《就是這樣了么?》,說(shuō)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不該像潮水似的出現(xiàn)低潮,不該才出了一兩種雜志就感到滿足。《盼望》,說(shuō)在報(bào)紙上看到《詩(shī)》將創(chuàng)刊,盼望這個(gè)刊物能向人們解釋清楚,什么是詩(shī),能喚起許多新詩(shī)人,來(lái)供給人們精神上的必需品。《骸骨的迷戀》,據(jù)理駁斥了東南大學(xué)《南高月刊詩(shī)學(xué)研究號(hào)》對(duì)新詩(shī)的挑釁性攻擊,他們反對(duì)博采新鮮的口語(yǔ)和自由的形式,認(rèn)為只有搬弄舊詞藻,遵守老格律,拼湊出來(lái)的才可以稱(chēng)作詩(shī)。《對(duì)鸚鵡的箴言》,希望寫(xiě)詩(shī)的人,能唱出自己心底的真切呼聲,不要跟著已經(jīng)成名的少數(shù)新詩(shī)人鸚鵡學(xué)舌。”(葉至善:《父親長(zhǎng)長(zhǎng)的一生》,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
《詩(shī)》問(wèn)世前,葉圣陶在上海報(bào)紙上寫(xiě)了《詩(shī)》創(chuàng)刊預(yù)告。1921年10月18、19、20日連續(xù)三天,上海《時(shí)事新報(bào)》副刊《學(xué)燈》刊登了葉圣陶寫(xiě)的《(詩(shī))底出版底預(yù)告》,形式很特別,是用一首短詩(shī)寫(xiě)的:
舊詩(shī)的骸骨已被人扛著向張著口的墳?zāi)谷チ恕?/p>
產(chǎn)生了三年的新詩(shī)還未曾能向人們說(shuō)話呢。
但是有指導(dǎo)人們的潛力的,誰(shuí)能如這個(gè)可愛(ài)的嬰兒呀?
奉著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誰(shuí)又能如這個(gè)嬰兒的美麗呀?
我們擬造這個(gè)名為《詩(shī)》的小樂(lè)園做他的歌舞養(yǎng)育之場(chǎng),
疼他愛(ài)他的人們快盡他們的力來(lái)捐些糖食花果呀!
本刊一月一期。創(chuàng)刊號(hào)明年一月一日出版。來(lái)稿歡迎,請(qǐng)寄本報(bào)《學(xué)燈》轉(zhuǎn)新詩(shī)社。
這則預(yù)告其實(shí)是《詩(shī)》月刊的“征稿之詩(shī)”(葉圣陶語(yǔ))。
創(chuàng)刊號(hào)1月15日出版,月刊,第1卷五期。第2卷次年四月十五日始,出兩期,共七本。每期發(fā)行約千余份。創(chuàng)刊號(hào)兩個(gè)月后曾再版一次。《詩(shī)》在倡導(dǎo)新詩(shī)上頗有功績(jī)。它的撰稿人有胡適、劉半農(nóng)、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俞平伯、朱自清、葉圣陶、王統(tǒng)照、郭紹虞、劉延陵、顧頡剛、康白情、馮文炳(廢名)、徐玉諾、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應(yīng)修人等人。陣容宏大,推動(dòng)新詩(shī)發(fā)展,影響深遠(yuǎn)。
《詩(shī)》的創(chuàng)刊號(hào)版權(quán)頁(yè)上注明“編輯兼發(fā)行者”是“中國(guó)新詩(shī)社”,葉老說(shuō),這是虛設(shè)的,并非真有這么一個(gè)實(shí)際存在的文學(xué)組織。《詩(shī)》的編者,或“中國(guó)新詩(shī)社”的成員,就是朱自清、葉圣陶、劉延陵三人。實(shí)際負(fù)責(zé)編輯工作的是葉、劉。編輯者除選定編好稿件,每期還要分頭將刊物分發(fā)給作者和讀者,并處理寫(xiě)信封、貼郵票等一切雜務(wù)。《詩(shī)》三號(hào)、四號(hào)封二刊登的記者所寫(xiě)《投稿諸君鑒》中說(shuō):“本刊系我們?nèi)龜?shù)同志所辦”,“今請(qǐng)以后諸君惠稿,都寄蘇州角直葉圣陶收,或杭州第一師范轉(zhuǎn)劉延陵收”。第四號(hào)收稿處為“蘇州大太平巷五十號(hào)葉圣陶;杭州第一師范轉(zhuǎn)劉延陵收”。第五號(hào)又申明“收稿處——蘇州大太平巷五十號(hào)葉圣陶;杭州第一師范轉(zhuǎn)劉延陵”,二卷第一號(hào)收稿處僅“上海閘北永興路八十八號(hào)弄內(nèi)第四家葉圣陶”。朱、葉、劉都是文學(xué)研究會(huì)會(huì)員。1921年秋,朱、葉、劉同任教于上海吳淞中國(guó)公學(xué)中學(xué)部,朱與劉是蘇北老鄉(xiāng),早就要好,朱自清來(lái)吳淞公學(xué)中學(xué)部任教,是劉延陵介紹來(lái)的,葉圣陶是學(xué)校聘請(qǐng)的,沒(méi)有人介紹。經(jīng)朱的介紹,葉、劉相識(shí)。出于對(duì)新詩(shī)的共同愛(ài)好,他們商定辦一個(gè)專(zhuān)刊新詩(shī)的雜志。秋末,他們?nèi)フ疑虾V腥A書(shū)局編輯部負(fù)責(zé)人左舜生(左也寫(xiě)新詩(shī))洽談,書(shū)局允諾承印,但不給稿費(fèi),每期僅送刊物部分(編者曾在刊物上公開(kāi)講明:“本刊每期出版,中華書(shū)局都以數(shù)十冊(cè)交同人分贈(zèng)投稿諸君;同人所能報(bào)答諸君盛意者不過(guò)如此”)。
創(chuàng)刊時(shí),編者未署“文學(xué)研究會(huì)”,是因?yàn)獒j釀辦這個(gè)刊物,不是文學(xué)研究會(huì)研究決定的,而是憑幾個(gè)人的興致弄起來(lái)的。第四號(hào)起編者改為“文學(xué)研究會(huì)”,據(jù)葉圣陶回憶,這是鄭振鐸的動(dòng)議。鄭振鐸是文學(xué)研究會(huì)最初的發(fā)起人,葉圣陶是文學(xué)研究會(huì)正式成立時(shí)的十二位發(fā)起人之一。在成立會(huì)上,鄭當(dāng)選為書(shū)記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經(jīng)管會(huì)務(wù)。新詩(shī)當(dāng)時(shí)頗遭守舊派的非難,鄭振鐸所編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文學(xué)旬刊》為新詩(shī)大聲吶喊。《詩(shī)》辦起來(lái)了,有相當(dāng)?shù)挠绊懀幷吆投辔蛔髡哂质俏膶W(xué)研究會(huì)的成員,將它改為“會(huì)刊”,加強(qiáng)新詩(shī)的陣地,是順理成章的事。第四號(hào)編者寫(xiě)的《讀者賜覽》中說(shuō):“現(xiàn)因本刊創(chuàng)辦人都是文學(xué)研究會(huì)底會(huì)員,故大家協(xié)議,將本刊作為文學(xué)研究會(huì)定期出版物之一。”從1卷第4期起版權(quán)頁(yè)編者署為“文學(xué)研究會(huì)”,為鄭重起見(jiàn),版權(quán)頁(yè)上還貼了文學(xué)研究會(huì)版權(quán)印花,印花上注明“文學(xué)研究會(huì)版權(quán)所有”。第五號(hào)封面上標(biāo)明“文學(xué)研究會(huì)定期刊物之一”。署為文學(xué)研究會(huì)辦之后,編者想增強(qiáng)論爭(zhēng)性,第四號(hào)《編輯余談》中說(shuō):“《學(xué)衡》雜志里常常有反對(duì)新詩(shī)的文章,有許多,已經(jīng)被《文學(xué)旬刊》駁過(guò)。最近《學(xué)衡》第六期里又翻譯了美國(guó)某教授底一篇《論新》,其中也說(shuō)到新詩(shī)。本刊第5期里將有一篇文字和他為有趣味的商酌;不妨在此預(yù)告一聲。”可惜,由于“作者患病”,這篇文章第五號(hào)未見(jiàn)。
葉老說(shuō),《詩(shī)》創(chuàng)辦雖是幾個(gè)人辦起來(lái)的,但決不是同人刊物,只刊我們幾個(gè)人的作品,雖然后編者署文學(xué)研究會(huì),是文學(xué)研究會(huì)定期刊物之一,但也決不是只刊文學(xué)研究會(huì)會(huì)員的作品。《詩(shī)》的編者在一卷第四號(hào)上就公開(kāi)表明了這一心跡:“我們并不愿意專(zhuān)門(mén)把自家?guī)讉€(gè)朋友底稿件顛來(lái)倒去地登載;如果讀者有佳妙之作寄來(lái),我們總當(dāng)盡先采用。”有言,有行。是期卷首發(fā)表了幾位陌生作者的作品,編者說(shuō)“我們故意把這些新的投稿者底作品編在頭上,用以表示我們的熱烈的歡迎”。
葉老說(shuō),《詩(shī)》終刊,沒(méi)有什么特別的原因。人手少,原來(lái)的幾位都分散到各地了,基本上就我一個(gè)人在支撐,而且我又有新的單位要去服務(wù),加上好的稿件來(lái)源不足,經(jīng)濟(jì)上也拮據(jù),不僅作者無(wú)稿費(fèi),做編輯等雜務(wù)事所用也自費(fèi),難以繼續(xù),所以辦完《詩(shī)》二卷第2期后就自動(dòng)停辦了。
我對(duì)朱自清、葉圣陶的創(chuàng)作業(yè)績(jī)還算了解,對(duì)劉延陵卻知之甚微。我向葉老討問(wèn)劉延陵的情況,葉老說(shuō),“在辦《詩(shī)》期間,我同劉聯(lián)系較多。延陵說(shuō)他的祖籍是安徽皖南旌德的,先輩才移居到江蘇泰興。我們?nèi)四挲g相差上下。編《詩(shī)》刊過(guò)程中,劉做了許多實(shí)際工作。”朱自清1935年在編選的《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詩(shī)集》中對(duì)劉有過(guò)評(píng)介,他叫我看看,朱自清在《選詩(shī)雜記》中談到《詩(shī)》創(chuàng)刊時(shí)說(shuō),“幾個(gè)人里最熱心的是延陵,他費(fèi)的心思和工夫最多。”葉老還說(shuō),延陵當(dāng)時(shí)在新詩(shī)作者中有影響,發(fā)表了不少新詩(shī),和翻譯外國(guó)詩(shī)的作品。朱自清在《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詩(shī)集》中,就收錄過(guò)劉延陵的新詩(shī)(經(jīng)查系為《海客的故事》和《水手》二首——作者注)。阿英在編選的《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史料·索引》集《作家小傳》部分中,在介紹為數(shù)不多的作家中,就有劉延陵的簡(jiǎn)介:“劉延陵,文學(xué)研究會(huì)干部、詩(shī)人。江蘇人。所作詩(shī)大都發(fā)表于《小說(shuō)月報(bào)》《詩(shī)》《文學(xué)周刊》。”葉老有點(diǎn)高興地說(shuō),他也喜歡劉的詩(shī),特別是他的一些小詩(shī),上世紀(jì)30年代的中學(xué)課本幾乎都選有他的詩(shī),最常見(jiàn)的是那首十一行不足八十字的《水手》。葉老曾寫(xiě)過(guò)《劉延陵的(水手)》。葉至善拿出葉老的《文章例話》給我看,書(shū)是1937年2月由開(kāi)明書(shū)店出版的。葉圣陶1936年12月20日在該書(shū)《序》中說(shuō),“今年《新少年》雜志創(chuàng)刊,朋友說(shuō)其中應(yīng)該有這么一欄,選一些好的文章給少年們讀讀”,“欄目叫做文章展覽。現(xiàn)在匯編成這本小書(shū),才取了《文章例話》的名稱(chēng)。”《例話》評(píng)介的“好文章”依次有《朱自清的(背影>》《夏丐尊的(整理好了的箱子)》《茅盾的(浴地速寫(xiě))》《俞慶棠的<一封公開(kāi)信>》《巴金的(朋友>》《魯迅的(看戲)》《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劉延陵的<水手>》《周作人的<小河>》《豐子愷的<現(xiàn)代建筑的形式美)》《蘇雪林的(收獲)》《趙元任的(科學(xué)名詞跟科學(xué)觀念)》《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夏衍的(包身工)》《郭沫若的(癰>》《沈從文的<辰州途中)》《韜奮的(分頭努力)》《丁西林的<壓迫)》《蕭乾的<鄧山東)》《老舍的<北平的洋車(chē)夫)》《蔡元培的<杜威博士生日演說(shuō)詞)》《徐盈的<從滎陽(yáng)到汜水)》《胡愈之的(青年的憧憬)》《尤炳圻的<楊柳風(fēng))序》。葉老說(shuō),《詩(shī)》的頭幾期部分是延陵負(fù)責(zé)編的,后來(lái)他兼職工作忙,參加的具體編輯工作就漸漸少了,有時(shí)寄點(diǎn)作品來(lái),甚至沒(méi)有了,后幾期肯定是我負(fù)責(zé)編輯的。能確認(rèn),《詩(shī)》最后兩期(即第二卷第一號(hào),第二卷第二號(hào))的《編輯余談》是葉圣陶寫(xiě)的(現(xiàn)已收入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葉圣陶集》第18卷廣告集中)。后來(lái)劉延陵漂泊南洋,后又聽(tīng)說(shuō)他定居在新加坡,和他的聯(lián)系也就少了。
1979年末至1980年,我為上海《解放日?qǐng)?bào)》寫(xiě)“藝文軼話”專(zhuān)欄,1980年9月就有專(zhuān)門(mén)介紹《詩(shī)》月刊的《我國(guó)第一份“詩(shī)刊”》,又陸續(xù)寫(xiě)了《詩(shī)的歡喜》,評(píng)介了《詩(shī)》刊的作者——詩(shī)人陳南士,再有《徐玉諾與散文詩(shī)》,詩(shī)人徐玉諾也是《詩(shī)》的作者。在寫(xiě)作過(guò)程中曾幾次向葉老請(qǐng)教過(guò)《詩(shī)》創(chuàng)辦的情況,文章出來(lái)后葉老又多次向我談起《詩(shī)》。由于該報(bào)規(guī)定專(zhuān)欄每篇字?jǐn)?shù)在千字左右,所以葉老所談的一些珍貴的內(nèi)容本該寫(xiě)而未能寫(xiě)進(jìn)去。1985年,上海書(shū)店準(zhǔn)備影印出版《詩(shī)》,書(shū)店考慮請(qǐng)一位創(chuàng)辦《詩(shī)》的主要成員寫(xiě)篇序,朱自清先生1948年已逝世,葉圣陶先生又久居醫(yī)院,難以動(dòng)筆,斟酌再三,最后決定煩請(qǐng)劉延陵先生,九十一高齡的劉延陵先生終于答應(yīng)了,并于1985年10月在新加坡寫(xiě)就。他在序中說(shuō),“我終于決定寫(xiě)寫(xiě)看,姑且談?wù)勥@個(gè)刊物的出版始末。倘若回憶中有記錯(cuò)了的,要請(qǐng)閱者原諒。”關(guān)于《詩(shī)》的創(chuàng)辦,他在序中追憶說(shuō):
這個(gè)刊物大概是1922年1月里創(chuàng)刊的。
早一年的9月里,朱、葉兩兄和我一同在上海吳淞某中學(xué)教書(shū)。吳淞濱江而近海,風(fēng)景與城市大不相同。我們?nèi)齻€(gè)都是過(guò)慣城市生活的;那時(shí)我們?nèi)杖湛匆?jiàn)的,無(wú)非是大都會(huì)里人群緊張擁擠來(lái)來(lái)去去的情形。一旦換了一個(gè)模樣完全相反的環(huán)境,而與大自然中恢宏闊大的景象早晚相見(jiàn),我們便像生活在另一個(gè)世界里面,而有一種新穎而興奮的情緒在胸中激蕩。后來(lái)我們匆匆地決定出版一種專(zhuān)載新詩(shī)的刊物,也與其時(shí)我們的這種情緒不無(wú)關(guān)系。……
有一天下午,我們從海邊回學(xué)校時(shí),云淡風(fēng)清,不冷不熱,顯示得比往日尤其秋高氣爽。因此,我們一路上談興很濃;現(xiàn)在我已不記得怎么一來(lái),我們便從學(xué)校里的國(guó)文課談到新詩(shī),談到當(dāng)時(shí)缺少專(zhuān)載它們的定期刊,并且主張由我們來(lái)試辦一個(gè)了。
那時(shí)我們都才二十幾歲,回到學(xué)校后,馬上寫(xiě)了一封信寄給上海中華書(shū)局的經(jīng)理,征求該書(shū)局為我們計(jì)劃中的刊物擔(dān)任印刷與發(fā)行。幾天后接到回信,邀我們于某一時(shí)刻,訪問(wèn)該書(shū)局編輯部的左先生,談商一切。我們?nèi)缂s而往,談了一小時(shí)就達(dá)成協(xié)議,規(guī)定這個(gè)刊物為三十二開(kāi)本的月刊;用上文已述的名號(hào);每期最少與最多若干頁(yè);創(chuàng)刊號(hào)于下一年元旦發(fā)行,其他各期也于各月的首日印成;我們負(fù)責(zé)編稿,中華書(shū)局負(fù)責(zé)印刷與發(fā)行。
我們?cè)诘玫缴鲜龅闹С种螅驮O(shè)法在上海《時(shí)事新報(bào)》的《學(xué)燈》版上登了一條新聞式廣告,宣布《詩(shī)》月刊出版的日期,并且征求投稿。兩三周后,就陸續(xù)收到外界響應(yīng)的稿件了。
那一年學(xué)校放寒假時(shí),我們?nèi)齻€(gè)人都離開(kāi)吳淞,準(zhǔn)備各到一個(gè)新地方去服務(wù)。但是那個(gè)月刊卻必須如期出版哩。它開(kāi)頭的若干期是我編的。那時(shí)我已回到杭州,在原來(lái)工作過(guò)的那個(gè)學(xué)校里效勞。我的職務(wù)很忙,又在另一個(gè)學(xué)校里兼課,所以我用于《詩(shī)》月刊的時(shí)間是很少的。現(xiàn)在每次有人對(duì)我提起它時(shí),我的中心深處都是對(duì)它很抱歉的。它出到某期時(shí),我有遠(yuǎn)行;以后關(guān)于它的情況,,我現(xiàn)記不清楚了。
劉延齡先生于1988年10月18日在新加坡謝世,享年九十四歲,他生前欣慰地看到了《詩(shī)》的影印本出版。
《詩(shī)》影印本出版后,葉老在病中見(jiàn)到了,至善說(shuō),劉的序讀給父親聽(tīng)了,父親說(shuō),“看來(lái)延陵身體還好,能回憶起那么多往事。我們幾個(gè)人在一起為詩(shī)壇所做的只是一點(diǎn)小事。”
“不看評(píng)我的文章”
葉圣陶先生作為“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先驅(qū)者之一,在小說(shuō)、散文、新詩(shī)、童話創(chuàng)作和發(fā)現(xiàn)、扶植青年作家等方面,對(duì)我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誕生和發(fā)展,都作出過(guò)重要的貢獻(xiàn)。但在上個(gè)世紀(jì)中葉之前,雖也有一些文章,在關(guān)注、議論先生的創(chuàng)作,卻多系對(duì)其某一名作的重復(fù)評(píng)價(jià),而缺乏全面的、系統(tǒng)的研究專(zhuān)著。那時(shí),沈金梅(筆名金梅)有意在填補(bǔ)這一空白,但因十年“文革”而未能完成。到七十年代后期又重拾舊稿,為了向葉老咨詢(xún)有關(guān)他創(chuàng)作上的問(wèn)題,并能得到他的支持,金梅從1977年8月起給他寫(xiě)信。信中除了向他匯報(bào)自己正在寫(xiě)作一部研究其創(chuàng)作的專(zhuān)著,還請(qǐng)求他在全稿完成以后,能審閱一遍。葉老在收到其第一封信后第二天即復(fù)信說(shuō):“大札昨日轉(zhuǎn)到,誦悉種種。我所作素不自滿,聽(tīng)人談起,常覺(jué)汗顏。足下乃欲綜論之,雖不敢勸阻,私心總以為似可無(wú)須。”葉老向來(lái)以那種謙遜與平常心,去看待有人在研究其創(chuàng)作這類(lèi)事。對(duì)金梅的此舉也不例外。
金梅的《論葉圣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書(shū)》之一,1985年4月初版。金梅是我的同窗好友,同在《河北文藝》工作過(guò),又是葉圣陶作品的愛(ài)好者。他不只“愛(ài)好”而且“研究”。
他在上世紀(jì)七十年代末開(kāi)始與葉圣老書(shū)信往來(lái),求得幫助,并希望葉老能審閱一下尚未出版但已完稿的書(shū)稿或其中部分章節(jié)。他在天津,和葉老沒(méi)有什么接觸。葉老當(dāng)時(shí)已八十多歲高齡,體力不濟(jì),眼睛更不便閱視。特別是對(duì)寫(xiě)自己的稿子一律不看。金梅求賢幫助心切,多次寫(xiě)信向葉老提出希望和要求,可以理解,葉老也多次復(fù)信,葉至善考慮到父親未能在復(fù)信中將自己的一貫想法講清楚,于1982年3月29日給金梅寫(xiě)了一封較長(zhǎng)的信,信中說(shuō),寄給我父親的稿子,我父親沒(méi)有看。有兩個(gè)原因:一是你知道的,他八十八歲,視力極度衰退,書(shū)報(bào)都沒(méi)法看,不要說(shuō)鋼筆書(shū)寄的上萬(wàn)字的稿子了;二是他一向不看談到他的稿子,他以為評(píng)論作者,是評(píng)論家的權(quán)利(當(dāng)然也有向讀者負(fù)責(zé)的義務(wù)),作者無(wú)權(quán)對(duì)評(píng)論家施加任何影響。父親不看,我還是看了。因?yàn)槲抑滥愀腋赣H是經(jīng)常通信的。如果毫不相識(shí)的作者,我也不看。我遵循父親的原則,只是把我能看出來(lái)的與事實(shí)不符的地方指出來(lái),對(duì)評(píng)論家的觀點(diǎn)不提任何意見(jiàn),不施加任何影響。我一邊看,一邊用鉛筆把見(jiàn)到的記在稿紙邊上,字跡不很清楚,筆淡也在所難免,請(qǐng)?jiān)彙_€附帶說(shuō)一聲,這樣的事,我也只能偶爾為之。我實(shí)在忙得不可開(kāi)交。父親的事幾乎全壓在我身上(從秘書(shū)到勤務(wù)員警衛(wèi)員),從生活到工作安排;我自己也不是個(gè)閑人。常看到有人給我父親寫(xiě)信,提出一連串問(wèn)題,最后說(shuō):“知道您年紀(jì)這么大,事情這么忙,是否請(qǐng)至善復(fù)一下吧。”我好像空著身子在等待任務(wù)似的,不由得只好苦笑了。他們大概不知道我也六十四了(許多文藝界的人都以為我是個(gè)青年),還想趕著把打算寫(xiě)的東西全寫(xiě)出來(lái)。而現(xiàn)在,我簡(jiǎn)直很難擠出時(shí)間來(lái)。
葉老在與金梅的十幾封通信中透徹談了被評(píng)作品的作者與評(píng)論者的關(guān)系,是平等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葉老在1980年6月24日的復(fù)信中說(shuō):
我向有想法,評(píng)論某人之為人或著作,只須直抒己見(jiàn),不必交某人過(guò)目。評(píng)論寫(xiě)成,刊布于報(bào)志,俟讀者辨別其當(dāng)否。在被評(píng)之某人,此時(shí)亦為讀者之一,如覺(jué)言之中肯,當(dāng)然會(huì)心一笑,如覺(jué)說(shuō)得欠當(dāng),亦宜承認(rèn)作者有其言論思想之自由,不加責(zé)備。
因我之想法如上述,每有友好寄示評(píng)論及我之文篇,輒不置可否,乞求容恕,返璧歸趙。今足下來(lái)書(shū),談此相同,故亦照此處理,務(wù)請(qǐng)諒解為事。
葉老在同年10月13日的信中又說(shuō):“我想作者評(píng)者各有其自由,作者只須自信其文值得寫(xiě),而且認(rèn)認(rèn)真真寫(xiě),就可以打算發(fā)表。批評(píng)是人家的事,評(píng)得對(duì),我接受,評(píng)得不對(duì),盡可不管。足下以為如何?”
在信中并且說(shuō):“‘教誨兩字,務(wù)請(qǐng)不要用。”葉老主張“作者評(píng)者各有其言論思想之自由”,葉老還在復(fù)信中多次談到過(guò)作家如何對(duì)待與己有關(guān)的評(píng)論問(wèn)題。1980年,金在吉林省《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雜志編輯出版的《現(xiàn)代文學(xué)論集》上,發(fā)表了一篇綜論葉圣陶童話創(chuàng)作的文章。葉老在“大略翻閱”之后復(fù)信說(shuō):“知稱(chēng)譽(yù)過(guò)甚,使我慚愧無(wú)已。以我妄想,評(píng)論最宜瑕瑜并舉,則于讀者作者兩皆有益。”葉老關(guān)于“作者評(píng)者各有其言論思想之自由”一說(shuō),對(duì)如何處理作家與評(píng)論家的關(guān)系問(wèn)題,是很有現(xiàn)實(shí)指導(dǎo)意義的。如果我們的作家和評(píng)論家,都能相互承認(rèn)并尊重對(duì)方的思想言論之自由,文壇上無(wú)謂的爭(zhēng)議,也許會(huì)少一些吧。葉老和金梅在通信中,還談到出版界存在的一些風(fēng)氣毛病。葉老在1979年10月13日的復(fù)信中說(shuō):“出版界唯名唯親之情形似乎確有之,只能盼望解放思想,逐漸去此一病。”葉老這番意思,我也曾聽(tīng)他談過(guò)。他說(shuō),現(xiàn)在有的寫(xiě)所謂名人的人,喜歡文章發(fā)表前請(qǐng)被寫(xiě)者先看一遍,如果被寫(xiě)者肯定了并說(shuō)了些好話,對(duì)有的作者有好的影響,有時(shí)也會(huì)給出版社、編輯以不好的影響,不利于編輯獨(dú)立地去處理作品的發(fā)表和出版。
我在北京,平日和葉老接觸比金梅稍多,與至善也比較熟悉,葉老多次說(shuō),不看評(píng)自己的文章,這點(diǎn)我早就知道,并且嚴(yán)加遵守。金梅請(qǐng)我為他的這本書(shū)寫(xiě)序言,一直在猶豫,“文責(zé)自負(fù)”嘛,序?qū)懞脹](méi)有送葉老和至善他們看就發(fā)了。
參加首屆全國(guó)文代大會(huì)
葉圣陶于1949年3月由山東解放區(qū)進(jìn)入已解放的北平市,中國(guó)來(lái)了個(gè)大新變化,好不興奮,他幾乎天天在忙,忙于見(jiàn)老朋友,又相識(shí)了一些新朋友。在新中國(guó)成立前,大家都在為新國(guó)家出力,獻(xiàn)計(jì)獻(xiàn)策。葉老要參加新政協(xié)籌備的會(huì)議,要參加準(zhǔn)備日后成立教育、出版機(jī)構(gòu)的商討會(huì),要參加全國(guó)文協(xié)籌備會(huì)等等。
葉老在4月7日日記中記了成立編審委員會(huì)事,“胡繩來(lái)談編審委員會(huì)組織事。此會(huì)屬于華北政府。俟將來(lái)中央政府成立,當(dāng)屬于中央政府。擬定余為主任委員,喬峰與胡繩為副主任委員云。又雜談編輯出版等事,十一時(shí)就寢。”又4月8日記載:“六時(shí),應(yīng)周揚(yáng)、陸定一、晁哲甫之招宴。陸定一為中央宣傳部長(zhǎng),晁為華北人民政府之教育部長(zhǎng)。蓋為編審委員會(huì)之事,故有此集。外有參加編審工作之人,及董必武、藍(lán)公武、范文瀾諸君。餐畢,略有談話,即作為此會(huì)已經(jīng)成立。”葉老曾談過(guò),這個(gè)“編審委員會(huì)”,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下屬的出版總署的班底,胡愈之任署長(zhǎng),我和周建人任副署長(zhǎng),我還兼任了編審局局長(zhǎng)。在這個(gè)崗位上,我干了五年,后才轉(zhuǎn)到教育部去的。
首屆全國(guó)文代大會(huì)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正式召開(kāi),7月19日會(huì)議結(jié)束,中華全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huì)(簡(jiǎn)稱(chēng)全國(guó)文聯(lián))正式成立。這次會(huì)準(zhǔn)備了3個(gè)月,先成立了中華全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huì)籌委會(huì)。大會(huì)籌備情況,葉老說(shuō),有文獻(xiàn)記載,隨著北平的解放,大批華北解放區(qū)的文藝工作者來(lái)到北平,不久許多長(zhǎng)期在國(guó)統(tǒng)區(qū)艱苦奮斗的文藝界朋友也陸續(xù)來(lái)到了這個(gè)文化古都,再加上原來(lái)在北平堅(jiān)持文藝工作的朋友,這就形成了中國(guó)新文藝大軍第一批的大會(huì)合。三月二十二日,華北文化藝術(shù)工作委員會(huì)和華北文協(xié)舉行招待在平文藝界的茶會(huì),郭沫若先生在會(huì)上提議:發(fā)起召開(kāi)全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大會(huì)以成立新的全國(guó)性的文學(xué)藝術(shù)界的組織。全體到會(huì)文藝工作者都表示贊成。接著,就由原全國(guó)文協(xié)在平理監(jiān)事和華北文協(xié)理事聯(lián)席會(huì)議產(chǎn)生了一個(gè)籌備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進(jìn)行召開(kāi)全國(guó)文代大會(huì)的一切籌備工作。
籌備委員會(huì)于三月二十四日舉行第一次會(huì)議,正式宣布成立。籌備委員為郭沫若、茅盾、周揚(yáng)、葉圣陶、鄭振鐸、田漢、曹靖華、歐陽(yáng)予倩、柳亞子、俞平伯、徐悲鴻、丁玲、柯仲平、沙可夫、蕭三、洪深、陽(yáng)翰笙、馮乃超、阿英、呂驥、李伯釗、歐陽(yáng)山、艾青、曹禺、馬思聰、史東山、胡風(fēng)、賀綠汀、程硯秋、葉淺予、趙樹(shù)理、袁牧之、古元、于伶、馬彥祥、劉白羽、荒煤、盛家倫、宋之的、夏衍、張庚、何其芳等四十二人。常務(wù)委員為郭沫若、茅盾、周揚(yáng)、葉圣陶、沙可夫、艾青、李廣田。郭沫若任籌備委員會(huì)主任,茅盾、周揚(yáng)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書(shū)長(zhǎng)。
葉老說(shuō),籌委會(huì)的具體工作他做得不多,但也做了一點(diǎn)。如葉圣陶在4月8日日記中記,3時(shí)偕雁冰于乃超所居之永安飯店,共商文協(xié)大會(huì)之邀請(qǐng)代表名單。再就是積極支持5月4日創(chuàng)刊的《文藝報(bào)》,這份報(bào)是中華全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huì)籌委會(huì)和首屆中華全國(guó)文學(xué)藝術(shù)界工作者代表大會(huì)的機(jī)關(guān)報(bào)。我既是籌委會(huì)委員,又是大會(huì)主席團(tuán)委員。葉老說(shuō),這次大會(huì)很重要,是長(zhǎng)期被迫分離的解放區(qū)和國(guó)統(tǒng)區(qū)兩支文藝大軍的隆重會(huì)師,毛主席、周恩來(lái)副主席、朱德總司令蒞臨大會(huì),并作了重要講話,使這次大會(huì)成為我國(guó)現(xiàn)代文藝運(yùn)動(dòng)史上重要的盛會(huì)。周恩來(lái)副主席為開(kāi)好這次會(huì),數(shù)次召集有關(guān)人士通宵達(dá)旦地了解情況,統(tǒng)一思想,明確方向。我作為一位代表,只能多做點(diǎn)實(shí)事。葉圣陶是《文藝報(bào)》的重要作者,給報(bào)紙多方面支持,為《文藝報(bào)》寫(xiě)了《劃時(shí)代》等文章,5月5日又和茅盾、胡風(fēng)等參加了北平報(bào)紙召開(kāi)的“作家論工人文藝”座談,并有發(fā)言,對(duì)留在工廠里的文學(xué)工作者如何幫助喜愛(ài)文藝的人進(jìn)行創(chuàng)作,說(shuō)了些實(shí)在的體會(huì),“我以為留在工廠里的文藝工作者盡可隨時(shí)留意,遇見(jiàn)工友們?cè)诠ぷ魃匣顒?dòng)上有什么可以寫(xiě)的,乃至吐露一段真切感想,說(shuō)出幾句精要的話的時(shí)候,如果他們沒(méi)想到寫(xiě),就給立刻點(diǎn)醒,鼓勵(lì),告訴他們說(shuō)不要愁沒(méi)有什么寫(xiě)的,這兒就是可以寫(xiě)的好材料。單是這么點(diǎn)醒與鼓勵(lì)還不夠的話,能夠幫助他們?cè)O(shè)計(jì)該怎么寫(xiě)自然更好。幫助設(shè)計(jì)不宜自作主張,應(yīng)該順著他們的心思,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訂正或補(bǔ)充,目的在讓他漸漸養(yǎng)成寫(xiě)作的習(xí)慣。
“再說(shuō)寫(xiě)成之后給他們修改,據(jù)我的經(jīng)驗(yàn),修改的時(shí)候原作者不在旁邊,修改好了送還他,讓他自己去揣摩;這樣的辦法對(duì)于原作者好處比較少。跟原作者在一塊兒,一路修改一路說(shuō)明所以然,原作者得到的好處就比較多。能夠與原作者商量,讓他覺(jué)察原作為什么不很妥當(dāng),該怎么修改才妥當(dāng),一切待他自發(fā),這是頂有效的辦法,熟練的作者能把自己的作品細(xì)心修改,達(dá)到完美的境界,也就是這么一回事兒。我希望工廠里的文藝工作者幫助工友們修改寫(xiě)成的東西,能夠采用前面說(shuō)的最后一種辦法。
“修改是對(duì)于不妥當(dāng)處而言。還有寫(xiě)得很好的地方,原作者未必自覺(jué)寫(xiě)得很好,也得給鄭重指出,并且說(shuō)明為什么好。原作者知道自己寫(xiě)的為什么好,跟知道為什么不妥當(dāng),同樣在寫(xiě)作能力方面可以長(zhǎng)進(jìn)不少。
“我不反對(duì)讓初學(xué)者學(xué)習(xí)一些寫(xiě)作的簡(jiǎn)要原理。可是我想,如果能夠一面習(xí)作一面自己悟出原理,進(jìn)境將會(huì)更多。”7月2日,也就是大會(huì)正式開(kāi)幕的當(dāng)天,他在《光明日?qǐng)?bào)》特刊發(fā)表了《祝文代大會(huì)》,熱情地說(shuō),“第一次文代大會(huì)開(kāi)幕了,這是文藝界空前的大集合,包括的部門(mén)這么多,代表所從來(lái)的地區(qū)這么廣,惟有在人民的政權(quán)之下才可能有這么個(gè)大集合,惟有在文學(xué)藝術(shù)真正跟布帛菽粟同樣切需的新時(shí)代才可能有這么個(gè)大集合。用老話說(shuō),無(wú)非以文會(huì)友,聲氣應(yīng)求那一套,用在這個(gè)大會(huì)上也未必不可以,可是實(shí)際的意義要超過(guò)那些話很多很多。來(lái)會(huì)的代表們目標(biāo)是齊一的,那目標(biāo)就是為人民服務(wù),態(tài)度是齊一的,那態(tài)度就是勤懇質(zhì)樸,精進(jìn)不懈,惟愿竭盡可能把各自的一份成就貢獻(xiàn)給人民。”
葉老說(shuō),這次大會(huì)有10個(gè)代表團(tuán)與會(huì),陣容強(qiáng)大,平津代表第一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李伯釗)、平津代表第二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曹靖華)、華北代表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蕭三)、西北代表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柯仲平)、華東代表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阿英)、東北代表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劉芝明)、華中代表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黑丁)、部隊(duì)代表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張致祥)、南方代表第一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歐陽(yáng)予倩)、南方代表第二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馮雪峰)。葉圣陶在南方代表第一團(tuán),葉老說(shuō),團(tuán)里代表熟人多,其中不少是從香港繞道來(lái)北平的,如,田漢、馮乃超、丁聰、宋云彬、茅盾、胡風(fēng)、柳亞子、柯靈、郭沫若、曹禺、戴望舒、許廣平等。葉圣陶是大會(huì)主席團(tuán)成員,常務(wù)主席團(tuán)有丁玲、田漢、李伯釗、阿英、沙可夫、周揚(yáng)、茅盾、洪深、柯仲平、郭沫若、曹靖華、陽(yáng)翰笙、張致祥、馮雪峰、鄭振鐸、劉芝明、歐陽(yáng)予倩,總主席郭沫若,副總主席茅盾、周揚(yáng)。大會(huì)的工作機(jī)構(gòu)也設(shè)了一些部門(mén),葉老說(shuō)他是小說(shuō)組委員兼召集人,委員有茅盾、周揚(yáng)、沙可夫、胡風(fēng)、劉白羽、荒煤、歐陽(yáng)山、何家槐、馮乃超、巴人、何其芳、趙樹(shù)理、陳學(xué)昭、楊朔。葉老說(shuō),他召集小說(shuō)組委員開(kāi)過(guò)二、三次會(huì),主要是就小說(shuō)如何提高質(zhì)量,更好地反映新的時(shí)代、新的生活,為人民大眾創(chuàng)作愛(ài)看的作品。
葉老說(shuō)這次盛會(huì)給他留下了許多難忘的記憶,這是他有生以來(lái)頭一次參加如此規(guī)模、內(nèi)容充實(shí)豐富的文藝界大會(huì),又見(jiàn)到了許多老朋友,認(rèn)識(shí)了一些新朋友。為了新文藝的發(fā)展,團(tuán)結(jié)協(xié)力,去名去利,踏實(shí)工作,他從許多與會(huì)代表的身上看到、感受到這種品質(zhì)和精神。他舉例說(shuō),《文藝報(bào)》他原以為茅盾是主編,后來(lái)聽(tīng)說(shuō)茅盾不同意設(shè)主編,建議他和胡風(fēng)、嚴(yán)辰三人為編輯委員。葉老還舉例說(shuō),梅蘭芳是全國(guó)文聯(lián)全委,又是中華全國(guó)戲劇工作者協(xié)會(huì)全國(guó)委員會(huì)常務(wù)委員,他也是中華全國(guó)戲曲改進(jìn)會(huì)籌備委員會(huì)常務(wù)委員,他卻主動(dòng)提出到該會(huì)資料室工作,說(shuō)自己對(duì)這項(xiàng)工作比較熟悉。該室負(fù)責(zé)人為楊紹萱、梅蘭芳、程硯秋。
葉老說(shuō),中華全國(guó)文學(xué)工作者協(xié)會(huì)(1953年改名為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首屆主席是茅盾,副主席人數(shù)少,只丁玲、柯仲平兩位。葉老說(shuō),現(xiàn)在我在文壇算年長(zhǎng)的,有人老說(shuō)我編《小說(shuō)月報(bào)》、《中學(xué)生》和在開(kāi)明書(shū)店長(zhǎng)期做編輯工作期間扶持提攜了多少文學(xué)名人,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又發(fā)現(xiàn)推薦了多少文學(xué)新人,這話言重了,其實(shí)在這方面我是做得不夠的,本來(lái)對(duì)促進(jìn)文學(xué)人才健康成長(zhǎng)可以而且應(yīng)該做得更多更好些。
葉老說(shuō),他對(duì)參加第一次全國(guó)文代大會(huì)記憶猶新,可惜文學(xué)圖片資料保存極少,研究他的人、研究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人也少涉及到這一方面內(nèi)容,他希望我有機(jī)會(huì)時(shí)留心一下,他說(shuō)這不僅是個(gè)人的事,這次大會(huì)是舉國(guó)的事。
“為俞平伯平反可以更早些”
葉圣陶一生,結(jié)交眾多,但摯友卻也是可數(shù)的。古人說(shuō),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葉老說(shuō),最后有幾個(gè)也就很難得了。我和葉老接觸期間,也就是他晚年時(shí)期,已八九十歲了,他的好友也多相繼過(guò)世,甚至更早,如朱自清1948年就走了。
在我的印象中,俞平伯(1900-1990)是葉老最后一位重要的摯友。他們之間走動(dòng)之勤、交談之多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葉老與俞平伯長(zhǎng)期有通信的習(xí)慣,在葉老八九十歲期間,他們通信更頻繁,葉老說(shuō)猶如“乒乓之情”,你來(lái)我往。葉老平日很少保存來(lái)信,看了,復(fù)了,信也就不留了。惟獨(dú)對(duì)俞平伯的信函保存完整。用大畫(huà)報(bào)紙將這些信及信封貼好或夾好,至善給我看過(guò)一本。‘葉老有次說(shuō),俞先生有學(xué)問(wèn),我愛(ài)寫(xiě)信向他討教;另外俞先生的字寫(xiě)得好,這是我喜愛(ài)保存他的來(lái)信的另一個(gè)原因。
葉至善2001年在《葉圣陶集》第10卷卷首一張圖片下說(shuō)明:
朱自清逝世已逾二十五年,因俞平伯信上一句話,作者“頓然念之不可遏,必欲托之于辭以志永懷。”自知思之損眠,而又排之不去,如此者七日,方得此闋《蘭陵王》之初稿;即封寄俞平伯,懇請(qǐng)推敲改易,是為一月三日。不意越四晝夜,即得俞復(fù)函,已于原稿上圈圈點(diǎn)點(diǎn)。一似嚴(yán)師所批之課卷。如首句“猛悲切”加密點(diǎn),批曰“筆真情,驀然而起。”又如“明燈座,杯勸互殷,君輒沉沉醉凝睫”句加密圈,批曰“可謂神似,昏燈殘酒,如見(jiàn)其人,然其人已千古矣,讀競(jìng)泫然。”擬改詞名則另列一表,供作者酌取。如是書(shū)信來(lái)往一月有馀,細(xì)微處一個(gè)字也不放過(guò)。如“擊槳”之改定。俞信中去:“‘撥弱。‘打顯得粗些;當(dāng)是‘擊。‘擊槳或‘擊棹均可,‘擊槳與周詞‘拂水正同。”“周詞”指周美成之《蘭陵王——柳》,“拂水”取之于“拂水飄綿送行色”句。作者填此闕所用四聲,固以周律為準(zhǔn)則也。二月二日,兩位老人家又相約詳談一次,最后又改動(dòng)數(shù)字方算定稿。共謂“傷逝之同悲,論文之深誼,于此交錯(cuò),良可記也。”
葉老于1988年除夕上午病逝,中午起來(lái)晚飯時(shí),至善叫我在他家和他、至誠(chéng)等家人商量葉老后事。至善叫我先別告訴俞先生,讓他自然知悉,另《文藝報(bào)》決不要去請(qǐng)他撰文。至善說(shuō),俞先生也在病中,經(jīng)受不起這種刺激,他們之間有六十五年友情了。
1986年1月20日,俞平伯所在單位——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為紀(jì)念他從事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六十五年,召開(kāi)了慶祝活動(dòng)。地點(diǎn)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禮堂,中國(guó)美術(shù)館南對(duì)過(guò)。出席慶祝會(huì)的有俞先生的同事、朋友、學(xué)生等方面人士共200余人。我有幸被邀請(qǐng)參加了。葉老身體不適,沒(méi)有出席。至善叫我會(huì)后有空來(lái)家里,談?wù)剷?huì)議的情況。我到會(huì)場(chǎng),在休息室首先見(jiàn)到了王力、吳組緗、王瑤幾位北大教授。北大的來(lái)人是乘同一部車(chē)來(lái)的,吳組緗說(shuō),今天的會(huì)重要,肯定要對(duì)平伯老師1954年《紅樓夢(mèng)》研究觀點(diǎn)遭受的非學(xué)術(shù)討論方式的圍攻和政治批判進(jìn)行否定,不僅對(duì)他個(gè)人,對(duì)今后學(xué)術(shù)界如何真正貫徹雙“百方”針都很重要。王瑤會(huì)后快上車(chē)時(shí)對(duì)我說(shuō),今天院里的講話中,對(duì)俞平伯在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上的貢獻(xiàn)評(píng)價(jià)不足,應(yīng)該是做出了重要的多方面的貢獻(xiàn)。會(huì)議開(kāi)始,俞平伯坐主席臺(tái)中間,右側(cè)坐的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胡繩,左側(cè)坐的是副院長(zhǎng)錢(qián)鐘書(shū)。俞平伯為出席這次會(huì),發(fā)言不發(fā)言;要發(fā)言,如何發(fā),談些什么等等,可真有點(diǎn)犯難。最后決定把《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國(guó)際紅樓夢(mèng)研討會(huì)書(shū)》,加上一篇舊作《評(píng)(好了歌>》一起整理出來(lái),冠以總題,叫做《舊時(shí)月色》作為他的發(fā)言。他自己講了三言?xún)烧Z(yǔ),至為簡(jiǎn)單,也都還是寫(xiě)在了紙上在會(huì)上逐字宣講的。《舊時(shí)月色》則由外孫韋柰代為宣讀。
胡繩以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的身份,出席這次慶祝大會(huì)并講話。胡繩話雖簡(jiǎn),卻頗有分量,也確實(shí)道出了正義的心聲: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開(kāi)始對(duì)《紅樓夢(mèng)》進(jìn)行研究,他在這個(gè)領(lǐng)域里的研究具有開(kāi)拓性的意義。對(duì)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diǎn),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見(jiàn)或批評(píng)本來(lái)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mèng)》研究而對(duì)他進(jìn)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這種做法不符合黨對(duì)學(xué)術(shù)藝術(shù)所應(yīng)采取的“雙百”方針。《紅樓夢(mèng)》有多大程度的傳記性的成分,怎樣估價(jià)高鶚續(xù)寫(xiě)的后四十回,怎樣對(duì)《紅樓夢(mèng)》作藝術(shù)評(píng)價(jià),這些都是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內(nèi)的問(wèn)題。這類(lèi)問(wèn)題只能由學(xué)術(shù)界自由討論。我國(guó)憲法對(duì)這種自由是嚴(yán)格保護(hù)的。我們黨堅(jiān)持四項(xiàng)原則。按照四項(xiàng)原則中的人民民主專(zhuān)政原則,黨對(duì)這類(lèi)屬于人民民主范圍內(nèi)的學(xué)術(shù)問(wèn)題不需要,也不應(yīng)該作出任何“裁決”。1954年的那種做法既在精神上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學(xué)術(shù)和藝術(shù)的發(fā)展。接受這一類(lèi)歷史教訓(xùn),我們要在學(xué)術(shù)界認(rèn)真實(shí)行“雙百”方針,提倡在正常的氣氛下進(jìn)行各種學(xué)術(shù)問(wèn)題的自由討論和辯論,團(tuán)結(jié)一切愛(ài)國(guó)的、努力從事有益于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學(xué)術(shù)工作者,共同前進(jìn),共同追求真理。在紀(jì)念俞平伯先生從事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六十五周年的時(shí)候,我想,說(shuō)一下這個(gè)問(wèn)題是必要的。
俞平伯先生從1953年起在中國(guó)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現(xiàn)在的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工作。他是我們?nèi)和舅鹬氐囊晃焕蠈W(xué)者。我相信我院和我國(guó)的文學(xué)研究工作者都會(huì)很好地吸收利用和發(fā)展俞平伯先生的一切有價(jià)值的研究成果。
敬祝俞平伯先生健康長(zhǎng)壽,并且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上做出更多的貢獻(xiàn)。
葉老知道了這次會(huì)議的大致情況,也知道了胡繩宣讀的講話內(nèi)容,他沒(méi)多說(shuō)什么,只說(shuō),會(huì)開(kāi)得是好的,對(duì)平伯學(xué)術(shù)上的評(píng)價(jià)高低意義不大,俞先生在學(xué)術(shù)上的成就是大的,歷史會(huì)作出正確的評(píng)價(jià)。對(duì)他的長(zhǎng)期的不公正,今天正式為他平反固然好,但可以更早些,這樣做不僅對(duì)他個(gè)人而且對(duì)整個(gè)學(xué)術(shù)界效果都會(huì)更好。這個(gè)歷史教訓(xùn)不該再發(fā)生,相信不會(huì)再發(fā)生了。
《花萼》·《三葉集》和《四葉集》
葉圣老開(kāi)玩笑說(shuō),人家愛(ài)說(shuō)我這個(gè)老作家?guī)С隽巳齻€(gè)子女作家。其實(shí),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我一生的職業(yè)編輯第一,教育第二,再輪說(shuō)到作家。第一第二的順序可以變動(dòng),寫(xiě)作,當(dāng)作家雖然我從事這項(xiàng)事漫長(zhǎng),但從沒(méi)有當(dāng)過(guò)專(zhuān)門(mén)從事寫(xiě)作、創(chuàng)作的作家,僅僅是位業(yè)余作家,業(yè)余的老作家。至于我的孩子們,也許受到我點(diǎn)影響,很小也都染上了文學(xué)愛(ài)好,并較早開(kāi)始寫(xiě)作品了,但他們各自的一生也都各有主要職業(yè),至善長(zhǎng)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至美長(zhǎng)期從事新聞?dòng)⒄Z(yǔ)翻譯工作,至誠(chéng)也是長(zhǎng)期編文學(xué)期刊,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他們也是業(yè)余的,當(dāng)作家也是業(yè)余作家。既然父子都是業(yè)余作家,大家有點(diǎn)交流很正常,作為父親對(duì)他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多點(diǎn)關(guān)心和幫助,希望他們把作品寫(xiě)好,這也是合情理的。
葉至善(1918—2006)、葉至美(1921—2012)、葉至誠(chéng)(1926—1992)三人有兩本作品的合集,第一本散文小說(shuō)集《花萼》,1943年8月桂林文光書(shū)店出版,第二本以小說(shuō)為主兼有散文的《三葉集》,1945年1月也是文光書(shū)店出版的。
《花萼》的原稿,都是經(jīng)過(guò)作者們的父親葉圣陶認(rèn)真修改過(guò),并選定了篇目,又取了集子的書(shū)名。抗戰(zhàn)期間,葉圣陶一家逃難到四川鄉(xiāng)下,“吃罷晚飯,碗筷收拾過(guò)了,植物油燈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親戴起老花眼鏡,坐下來(lái)改我們的文章。我們各據(jù)桌子的一邊,眼睛盯住了父親手里的筆尖兒……”全書(shū)編好以后,“父親復(fù)看一遍,剔去若干篇,成為這本集子。父親替這本集子題了個(gè)名字,叫做《花萼》”,葉至善在《花萼》自序中這樣敘說(shuō)。《花萼》除了至善的自序,還有宋云彬?yàn)樗麄儗?xiě)的序。宋先生說(shuō),他們弟兄三個(gè)能受到父親如此嚴(yán)格的訓(xùn)練,實(shí)是不可多得的幸福,使他“艷羨不置”。又說(shuō)弟兄三個(gè)各有自己的風(fēng)格,但是有一個(gè)共同的優(yōu)點(diǎn),都“平常留心各樣的事情,觀察得深刻了,覺(jué)得非寫(xiě)不可,才動(dòng)筆寫(xiě)的”。從宋先生的評(píng)語(yǔ)中,可以看出他們都繼承和保持了父親凡事認(rèn)真的作風(fēng)。
《花萼》共收二十七篇,作者們描寫(xiě)戰(zhàn)時(shí)后方生活小景的那些篇章。雖然時(shí)間愈隔愈遠(yuǎn)了,可是那一階段的人物和故事,生活與風(fēng)俗等等,仍然能吸引著讀者。葉至誠(chéng)的《樂(lè)山遇炸記》、《夜襲》、《宣傳》屬于這類(lèi)作品,葉至美的《坐雞公車(chē)》、《我是女生》、《物價(jià)》、《“工作”小記》等亦留下了那個(gè)時(shí)代的掠影,很能說(shuō)明作者們的寫(xiě)作,啟示便有一個(gè)良好的傾向,即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從生活出發(fā)。
葉至善是長(zhǎng)兄,年齡稍大,他對(duì)生活的觀察似乎更深透些,文風(fēng)不如至美、至誠(chéng)那么活潑,卻著力嚴(yán)謹(jǐn),讓我們聯(lián)想起乃父的風(fēng)格。他寫(xiě)的《寄賣(mài)所》、《司機(jī)們》、《擦皮鞋的》都富有戰(zhàn)時(shí)后方的氣氛;《腳劃船》和《成都盆地的溪溝》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贊許,認(rèn)為:“他(指至善)的寫(xiě)作強(qiáng)國(guó)富民而明確,可見(jiàn)他訓(xùn)練的切實(shí)。”(見(jiàn)《三葉》朱自清序)我特別要提到《化為劫灰的字畫(huà)》一篇,娓娓道來(lái),動(dòng)人以情,通過(guò)記述兩幅字畫(huà)的毀失,實(shí)際寫(xiě)出了葉圣陶先生一家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火。一幅“天女散花圖”,是父親結(jié)婚時(shí)候的一份紀(jì)念禮物;一副小對(duì)聯(lián)是李叔同的手跡:“寒巖枯木原無(wú)想,野館梅花別有春”。這兩幅字畫(huà)當(dāng)年布置在上海三樓的亭子間,即小小的“未厭居”里。冬夜,亭子有一個(gè)火缽,每當(dāng)葉圣陶擱筆之后,常與家人圍火取暖,一片平靜。“一·二八”戰(zhàn)火起,天井里落了一枚炮彈,大門(mén)和前樓的門(mén)窗全給震倒了,三樓亭子間的兩幅字畫(huà),雖然蒙上一層灰土,卻完好地保存下來(lái)。抗戰(zhàn)開(kāi)始,全家逃難來(lái)到樂(lè)山。在用木板隔出來(lái)的一間斗室,又把這兩幅字畫(huà)掛起來(lái),每到晚上,一家人又團(tuán)聚在“未厭居”里。然而,樂(lè)山被炸,“天女散花圖”和弘一法師的墨跡終于化為劫灰了。通篇雖然并沒(méi)有一句強(qiáng)烈地控訴敵人的字眼,讀后卻對(duì)日本侵略者懷有一腔仇恨。
《三葉集》的原稿先由朱自清看了一遍,1944年9月為之作序,至善說(shuō),這些也都是父親請(qǐng)朱自清先生幫助的。至善還說(shuō),父親不贊同這兩本書(shū)由開(kāi)明書(shū)店出版,父親聯(lián)系了文光書(shū)店。全書(shū)共收作品十九篇。朱自清先生欣賞集子里的小說(shuō)以紀(jì)實(shí)為主,“這種寫(xiě)實(shí)的態(tài)度是他們住宅寫(xiě)作的根本態(tài)度,也是他們老人家葉圣陶兄寫(xiě)作的根本態(tài)度。”他在序中這樣說(shuō)。
《四葉集》是漓江出版社于葉老1988年過(guò)世后請(qǐng)商金林先生編選的,并于1989年8月出版。“四葉”即葉圣陶、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chéng),每人一輯,共四輯,全書(shū)54萬(wàn)余字。幾乎都是選自“四葉”已發(fā)表或出書(shū)過(guò)書(shū)的篇目,基本上是散文一類(lèi)的短文。我以為,《四葉集》的出版,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子女們對(duì)父親的深切懷念。記得葉老在世時(shí),1987年,他和至善、至誠(chéng)和我在庭院海棠樹(shù)下散步閑聊時(shí),曾談起過(guò)以后我的三個(gè)孩子湊熱鬧要和父親合出本書(shū),就叫《四葉》。葉老說(shuō),這是件有意思的事。文章要選好,書(shū)要出好,我希望能看到。他還說(shuō),孫子輩里也有些業(yè)余搞文學(xué)的,特別說(shuō)三午有點(diǎn)才華,可惜有病表現(xiàn)短暫,兆言有文學(xué)才華,若能堅(jiān)持下來(lái),作品多,有穩(wěn)定的風(fēng)格更好。將來(lái)至善你們也可以和這些孩子出本合集,算上我一個(gè)我也不會(huì)有意見(jiàn)的。遺憾,真遺憾,葉老的愿望,至今沒(méi)能落實(shí),子女們陸續(xù)過(guò)世,至美算是活得最長(zhǎng)的一位,她過(guò)世最后的年卅中午,我和兀真、小沫、永和、燕燕在至美家陪她吃年夜午飯,席上永和打通了兆言的手機(jī),我們還提前相互拜年。至美那天精神還好,她知道我將寫(xiě)葉老的這本書(shū),她說(shuō)你是我們家三、四代人的朋友,有需要問(wèn)我的事就說(shuō),或通過(guò)永和轉(zhuǎn)告。她當(dāng)場(chǎng)還送了兩本她過(guò)去翻譯的書(shū)新近重印的。萬(wàn)萬(wàn)想不到,不久,她也過(guò)世了,這使我想起葉老說(shuō)的這句話:“年歲高了的人,生死難料。”葉老的長(zhǎng)孫葉三午,在葉老過(guò)世次年1989年,年才46歲也就走了。至善在父親過(guò)世之后,花了幾年的精力,艱難地寫(xiě)完并出版了《父親長(zhǎng)長(zhǎng)的一生》。回想起這些,我覺(jué)得葉老期望的子孫三代也出個(gè)合集的愿望實(shí)際上也算如愿了。葉老的墓在他的第二故鄉(xiāng)蘇州市甪直,至善、滿子過(guò)世后的墓與父親緊連一起,墓上刻的是父親寫(xiě)的篆字“善滿居”三個(g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