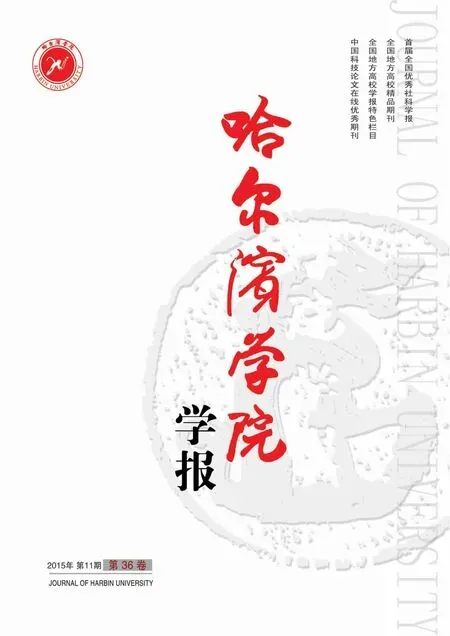論薩特自由觀的本體論內涵——從人為性和超越性角度剖析薩特的自由觀
闕玉葉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875)
自由是在世的人所固有的,自由在薩特那里具有本體論的意義。人的存在沒有本質,人從一開始就是自由的。薩特總是不停地在思索自在的世界和人的存在的關系,他圍繞著一個核心的概念——自由,從本體論意義上探討了人的存在的本質。
自由在薩特這里,并不同于以往哲學中的自由。以往的哲學家往往把自由和意志相關聯,每當談到自由,就認為是意志自由,這種看法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康德。在薩特看來,自由是純粹意識的活動。人的意志,人的情感以至于人的整個存在都應該也必須是自由的,自由即是人的全部存在。自由是命定的,這不是人選取是自由的,而是自由是人的存在,人是存在先于本質的,先存在,之后才可以進行選擇,選擇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選擇做什么樣的事情。正如薩特所說的,人是被拋在世上的,當人意識到時,就已經存在了,所以,并沒有什么可以決定我們的本質,我們就是自由的,沒有什么先驗的東西規定我們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什么所謂的本質。在薩特看來,焦慮的產生在于自由就是人的存在,人沒有固有的本質,但卻固有著自由。自由是在人的選擇中實現的,即使遇到各種處境,也不會阻止人的自由,因為在處境中人是絕對自由的,而無論人是以人為性的方式存在著,還是以超越性的方式存在著,人的存在都是自由的。人的自由是先天的,人無法逃脫自由,自由在薩特這里被上升到本體論的意義。
一、薩特自由理論的本體論基礎
1.本體論證明
雖然在傳統意義上,對秉承笛卡爾傳統的歐洲哲學來說,自我才是意識的住所。對此,康德說:“我思應能伴隨我們的所有表象。”薩特則提出不同的觀點:自我有著超越性,“自我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質料上,都不存在于意識之中,自我在意識之外,在世界之中;自我屬于世界的存在,就像他者的自我一樣。”[1]所以,在薩特看來,意識是無我的。“我”并不是意識的源泉,其實我是通過意識的反思而構造出來的,和世界的其他存在一樣。
在非反思的意識中,并沒有“我”的存在,但是當我的意識進入反思狀態中時,“我”就出現了,比如說我回憶我的過去和我發覺我正在回憶我的過去就是完全不一樣的。前者是意識本身,而后者是對意識的意識。在薩特看來,對意識的意識會把意識異化為“現象”。而現象學的目光,來自對于世界是否存在的判斷不感興趣的旁觀者,而這個目光中只有“他”而沒有“我”。薩特把這個目光稱之為哲學在失去樸素態度后留下的“我”。可以看到,薩特把“反思前的我思”看成純粹的虛空,這種抽象的意識是實存的源泉。意識是具有主觀性的,意識的存在同樣可以成為一個感知的存在,是存在的絕對,薩特要對存在進行深層次的評估,他要從反思前的“我思”,而不是從反思的“我思”出發進行存在的本體論證明。
在薩特看來,“任何意識都是對某物的意識”,超越性是意識的構成結構,即意識生來就是被一個不是自身的存在支撐著,這就是意識的本體論證明。薩特從“反思前的我思”出發的本體論證明不同于神學家和笛卡爾的本體論證明,因為他們是從本質出發,把人視作思維的、有局限的存在,力求證明一個無限的、完善的和至高的存在。而薩特要找的是一個超越的本體,這個本體并不是上帝,而是世界。薩特要證明的是,由于意識本身是半透明的,當意識不指向一個對象時,它就變成了“烏有”,變成空的了,正是這種絕對的無人稱的主觀性只有面對一個被揭示的東西時才能夠被確立:“對于意識來說,在作為揭示某物,揭示一個超越的存在的直觀這一明確的義務以外,是沒有存在的。”[2]
綜上所述,薩特的本體論證明了意識是一種絕對的主觀性,是自我的內在性,是顯現與存在的統一,意識在它顯現時存在。
說明了意識的本性后,我們就可以對存在進行一些探索。在他那里,存在有三個特點:“存在存在、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2]這也就意味著存在自身充實并固有,是絕對的肯定。存在脫離時間性,是不被創造的,也無法消失。因此,相對于意識而言,存在是多余的,是毫無意義的存在。意識由于要求認識存在而具有著被動性,并且也是能動性。但是,意識永遠達不到存在而只能達到存在物,存在物在存在的基礎之上表達自身,而作為“本體論狀—本體論的”意識則“可以超越存在物,但在超越的同時不是走向它的存在,而是走向這存在的意義”。[2]
意識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就成為了存在的兩種類型:自為的存在與自在的存在。我們對自在的存在知之甚少,但是,作為自為的存在,我們則可以對其進行深入的探究。而這就要涉及到我們對于虛無的探討,因為虛無是自在與自為相聯系的中心環節,正是因為虛無,自在與自為才能發生存在關系。
2.虛無
可以明確,虛無起源于人的存在。虛無從存在那里獲得存在,它是“借來的存在”,虛無自為的,虛無“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是與自在“是其所是”的特性相反的。
虛無是否定的基礎。薩特舉例說:我不知道我所尋找的、與我有約的皮埃爾是否在咖啡館內,為了找到他,我的視線在咖啡館內游走,在我發現每一個人都不是皮埃爾的這段時間中,包括咖啡館在內所有的事物都因為不是皮埃爾而被我否定了,這是第一次虛無化。咖啡館里沒有皮埃爾,所以我不再注視咖啡館,咖啡館此時在我的眼中就沒有意義了,成了與我無關的東西,所以這次就是第二次虛無化,使得咖啡館與我失去了連續,咖啡館于是消隱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是我的尋找和否定使得我和咖啡館還有皮埃爾之間發生了聯系。所以說,存在被虛無是人與此在的存在發生關系的中心環節。可見虛無是否定的基礎。
那么,什么是虛無的基礎?虛無是不能來自外在的,也不能虛無自身,所以虛無必須要有一個存在基礎的,可是這個存在究竟是什么呢?第一,這種存在對于虛無來說應該是主動的,可以接納虛無,中介不需要其他的環節。第二,這個存在使虛無來到世界上,虛無化的行為就是這個存在的活動,這個存在不僅可以使世界上的其他存在虛無化,還能虛無化自身。所以,在經過這樣一系列的分析之后,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首先,“虛無化通過人的存在來到世界上”,[2]人的存在具有否定的功能,使得虛無得以顯現。其次,“虛無由于人的自由而出現在世界上”。[2]雖然,人不能使存在完全轉變成為非存在,但是,人可以轉變自身與存在之間的關系,這就是人的自由。這種自由是作為人的存在能夠虛無化世界的條件。人的存在其實就是自由,而自由可以限制虛無。
作為自由的人是如何與虛無發生關系的呢?薩特認為,“這一關系是建立在時間性上的。虛無存在于過去和現在之間,是不可愈合的。我們在這里正是把時間過程中的這種對自我的關系看做虛無化的條件。”[2]虛無是介于過去與現在、存在與非存在之間的縫隙。自由由于虛無得以可能,使其脫離了因果的必然性從而成為了絕對的。而作為存在于存在與非存在之間的虛無,是無法被人所超越的,正是它連接著反思前的我思的意識與我思的意識。“人的實在能全部或部分地否認世界的條件就是,他把自身包含的虛無當做那種將它的現在和他的全部過去分割開來的烏有。”[2]虛無是意識的存在結構,不是意識要認識的對象,而是意識要認識對象的手段。虛無使得意識成為了意向性的。
虛無作為人對存在的否虛無化,不是意識所要認識的對象,而是作為意識的存在結構而存在的,人的意識正是因為虛無才能夠成為意向性的,它相對于過去構成自身的存在,恰是虛無分開了人的過去與現在,由此我們看到時間不可被分割,因為它的中間只有烏有而非實在,意識是不間斷的。
所以,人是虛無由此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存在。人的存在永遠是一欠缺,是永遠達不到與自身、自在統一的自為的存在。人的虛無化的能力意味著人不會被固定在某一種樣式或框架中,人可以擺脫外在的世界的規定,永遠存在著未來的希望和可能。總之,意味著自由。
二、自由與人的存在
人在意識意向性的面對世界的過程中,不斷虛無化著這個世界,使得人總是處在一種存在的裂縫之中,因為他既不是過去,也不能決定,他總是處于現在的虛無化中,人的這種存在方式就是“焦慮”。
可見,焦慮就是面對世界的一種根本性的體驗和把握。在薩特看來,自由是焦慮的根本原因,在自由中,焦慮得以產生,也是在焦慮中,自由得以表現出來,二者之間存在著一致性,同時在焦慮中,人才得以懷疑自身存在方式的合理性。也就是說,人在行動的選擇時,必然面對各種選擇的可能,正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可能,人才會感到無所適從,領略到焦慮的痛苦。但是,“焦慮”和“恐懼”是不同的。恐懼是一種對外在世界直觀的領會,而焦慮確實通過反思后才得以出現。由于反思,焦慮發現了自己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可是卻無法通過某種行為為未來的自己提供某種確定性。在焦慮中,我發現,我的現在和未來之間永遠都有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這個裂縫就是虛無。所以“我的現在不是我的未來,第一個原因就是我的現在和未來被時間分隔開來;第二個原因是我的現在不是我的未來的基礎;第三個原因就是沒有什么存在能夠絕對的規定未來的我是什么。”[2]
焦慮表現出來的是人的自身存在的虛無化能力。由于人未來的不確定性,讓人有著焦慮的痛苦。在焦慮中,很多不屬于意識的東西被分離出來,意識得以純粹化。所以,焦慮使得意義和價值被架空,而沒有了存在的基礎,與此同時,也更使我們明白了存在是沒有本質的,自由就是人的存在,因而“沒有什么能證明某種意義和價值是我們必須要接受的”。[2]焦慮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自由,焦慮的原因也是由于自由,因為世界的意義是通過我顯現出來的,而我卻沒有能夠賴以支撐的基礎。雖然我出生的這個世界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規定性,但是焦慮卻讓我明白我自身才是賦予世界以意義的,“焦慮使我發覺自己是自由的,世界的意義通過我才能得以實現”。[2]所以,焦慮的原因,不是因為外部世界的壓力或者別的什么,焦慮的原因,恰恰是因為人命定的自由的,人具有自由不是人的抉擇,而是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由。而薩特的“存在先于本質”的著名命題,則代表了他對人的自由的基本看法。
薩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質”這個命題,體現出了他獨特的存在主義自由觀。這個命題的前提是否認上帝的存在為基礎的:“以上帝不存在為前提,可以得出有某種東西在本質被規定之前就存在了,而人就是這種存在”,[3]上帝不存在,就表明人不是上帝的創造物,可見先天的規定性是不存在的,自由的前提在這里得到確立。
“存在先于本質”究竟包含著什么樣的意義?“這里的意思是,人在存在之后,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可能,才會在這個世界中活動,從而與這個世界發生關系,進而才開始限定自身。”[3]可見,本質其實就是一種后天的規定性。本質就是人將會成為某種人的這種規定性,但實際上,人在存在的時候并不具有某種規定性,也不會知道自己究竟有著怎么的規定性,而才開始對自身進行規定,在與世界發生關系的過程中。可見這個規定在一開始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后來與世界相互接觸的過程中,才得到這種外來的本質。由此可見,本質都是后天的和外在的,人從存在的一開始就是自由的,人是自己的主人,他要自己決定成為什么樣的人,他要為自己選擇和爭取,“人要對自己負責”,[3]要為自己的行為和自己的選擇負責。
同時,“存在先于本質”還表明,人是孤獨的存在。上帝是并不存在的,那么就沒有先驗性規定人應該是什么,于是就會無所適從。因為除了自身,沒有什么可以依賴。“自由就是這樣一種人的存在,他通過散發出自己的虛無而使自己的過去不發揮作用,同時他自己的處于虛無化形式中的過去也就是他自己的未來。于是,人的存在就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搖擺不定,自然就產生了焦慮的情緒。”[4]人從一開始來到這個世界就是偶然的和荒謬的,當人意識到自身時,就已經存在了。人被無緣無故的拋到這個世界上,人的存在是不可解釋的,人的存在沒有依托,也沒有什么東西能決定人的存在的本質。沒有什么能規定人們應該怎樣的去生活。人是不可以被先天定性的,在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之前,人的具體存在狀態只是潛在。人有選擇的和重新選擇的自由,正是這種選擇決定了你是什么樣的人。人生就是一系列選擇的結果,人也必須不停地去選擇,當人說他不愿意去選擇時,這仍然是一種選擇,也就是不選擇。所以,人唯有自己是可以依賴的。因此,人必須要對自己負責,設定自身,人必須要對自己負責,也只有自己才能對自己負責。還有就是,人不僅要為自己去負責,還要為這個世界來負責,因為是人賦予這個世界以意義的。
所以,“存在先于本質”的命題表明,“自由先于本質,自由使本質得以可能,人的本質是自由的抉擇”。[2]人存在于本質被規定之前,所以存在與自由本來就是同一的,自由即存在,人的存在就是自由,“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自由與存在是沒有先后的”。[2]薩特還引用海德格爾的重要觀點:“存在是自由的,存在先于并支配本質。”[2]一言以蔽之,人的存在即人的自由。
那么,這種自由有著什么樣的含義?這是接下來要討論的,自由在他這里,指的是選擇和行動的自由。可以說,人的存在就是選擇和因而進行的行動,這種選擇和行動的自由體現了人的超越性,而人的處境又體現了人的人為性。
三、自由的選擇與人的處境
1.自由與超越性——選擇
從上面的論述得出,自由是絕對的,自由就是人的存在。“存在主義的宗旨即自由是絕對的。”[3]這并不是行動的結果,而是行動的前提。[2]自由是行動的動力,自由讓人的行動面對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自由是絕對的,這表明,自由是不會受到限制的,“自由沒有目的,自由就是自由”,[3]而且“自由沒有本質,沒有任何的邏輯必然性”。[2]可以這么說,自由是無關乎功利性的,自由就是它自身。
自由并不是人的選擇或者是決定,自由永遠都伴隨著人的存在,“我們一直處于自由之中,就像是被拋入其中一樣”,[2]人從存在的開始就意味著自由,自由永遠屬于人的存在,人必須是自由的,這種自由表明,沒有人會對他人的命運負責,人要為自己負責,為自己自身存在的規定性負責。
這種自由其實就是選擇的自由,人的選擇永遠都是自由的。人從存在的那一刻起,就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選擇,在選擇中不斷實現著自己的命運。在自由的選擇中,人不斷地去行動,不斷地充實著自己的過去。選擇是人的存在所必須的,人必須去選擇和行動,自由在這種選擇和行動的過程中不斷地實現著。
但是實際上,這種選擇也意味著一種荒謬性。這種選擇的荒謬性就體現在,人必須去選擇,人的存在沒有不選擇的可能。選擇是必須的,就和自由是必須的一樣,它們的存在都是沒有理由的。選擇使得人的未來充滿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選擇意味著一種未來的可能性,人在選擇的過程中總是否定著過去,進而面向著未來,“人在選擇的過程中不斷否定著自己所是的過去,體現著人的存在的虛無化”。[2]而且在這種選擇的過程中,人在不斷地否定著他的過去和現在,趨向著未來,可見人的價值和意義都是取決于在未來的,過去的一切不能決定著一個人的一切,“因此,自由、現在、時間化、虛無化便是同一的”。[2]
人的自由讓人在選擇和行動的過程中不斷的超越著自身。選擇就是自由的選擇,行動就是自由的行動,自由就是選擇和行動的自由,這三者都是不可分的。的確,這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中非常有吸引力的部分,因為他指出了人在面對自身存在的迷茫。薩特看來,人的存在就是一種超越的存在。人不會固定在某一種框架中,不會只局限于某一種規定性。人的存在充滿著各種各樣的荒謬的同時,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人在行動和選擇中不斷地實現著這種可能性。
行動的意義在此也就更加明了,行動使得人的存在和外在的世界發生聯系,行動通過意識的意向性來實現,人在行動的過程中,總是面對自我不斷地造就。自為的人就是超越的,讓人的存在永遠都不能達到一種實在的充實,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和持續不斷地行動的創造更加體現了人的存在的核心中的自由虛無。自由讓人永遠不能停留在現在的狀態之中,讓人按其所是的方式存在。薩特因此就把人的存在歸結為行動,這樣看來,自由與行動統一了。
人的選擇是絕對和無條件的,人并沒有不選擇的可能。盡管人的選擇在一定的環境中進行,并會受到一些限制,但是,這些限制不會妨礙人的自由的,因此,人的自由是絕對的。人的這種自由使得人不會總是局限在某一個框架中,從而總是處于一種向著未來的造就中。自由與選擇和行動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自由就是選擇的自由,自由是絕對的,自由就是人的存在。而在選擇的行動中,自由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薩特認為,自由是絕對的,不會受到條件的限制,人永遠都是自由的人,在自由的選擇中實現自身,存在于這個世界就要在選擇中不斷創造著自身,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成為什么樣的人。
總之,人總是要超越自身,超越現有的存在,不斷地去選擇和行動,但永遠不能達到自在的穩定性。既然行動和選擇是人在面對自由時所具有的超越性,但人真的能完全如此嗎?
2.自由與人為性——處境
雖然人的存在是自由的,但總是會產生某種困惑,那就是,如果自由是絕對的,選擇也是絕對的,那么為什么在很多情況下,人們都會感覺到自己并不是那么的自由,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而且在相同的情況下,可能采取同樣的行動但卻并不能得到同樣的結果。對于這些困惑,薩特認為這是因為沒有區分兩種自由的概念。這兩種自由是屬于不一樣的范疇,人們產生困惑的是一種常識上的自由,主要指的是實現某種目的的自由,薩特這里自由指的是一種選擇上的自主性,是哲學范疇上的自由。
選擇的自主性并不依賴外界的因果關系,意識的自由除了自身,并沒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說囚徒可以試圖逃離監獄,而且可以自由的籌劃自己逃離監獄的行為,但是并不能說囚徒就可以自由的離開監獄。可見,選擇的自由和實現某種行為的自由并不是一個范疇上的,選擇的自由是永遠伴隨著人的存在的,雖然也許選擇的自由并不表現得十分明顯,但是人們永遠都可以自由的選擇,去行動。在這里,就可以看到這種選擇的自由和實現的自由的兩個范疇之間涉及的自由和處境的關系。
如何解釋這種關系呢?薩特有這樣的一段描述文字:“……這塊巖石,當我搬起她的時候它就表現出一種阻撓,但當我站在巖石之上欣賞景觀時,這塊巖卻幫助了我……因此巖石是中立的。”[2]薩特的這段話形象地描述了處境與選擇之間的關系。可見處境并不是絕對的,處境可以提供一種幫助,來幫助人們實現某種目的,但是同樣也可以提供一種障礙,妨礙人們去實現某種目的。可見,無論處境提供的是什么,都只能在人的選擇過程中,才能獲得意義。所以在薩特這里,處境這個概念并不是表明所謂的人的存在和客觀的環境的關聯。而是表明在處境中人的意識作用,處境既可以對人的行為提供幫助,也可以對人的行為提供某種限制,而處境最終對于人的行為的影響作用,都是在選擇過程中才能得以實現。而且,即使是在處境中的選擇,同樣也是自由的人的意識的自主的選擇。
所以,即使在處境中,人的自由也是絕對的。而且,無論是在什么樣的處境下,自由都是一樣的,處境也是由自由產生出來的,處境對于人的意義,也是在自由的選擇和行動的過程中實現的。總而言之,因為處境的存在表示了自為的特性,自為對自己的存在方式負責但又不是這存在方式的基礎,自由決定處境而不是處境阻止自由,自由是絕對的。可見,自由對于人的存在來說是絕對的,但人在面對無所不再的自由時究竟是怎么樣去應對?這就是接下要探討的問題:自由和人的存在的兩種屬性。
四、自由與人的兩種屬性
把自由本體化是薩特自由理論的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在他那里,人沒有固有的本質,但是卻固有著自由。而且這種自由是先天的,人無法逃脫自由,自由被他上升到本體論的層面上。
在這個層面上,人的存在是自由的,是有著超越性的。巴耐斯在書《存在于虛無》英譯本的關鍵術語說明中指出了“超越性這個詞有時指的是獨立的存在,有時則指的是一個過程。”[5]莫瑞斯進一步指出這個詞有三個不同的含義,首先超越性是與人為性相對的,超越性指的是意識的能力;其次,超越性是與內在性相對的,指的是對象不再意識之中,意識不是一個容器,對象對于意識而言是具有超越性的;再次,超越性是與局限特殊經驗相對的,是指被給予的對象在時間上超出當下的顯現,指對象的超現象性,當我們停止想這個桌子時,這個桌子仍然在那里。[6]
是自由讓人超越現有的存在,不被固定在一個框架之中。不像自在的存在的形式之一桌子那樣,它只能是桌子,而不會是其他的什么,它“是其所是”,自身充實且固有。但是,人的存在,不是只是某一種樣式。而一個醫生,他與患者交談的神態、診病的動作,都會讓人覺得他是醫生,他通過自己的動作和神態表明了自己醫生的身份。但是,一個醫生,并不像桌子就是桌子那樣,干脆就只是一個桌子,桌子作為桌子,它并沒有選擇的余地,作為桌子那不是桌子自己的意愿,而是它本來就是一個桌子,自身充實且圓滿。可是,醫生并不只是一個醫生,他還可以選擇別的身份,他還有別的很多種的可能。他有著選擇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只要他想去改變,他就可以向著一個別的選擇去行動,并有著改變自己現狀的意識。自由在于是表現為人的選擇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即人的身上的超越性。他有著改變的自由,并可以向著自己的選擇去行動。但是其實醫生是自愿選擇成為醫生的,他對自己的身份很了解,他明白,自己在他人的眼中就是一個醫生,所以他的所有的行動都要符合他的醫生的身份。因此,他是在維持這種身份,維持他在別人眼中的醫生的這一種身份,但事實上,他本人的存在與醫生并不具有一致性。
可見,人命中注定是自由的,這種自由其實是本體論層面上的自由,人從開始就是自由的,人的存在不是由自己決定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偶然性。人自出生就處在時間的裂縫之中,過去的我,現在的我,未來的我組成了自為的存在的欠缺。過去的我是已經確定的了,未來的我是不確定的,充滿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所以是一種非存在,而自為的人,也就是現在的我,是處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間的。所以自為的人是存在的欠缺,他缺少的是存在,他追求的也是存在。自由讓人焦慮,自由給人的其實是負擔。自由讓人發現,現實的世界是荒謬的,充滿著偶然性,讓人感覺不能理喻。所以自由用杜小真老師的話來說就是一種重負。我們自由而偶然,荒謬而沒有道理。人的存在永遠都是一場失敗,自為的存在作為一種欠缺,總是向著自在超越,因為自在是圓滿的,自為追求圓滿但卻永遠不能達到,“自為向著自在超越,但是卻永遠不能與之合一”,[2]自為的存在永遠不能與自在的存在重合,這也就是人在自身感到痛苦的最原始的根源。所以,人們很難承受自由的重負。但是在現實中,焦慮的狀況是如此的少見,那是因為,人的存在還有另外一種屬性,也就是——人為性。
“人為性指一個存在為什么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更多地與自在的存在的另外兩個特點(即‘存在是自在’和‘存在是其所是’)相關。”[7]人為性在薩特這里,有著自欺的意義。但是在這里必須要強調的是,這種人為性的方式即是人在世的方式,人們以這種方式存在著,不是因為外部世界的壓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因為,自為的存在本身是以人為性的方式存在著。人的整個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他人眼中成為自在的存在,擁有自在的存在的圓滿和充實。但是還需要注意的是,人的這種人為性,并不是對自由的否定,而是人在面對自己的存在的自由的一種在世的反映。人的人為性是“是其所是”,“人被限定某一個框架內,并被承認一個固定的本質”,[8]比如說,稱贊就是贊美,醫生就是醫生,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不會向另外的別的東西轉變,而且人的所是就是他的身體,這個身體也可以被稱之為人的實在的人為性,人為性指一個存在為什么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更多地與自在的存在的另外兩個特點(即“存在是自在”,“存在是其所是”)相關。這種人為性的確定性就是人的在世的生存方式。當然人的這種人為性還體現在處境上。雖然人在處境中的自由也是絕對的,這一點在之前也論述過,但是人在面對處境時,還是會不由自主的把自由看成處境中的自由,是自己適應某種本質和地位。在處境中選擇和行動,體現出了人的存在人為性。
于是,自由在薩特這里是具有本體論上的意義,無論是人以“是其所是”的人為性方式存在,還是以“是其所不是”的超越性方式存在,人都是自由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9]人的存在的超越性能夠讓人不被某一種框架所限制,自由的選擇和行動。人的存在的人為性能夠讓人以自在的方式存在著,以承擔著自由的虛無化重擔。因此,自由對人的存在來說是必然的,自由就是人的存在。
以上闡述表明,薩特的自由理論,實際上就是從意識出發去揭示人與世界的關系,他的自由是一種本體論層面上的自由。在他看來,人首先要對存在提出否定,進而把自己至于一種自由的境地,就好像在面對自我在場的瞬間中包含著一種逃離自身的意識一樣,這樣就反映出人的存在的虛無化,反映出人的自由和人的存在的欠缺。總之,人的自由是命定的。人從一開始就是自由的,沒有什么所謂的先驗的規定性,這種自由是選擇中實現,即使人遇到各種處境,也不會阻止人選擇的自由,因為在處境人是絕對自由的。而無論人是以“是其所是”的人為性的方式存在著,還是以“是其所不是”的超越性的方式存在著,人的存在都是自由的,人沒有固有的本質,但是卻固有著自由,而且這種自由是先天的,人無法逃脫自由,自由在薩特這里被上升到本體論的意義。
[1]薩特.杜小真.自我的超越性[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薩特.陳宣良,等.杜小真.存在與虛無[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3]考夫曼.陳鼓應,等.存在主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4]莫偉民.“我思”:從笛卡爾到薩特[J].哲學月刊,2006,(3).
[5]Sartre Jean-Paul,H.E.Barnes.Bring and Nothingness[M].Beijing:ChinaSocialScicncesPublishing House,1999.
[6]Morris Phyllis.Sartre on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J].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85,(2).
[7]Husson Laurcnt.De la contingence la situation:dimentions et configurations do la facticite duns L’Etre et le Neant[M].Paris:ENS Editions,2000.
[8]李守利.以事件的方式存在——人的實際性與超越性[J].江蘇社會科學,2010,(2).
[9]郭婷婷.黃峰.論《蒼蠅》中所體現的自由選擇理論[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