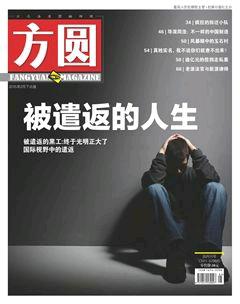真姓實名,我不說你們就查不出來?
沈寅飛
為了解決被告人身份信息不明的情況,避免“不詳”再次違法犯罪時無從查起現象的發生,一些法院的判決書也作出了進一步改進,各地紛紛產生了“照片判決書”。但查清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仍然是刑事訴訟中首要解決的問題
在1997年的廣東佛山,曾發生過一起久久未能偵查終結的搶劫殺人案,犯罪嫌疑人程玲濱逃脫后便銷聲匿跡。時隔十余年,程玲濱被緝拿歸案并于2014年底被判處無期徒刑。然而,司法人員竟然發現,程玲濱還曾在2004年因為另一起搶劫案被浙江省紹興縣法院判處過有期徒刑,當時他卻用表弟“姚忠平”的身份蒙混坐牢,成功隱藏了自己的搶劫殺人嫌疑犯的身份。
事實上,類似的犯罪嫌疑人故意隱瞞個人身份信息的案件并不罕見。記者近日從北京市石景山區檢察院了解到,該院就曾辦理過一起犯罪嫌疑人拒絕提供任何個人信息而又無法查證的案件。最后,犯罪嫌疑人以姓名“不詳”被提起了公訴并最終獲刑兩年。
這種倚賴撒賴的做法或許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氣,有人為了所謂的“面子”,有人為了掩飾前科,凡此種種都造成了身份識別成為開展刑事偵查或司法活動的阻礙。
冒用別人的名字去坐牢
在民事法律關系中,發生侵犯名譽權的案件似乎不足為奇,更有甚者竟然在刑事案件中冒用別人的名字去坐牢。
2004年,姚忠平的父親意外地收到了來自浙江省紹興縣法院的一份刑事判決書,該判決書載明,姚忠平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10個月。但是,姚忠平在此之前一直在家,從未去過紹興,怎么會在紹興犯罪呢?
通過比對判決書中所附的照片,姚父發現此人不是自己的兒子而是自己的外甥程玲濱。回想起前不久,當地公安機關來他們家核實程玲濱的身份信息,為了避免程玲濱因廣東佛山的搶劫案被追查,姚父就沒有提出任何質疑。
那么,程玲濱是如何能夠冒用姚忠平身份的呢?據姚忠平回憶,早在2000年的時候,程玲濱就跟他打過招呼,用他的身份在當地派出所辦理一張身份證。而姚忠平的母親當時還見過那張身份證,除照片有所區別之外,其余的信息與姚忠平的完全一致。就這樣,無論被捕入獄還是漂泊在外,程玲濱一直冒用姚忠平的身份長達十幾年且從未被人識破。
事實上,在公安機關偵辦的案件中提供虛假身份信息或不提供個人信息的情況并不罕見。采訪中,記者從北京市大興區幾名基層警務人員的介紹中了解到,在他們的辦案經歷中均遇到過不愿意告知個人身份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并且這些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基于以下各種原因:有的為避免留下違法犯罪記錄,捏造姓名或冒用他人身份;有的為顧及顏面,不想讓家人或所在單位知道而極力隱瞞真實身份;有的為逃避打擊,隱瞞真實身份從而掩蓋前科劣跡;有的為在逃人員,為逃避偵查直接隱瞞在逃身份;有的為累犯,為逃避從重打擊而隱瞞身份自報姓名。
與此同時,我國法律對此類現象的規制也存在“漏洞”。2014年11月,浙江省杭州市中級法院課題組公布的一份司法調研報告中指出,由于在我國“冒名”行為尚未入罪,司法上對之從重處罰也體現不足,刑罰執行上的懲戒制度更是闕如,造成違法成本較低。因此,一些不法當事人鉆法律空子,相互效仿,隱瞞真實身份從而達到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自身懲戒的目的,因為即使被發現冒用身份或捏造身份也不會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而對于社會大眾而言,原本看來嚴肅而又神秘的刑事訴訟似乎變得不那么嚴謹,為何個別不法分子通過自報姓名或冒用他人身份等規避行為能僥幸得逞?偵查部門是如何審查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的呢?
不提供身份信息就可能被釋放?
目前,對于公民個人最直接有效的身份信息證明就是身份證。平常警察會在火車上、大街上等地要求查驗個人的身份證。警察的這項權力來自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按照規定,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經出示執法證件,可以查驗居民身份證。在此過程中,警察通過專用的核查錄入儀,不但可以查驗身份證的真偽,還能對個人身份信息進行報警。“通常顯示紅色為逃犯,顯示黃色的為有前科,除此之外則顯示綠色。”大興區公安分局一位民警告訴《方圓》記者。
同時,根據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機關適用繼續盤問規定》,人民警察可以將有違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嫌疑且身份不明的人員帶至公安機關繼續盤問。在此過程中,警察通過身份證信息識別器,甄別提供的身份證的真假情況。當掌握了個人的姓名或者身份證號等內容后,通過公安機關內部的公民身份信息查詢系統,警察可以對常住人口的基本信息進行進一步識別。該系統中顯示的內容包括個人的免冠照和他(她)的姓名、曾用名、身份證號碼、性別、出生年月、戶籍地、戶籍地縣級公安機關和戶籍地派出所信息。
此外,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例如北京市公安機關已經配備了人員信息標準化采集系統,通過指紋信息比對等方式,可查驗犯罪嫌疑人有無犯罪記錄。
“不過在遇到提供的是虛假身份信息時,公民身份信息查詢系統中就只能找到與之重名人員的信息。”這位民警指出了該系統的不足之處。因此,很多犯罪嫌疑人認為不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阻礙刑事偵查工作的進行,并且可能會因為受到偵查期限的限制獲得釋放。對此,我國《刑事訴訟法》作出了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偵查羈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計算,但是不得停止對其犯罪行為的偵查取證。
事實上,即使犯罪嫌疑人故意提供虛假身份信息,偵查人員也可以按照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社會關系、證人證言等間接獲取其準確身份信息。除非犯罪嫌疑人沒有戶口,沒有犯罪記錄或者不是被通緝人員,并且不存在任何社會關系,使得偵查人員窮盡所有方式都不能獲得他的身份信息。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刑事訴訟法》亦有明確規定,“對于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報的姓名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更是具體到了如何對外國籍犯罪嫌疑人身份進行確認,“可以依照有關國際條約或者通過國際刑事警察組織、警務合作渠道辦理。確實無法查明的,可以按其自報的姓名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一些不法分子在實施違法犯罪的行為后常常會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而且通常在案發之前他們就會有所準備。除了使用與他本人長得有幾分相似的人的身份證外,他們還會了解被冒用對象的一些基本情況,以免在被審訊時露出破綻。偵查人員如果只是簡單地對個人信息和家庭信息進行比對,尤其是核實原籍位于偏遠地區不法當事人的身份就會很容易出現紕漏。 因此,在核實這些人員的信息時會更加細心、謹慎。”一位長期從事預審工作的警官告訴《方圓》記者。
根據1998年就開始實施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對異地公安機關提出協助調查、執行強制措施等協作請求,只要法律手續完備,協作地公安機關就應當及時無條件予以配合,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費用。”因此,在異地核實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的操作過程中,辦案單位一般采用電話或者發函聯系戶籍管理機關的方式進行查詢,進而得出文字資料比對基礎上的核實結果。
“但是,如果當地戶籍管理部門在核實過程中沒有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就會讓偵查人員‘確信他提供的身份信息是準確的。而為了進一步確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他們常常會通過他的親朋好友、受害人、證人等了解情況,來印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所交代的關于個人身份信息的內容。”這位負責預審工作的警官告訴記者,尤其是對于一些影響力較大或者后果嚴重的重大案件,則幾乎不可能出現差錯。這些案件在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的確認上往往會更加嚴格,力求達到準確無誤,沒有瑕疵。所以,當遇到此類犯罪嫌疑人存在疑點時,無論犯罪嫌疑人戶籍在何地,辦案人員都會進行實地走訪,多方面了解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必要時還會采取專業的照片比對、DNA鑒定等措施。
檢察機關的“二次核實”
采訪中,記者從北京市石景山區檢察院了解到,該院曾有過這樣一個蹊蹺的案件:2011年,外來務工人員王強(化名)因為盜竊被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但是在查驗王強身份信息的時候,發現他在幾年前曾有過犯罪記錄,屬于累犯,應當從重懲處。但是王強卻辯解稱,在此之前自己從未有過違法犯罪的行為。同時他還提出自己使用的是哥哥的身份證,自己的真實姓名叫王明。在幾經周折之后,王強的母親帶著真“王強”拿著當時的判決書等證明材料來到檢察機關進行澄清,最后證實王明確實并不構成累犯。
對于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負責承辦相關案件攻速的檢察官都會進行再次確認。這并不是簡單地要求犯罪嫌疑人再陳述一遍他的個人信息,而是在細枝末節中進行對比,如通過他的口音、年齡等特征,發覺其中是否存在矛盾。如果發現了相互之間不能印證的信息,則需要進行多方面的求證,進行“二次核實”。石景山區檢察院檢察官張云波告訴《方圓》記者。
據石景山區檢察院組宣科科員成于慶介紹,近年來該院辦理的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不明的情況很少,僅有的一起以姓名為“不詳”提起的公訴發生在2013年。
該案的審查報告顯示,2012年年底,聾啞人“不詳”在一報亭盜竊電話充值卡6900余元后被當場公安機關抓獲,但在到案過程中,“不詳”除了供述了自己的年齡和承認盜竊行為之外,便不提供自己的任何身份信息。
辦案人員還聘請了手語翻譯、去醫院對“不詳”進行了聽力檢查,鑒定是否為真正意義上的聾啞人,并將他的指紋錄入北京市公安局人員信息標準化采集系統,經比對也沒有發現其的犯罪記錄。
“身份信息不應該成為偵查、起訴和審判活動的障礙,該案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不詳拒不交代自己的真實身份并不影響以盜竊罪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反而可能因為認罪態度不好成為從重量刑的考慮因素之一。”承辦該案的檢察官張云波說。最終,“不詳”以判決書中顯示的“無名男子1號”被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元。
據了解,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絕提供個人的真實身份信息,那么,他將會在刑事訴訟中喪失一些權益。如一般案件中因不能及時告知家里人而無法聘請辯護律師;偵查機關在用于查清犯罪嫌疑人身份所花費的時間將不計入導致偵查羈押期限等。在司法實踐中,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中規定:“拒不交代真實身份……不得減刑、假釋。”另外,在民事權利方面則更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如因與家人長期失去聯系長達兩年以上可根據《民法通則》被宣告失蹤,時間更長的被宣告死亡,此后個人財產被繼承、夫妻關系結束等一系列法律關系將徹底發生改變。
“自報身份”制度
盡管可能存在不利后果,但對于一些在個人身份信息上“做文章”的犯罪嫌疑人而言或許逃避法律責任追究和個人“面子”等因素能帶給他們更多的實惠。為了能及時打擊犯罪,在偵查人員最大限度地識別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的前提下,我國刑事訴訟中對“無法查清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案件已經明確形成了“按自報的姓名起訴、審判”制度(“自報身份”制度),即《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規定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81條規定:“被告人的真實姓名、住址無法查清的,應當按其綽號或者自報的姓名、自報的年齡制作起訴書,并在起訴書中注明。”同時,為了解決被告人身份信息不明的情況,避免“不詳”再次違法犯罪時無從查起現象的發生,一些法院的判決書也作出了進一步改進,各地紛紛產生了“照片判決書”。如2014年7月,安徽省合肥市瑤海區法院發出了合肥市首例“照片判決書”,這份不同以往的判決書中,由于被告人身份信息不明確,判決書姓名一欄附上了被告人的彩色大頭照。被告人因盜竊被抓,并說自己叫“陳寶海”。然而,警方在偵查過程中發現,戶籍系統中根本找不到有關“陳寶海”的任何身份信息。盡管身份無法確定,但其犯罪事實明確,此人因涉嫌多起盜竊犯罪被起訴到法院。最終,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雖然刑訴法128條之規定為追究身份信息不明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掃清了障礙,但查清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仍然是刑事訴訟中須首要解決的問題。”張云波說。